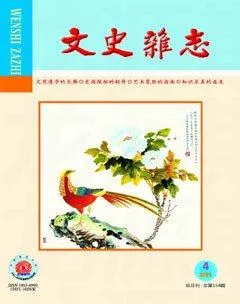再探“孔雀東南飛” 的文化內(nèi)涵
《孔雀東南飛》是樂(lè)府雙璧之一(另一個(gè)是《木蘭辭》)。僅正文字?jǐn)?shù)就達(dá)1830字,故被沈德潛稱為“古今第一長(zhǎng)詩(shī)”。由于其內(nèi)容敘述的主題是永恒的愛情,故而傳誦不衰。不過(guò),對(duì)首句“孔雀東南飛”中“東南”二字含義,歷來(lái)確有不同理解。
一是認(rèn)為“東南”是虛指,具有隨意性
這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在中國(guó)古代的許多詩(shī)文中,很多方位名詞的意義是虛指的,并沒(méi)有什么實(shí)在意義。比如《孔雀東南飛》中“東西植梧桐,左右種松柏”一句,并不是說(shuō)南北就不可以植梧桐,前后就不可以植松柏。又如柳宗元《捕蛇者說(shuō)》中的“叫囂乎東西,突乎南北”,這里的“東西”和“南北”只是虛指一個(gè)方向,可以解釋為“到處、處處”等等。
但是,只要我們稍作推敲就會(huì)發(fā)覺,所謂意義虛化說(shuō)并非站得住腳。因?yàn)樽匪莸皆?shī)歌源頭——《詩(shī)經(jīng)》,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詩(shī)中許多方位詞往往包含著先民的集體心理,體現(xiàn)著某種感情傾向。比如在先民思維中,“東”往往是與太陽(yáng)、愛情 等聯(lián)系在一起的,“南”則與長(zhǎng)養(yǎng)、山、尊貴等聯(lián)系在一起,如《詩(shī)經(jīng)·小雅·天保》中:“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北”則與陰冷、水、憂傷等聯(lián)系在一起,如《國(guó)風(fēng)·邶風(fēng)·北門》中“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即使聯(lián)系漢樂(lè)府民歌,我們也不難看出,并不是所有方位名詞用意義虛化說(shuō)就能講得通。比如“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中“東南”即指日出方向。
二是認(rèn)為“東南”是實(shí)指,具體指劉蘭芝的家
近些年來(lái),有學(xué)者從地理位置的角度對(duì)“東南”具體何指這一問(wèn)題進(jìn)行研究。據(jù)他們實(shí)地考證,焦、劉的婚姻悲劇發(fā)生在今安徽懷寧縣小吏港(小吏港又名小市港,因漢廬江小吏焦仲卿得名),焦家位于小市港河對(duì)岸的焦家坂(今屬潛山縣),劉家則在小市港東半里處。從地理位置看,劉家正好位于焦家的東南方向。劉蘭芝被遣送回家,正如孔雀東南飛一樣,卻又充滿對(duì)焦仲卿的眷戀,所以五里一徘徊。
故事最后,劉蘭芝被遣送回家后,被兄長(zhǎng)所逼,被迫改嫁,中途在小市港投水而死。焦仲卿得知情況后,最后也“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而這殉情方向,正好與開篇的興句——孔雀東南飛首尾呼應(yīng)。
這種觀點(diǎn)從表面看似乎有理有據(jù),但細(xì)思之下。讓人總覺得有些牽強(qiáng)。首先,有什么證據(jù)能證明“孔雀東南飛”中的“孔雀”是單指劉蘭芝一人,而不是指焦仲卿和劉蘭芝兩人呢?孔雀是否與鳳凰一樣,雌雄共飛;是否與鴛鴦一樣,同嬉同游,這還是一個(gè)問(wèn)號(hào)。其次,這一故事的形成年代與這些地名的最早出現(xiàn)之間是否有著合理的先后順序,有無(wú)信史可以查對(duì)?再次,作為文學(xué)作品的《孔雀東南飛》,內(nèi)容雖來(lái)源于現(xiàn)實(shí)生活,但又絕非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完全翻版。依據(jù)些許傳說(shuō)便作下如此判斷,其可信度有多少?如此諸多問(wèn)題,尚未見有說(shuō)服力的證據(jù)。
那么,“東南”到底指什么呢?結(jié)合詩(shī)歌創(chuàng)作背景,筆者認(rèn)為“東南”是指與西北繁華的俗世社會(huì)相對(duì)的,代表焦仲卿和劉蘭芝所追求的、能擁有幸福和美好生活的理想之所。理由如下:
首先明確“東南”在現(xiàn)實(shí)中的代指意義
通過(guò)認(rèn)真查閱與《孔雀東南飛》同時(shí)代的《玉臺(tái)新詠》,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一個(gè)帶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在漢魏兩晉時(shí)代中,“東南”一詞確有象征意義——象征鄙野之處;比如《玉臺(tái)新詠·古樂(lè)府詩(shī)》的“飛來(lái)雙白鵠,乃從西北來(lái),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雙白鵠”從“西北”而來(lái),向“東南”而去,“羅列不齊”,何其不幸也。再如晉代陸機(jī)有“東南有思婦,長(zhǎng)嘆通幽闥”,是寫思婦之苦,也以“東南”隱喻其處境之凄惶。
反之,“西北”則象征高貴、典雅、吉祥。我們至少可以在成詩(shī)于東漢的《古詩(shī)十九首》里得到印證。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云齊。”西北能夠建高樓,而且與浮云齊高,只能說(shuō)明西北是一個(gè)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人口眾多之地。漢代李延年有“北國(guó)有佳人,絕世而獨(dú)立”,魏曹植的“北國(guó)有織婦,綺縞何繽紛”等,都將西北隱指美好的事物。
如果再聯(lián)系歷史,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無(wú)論是傳說(shuō)中的黃帝,還是典籍中述及的周秦,他們的發(fā)祥地均在西北。退一步,遠(yuǎn)如羌人黃帝不說(shuō),從周秦至大唐千多年,西北一直為我國(guó)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之中心,此乃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只是魏晉以后,東南開發(fā)而西北漸衰,所以“孔雀東南飛”一語(yǔ)也有了新的解釋,此乃后話了。
其次,明確“東南”在文化上的象征意義
而要分析文化象征的意義,就不能脫離具體的語(yǔ)言環(huán)境。
先從詩(shī)歌內(nèi)容來(lái)看。此詩(shī)主要敘寫焦、劉二人的愛情悲劇,其感情基調(diào)是悲傷的。追溯此詩(shī)的母本,最早是來(lái)自漢代民歌中一篇《古艷歌》,其詩(shī)曰:
孔雀東飛,苦無(wú)寒衣。
為君作妻,心中惻悲。
夜夜織作,不得下機(jī)。
三日載匹,尚言吾遲。
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從漢末建安(196—219)年間到南北朝陳朝徐陵(507—583)《玉臺(tái)新詠》這三百多年間,焦、劉殉情的悲劇故事逐漸被文人加工而臻完善,也更加突出了故事的悲劇性。如開篇?jiǎng)⑻m芝被焦母遣歸,然后被兄長(zhǎng)逼迫改嫁,被焦仲卿誤解,最后投水而死。焦仲卿聞?dòng)嵰沧钥O而死。
再聯(lián)系此詩(shī)的浪漫結(jié)尾。詩(shī)歌最后寫道:“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仰頭相向鳴,夜夜達(dá)五更”。這些詩(shī)句既是劉、焦二人墓旁自然景觀的寫照,也是詩(shī)人主觀愿望的表現(xiàn)與寄托。然而細(xì)想,沒(méi)有情感的樹木尚能彼此覆蓋,情意綿綿;沒(méi)有思想的鳥兒尚能成雙成對(duì),相向和鳴,可是長(zhǎng)眠在這景觀之下的劉蘭芝和焦仲卿,他倆生前雖也像這里的良木良禽一樣恩愛眷戀,卻有情人最終難成眷屬。無(wú)情的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zhǎng)活活地將他們拆散,甚至被逼而死。殘酷的現(xiàn)實(shí)、悲慘的命運(yùn)與墓地美好的自然景觀所營(yíng)造的充滿幻想、情趣的意境,彼此鮮明地對(duì)照,作者這里的用意不言而喻,同情之心溢于言表。
因此,我們不難看出,世俗的社會(huì)雖繁華,但對(duì)劉蘭芝、焦仲卿來(lái)講卻容不下他倆,不是幸福所在。他們于是不惜以死來(lái)抗?fàn)帲畴x世俗而去東南。東南雖是一個(gè)鄙遠(yuǎn)之地,卻為自由開放所在,也即是劉、焦的幸福所在。
最后,倘從神秘文化的角度分析,在生產(chǎn)力還不發(fā)達(dá)的漢魏或更遠(yuǎn)的時(shí)期,人們對(duì)大自然有著種種猜測(cè),認(rèn)為人類自身與自然界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lián)系,于是產(chǎn)生了一套嚴(yán)密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yīng)”、“天人相通”的思想體系,以為人類社會(huì)的某些事物與自然界的某些事物存在著相互對(duì)應(yīng)的關(guān)系。這體現(xiàn)在《易經(jīng)》八卦方位中。(參見《易·說(shuō)卦傳》)
《孔雀東南飛》中的起興句——孔雀東南飛,孔雀屬于禽鳥。按《易》之說(shuō),禽鳥從風(fēng),風(fēng)在東南。對(duì)照季節(jié),在春夏期間。孔雀東南飛就是回到自己來(lái)時(shí)的地方,東南才是它的歸屬。那里是春風(fēng)習(xí)習(xí),夏陽(yáng)普照,才是它的理想之地。(而西北在方位上,代指秋冬寒冷季節(jié))。結(jié)尾處,焦仲卿“自掛東南枝”,既體現(xiàn)了他對(duì)封建家長(zhǎng)制的抗議,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他對(duì)自己幸福愛情生活的向往。從哪里來(lái),回哪里去,現(xiàn)實(shí)中不能實(shí)現(xiàn)的愿望,就只有在另一個(gè)世界去尋求。這既是死者對(duì)現(xiàn)實(shí)冷酷社會(huì)的一種抗?fàn)帲彩巧邔?duì)死者的一種慰藉。
作者單位:四川省宜賓市第一中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