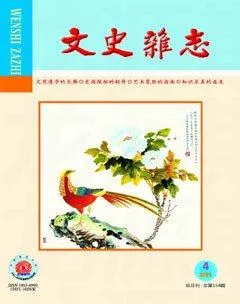略說(shuō)揚(yáng)雄的思想自由與學(xué)術(shù)獨(dú)立
揚(yáng)雄(公元前53—公元后18)為成都郫縣人,祖籍河?xùn)|(在今山西)揚(yáng)縣。《漢書(shū)·揚(yáng)雄傳》說(shuō)揚(yáng)雄先祖本為姬周支系,因“食采于晉之揚(yáng)”,故以揚(yáng)為氏。戰(zhàn)國(guó)至漢初,揚(yáng)氏一族因避戰(zhàn)禍,經(jīng)萬(wàn)里輾轉(zhuǎn)而經(jīng)三峽至江州。這時(shí)揚(yáng)雄的五世祖揚(yáng)季曾在廬江為太守,那是文翁的老家。大約在漢武帝元鼎時(shí)期(公元前116—前111年),揚(yáng)季因避仇家又溯江而上,最后才定居岷山之陽(yáng)的郫縣。
揚(yáng)雄在不惑之年以前(四十余歲后則出蜀宦游京師)可以說(shuō)一直承受著文翁興學(xué)雨露的沾溉。他青少年時(shí)曾在成都求學(xué),拜在嚴(yán)遵門(mén)下,深得老師學(xué)問(wèn)真諦。
嚴(yán)遵著《老子指歸》,闡述宇宙演化模式:“道為之元,德為之始,神明為宗,太和為祖”;“道體合和,無(wú)以物為,而物自為之化”。他從宇宙的演化是遵循無(wú)為這一根本規(guī)律出發(fā),導(dǎo)引出萬(wàn)物自生自化的法則,進(jìn)而提出“非有政教,物自然也”的觀點(diǎn),說(shuō)明天地萬(wàn)物并非天命所賦,亦不是政教所為,而是自為生成,自然而然的;強(qiáng)調(diào)主觀能動(dòng)性在矛盾變化中的作用。揚(yáng)雄則在此基礎(chǔ)上仿《易》寫(xiě)就《太玄》,以西漢相對(duì)進(jìn)步的“渾天說(shuō)”為依據(jù),闡述他的“玄”的哲學(xué)范疇與基本原理,說(shuō)明“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的自然規(guī)律,將天、地、人的對(duì)立統(tǒng)一與和諧發(fā)展視為世界的理想模式。更為重要的是,揚(yáng)雄認(rèn)為“其動(dòng)也日造其所無(wú),而好其所新;其靜也日減其所有,而損其所成”,提出運(yùn)動(dòng)乃是一切事物產(chǎn)生并得以強(qiáng)大的根源,而靜止則導(dǎo)致事物衰亡的觀點(diǎn),從而推陳出新,發(fā)展了自老子、嚴(yán)遵以來(lái)的自然辯證法,初步建立起具有巴蜀特色的唯物主義哲學(xué)體系。由于嚴(yán)遵《老子指歸》及揚(yáng)雄《太玄經(jīng)》的倡導(dǎo),易學(xué)、老莊哲學(xué)遂成為巴蜀學(xué)術(shù)界的熱門(mén)學(xué)問(wèn)而影響深遠(yuǎn)。后人所謂“天數(shù)在蜀”、“易學(xué)在蜀”,即此。
揚(yáng)雄是以儒學(xué)名世的。他在《漢書(shū)·藝文志》里被歸入儒家。然而,他對(duì)老、莊之學(xué)的欣賞與運(yùn)用,在其得意之作《太玄》里卻表現(xiàn)得特別熱烈和精彩。所以朱熹指出:“揚(yáng)之學(xué)似出于老子”(《朱子語(yǔ)類(lèi)》卷一百三十七);又說(shuō):“《太玄》之說(shuō),只是老莊。”(《朱子語(yǔ)類(lèi)》卷六十七)現(xiàn)在細(xì)讀《太玄》,可以發(fā)現(xiàn)揚(yáng)雄思想里不僅貫穿了老、莊“道法自然”的觀點(diǎn)與“清靜無(wú)為”的政治觀,而且還綻開(kāi)著人本主義的花瓣。揚(yáng)雄憂心忡忡地評(píng)論時(shí)政說(shuō):“懷威滿虛,道德亡也”,告誡統(tǒng)治者忽濫施刑罰,視人之生命如草芥。這與他在《長(zhǎng)楊賦》里諷諫漢武帝時(shí)所說(shuō)的“人君以玄默為神,淡泊為德”是一致的。他高揚(yáng)“玄”之旗而廣言“無(wú)”,提出“自然仁義”(意即自然而然就行仁行義,行仁行義沒(méi)有人為造作)之說(shuō),成為魏晉玄學(xué)的濫觴。
揚(yáng)雄本人其實(shí)也是一個(gè)優(yōu)秀的教育工作者。他編寫(xiě)的《訓(xùn)纂》,修訂的《蒼頡》,是當(dāng)時(shí)面向少年兒童的主要蒙學(xué)教材。而他經(jīng)過(guò)長(zhǎng)達(dá)27年的積累,耗盡心血完成的《輶軒使者絕代語(yǔ)釋別國(guó)方言》(簡(jiǎn)稱《方言》),更是小學(xué)名著,直至今天,仍是治漢語(yǔ)言文字、音韻詞義者的案頭書(shū)。
作為私學(xué)教師的揚(yáng)雄平生招收學(xué)生不多,但都是有才講義者。當(dāng)時(shí)的古文經(jīng)學(xué)派的開(kāi)創(chuàng)者劉歆之子劉棻就曾拜揚(yáng)雄為師,“學(xué)作奇字(古文字)”。鉅鹿人侯芭則食、宿于揚(yáng)雄家,研習(xí)先生的《太玄》、《法言》等艱深著述,深得揚(yáng)雄器重。《漢書(shū)·揚(yáng)雄傳》說(shuō),劉歆去揚(yáng)雄家探望,看到侯芭在鉆研《太玄》、《法言》,就對(duì)揚(yáng)雄說(shuō):“空自苦!今學(xué)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醬瓿也。”但揚(yáng)雄笑而不答,他相信侯芭的毅力和能力。他和侯芭相交,既是師生,又是知己。揚(yáng)雄逝世后,“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漢書(shū)·揚(yáng)雄傳》)
作為一名先生,揚(yáng)雄不僅看重向?qū)W生傳授知識(shí),更強(qiáng)調(diào)育人樹(shù)人。為此他指出,作為學(xué)生的老師,當(dāng)是道德的楷模,為人模范。他在《法言·學(xué)行》中寫(xiě)道: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lèi)我!類(lèi)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wù)學(xué)不如務(wù)求師。師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為不少矣!……一卷之書(shū),必立之為師。
這既是揚(yáng)雄對(duì)自己的告誡與勉勵(lì),亦是他自己的形象寫(xiě)照。與他同時(shí)代的經(jīng)學(xué)大師劉向、劉歆父子及晚一輩的桓譚都很尊重他,敬服他。吳郡陸公紀(jì)尊稱他為“圣人”(《華陽(yáng)國(guó)志·先賢士女總贊論》)。《漢書(shū)·揚(yáng)雄傳》則稱揚(yáng)雄“少好學(xué),不為章句,訓(xùn)詁通而已,博覽無(wú)所不見(jiàn)。為人簡(jiǎn)易佚蕩”,“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耆(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dāng)世。”
公元8年揚(yáng)雄暮年之際,安漢公王莽代漢,改國(guó)號(hào)為“新”。此前三年,王莽篡位已成必然之勢(shì),于是不少人爭(zhēng)獻(xiàn)符命,求賞邀寵。精通奇字的揚(yáng)雄則不肯以此為資本而獻(xiàn)媚于王莽。王充《論衡·佚文》還有過(guò)一段記載:
揚(yáng)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賚錢(qián)十萬(wàn),愿載于書(shū)。子云不聽(tīng),曰:“夫富賈無(wú)仁義之行,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亡載!”
揚(yáng)雄不論為人做事還是做學(xué)問(wèn),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巴蜀文化傳統(tǒng)中的樸實(shí)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風(fēng)與求真求實(shí)的精神,可以說(shuō)由揚(yáng)雄而有犖犖大端。
作為晉地移民的后代,蜀人揚(yáng)雄更是一位站在西漢而面向東漢的思想家。這樣說(shuō)倒不僅僅在于他的活動(dòng)正好處在西漢末年與向東漢過(guò)渡的新莽時(shí)期,而主要在于他以一位理想主義者與全才型學(xué)者(思想家、文學(xué)家、哲學(xué)家、語(yǔ)言學(xué)家、天文學(xué)家、歷法家)的姿態(tài)開(kāi)啟了東漢一代理想主義和知識(shí)主義的風(fēng)氣。揚(yáng)雄及揚(yáng)雄以后的時(shí)期,國(guó)家政治生活幾經(jīng)風(fēng)云激變,主政者以強(qiáng)權(quán)闖入思想領(lǐng)域(如漢平帝至新莽時(shí)期,王莽強(qiáng)行扶持古文經(jīng)學(xué),打擊今文經(jīng)學(xué);光武中興,再興今文經(jīng)學(xué)而視古文經(jīng)學(xué)為“異端”),使“擁有思想與學(xué)術(shù)的人”,“被擠到了歷史的角落”(葛兆光:《七世紀(jì)前中國(guó)的知識(shí)、思想與信仰世界》)。與此相應(yīng),這些受壓抑的知識(shí)分子則一方面“恪守一種近乎教條的理想主義”,“一方面頑強(qiáng)地恪守古典知識(shí)”,以此來(lái)“凸顯自己的存在”,“抗拒世俗社會(huì)的侵蝕,批判世俗社會(huì)非文化的傾向”(同上)。揚(yáng)雄正是在政治嬗變和強(qiáng)權(quán)擠壓下堅(jiān)持獨(dú)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第一人。他將這種思想精神引入立言、立德、立功的實(shí)踐中,將自先秦以來(lái)逐漸形成的獨(dú)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推向一個(gè)新天地。揚(yáng)雄以后,巴蜀地區(qū)又相繼涌出像陳壽、常璩、陳子昂、李白、梁令瓚、秦九韶、龍昌期、蘇軾、圓悟克勤、張栻、魏了翁、李燾、李心傳等一批又一批的國(guó)家級(jí)甚或世界級(jí)的文化大師和他們的學(xué)術(shù)成果,使巴蜀文化呈現(xiàn)出一種星光燦爛、花團(tuán)錦簇的面貌。
另一方面,揚(yáng)雄的獨(dú)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在東漢贏得普遍尊重與回應(yīng)。班固稱羨說(shuō):“淵哉若人!實(shí)好斯文。”(《漢書(shū)·敘傳下》)王充亦有云:“玩揚(yáng)子云之篇,樂(lè)于居千石之官。”(《論衡·佚文》)桓譚則大膽預(yù)言揚(yáng)雄之書(shū)必傳諸后世。(參見(jiàn)《漢書(shū)·揚(yáng)雄傳》)王充、桓譚和尹敏、鄭興、張衡、馬融、鄭玄等以及以李膺、杜密為領(lǐng)袖的漢末“清流”士大夫,緊隨揚(yáng)雄之踵而普遍主張思想解放與學(xué)術(shù)獨(dú)立,從而為讖緯盛行的東漢思想界、學(xué)術(shù)界輸進(jìn)一股清風(fēng)。
作者單位: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