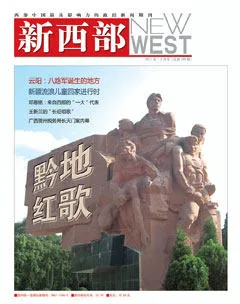新疆流浪兒童回家進行時
如果不積極消除負面因素,隨著新疆與外界交流機會的增多,很可能帶來更大的誤解甚至敵意,其中流浪兒童問題就是一個焦點。就在“讓內地新疆流浪兒童全部回家”的新聞發布以后,一名在內地工作的維吾爾女孩發短信給柯木說:“想哭,還有想親一口張春賢書記的沖動。”
“像父母一樣、像醫生一樣、像老師一樣。”這個標語,出現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工讀學校的一面墻壁上。
成立于2009年6月的這所工讀學校,是全疆惟一集收容、救助及矯治于一體的未成年人教育機構。自2011年4月底以來,這所學校開始擴建,準備安置從內地省市“接”回來的新疆籍流浪兒童。
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維吾爾族副研究員吐爾文江估算,目前新疆在外省市的流浪兒童人數大約為3至5萬人。
從4月20日至6月17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救助管理站已從內地接回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144名。“年底以前,我區將把內地新疆籍流浪未成年人全部接回,采取多種措施保障他們的生活、教育、管理、返鄉和安置。”新疆自治區民政廳副廳長周俊林說。
新疆當地官員承認,過去發生的許多事情,已經讓外界對新疆的評價變得毀譽參半。接回新疆流浪兒童的行動,應該是當地試圖重塑形象的開始。
貧困仍是主要因素
吐爾文江最近完成了一項調研,內容正是“新疆籍流浪兒童”。截至2011年4月初,身為維吾爾族的他對80名新疆流浪兒童進行了“一對一”的訪談調研。
“沒有緩解,與10年前相比反而出現加劇趨勢,并且開始向內地二、三線城市蔓延。”他說,“1999年,我參加過一次針對新疆籍流浪兒童情況調研,當時問題已經凸顯出來,并受到自治區領導的關注,不過當時情況僅限于京廣滬等線發達城市。”
同樣參與1999年調研的新疆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所長李曉霞回憶,調研人員訪問了很多人,包括流浪兒童、兒童家長、群眾、遣送站的管理者、警方人員,對內地城市和本地城市,流入地和流出地,都進行了廣泛調查。
吐爾文江表示:“當時估算在其他省份流浪的新疆籍兒童大概是5000到8000人左右。而這次調研估算出的數字增加到了3至5萬人左右,由于其隱蔽性等因素干擾,一直沒有得到精確的數據。”
“全疆各級救助管理站每年救助回來的是3000人,如果按照這個數字乘以5年就是15000人。實際上,現在救助回來的只占新疆在內地流浪兒童的一部分。”他說,“如果按照50%推算的話,我們估計3萬這個數字是靠得住的,這也說明問題在加劇。”
吐爾文江是根據一座城市可能存在多少團伙,每個團伙控制了多少流浪兒童進行估算的,“200多座城市,一座城市一個團伙,一個團伙控制150人或200人。一般來說,除了個別大城市可能存在幾個團伙,一般一座城市只有一個團伙。”
吐爾文江同時注意到,新疆籍流浪兒童的主要流出地與10年前比較并未發生變化,依然為南疆的喀什、和田和阿克蘇等地區。
“一方面是這些地方人口基數大,另一方面也和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在吐爾文江看來,貧困仍然是誘發流浪兒童現象的主要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認知,內地發達地區的生活方式和條件對于邊疆和其他偏遠地區的人仍然有很大吸引力。”
吐爾文江同時表示,最偏遠農村地區的兒童其實更不容易被誘拐,那里有可以依賴的生產資源,不易剝離這種生產關系;而城市及周邊的貧困人員,其子女往往游蕩在社會上成為主要“獵物”,“被誘拐的比例更大,也有個別兒童是被強行拐賣的。有些兒童甚至剛從學校門口出來,就被麻袋一裝拐走了,不過這種情況不算常見。”
李曉霞的發現是,媒體的宣傳,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特別是南疆地區很多相對貧困家庭的孩子對現代城市生活很向往,使得這種孩子容易被誘拐。
“被誘拐的兒童基本生活在城市或城郊位置,因為‘蛇頭’、‘賊頭’也要考慮如何將被誘拐而來的兒童運往內地省市。”李曉霞說,“他們也會考慮成本等問題,而偏遠農村地區交通不便。”
吐爾文江表示,一般流浪兒童都在14歲以下,因為年齡再大的不易被控制,同時偷盜只是一般治安案件,選擇兒童作為作案工具,可以逃避法律責任,“這些團體已經高度組織化,分工明確,同時還對流浪兒童訓練了一些反偵察措施,比如通過自殘、偽裝語言不通等方式來規避,這也為內地有關部門救助和打擊增加了難度。”
長期參與相關案件破獲的烏魯木齊鐵路公安處宣傳科科長李國賢證實了上述兩名學者的觀點:“雖然各級政府、兄弟省份一直在幫助新疆,但是我感覺扶貧的力度還需要加大,尤其是交通、醫療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包括計劃生育政策的具體落實。”
出生于新疆和田地區的民謠歌手洪啟早在2000年就創作了一首名為《阿里木江,你在哪里?》的歌曲,此舉緣于1992年他在烏魯木齊市公共汽車站牌上看見的一則《尋人啟事》,一個漂亮可愛的維吾爾族小男孩的照片旁邊有一行黑體大字:“阿里木江,你在哪里?”顯見孩子父母的悲痛欲絕。自此他一直關注著新疆籍流浪兒童的事情,希望用音樂的形式撫慰流浪兒童家人的心靈,同時也希望借助藝術的力量,呼吁全社會重視。
成長于新疆和田地區,內地大學畢業的維吾爾族青年柯木現在就職于杭州,他和朋友們早在2007年就開始關注新疆流浪兒童問題,并以“救助內地新疆流浪兒童”新浪微博等方式,借助網絡力量積極呼吁。
“這次新疆政府是下了狠心的,希望從根源上解決這個弱勢群體的生存問題。從以前的低調宣傳,到現在實質性的幫助,包括我們在網絡上如此高調,是對張春賢書記有信心。”柯木說,“將近兩年時間了,從我身邊維吾爾朋友中稱他“春哥”、“賢哥”的語氣中,可以深切感受到張書記給新疆帶來了春天,其‘不讓一個內地維吾爾族流浪兒童在內地盜竊,全部接回新疆’的表態,已經得到了維吾爾族群眾的認可。”
就在“讓內地新疆流浪兒童全部回家”的新聞發布出來以后,一名在內地工作的維吾爾族女孩發短信給柯木說:“想哭,還有想親一口張春賢書記的沖動。”
新疆形象大打折扣
5月5日,經過近一個月的慎密偵察及千里追捕,烏魯木齊鐵路公安處在多家部門的配合下,成功破獲一起特大拐騙新疆籍兒童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4名,解救被拐兒童8名,一名兒童當時還身著小學生校服。
李國賢表示,隨著新疆警方打擊力度加大,一些“賊頭”也改變了拐騙兒童的方法,比如同時給孩子們購買“烏魯木齊至吐魯番”和“烏魯木齊至濟南”兩種車票,進站時用前者,上車后用后者,企圖騙過檢查。
“事實上這些解救孩子的工作我們警方一直都在做,并沒有將其當作是什么特殊的任務,只是由于以前考慮到地區及事件的敏感性,所以很少公開報道。”李國賢說,“隨著國家政策以及自治區領導工作風格的轉變,我們也積極按照上級的要求進行工作。”
他介紹,一些維吾爾族孩子同時扮演著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兩個角色。例如2007年3月,10歲的和田小學生塞某碰見一個名叫買某的成年人,后者以到烏魯木齊玩幾天為由,將從沒有離開過家鄉的他拐騙到了成都,隨后采用毆打、餓肚子等方法逼迫他去偷錢,塞某經常被打得舊疤未好又添新傷。2008年9月,逐漸懂事的塞某借機逃回家鄉和田,但年底再次被一個名叫努某的叔叔拐騙到了哈爾濱從事盜竊活動。隨著塞某“技能”的日益提高,2009年初,努某將其以1萬元的價格轉給了在沈陽以開飯館為掩護的庫某,直至2011年4月被查獲。
一直有人在質疑,小偷到處都有,為什么新疆小偷如此突出?事實上,從目前內地警方所掌握的一些情況來看,如果不迅速對這些盜竊團伙進行打擊,他們還可能被一些恐怖和分裂勢力拉攏、利用,甚至為其籌集活動經費,未來所形成的后果將非常嚴重。由此也可以看出,新疆方面此次接回流浪兒童的決心和行動是包含著多層意義的。
“犯罪團伙以暴力或麻醉藥等綁架、拐賣、誘騙或挾持維吾爾族兒童,到強制和逼迫他們盜竊和搶劫,甚至因為孩子‘完不成任務、不聽話、逃跑反抗’。慘遭割斷腳筋甚至殺害,以及女性兒童和未成年人遭受犯罪團伙的性侵犯。”柯木說,“這不但是影響新疆形象的問題,也涉及我們這些在內地生活的新疆人形象。因為存在前面的情況,我們住旅館被拒絕過,坐公交車被內地人躲避過,還因為新疆人的長相,被警察從街頭帶到派出所盤問過。”
他表示,網絡上有人說維吾爾族兒童“流浪是一種習慣”,這真是笑話,如果有書讀、有飯吃、有衣穿、有地方住,哪個孩子會希望擁有這樣的“流浪權”?從流浪兒童的一般情況來看,除了語言上的障礙,他們缺少社會知識,缺少與政府機構(包括救助管理機構)打交道的經驗,多數并不懂思考自己今后的生活問題,再加上他們多數受到不良家庭關系的傷害,所以主動求助的觀念并不強。
吐爾文江也承認,新疆流浪兒童被逼偷盜的行為已經影響到了新疆人的形象,影響到新疆與內地省市的交往,“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鍋湯,其實大多數新疆人都是熱情、好客的,無論是維吾爾族還是其他民族。”他指出,“當前新疆正在擰成一股繩謀發展,在中央援助新疆工作座談會一周年之際,新疆各項建設有序進行。同時,從早前的‘內高班’到現在大中專畢業生到內地培訓實踐,新疆與內地省市交流的機會越來越多。”
“如果不積極消除負面因素,新疆與外界交流機會增多,卻可能帶來更大的誤解甚至敵意,其中流浪兒童問題就是一個焦點。”吐爾文江表示,現在很多新疆人到內地后都覺得不受歡迎,內地有些地方甚至出臺一些“土政策”,千方百計限制新疆人在當地居住、經商等。
例如在昆明等一些城市,當地社區四處張貼“不允許將房屋出租給新疆人,發現有新疆人停留居住必須馬上匯報”的公告。昆明市的一些出租車,有一段時間對維吾爾族長相的人基本拒載。一名女司機回憶:“一次一名衣著淳樸的維吾爾族男子強行上了我的車,一邊用不太熟練的普通話哀求我載他走,同時拿出一張維吾爾族兒童的照片表示自己是來找丟失的侄子,因為有消息說孩子可能被逼在昆明做小偷。”
覺得有些過意不去的女司機向男子作了一些解釋,不料他哭了起來,并且狠狠地抽自己的耳光:“我們維吾爾族人的臉都被他們丟光了,無論如何我這次一定要把孩子找回去。”
“內地很多城市都要求新疆派維吾爾族警察去幫助打擊新疆小偷,但那樣的辦法只能奏效一時,不日后又會卷土重來。”柯木說,“新疆流浪兒童問題已經變成一個全社會問題,需要公安、民政、教育、勞動、宗教、民族、街道、社區等部門的綜合協調,拉網式全過程救助使他們脫離街頭流浪的困窘和來自賊頭黑手的殘害,避免其滑向更嚴重的犯罪深淵,產生更復雜的社會影響。”
接回孩子只是開端
“許多孩子在外面都受到過深深的傷害,部分甚至已經染上了許多不良習氣,如果不對他們進行長時期的教育,馬上送到社會上或交給父母肯定不行。”李國賢說,“必須讓接回來的流浪兒童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勞動技能及塑造思想道德,所以自治區已經決定投資5000萬元新建一所流浪未成年人安置培訓中心,幫助他們未來更好地融入社會。”
他介紹,以前警方的工作方法是盡量聯系上孩子的親人接回去,找不到就移交給民政部門處理,現在看起來并非最恰當的方法。
柯木也認為,孩子被救助后的心理輔導非常重要,因為救助站不可能長期提供幫助,他們終歸要步入社會,如果未成年期的心理傷痛沒有被撫平,他們完全可能以成年的身份繼續危害社會。
新疆藝術學院的維吾爾族女大學生迪麗熱巴說:“這次解救流浪兒童行動在新疆是史無前例的,投入的人力和財力都很大,如果能徹底地貫徹落實相關政策,肯定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就。”她期待的是,盡可能將在內地流浪的新疆兒童接回,“應該從拐賣誘騙的源頭著手,除了要接回這些孩子,更重要的是能切實地打擊疆內的拐賣團伙,從源頭制止這些情況的發生。”
新疆南部的和田地區是維吾爾族兒童被拐騙出去的重要區域,該地區既是維吾爾族重要的集居地,也是新疆目前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當地有許多相當于內地集貿市場的大巴扎,每天熙熙攘攘人流很多,尤其輪到趕集天,四面八方的維吾爾族群眾都會拖兒帶女前來,年幼的孩子們往往會在這樣的地方走丟,甚至被人拐騙走。
無論在烏魯木齊還是在和田街頭,經常可以看見各種尋找丟失孩子的維吾爾文“啟事”,很多維吾爾族男子更是愿意主動為外來者進行內容翻譯,同時向后者表達著自己的無奈和憤怒。和田市公安局納爾巴格派出所的維吾爾族警員伊木然說:“幫助本地老百姓尋找丟失的孩子,已經成為各個派出所的一項重要工作,由于他們的父母對孩子管理疏忽,所以不斷發生丟失的情況。”
他介紹,10歲以下的走丟孩子,七八成都能夠找回來,被拐走到內地的情況不多,但10歲以上的情況就嚴重了,一般都不會是正常走丟,而是被他人拐走了,尋找到的機會就小了。
“出現后面一種情況,基本就是被人帶到內地了,眾所周知很多被逼成為了小偷。”伊木然說,“被拐走的幾乎都是維吾爾族孩子,很少發現漢族、回族等其他民族,這也說明那些‘賊頭’都是維吾爾族,因為這樣他們才可能把維吾爾族孩子騙走,其他民族的孩子不容易信任他們。”
事實上,丟失孩子的情況在全國各地、各民族里都可見到,原因也大同小異。不過新疆籍流浪兒童和其他流浪兒童遭遇不一樣,后者一般是被逼從事乞討,而新疆籍流浪兒童基本上是被逼從事偷盜活動,有些孩子還不止一次被騙到內地。
李國賢說:“從一些孩子的被拐經歷可以感到他們的無知。2011年4月8日,3名兒童結伴在葉城縣人民公園里玩耍,維吾爾族青年‘米熱迪力’主動請他們吃烤肉,隨后給他們介紹了可以天天請他們吃烤肉的‘買爾旦’,3名兒童就此失去了自由。隨后他們被帶到烏魯木齊交給塞某,后者準備帶其至內地從事違法活動,幸好被烏魯木齊火車站派出所民警查獲。”
柯木表示,在關注新疆穩定與經濟發展的同時,政府也要重視解決少數民族同胞的民生問題、就業問題,正確處理好少數民族群體教育、貧困和權益保障等問題的關系。“雖然‘7·5’事件后政府普遍提高了當地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但如何發展民族經濟,提高少數民族的就業率,加快新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輸出,都是政府需要考慮的問題,否則解決流浪兒童的問題只會事半功倍。”
在此前的5年間,中央政府共下撥3460萬元資金,資助新疆在和田、喀什和阿克蘇等地新建了15個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護中心,增加了1533張床位,使新疆擁有了基本的流浪兒救助和保護能力。目前新疆還將出臺相關優惠政策,要求各地勞動保障部門將流浪兒童職業技能培訓納入當地培訓計劃。
“流浪兒童想重新回歸學校、回歸社會,都成為了很困難的事情,因此教育問題和就業問題最為棘手。”吐爾文江建議,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還是要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讓流浪兒童擁有一技之長。
“這一次政策格外地強調建設更多的安置中心,不像以前建的流浪兒童救助中心,流浪兒童回來待上半年或者一年時間,實際上最多就起到基本的‘脫敏’作用。”他表示,“職業技術教育的引入可以讓這些孩子有一技之長,防止他們反復流浪,同時應該按照流浪兒童在外時間長短進行分類管理。”
吐爾文江說:“年底前全部接回來只是開端工作,后續是如何讓這些孩子重新融入社會。如何讓他們走出陰影重新生活,不僅僅是新疆政府的責任,全社會都應參與進來,以極大的包容心接納這些特殊的新疆流浪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