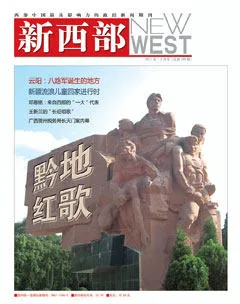息烽集中營的英雄們
楊虎城、許曉軒、韓子棟、張露萍、“小蘿卜頭”……一座號稱“行轅”、“大學”的集中營,曾經關押的知名和不知名的愛國人士及共產黨人超過千人,其中許多人在這里慘遭殺害。時光荏苒,但息烽集中營的英雄們留在一代一代人心目中的形象卻越來越高大。
陽朗壩并沒有它的名字所展示的那般陽光明朗。
參觀完息烽集中營,天氣驟變,下起了雷陣雨。息烽集中營革命紀念館年輕的干部袁萍陪我們在辦公室里避雨,轟隆隆的雷聲不時響起。
位于貴陽市息烽縣以南6公里的陽朗壩,是貴州中部一個偏僻的小鎮,四周山巒疊翠、靄霧朦朧。1938年,國民黨軍統局將一個龐大的秘密監獄——息烽集中營設在這里。雖然黔渝公路從它面前穿過,但因山形掩蔽,路過此地的人,若非有人指點,絕不會知道里面曾是一個秘密魔窟。
1997年,息烽集中營修復后正式向游客開放,袁萍正是那年大學畢業分配到紀念館的。10多年間,她跟隨資料組搜集各種與集中營有關的資料,尋訪每一位幸存者,這段隱秘的歷史便漸漸走進她的心靈深處。也不知從何時起,她對陽朗壩的“雷雨”有了一種莫名的懼怕。
“他們都說這里的冤魂太多了。”袁萍說著這句話,淡淡的笑容里有一絲不安。
天字號大招牌
“很多人都被這個‘行轅’給誤導了,以為這里是辦公的地方。”袁萍說。
到息烽集中營參觀,游客常常會對營區大門上赫然掛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息烽行轅”的招牌疑惑不已。
1938年,日軍進逼南京,國民黨政府棄祖國大片河山于不顧,卻惟獨不肯釋放堅決主張抗日的共產黨員和愛國民主人士。
那年秋末冬初,在漆黑不見五指的夜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王牌汽車隊,靜悄悄地開進了息烽縣陽朗壩。“擠在大卡車里的囚徒們,戴著沉重的手銬、腳鐐,手銬還用鐵絲穿起來,十個囚徒穿成一串。囚犯們被趕進一片民用房屋里睡下……”息烽集中營的幸存者韓子棟在回憶錄中記下了初到息烽的那個夜晚:“粗大的柱子密密匝匝地立在那里。亮光只能從空隙中射進,茶油燈在輕風的吹拂下,晃晃悠悠,影影綽綽。囚徒們在似睡非睡的迷離中,常常把這些大柱子誤認作監獄站秘密崗哨的看守……”
韓子棟,小說《紅巖》中“瘋老頭”華子良的原型,他是山東陽谷縣人,1933年入黨,1934年因叛徒出賣被捕,并被輾轉關押于北平、南京、武漢、益陽、息烽、重慶等地的國民黨秘密監獄,時間長達14年之久。
到息烽以后,韓子棟才知道秘密監獄對外稱作“行轅”,監獄的小頭子不稱典獄長,對外稱行轅主任,對內才是新監主任:看守稱“管理員”,犯人也換上了“休養人”的稱呼;牢房被稱為“齋”,并冠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這些美好字眼。
在蔣介石“息烽行轅”這塊天宇號大招牌下,集中營儼然是一個獨立王國。
據說,息烽當年是一座僅有2000多人的縣城,但在1938年至1946年的8年中,卻駐扎了國民黨軍統特務機關等各類人員15DC0多人,相當于縣城人口的7倍多。縣城周圍設立了軍統局辦事處、特種技術訓練班、軍統第二電訊總臺等16個特務機構。當時息烽自縣長到鄉鎮長,清一色的都是軍統人員,一時成為軍統的大本營。
但對那些被關押的囚徒們來說,這里就是一個人間地獄。
人間地獄
息烽集中營營區所占的地盤,原是陽朗壩一個大地主的莊園,四面崇山峻嶺,古樹參天,路人很難看到其中的建筑。軍統進入后,又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擴建改造,修鑿了個人工湖,湖中建有涼亭,一片湖光山色。集中營的圍墻之外,架設著密密的鐵絲網,安裝了電力設備,但圍墻之內電燈設備只限于辦公處所及交通要道,牢房那邊則是黑暗陰森的另一個世界。
愛國將領李濟深的秘書李任夫在息烽集中營度過5年苦難的生活。若干年后,在一篇回憶文章中,他將息烽稱作“莊園式的大魔窟”。“初來者倘無向導,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間,即在內部行動,也有一般的與特別的口令,對答不來,有遭槍殺的危險。”
尤其是自張學良、楊虎城等幾位重要政治人物先后囚禁到這里以后,警戒更為森嚴。營外每一個山頭都建有碉堡,日夜守衛。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數,決不敢冒昧進入這個禁區。
1941年,李任夫被解押到息烽集中營時,韓子棟已經在國民黨的秘密監獄輾轉關押了7年之久。李任夫經常聽人指說,某某是“白頭公”,后來才明白,“白頭公”是指重大的政治嫌疑犯,因無確證,既不能殺,又不能放,成了不決的懸案。韓子棟就是其中之一。
息烽的囚犯只許用號碼代名,不準講出自己的真實姓名。每個人先要過一段單獨禁閉生活,才能調到大房去過集體生活。最初和韓子棟同一個牢房的,除了一位第三黨人241,楊虎城的副官392(閻繼明),多半是特務紀律犯。
“特務紀律犯也是滿肚皮牢騷,但是你如果把他們同政治犯一樣看待,那你就要上大當的。一些囚犯沒有認清這一點,糊里糊涂送掉了性命。”韓子棟回憶道。
一間長不及兩丈、寬不及一丈的監房,住17個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在這個狹小的天地里。而且每個監房的窗戶都糊得嚴嚴的,不僅光線不足,而且空氣惡濁,管理員走近門口,多用手巾蒙起鼻子。
囚犯們的伙食也是非常差。韓子棟說,他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吃的是霉米飯、菜葉湯,在南京吃的是砂子、石頭、谷子、稗子“四寶飯”,到了息烽就成了“八寶飯”了。不斷有年青少壯的囚犯被腸胃病、痢疾奪去性命。
“說他們是在人間,人間沒有他們,說他們是在陰曹地府,閻王爺也斷然否認!這是一個人間絕無,陰曹也沒有的‘秘密世界’。”韓子棟回憶道。
“升學”與“留學”
每年4月1日前夕,都是息烽囚徒們最恐怖的日子。
“四一”是軍統前身特務處成立的時間,戴笠會一面釋放一批可以釋放的人,一面處決一些認為該殺的人,作為慶祝這個日子的行動。韓子棟說,“每次戴笠將來未到時,內外警衛加嚴,整個監牢如臨大敵,犯人連窗外都不準張望。”
往往戴笠一到,即有不經審訊立即處死的人。這種緊張情緒,一直要到戴笠離去以后,才慢慢平靜下來。
不過,與死亡相比,囚徒們“活受罪”的日子更不好過。
息烽集中營的另一個名字叫“貓洞集中營”,是因為集中營的審訊室和行刑處都設在一個被稱為“貓洞”的天然溶洞里。這個溶洞有百米深,相傳曾有老虎出沒,當地人把老虎稱為大貓,便將溶洞稱為“貓洞”。
據說在洞內用刑,無論發出怎樣撕心裂肺的喊叫,洞外是一點也聽不見的。所以第二任主任周養浩上任后,就把貓洞取名為“妙洞”。
在“貓洞”里被折磨至死的犯人,常被隨即掩埋在洞底。解放后,人民政府挖開被國民黨特務封死的貓洞,發現了無數烈士的遺骨。至今人們無法統計,在這個溶洞里,有多少革命先烈被殺害。
息烽集中營在軍統內部被稱為“大學”,而重慶的白公館監獄和望龍門看守所則被稱為“中學”和“小學”。凡被送到息烽集中營的“政治犯”,軍統內稱之為“升學”。凡是升到這里的囚犯,都作了隨時“留學”的思想準備。“留學”,是被處死的代名詞。
集中營里殺人通常都是夜里執行,因此,每個人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膽怕被提審。在被提審人未回來之前,同室難友都在緊張的心情下等待著。如果久無消息,心驚膽顫之余,就只有悲憤交集、凄然無語了。
軍統的劊子手,不只以殺人為職業,而且以殺人為娛樂。“他們對于死刑的執行,事前絕對秘密,事后則隨便談論,如何殺法,也說得有聲有色。我從他們那里聽到,殺人方法經常采用的是三種:即槍決、棒殺、活埋,而以槍決者為多。槍決又有‘快板’與‘慢板’之別……”李任夫寫道。
在首任主任何子楨管理時期,犯人放風時被驅趕進大木籠里面。久不見陽光的囚犯,經不住風吹日曬,常有暈死過去的,但死者仍然是站立著,因為木籠里面人挨人,人擠人,每個犯人只有立錐之地。
何子楨的百般酷刑把息烽集中營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活人墓。在國民黨秘密監獄的14年,韓子棟從來沒聽說過哪個共產黨員被判決過。“息烽監獄沒有放過一個暴露共產黨員身份的囚徒,沒有,一個也沒有!這是個死牢!”
如今,在息烽集中營舊址,仍能看到當年的刑訊室——“貓洞”,放風時的木籠,和圍繞四周的“銅墻鐵壁”。“天堂地獄,惟人自擇”;“迷津無邊,回頭是岸”……墻上的感化標語,仍靜靜地訴說著那段血腥的歷史。
不屈的抗爭
由于政治犯的反抗,獄內風波迭起。戴笠惟恐影響軍統名聲,難以收場,遂于1941年將何子楨免職,改由“面善”的周養浩接替息烽集中營主任一職。
周養浩一上任,就打出“改革獄政,建設新監”的旗號,并提出“監獄學校化”、“監獄勞動化”的口號,一反何子楨的高壓殘暴之道,擺出一副“開明管理”的面貌。
于是,“修養人”每天可“散步”1小時,后來又改為上、下午各1小時,最后白天齋房門也不關了,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動。房間的窗戶盡量多開,伙食雖始終未搞好,但比何子楨時強多了。
“實行‘新政’以來,我整日曬太陽,已經曬得成了‘黑人’,我的風濕病、皮膚病都因為經常實行日光浴的關系,漸漸痊愈。”這是韓子棟健康恢復的開始。
周養浩還將全監的犯人組織起來,參加生產勞動。集中營建了十幾個生產單位:印刷所、縫紉部、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洗衣部……同時還直轄汽車運輸隊和消費合作社。沒多久,息烽主任就成了軍統內部人所共羨的肥缺了。
據李任夫回憶,集中營規模一再擴張,“有可容幾千人的大禮堂,以及大小教室、大操場、球場、合作社、菜圃等,五花八門。監牢部分經常可住幾千人之多,但仍時有人滿之患,又屢加擴建。”
1941年,羅世文、車耀先、許曉軒、宋綺云、張露萍等政治犯從重慶押解到息烽。羅世文被捕前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抗戰時期八路軍駐成都辦事處主任,新華社分社社長。他和韓子棟關在一個牢房。
羅世文的到來,成為韓子棟獄中生活的一個轉折點。他對韓子棟講了抗戰爆發后,全國青年向延安去的熱烈情形、紅軍的現況等等。幾天的談話,點燃了韓子棟的希望,他開始以一種新的心情來對待獄中生活。
在羅世文的領導下,監獄成立了秘密黨支部,羅世文任支書,車耀先和韓子棟任支委。車耀先還爭取了被特務抓來做雜役的貧苦農民楊文富替他們在牢房之間傳遞信息,開展統一斗爭。不久,宋綺云、許曉軒、張露萍等政治犯也加入了獄中支部。
針對周養浩宣布的“獄政革新”計劃,獄中秘密支部進行了研究,決定將計就計,把敵人的“獄政革新”變成迷惑敵人、團結朋友、了解情況、改善處境、鍛煉身體、開展斗爭的機會,動員大家去參加各種活動。
站在監獄長(主任)的位置看,周養浩覺得政治犯并不比貪污、小偷、開小差的小特務更使他擔心,因為思想犯都是有知識的,能衡量利害的,不會因一時感情沖動胡鬧亂干。這也是他一再聲明同志(特務紀律犯)、非同志一樣待遇、不分彼此的原因。
“我們這批政治犯,在不損害我們思想信仰的原則下,獲得了足夠的空氣,充分的陽光、運動、工作,使很多人的身體漸漸好起來。”韓子棟回憶道,“我們也得到了公開的或秘密的看報紙雜志的機會。最幸運的還是布置好了通信的方法。”
253號媽媽張露萍
1945年的春天來了,全世界都感受到這個春天帶來的曙光: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在望!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中國歷時8年的抗日戰爭即將勝利!息烽集中營的政治犯也同樣看到了勝利的曙光。但他們清楚地知道,抗戰勝利絕不等于他們個人厄運的結束。
果然,在抗戰勝利前夕,蔣介石派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到息烽集中營。戴笠向周養浩傳達了“蔣委員諭示”趕在戰爭結束之前,對集中營全部犯人進行一次清理。
1945年7月的一天,張露萍剛過24歲生日,就和張蔚林、王錫珍、馮傳慶、陳國柱、楊洗、趙力耕等6人一起被押出集中營。特務告訴他們去重慶,但車至離陽朗壩數里的快活嶺,他們全部遭秘密屠殺。
張露萍是1939年接受南方軍事組派譴,打入國民黨軍統局里電訊總臺的地下黨員。她在電訊總臺組織了軍統局內的7人特別支部,為中共獲取了軍統局電訊總臺人員的全部名單、軍統局各處電臺的呼號與波長等大量機密情報,像一把戳入國民黨心臟的尖刀,攪得國民黨上下惶惶不可終日。1941年,張露萍等7人全部落入戴笠的魔爪之中。
半個世紀后,一位作家在成都中國科學院生物研究所職工宿舍采訪了息烽集中營最年輕的幸存者孫達孟。在集中營跟“253號媽媽”張露萍一起度過的4年鐵窗生涯,讓已年過花甲的孫達孟銘記了一輩子。
孫達孟出生在重慶渣滓洞監獄里。隨父母到息烽集中營時,她剛剛過了一歲,呀呀的叫聲,燦爛的笑容,讓牢房里一下子充滿生機和歡樂,難友們欣喜地叫她“監獄之花”。
剛到息烽時,孫達孟的身子比只貓大不了多少,哭起來幾乎聽不見聲。媽媽告訴她,是露萍阿姨花錢請看守買了只雞燉湯給孫達孟補身子。貴州太陽稀罕,只要太陽出來,露萍阿姨就將孫達孟抱到院子里。不到半年,孫達孟就長結實了,臉上有了血色,能獨立行走,能大聲哭,也能高聲笑了。
“媽媽還告訴我,我說話也晚,一歲多了還只會呀呀地叫,像個小啞巴。忽然有一天,我跟著小蘿卜頭清清楚楚地喊了聲‘253號媽媽’,露萍阿姨驚喜地看著我,然后就把我高高地舉起來,在牢房里一面轉圈子一面歡呼:‘我有女兒啦,監獄之花就是我的乖女兒!’”
3歲后,孫達孟就有清晰記憶了。她記得息烽集中營的冬天特別難熬,露萍阿姨用被子把她和小蘿卜頭圍起來,講故事給她們聽。張露萍犧牲時,孫達孟已經5歲,她曾經無數次哭著喊著:我要253號媽媽!我要253號媽媽!
逃出魔窟
解放戰爭開始了,國民黨在廣西敗退,又準備放棄貴陽。戴笠路過息烽,命令集中營急速搬家。
1946年夏,被關在息烽集中營的數十名重要政治犯,被轉移到重慶“渣滓洞”。不久,羅世文、車耀先被秘密殺害。韓子棟和宋綺云、許曉軒等人又被轉押至白公館。
隨著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反攻,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革命志士被秘密殺害,形勢越來越嚴峻。獄中地下黨支部根據情況認為,集體越獄很難,于是做出“逃出一個是一個”的決定。
為迷惑敵人,韓子棟借一次刑場“陪斬”受到驚嚇裝成了瘋子,從此神情呆滯,蓬頭垢面,無論刮風下雨,總在白公館放風壩里小跑。特務看守叫他“瘋老頭”,對他也比較放心,常常讓他隨看守所的采買當挑夫,去磁器口鎮上買菜。
1947年入夏,獄中黨組織研究決定,讓最有條件的“瘋老頭”韓子棟先行出逃。“小蘿卜頭”的媽媽知道后,用舊布給做了一件衣服和一個白布口袋,叫“小蘿卜頭”送給韓子棟。看到針線縫里有血跡,韓子棟的眼淚唰地流下來。
韓子棟是在息烽集中營認識“小蘿卜頭”一家的。“小蘿卜頭”是宋綺云的兒子,學名宋振中,因頭大身細,像在砂礫亂石中生長的小蘿卜頭,因此得了這個外號。他和父母一起被捕時,還是個嬰兒。
宋綺云一家被殺害時,“小蘿卜頭”只有9歲,他短暫的一生都是在監獄中度過,不知道監獄以外的天地。在息烽集中營,他們一家是被分開關押著的,“小蘿卜頭”和媽媽被關在山坡上“義齋”女牢。
“小蘿卜頭”到了上學的年齡,幾經斗爭,監獄同意在男監里找人教他。“小蘿卜頭”的第一個老師是羅世文,羅世文犧牲后,他又跟著黃顯聲學習。他趁上課的機會,在監獄里傳遞了不少信息。
1947年初秋的一天,韓子棟抓住機會,趁外出采購時逃跑了。靠著天天在白公館跑步的鍛煉,他日夜兼程,經過45天的長途跋涉,終于到達了解放區。當他終于找到黨組織時,竟激動得語無倫次。
逃出魔窟后,韓子棟多次深情地談到了“小蘿卜頭”這位在獄中傳遞情報的“老戰友”。“他年齡小,這不假,但他在監獄里關了8年。更主要的他是我們黨在這特殊環境下培養出來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員,他在監獄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無法代替的。他的事跡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是惟一的。”
陽朗壩的忠魂曲
“我們請他們(幸存者)來,他們都不來。”袁萍對記者說。
對幸存者來說,息烽集中營是一段無法抹去的陰影。苦難的戰友、兇惡的敵人、殘酷的刑罰……幾十年來,噩夢始終縈繞著他們。
“當我想到最痛苦、最悲慘的地方,有好幾次不能不放下筆,跑到河邊上,默默地看那流水,一陣突然的憤怒,想把那河抓起來摔到天的那邊去!”韓子棟這樣寫道。
韓子棟的女兒韓秀融記得,爸爸對炒菜的聲音和弄鑰匙的響聲特別敏感和厭恨。聽到菜放到熱油鍋里發出的吱吱聲響,爸爸的頭發、汗毛都會豎起來。這種聲音使他回想起當年敵人對他用刑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飯也吃不下去。“有一次,爸爸非常生氣地把一串鑰匙從弟弟手里奪去,因為弟弟玩鑰匙的叮當響聲,讓他想起監獄看守開牢門拉他或別的難友去審問、受刑甚至槍殺的情形。這使他很難受,往往要過好幾天才會不想。”
1958年,韓子棟調到貴陽工作期間,重訪了息烽集中營舊址,去“貓洞”憑吊自己死難的戰友們。
當年的秘密監獄早已面目全非,軍統修建的牢房早已了無痕跡,只剩下一片破舊的民居。“誰會知道,這些破爛的土屋,竟是一個時代真正面貌的歷史見證?”韓子棟說。
據說,當年蔣介石選擇息烽關押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就是為了在這里“熄滅革命烽火”。但是,他的意圖不僅沒有實現,反而被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改寫成一段可歌可泣的抗爭史。
如今的息烽集中營革命紀念館已成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也是貴州紅色旅游線路上的經典景區。一次次擴建之后,廣場上矗立的群雕《忠魂曲》漸漸顯得有些矮小了。不過,在袁萍的心里,這些距今并不久遠的人物形象,卻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