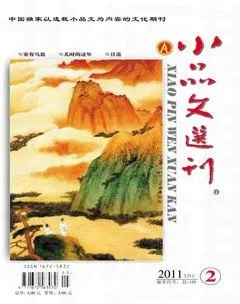春發(fā)草梢頭
無論是在城里還是鄉(xiāng)下,春天最早都是從青草梢上冒出來的。
對(duì)莊稼人來說,田中的野草不僅無用還會(huì)影響莊稼的收成,必須拔除。可莊稼人對(duì)田邊地角上的野草從來都是寬容的、友善的。在鄉(xiāng)下,地里的農(nóng)作物諸如小麥豌豆油菜還來不及開花,甚至連葉子都還沒有舒展出春天的俊俏的時(shí)候,纖細(xì)的田埂上,碧絲般的野草鮮活健康,宛如一群淳樸的孩子樂呵呵地迎風(fēng)舒展開筋骨,隨時(shí)擁抱屬于自己的那份陽(yáng)光。如果是清晨,嫩葉尖上還跳著露水珠,恰似快樂的孩子眨巴眨巴著清澈透明的眼睛。太陽(yáng)是噴香的,幾朵好看的蒲公英斜斜地?fù)伍_小黃傘,把依然有些冷的早春打扮得嬌媚動(dòng)人。
由鋼筋混凝土構(gòu)筑起來的城市從來都需要綠色來妝點(diǎn),但城市人對(duì)于野草的態(tài)度卻說不出的別扭。城市人的綠色是養(yǎng)在花盆里、栽種在被圖紙規(guī)劃得循規(guī)蹈矩的花圃里的。也就是說,城市的花草樹木是被人計(jì)劃好的,哪兒該長(zhǎng),哪兒不能長(zhǎng)……
在我家屋外,有一塊小草坪。自從進(jìn)城以后,每年我都是從這塊草坪上最早得到春天的消息。可是,它沒有長(zhǎng)在指定的地方。沒有長(zhǎng)在指定的地方,就意味著它是一叢脫離規(guī)劃的野草,隨時(shí)都有被刪除的可能。這不,每隔一段時(shí)間,就有園藝工人來把它們鏟除干凈。有一天正好被我遇上。我說,你可不可以不鏟?花圃里的草是綠色,房前屋后隨便長(zhǎng)出來的,也屬于城市的綠色。他說不行。他是負(fù)責(zé)小區(qū)衛(wèi)生的,他靠清除房前屋后的雜草、雜物獲得報(bào)酬。
城市人對(duì)綠色的態(tài)度很有意思,一面嫌城市綠色太少,想盡一切辦法、花不少心思用精巧的盆盆罐罐栽花種草,呼喚綠色;一面僅僅為了整飭環(huán)境而將房前屋后生機(jī)盎然的野草鏟除得干干凈凈。
白居易說得好:野火燒不盡,春風(fēng)吹又生。在被鏟除之后第三天,屋前的野草又長(zhǎng)出來了,依然是那樣生機(jī)勃勃。風(fēng)來的時(shí)候,它們像一小塊被裁剪的小海,淺淺地翻卷起綠色的波濤;雨來的時(shí)候,它們靜穆成接受洗禮的虔誠(chéng)教徒。
草是有根的,怎么能鏟除得了呢?被鏟了又長(zhǎng)出來,長(zhǎng)出來又被鏟除,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高智商的人與一叢沒有絲毫思維的野草展開曠日持久的拉鋸戰(zhàn),想想都有意思。還是園藝工人說得好,要沒有野草,他離被辭退的日子也不遠(yuǎn)了。于是草與人之間達(dá)成了某種默契,人盡管鏟,草盡管生。
那一天,送一個(gè)朋友,這個(gè)朋友放棄條件優(yōu)裕的江南,即將西出陽(yáng)關(guān),獻(xiàn)身大西北建設(shè)。關(guān)于他的這個(gè)選擇,誰(shuí)都不理解,包括我:長(zhǎng)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黃河三角洲是多少人求職就業(yè)向往的地方?他說,我需要一點(diǎn)“野性”,我需要一點(diǎn)蒼涼,我希望生存在能把我的潛力發(fā)揮到最大而不是最小的環(huán)境,我不想被高度發(fā)達(dá)的教條捆住手腳……他的理由還很多。說這話的時(shí)候,我們就坐在屋前那一灘青草前面,有好多天園藝工人都沒有來,那灘草綠成一片旺旺的云,春天的光澤在草葉上閃爍跳躍。風(fēng)之手指是那樣輕柔,彈著翠葉間耳墜一般懸掛的露水珠,一顆一顆地掉到地上,碎成滿地的宮商角徴羽……我頭上有無數(shù)的鳥兒在或遠(yuǎn)或近的地方鳴叫,鳴叫出唐詩(shī)宋詞的意境,從這棵樹到那棵樹,從這種聲音到那種聲音。
那一刻,我讀懂了青草,也讀懂了朋友。
選自《文匯報(bà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