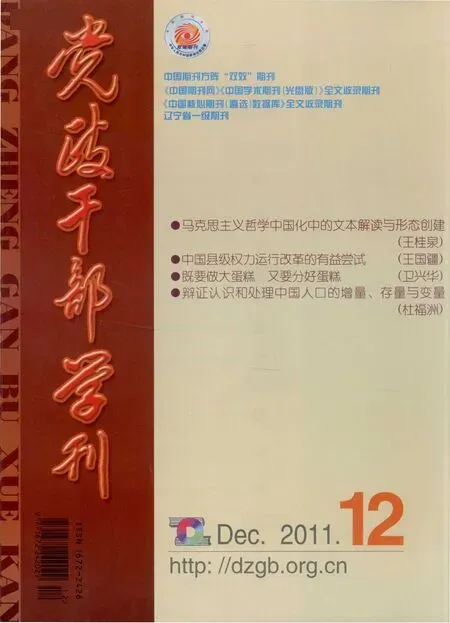政府與社會協商的主體實質性不平等初探
——關于固有性及負面影響的規范性分析
楊守濤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政府與社會協商的主體實質性不平等初探
——關于固有性及負面影響的規范性分析
楊守濤
(北京大學,北京 100871)
政府與社會協商實踐中也存有種種協商主體不平等,為深入分析諸般不平等及其對政府與社會協商實踐的影響,文章以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實質性不平等為分析切入點,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對這種不平等及其相關影響做了進一步的探討。研究發現,政府與社會之間存在著若干固有的實質性不平等,對于政府與社會協商實踐來說,這種實質性不平等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也由此對政府與社會協商實踐產生了種種負面影響,主要包括選擇的強制性、形式上的包容及其導致的協商排他性、協商過程的操控、協商信用喪失等八個方面。
協商民主;政府;社會;實質性不平等
西方協商民主理論發端于20世紀末期,其所倡導的協商模式曾被視作當代民主理論中最具影響力的民主模式[1],但在實際的民主過程中,該模式要產生有用效果,還必須正視和處理好若干現實問題,協商主體平等問題正是其一。然而,目前這一問題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2],故文章擬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對協商主體平等問題進行些許規范性的思考。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在協商民主理論中,對平等的關注存在著兩個維度,一個是把平等作為追求的對象,即解決不平等問題、實現平等是協商民主理論的重要旨歸之一;另一個是把平等作為發揮協商民主作用的前提條件,即把協商主體平等作為提高協商有效性的必要基礎,文章涉及的主要是后者。第二,平等既包括形式上的平等,也包括實質上的平等,前者主要是指那些規定性的、理念方面的平等,如常說的機會平等、政府與社會之間平等交流中的平等,后者是指那些基于地位、資源、能力的平等,文章重點分析的是后者的相對面,即實質性不平等。第三,協商民主理論應用廣泛,除政治學與行政學領域外,哲學與社會學和法學及其他領域也有涉及,如司法審判中的協商、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協商、勞動關系與合同管理中的三方協商,文章關注的核心對象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民主對話。總之,我們這里關心的是政府與社會協商中的協商主體不平等,并且是雙方的實質性不平等。
為此,文章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論述:第一,這種實質性不平等問題是協商民主理論不可能繞開的,它是政府與社會協商過程中的固有問題,有關這一點的論述分為兩個部分,即文章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第二,在政府與社會協商過程中,這種實質性不平等會產生一些什么樣的影響——這主要集中于那些有悖于協商民主理想的內容,有關這一點的論述構成了文章的第三部分。
一、協商民主理論中的政府——社會觀
在協商民主理論中,政府依舊被賦予了必要的角色,盡管不同派別的協商民主理論家們在具體闡述上各有不同,但他們都未曾否認過政府的重要性,他們只是在政府與社會互動的具體方式上各有主張而已。當然,與以往各種民主理論不同的是,他們在不否認政府重要性的同時,更加關注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民主對話、關注在這種雙向溝通過程中呈現出來的民情與民意。
首先,協商民主理論不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民主理論,其創立者與發揚者們肯定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對協商民主理念在當代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德國學者哈貝馬斯曾指出:“行動者能獲得的只能是影響,而不能是政治權力”[3],現今的研究者們仍然堅持著協商民主實踐及其結論只能產生影響力而不可能取代行政權力的觀點,如澳大利亞的何包鋼認為:“民意所產生的溝通權力并不能取代行政權力”[4],臺灣的黃東益和杜文苓也稱:“公民審議所創造的結果是一種‘影響力’,而非‘權力’”[5]。
協商民主理論之所以肯定政府的必要性,主要源于兩大考慮:第一,在利益多元化、基于各利益攸關方完全滿意的共識不可能達成、各利益攸關方自利傾向自私化危險等背景下,出于盡可能保證公平正義、平衡各方利益、保證決策效率、避免議而不決等方面的考慮,協商民主需要一個能從全局出發、通盤考慮決策相關事宜的主體,而政府正是現有條件下的最佳選擇——它通過詹姆斯·S.菲什金(James S.Fishkin)所說的過濾器將原初公民意見轉換成精煉后的公民意見以供決策使用[6]。第二,除了決策的形成有賴于政府之外,決策形成之后的施行一樣離不開政府,正如科林·法雷利(Colin Farrelly)所論述的那樣:依靠行政機關是實際民主社會的特征之一……現代民主社會必須依靠行政機關執行政策與法律[7]。
其次,協商民主理論在肯定政府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時,也要求政府決策必須具備足夠的民意關切。協商民主理論家們特別強調公共決策要以協商民主的方式充分考慮公民意見,在他們看來,公民意見不是鐵了心要和政府決定作對,只要能公開地證明正當性,決策主導者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秘密。也就是說,公民及其負責任的代表要相互給出可被彼此接受的理由以證明所采納的法律與政策是正當的[8]。
至于為什么要充分考慮公民的意見,協商民主理論家圍繞行政機關施行“強制力量”可能導致的非正當性及公民意見的積極作用給出了理由:一方面,由于各種主客觀原因,決策可能存在科學性與民主政治性不足的缺陷,要盡量克服甚至消除這些缺陷及其不利影響,決策有必要在正式制度之外引入協商結論以作參考。正如簡·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指出的:任何論證強制正當性的闡述都不可能是完備的……當認識到強制不可或缺、也認識到任何強制都不可能實現無可爭辯的公平或理所當然的正當時,民主就必須在利用強制的同時找到對抗強制的方法,在政黨、利益團體與其它可作為正式對抗手段的傳統制度外,民主還需要培育和珍視非正式的協商性抵抗領域[9]。另一方面,因為經由協商過程形成的公民意見能“呈現社會的重大關切、核心價值和多元觀點,也顯示經過審慎思辨之后的民意對具有爭議性的政策所持的立場……行政機關必須公開地回應審議民主公民參與所產生的結論……政策決定必須‘給個說法’向公眾說明政策選擇的理由”[10]。
總之,協商民主理論既沒有忽視政府的積極作用,也強調了公民意見這種決策參考或決策影響力的重要價值,而將政府權力的強制與公民意見的影響有機地勾連與整合起來的核心機制就是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特定對話,即喬舒亞·科恩(Joshua Cohen)所論述的那種基于自由、平等及理性的公共推理[11]。
二、政府與社會協商中的主體實質性不平等
前文指出,在協商民主理論中,基于自由、平等及理性的公共推理是有機地勾連和整合政府權力與公民影響的核心機制。然而,政府行使著公民讓渡自身若干權利而形成的公共權力,這使得政府與社會之間存有很多影響彼此有效協商的差異,這里集中分析它們之間的各種實質性不平等。
第一,政府較公民而言,具有若干固有的強勢特征。一方面,政府的集中與公民的分散,即政府部門權力集中、組織嚴密,而公民個人或團體則相對分散,難以有效地組織起來為自身利益辯護或斗爭;另一方面,政府具有公民所沒有的強制力,即政府部門具有合法地使用警察甚至軍隊等暴力手段的權力,公民個人或團體則不可能合法地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再者,政府部門對公民的要求是明確而又具體的,是特定地指向某一個公民或公民組織的,而公民個人或團體對政府部門的要求則往往不那么明確和具體,也往往難以界定為某一政府工作人員或政府部門的責任與義務。此外,政府部門以強制性的稅收來保證自身存續的資金和物力與人力資源需要,先收錢再提供相應公共服務,作為服務對象的公民對政府部門的控制權及對公共服務的選擇權因此大大喪失。
第二,前述強勢特征往往與各種可利用的資源互為強化,如專家智力的獲取、輿論渠道的操控、信息優勢的占據。就政府部門對專家智力的獲取而言,盡管關于專家智力要具有公益關切的呼聲從未間斷甚至日漸趨強,但就像邁克爾·舒德森所指出的那樣:“很多學者對于為權力服務這件事也是樂此不疲的”[12];而在輿論渠道的操控方面,盡管新聞自由度越來越高,但傳統的或新興的傳媒工具出于威逼或利誘抑或其他原因而服務于政府部門的實例確實俯拾皆是。至于政府部門對信息優勢的占據,也是相當明顯的,這不僅體現為政府部門對信息的擁有方面,還體現為政府對所擁有的信息進行處理的能力方面[13]。當然,政府部門相對公民而言固有的那些強勢特征也與政治資源和金錢資本存在著互為強化的關系。
上述諸種固有的強勢特征及其與各種可利用資源的相互強化,意味著政府與社會之間本身就存在著實質性的不平等。加之前一部分闡述所指出的,協商民主理論中公民意見僅僅是一種決策參考或決策影響力,這就造成了政府與社會協商時雙方的實質性不平等,這種不平等也是固有的。在當前現實條件下不可能根除,甚至在未來也沒有將這種不平等根除的可能,換句話說,在政府與社會協商關系中,我們似乎永遠不能實現協商民主理論預設的那種基于自由、平等及理性的理想狀態。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沒有必要再重視協商民主理論甚至拋棄它,分析協商民主理論局限性的目的在于更加全面地認識和理解它,進而更加客觀冷靜地運用它,畢竟在決策制定領域沒有任何決策方法是完美無缺的[14],協商民主理論和其他的任何一種民主理論一樣,是優勢與局限性并存的,我們要做的事情不是拋棄協商民主理論,而是要去探索與創造發揮其應有作用所必須的條件,去盡量完善它并實現它的積極意義。不過,我們現在要做的不是貿然地探索和創造發揮協商民主理論應有作用所必須的條件,而是先理清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實質性不平等對政府與社會協商的負面影響,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
三、實質性不平等對政府與社會協商的負面影響
關于實質性不平等對政府與社會協商的負面影響,文章首先要說的是,一般意義上的協商過程中出現的情況也會出現在政府與社會協商過程中,比如不平等成了強勢方對協商持傲慢與消極被動態度的致因,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強勢方對協商過程的控制與操弄、不平等影響了協商結果的有效性。另外,政府與社會協商的情況肯定有其特殊之處,下文將較為細化地分析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實質性不平等對相關協商民主實踐造成的負面影響。
第一,不告知與不公開。不告知與不公開的情形說到底就是一種內部決策模式,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決策過程和決策所必須的信息對公民隱秘,連決策議程的確定、決策議題的選擇、決策方案的擬定也對公民隱秘,公民根本就沒有機會知道決策一事,更別談參與決策的協商對話了。當然,這是一種比較極端的情況,在民主化浪潮日益推進的今天,除了那些確有必要的涉密決策外,一般都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第二,部分地告知或公開。部分地告知或公開也被稱作選擇性告知或公開,這通常是指在事關公共生活的各種決策中,選擇部分決策以開展政府與社會協商活動,或在某一決策過程中,選擇部分環節與部分信息公開,而被選擇的對象通常都是無關痛癢的,前者如選擇教育、交通、文娛、環保、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決策活動開展政府與社會協商活動,后者如在預選方案確定之后將方案公布以征求意見。
第三,選擇的強制性。選擇的強制性即政府與社會協商中處于強勢地位的政府對決策議程、決策議題、決策備選方案的限制。也就是說,政府部門事先準備了決策所針對的問題、為解決問題要討論的具體議題、要評估擇優的方案,因而協商過程帶有強烈的強制選擇色彩,不是一個自由而開放的過程,完全背離了“論爭是決策過程任一階段的核心”[15]這一協商原則,協商主體在這樣的政府與社會協商活動中,不可能進行充分的論辯,彼此間難以真正地實現作為協商民主理論關鍵期許之一的理性交換。
第四,形式上的包容及其導致的協商排他性。受到決策影響的社會成員全員參與政府與社會協商過程是不可能的,公民一方的協商代表選擇問題由此被提出,而處于強勢地位的政府部門具有意向性選擇代表的可能,協商代表的選擇也因此備受爭議,即便協商代表的產生通過隨機抽取的方式實現,政府與社會協商過程中協商代表的選擇依舊飽受批評。說到底,就是因為處于強勢地位的政府部門容易有意或無意地、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協商代表的進入和討論,以致協商代表所體現出來的包容只是一種形式上的包容,進而使得政府與社會協商過程具有某種意義上的排他性質。
第五,協商過程的操控。在這里,協商過程的操控是指通過提供有利于政府部門立場的決策信息,以便協商在這種真實性和中立性不足的信息導引下達到政府部門所期望的目的,或通過限制協商代表發言時間的方式避免主體對話深挖問題,更有甚者可能會修改記錄主體發言與對話的協商檔案以實現對協商的控制。正如保羅·J.麥金(Paul J.Maginn)在考察西澳大利亞州州政府推行政府與社會協商時所指出的:協商過程處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并且被政府修改,協商過程中缺乏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以便公民參與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論辯和社會學習[16]。
第六,協商結果運用不當。在政府部門與社會關系方面,協商民主理論家們抱有以下期許:馴服權力以使它與多元主義及其他的民主原則和價值更加相容[17]其主要手段就是前述的以協商結果影響政府決策。但政府部門舉辦政府與社會協商活動的目的通常是“為了滿足上司的吩咐或者政治壓力,但無心參考或采納活動結論”[18],所以它們往往會以某種恰當或不恰當的理由為其業已擬定的決策辯護,稱它們的選擇更加有利于公民利益,有的甚至只用結論式的斷語予以回應,連個解釋都沒有,或解釋缺乏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
第七,協商不足之下的決策實施問題。如前所述,政府部門與公民間的實質性不平等影響了協商的公開與透明程度;影響了選擇和辯論的自由與開放性;影響了協商結果的有效運用,這些都是協商不足的表現,與之相伴的便是公民立場與利益得不到體現,這樣的決策付諸實施時必然引致若干問題。關于這一點,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趙成根在論述公民參與政府決策時曾指出:對于涉及到自己具體利益的政府決策,公民一定會有反應,當相關政府決策傷害到公民利益時,盡管他們可能出于避免強制性懲罰的考慮而選擇容忍,但他們一定會采取各種手段來限制其對自己利益的影響,如消極對抗、陽奉陰違,甚至出現意志消沉、頹廢、自殺、偷盜搶劫等社會病[19]。雖然他的闡述和政府與社會協商沒有直接的關聯,但同樣適合于這里的分析。
第八,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協商民主信用喪失。作為前述諸種影響的必然邏輯延續,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協商民主信用喪失主要是指公民不相信他們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商民主是一種事實存在。同時伴隨著公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甚至漸漸出現公民對政府部門所舉辦的協商民主活動持冷漠態度,就像海倫·英格蘭姆和安妮·斯奇內德就美國狀況總結他人觀點時所論述的那樣:“社會中存在著許多對政府行為不滿同時也對政治活動高度冷淡的現象”[20]。
最后,這里需要附帶說明的是:其一,這里的八種負面影響只是一種學理上的劃分,在實際的協商民主情況下,實質性不平等的負面影響或許難以列舉,而且各種影響必將相互交織、更加復雜;其二,在這八種影響之中,前六種屬于實質性不平等對協商活動的直接影響,而后兩種則可以視為前六種影響的邏輯延續,屬于間接影響的范疇;其三,就目前的民主化現實來看,不告知與不公開、不回應、不解釋等較為極端的情況一般不會發生,就像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曾指出的那樣:很多復雜社會中的公民并不是沒有機會協商,而是他們似乎不能有效協商[21]。
總之,在政府與社會的協商實踐過程中,因為雙方之間存在著實質性的不平等,那些擁有權力的政府官員們沒有動機協商,即便他們真的同意協商,他們也有權力不公正地主導論辯過程[22]。
綜上所述,協商民主理論在尊重民意、重視民智的同時,也沒有走向拋棄政府的極端,這當然是一種較為切合實際的民主理念。但正是因為這種兼顧二者的兩不誤立場,使得協商民主理論應用到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民主對話時,遭遇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各種固有的實質性不平等,進而產生了選擇的強制性等八個方面的負面影響。
但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第一,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實質性不平等也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如節約決策成本、提高決策效率、把握決策全局;第二,盡管政府部門與社會之間的實質性不平等對政府與社會協商造成了如此多的負面影響,但這種實質性不平等未必就是造成這些影響的根本原因,它的存在只能說明政府部門有可能干預和破壞協商的真實性,使這種可能變為現實的因素才是更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比如吳興智曾指出的壓力型體制[23],再比如莫哈默·奧克德雷 (Mohamad G.Alkadry)提到的技術理性、官僚經歷、組織內的規則與層級及控制[24];第三,毫無疑問的是,協商民主及政府與社會協商是必要和重要的、“是理論上有力和制度上可行的”[25],我們要做的是去探索盡量避免前述實質性不平等造成負面影響的方法。所以,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結合既有的政府與社會協商實踐去深究實質性不平等、深挖潛藏在其背后的影響因素,并在原因分析的基礎上盡力探究有益于減少實質性不平等及各種相關因素負面影響、提升政府與社會協商效用的參考措施,這一研究工作將留待日后去做。
[1][17]Will Kymlicka,BashirBashir.The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2]Kevin M.Morrison,Matthew M.Singer.nequality and Deliberative Develop-ment:Revisiting Bolivia's Experience with the PRSP [J].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Nov2007,Vol.25 Issue 6.
[3][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M].北京:三聯書店,2003.
[4][澳]何包鋼.協商民主理論、方法和實踐[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5][10]黃東益,杜文苓.行政民主與審議民主之實踐與參與手冊(Ⅱ)[M].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8.
[6]James S.Fishkin.When the People Speak: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Public Consulta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7]Colin Farrelly.Justice,democracy and reasonable agreement [M].Basingstok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8][14]Amy Gutmann,Dennis Thompson.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2004.
[9]Jane Mansbridge.Using Power/Fighting Power:The Polity [A].Seyla Benhabib.Democracy and difference: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C].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1996.
[11]Joshua Cohen.Democracy and Liberty[A].Jon Elster.Deliberative Democracy[C].Cambridge,U.K.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8.
[12][美]邁克爾·舒德森.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M].北京:華夏出版社,2010.
[13]周志忍.政府管理的行與知[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5]Giandomenico Majone.Evidence,argument,and persuasion in the policy process[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c1989.
[16]Paul J.Maginn.Deliberative Democracy or Discursively Biased?Perth's Dialogue with the City Initiative[J].Space and Polity, Dec2007,Vol.11,No.3.
[18]林國明,黃東益.行政民主之實踐:縣市型議題審議民主公民參與[M].臺北:“臺灣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8.
[19]趙成根.民主與公共決策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20][美]海倫·英格蘭姆[美]安妮·斯奇內德.建設公民權:政策設計方案中的微妙信息[A].[美]海倫·英格蘭姆[美]斯蒂文·R·史密斯.新公共政策——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C].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21]James Bohman.Public deliberation: pluralism,complexity,and democracy [M].Cambridge,Mass.:MIT Press,c1996.
[22]Iris Marion Young.Activist Challenges to Deliberative Democracy[J].Political Theory,Oct2001,Vol.29 Issue 5.
[23]吳興智.公民參與、協商民主與鄉村公共秩序的重構——基于浙江溫嶺協商式治理模式的研究[D].浙江大學,2008.
[24]Mohamad G.Alkadry.Deliberative Discourse between Citizens and Administrators:If Citizens Talk,Will Administrators Listen?[J].Administration & Society,May2003, Vol.35 No.2.
[25][南非]毛里西奧·帕瑟林·登特里維斯.作為公共協商的民主[A].[南非]毛里西奧·帕瑟林·登特里維斯.作為公共協商的民主:新的視角[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責任編輯 侯 琦
D60
A
1672-2426(2011)12-0046-04
楊守濤(1985-),男,貴州畢節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公共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