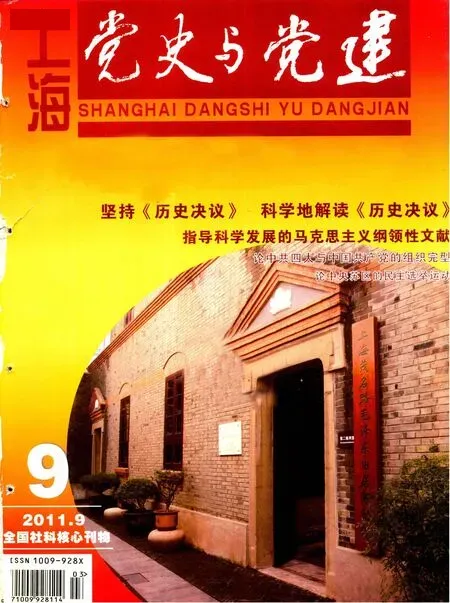近三十年中共黨史日記論略
●趙金平
近三十年中共黨史日記論略
●趙金平
作為中共黨史研究非常重要的史料類別,中共黨史日記數(shù)量不多,因而很長時期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近三十年來,中共黨史日記的刊布有了很大發(fā)展,中共黨史研究中的私家史料的價值,包括日記,引起越來越多的重視。這一切都說明,對中共黨史日記的總結(jié)已經(jīng)成為必要。
中共黨史日記;刊布概況;史料價值
本文所說的中共黨史日記,主要是指在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過程中中國共產(chǎn)黨人留下的記述個人革命經(jīng)歷的日記資料,也包括親歷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直接接觸的國內(nèi)外人士留下的相關(guān)日記史料。在革命戰(zhàn)爭中,作為革命黨的中國共產(chǎn)黨面臨的政治環(huán)境非常惡劣,無論是黨內(nèi)同志還是黨外友好,都缺乏寫作和保存有關(guān)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日記的條件,因而這類史料留存不多。經(jīng)過建國后的政治風暴,特別是“文革”的破壞,幸免于難的中共黨史日記更少。可喜的是,隨著“文革”結(jié)束后思想解放運動的蓬勃開展,中共黨史上幸存的日記史料大量刊布,為中共黨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和視角。同時,受歷史學研究的發(fā)展趨勢影響,中共黨史研究也從宏大敘事向微觀實證方面延伸,因而對私家史料的重視日甚,黨史日記的價值逐漸凸顯。以上兩點為中共黨史日記研究的總結(jié)提供了必要。
一、中共黨史日記出版概況
根據(jù)中共黨史日記記述的內(nèi)容和寫作者的身份,近三十年來刊布的中共黨史日記,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反映中國共產(chǎn)黨從建黨前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期間不同階段的歷史。具體如:1.有關(guān)建黨前后的日記。該類日記記述撰者如何從一個舊時代的知識青年轉(zhuǎn)變?yōu)闊o產(chǎn)階級革命者以及他們在入黨前后的斗爭經(jīng)歷。主要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楊闇公日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惲代英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旅日日記》等。2.有關(guān)紅軍長征的日記。在中共黨史日記中,比較集中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長征的,如肖鋒的《長征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林偉的《“戰(zhàn)略騎兵”的足跡》,戰(zhàn)士出版社出版;張南生的《一個紅軍戰(zhàn)士的日記(1930年5月-1934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童小鵬的《軍中日記(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解放軍出版社出版;《陳伯鈞日記(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陳伯鈞、童小鵬、伍云甫、張子意等的《紅軍長征日記》,檔案出版社出版;《彭紹輝日記》(長征部分),解放軍出版社出版;趙镕的《長征日記:1933年12月14日——1936年10月24日》,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等。3.記述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日記。主要有:《陳賡日記》,戰(zhàn)士出版社出版;《邵式平日記》,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皮定均日記》,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王紫峰的《戰(zhàn)爭年代的日記》,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蔡邁輪日記》,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保中的《東北抗日游擊日記》,人民出版社出版;《佩劍將軍張克俠軍中日記》,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秦叔瑾的《戰(zhàn)地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陣中日記(1946年11月—1948年11月)》(上下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此外,還有完整記述長征、抗日戰(zhàn)爭和人民解放戰(zhàn)爭三個歷史階段的日記,如:《謝覺哉日記》(上下冊)、《賴傳珠日記》、《王恩茂日記》(共五冊)、《獨臂上將彭紹輝日記》等。
(二)文藝界共產(chǎn)黨人的日記。無產(chǎn)階級文藝界人士的日記也有很多,記錄了文藝工作者的心路歷程和生活實踐及他們在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道路上的困惑與彷徨、激越和奮進。研究他們的日記,對于了解知識分子無產(chǎn)階級化過程很有幫助。其中有些日記充滿情景描寫,語言優(yōu)美,也有許多情感抒發(fā),細膩生動,但對于黨史研究價值甚少。也有如《郭沫若日記》寫作時即為發(fā)表,失去了日記本身的特點和本身的史料價值。但絕大多數(shù)此類日記的史料價值是很高的。無產(chǎn)階級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帶著對生活細膩的體驗和敏銳的感知,用他們真摯的筆觸記錄下來。改革開放以后這些日記得以出版,他們自己或后人懷著時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日記內(nèi)容基本不做修改,真實地呈現(xiàn)作者各種各樣的情感、生活經(jīng)歷,成為研究者不可多得的史料。這類日記主要有:阿英的《敵后日記》(上下冊)、《阿英日記》,《陽翰笙日記選》,楊沫的《自白——我的日記》,查國華、查汪宏編的《茅盾日記》,趙帝江、姚錫佩編的《柔石日記》,等。
(三)親歷中國革命的外國人日記。一些外國人親歷中國革命,其中為數(shù)不多的人留下了日記記錄他們見聞中的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國革命。獨特的他者視角,賦予這類日記彌足珍貴的價值。如:(蘇)維·馬·普里馬科夫著、曾憲權(quán)譯的《馮玉祥與國民軍——一個志愿兵的札記(1925—1926)》,巴庫林著、鄭厚安等譯的《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札記》,比·庫·巴蘇著、顧子欣等譯的《巴蘇日記》,(蘇)彼得·弗拉基米洛夫著、呂文鏡等譯的《延安日記》,馬細譜等譯的《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美)德克·博迪著,洪菁耘、陸天華譯的《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奧)卡明斯基主編、杜文棠等譯的《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等。
還有一些黨史文獻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把相關(guān)書信、日記按照著者或者內(nèi)容放在一起出版,如《彭雪楓書信日記選》、《黃勇書信日記選》、《但求身后有靈魂:革命書信、日記選》、《名人千字文書信·日記卷》等。
二、中共黨史日記的史料價值
日記是第一手資料,絕大多數(shù)的日記作者寫作純粹是給自己看的,作者毫無顧慮地抒發(fā)自己的感受,盡情臧否人事,中共黨史日記也有這樣的特點。可見,日記的個人私密度高,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同時,日記的價值還在于其即時性。和回憶錄不同,日記是作者第一時間記錄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其真實性是無法替代的。
需要注意的是,日記的史料價值正在于其即時性和私密性。失去了這兩點,日記本身的特點和價值也就不存在了。就前者而言,如果作者當時并沒有撰寫日記,一段時間后根據(jù)自己回憶或者有關(guān)檔案以日記形式撰述,并且公開刊布,其本身即便沒有欺騙讀者的意圖,卻的確會造成讀者誤認這樣的寫作為其形式所體現(xiàn)的內(nèi)涵而產(chǎn)生輕信。而一些作者在公開出版時出于種種考慮往往對原始日記予以修改,這種做法也會極大損害日記的原始性和真實性;①就后者而言,如果作者在寫作日記時,目的即為公開刊布,其史料價值顯然也大打折扣。如有一些名人知道身后日記會被公布,因而也會在日記中偽造史實,說假話,以欺騙后人。[1]這樣的情況在中共黨史日記中也很難避免,研究者利用有關(guān)日記時需要謹慎考證。
除了上述主觀因素,客觀因素也影響了中共黨史日記的史料價值。主要表現(xiàn)為:首先,鑒于革命戰(zhàn)爭年代的危險及由此而來的高度警惕和組織紀律性,作者在日記中涉及軍事、政治機密或行動時,往往語焉不詳,還有許多只有自己能夠了解的代號、暗語等。同時,由于年代久遠,原始日記中的字跡模糊甚至紙張損壞,導致內(nèi)容缺失。如果作者不能親自解密,則其引用顯然受限。②其次,相關(guān)黨史日記經(jīng)歷革命戰(zhàn)爭年代和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也有許多佚失。③第三,以往在刊布時,由于政治影響,作者或出版機構(gòu)也會對日記進行節(jié)選甚或改編,這就嚴重影響日記的完整性,進而影響其史料價值。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可喜的是,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作者認識到,“日記的價值是真實,這是它存在的關(guān)鍵”,因此作為“一個平凡的人,一個普通的共產(chǎn)黨員”,日記中流露的在逆境中的“不健康的情緒”或者“不大正確的東西”也應當展示給讀者,“不管我有多少缺點毛病,但日記中的‘我’是個真實的人,是個沒有矯揉造作、沒有喬裝打扮的人”。[2]這樣的認識對于中共黨史日記的出版、刊行和利用是一個福音。
不同時代日記內(nèi)容變化很大,同一部日記的史料價值也隨著時代發(fā)展而不斷被挖掘,中共黨史日記也不例外。就前者而言,傳統(tǒng)“日記偏重于修身、為人之道,是封建士大夫的習慣,十九世紀中葉,還有相當大的勢力”[3]。近代以來的日記也保留了一些類似的傳統(tǒng),中共黨史人物,如周恩來、惲代英等人的早期日記中,也都有大量類似記載。但總的來說,這一趨勢隨著革命時代的到來而發(fā)生很大變化。特別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投身于民族獨立的革命和人民的解放事業(yè),成為職業(yè)的革命家,他們的日記所及也就主要是個人在革命中的經(jīng)歷和感受,有關(guān)個人修養(yǎng)也是針對適應革命需要而言的。傳統(tǒng)的修身養(yǎng)性、待人接物為主已經(jīng)為憂國憂民、政治革命所取代。當然,日記中個人對革命的認識和感受,相對于公開發(fā)表的文集等私家史料是不一樣的,和各類文書、檔案更不可同日而語。就后者來說,中共黨史日記在長期專注于宏大敘事題材的中共黨史研究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相當長的時期,許多的黨史日記節(jié)選本,都刻意展現(xiàn)正面宣傳功能。但隨著史學研究的發(fā)展,中共黨史研究也從宏大敘事逐漸向微觀實證延伸,社會學、心理學等研究方法在中共黨史研究中應用日益廣泛。與此相應,私家史料,特別是日記、書信等記述史料,日益受到重視。中共黨史日記的史料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對一些個人的研究方面,有助于深入研究對象的內(nèi)心世界,更準確全面地把握和評價研究對象;也有助于中共黨史研究的關(guān)注重點從政治、軍事、革命等宏大題材到家庭生活、社會、個體成長等微觀領(lǐng)域的轉(zhuǎn)變,從政治精英到普通大眾的轉(zhuǎn)變。這種轉(zhuǎn)變及隨之而來的對私家史料的重視顯然與1980年代以來歷史學界研究重點的轉(zhuǎn)移和研究領(lǐng)域的拓展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4]在歷史研究視野不斷擴大的今天,中共黨史也不再僅僅是政治史、經(jīng)濟史、階級斗爭史,即便是純粹的生活記載,也有其社會生活史研究的意義,在這一點上研究者和1980年代中期的認識已經(jīng)不可同日而語。那種認為,一些日記中關(guān)于日常生活的記載,多數(shù)沒有史料價值,而只有一些擔任重要職務、地位顯要的人,其日記涉及政治內(nèi)幕,才稱得上是重要的史料,[5]這樣的觀點隨著近三十年歷史學以及中共黨史研究的發(fā)展,已經(jīng)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考評中共黨史日記的史料真實性和客觀性時,記述者的立場也值得特別注意。以上述在華共產(chǎn)國際、蘇聯(lián)人士日記為例,如上所述,在中共黨史發(fā)展中,有一些外國人介入其中,他們親歷中共黨史并留下了日記。這樣的記錄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自身的日記不同,帶著全新的視角和不同的立場來觀察、接觸中國共產(chǎn)黨人。他們或許因為對中國文化、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理解不深,日記缺乏深刻,需要仔細鑒別利用。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些日記有助于完整全面地研究中共黨史。如季米特洛夫日記,對于我們研究抗日戰(zhàn)爭前后的中共黨史就有很大幫助。但其中也有一些日記記述突出甚至夸大蘇聯(lián)對中國革命援助的作用,或者夸大自己在急劇變化的革命年代的超前意識,如普里馬科夫的《一個志愿兵的札記》、巴庫林《中國大革命武漢時期見聞錄: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札記》等。其中尤其突出的是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該日記是中蘇關(guān)系惡化后,蘇聯(lián)領(lǐng)導集團對原稿進行篡改,于1973年以《中國特區(qū):1942—1945》為名發(fā)表的,旨在適應反華需要,對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共領(lǐng)袖毛澤東等人進行攻擊。1975年美國出版了英譯本,改名為《弗拉基米洛夫日記》,中文本即根據(jù)英譯本翻譯出版的,改名《延安日記》。該日記修改之嚴重,就連該書英譯本的出版說明中都指出:“本書前后有不一致之處,可能加進了新的‘說明’材料。因此,這本書既可以作為一個歷史文獻,也可以作為一個現(xiàn)代文獻來讀。”(《延安日記》翻譯的“德布爾戴公司的出版說明”)中國的研究者同樣應重視這個問題。
總的來說,近三十年中共黨史日記的出版、利用幾乎是經(jīng)歷從無到有以至逐步繁榮的巨大進步。但相對于近現(xiàn)代史而言,中共黨史日記的出版、利用仍然存在不足。諸如公開出版時的刪節(jié)、修改等現(xiàn)象仍舊存在。研究者在此基礎(chǔ)上引用日記史料或者躊躇不決,或者不加分析地簡單直接引用,都不利于中共黨史日記本身的價值。因而諸如蔣介石日記所引起的廣泛關(guān)注和充分研究在中共黨史研究中還未有聞。只有中共黨史日記盡可能全面完整地出版和研究者利用過程中嚴謹規(guī)范的形成,才標志著中共黨史日記史料應用的成熟。
[1][5]張憲文.中國現(xiàn)代史史料學[M].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6.227.
[2]楊沫.自白——我的日記[M].花城出版社,1985.
[3]陳恭祿著.中國近代史料概述[M].中華書局,1982:199.
[4]鄒兆辰等.新時期中國史學思潮[M].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161-166.
注釋:
①如《肖鋒日記》就受到類似批評,肖鋒《長征日記》,經(jīng)過1937年、1945年和1970年代的多次修改。盡管作者是對有關(guān)事件的確認,但日記不是回憶錄,當初的原始記述最可珍貴,修改后顯然也影響其原始真實性,甚至內(nèi)容是否有所改動,也需要考證。有一些研究者即視其為回憶錄。見洪小夏.對金門戰(zhàn)斗“三不打”的質(zhì)疑與考證——兼論回憶錄的史料價值及其考辨[J].近代史研究,2002,(3).
②如《謝覺哉日記》中1921年6月29日條,就記錄作者和毛澤東一起去上海,是“赴全國OOOOO之招”。其中圓圈作者自注是“共產(chǎn)主義者”代指。如無作者解釋,他人根據(jù)猜測難免失之偏頗。
③仍以謝覺哉日記為例,其中就佚失了作者大革命時期和長征途中部分(1923—1936);另如周保中的日記就有部分(1931—1936年初)落入敵手;林伯渠日記就有部分在“文革”中被焚毀;張聞天日記則已無從查考。
D239
A
1009-928X(2011)09-0028-03
作者系淮陰工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學部講師
■責任編輯: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