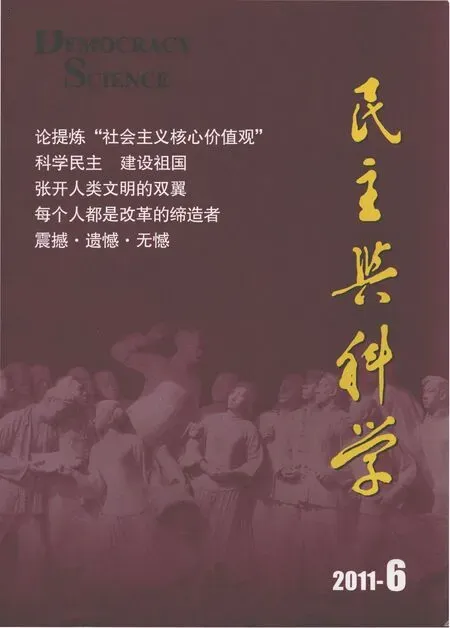以正義構筑道德大廈
■蔡 偉
近年來,關于道德重建的討論和報道鋪天蓋地,連高層也發出“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的感嘆。種種道德淪落的事件不斷刺激著人們的神經。
事實上,我們一直以來都在不斷強調道德建設。比如要求學生“德智體美勞”,德便放在首位,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發布了《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等種種舉措,在社會大張旗鼓地開展道德教育活動。然而,從現實來看,收效甚微。道德滑坡的背后隱藏著更深層次的是價值信仰危機和社會制度危機,比如社會分配不公,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拜金主義,越演越烈滲透于社會各個部門和行業的貪污腐敗,公權力對私權的侵犯,“良法”沒法得到有效的尊重和執行,投機主義等等。這些形成一個很壞的示范效應,而使得惡人和惡行肆無忌憚,而老實人、好人只能吃虧,從根本上動搖了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和價值信仰。
道德的現代核心:正義
道德是適用于全族群、對該群體的內在價值和外在生活具有普適性的精神要求。不同人,不同時代對道德有著不同的理解和要求。
中國歷史上對道德有過六德(知、仁、圣、義、中、和)、三德(禮、義、仁)、五常(仁、義、禮、智、信)等的論述。根據周輔成先生的考證,古代的“義”是指“公正”,“義行”就是“公正行為”。然而,這種“義”與現代社會具有普適性的正義要求有很大的距離。在傳統的農耕時代,“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的大小要依著中心勢力的厚薄而定”,“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別人所聯系成的社會關系不像團體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個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費孝通)正義的要求和適用在不同人群中也常有不同。于是,我國傳統上的道德觀,更多的體現為私德。梁啟超把中國古代的道德稱為“私德”,而把現代道德命名為“公德”。“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闕如……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為德育之中心點”。
無疑,人們在不同的時期和社會有不同的道德觀,但無論何種道德觀它總是要維護某種正當性的價值外觀,這種正當性便體現為正義,無論它實質上是否是真正的正義或者是大多數人所認可的正義。正義是一種社會道德準則和人們的道德行為規范,自從是非觀念產生以來,道德便有了公平公正等正義的理念,雖然這一理念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理解;比如正義有時僅僅在某個特定群體內有效,甚至有時有著根本的對立,但是它卻一直引領著相應法律規則的制定和發展。
正義的精神內核和核心價值,使得某些道德戒律能夠上升成為法律,并得到國家暴力機器背后的支持。當代社會是一個商業社會,是以契約為中心連接起來的,每個個體都需要和其他社會個體互通有無,交換產品或者服務,于是人與人之間的依賴程度大,每個人的行為也容易影響到其他個體。以傳統血緣為紐帶的道德行為規范不足以規范人們的行為,這為正義提供了基礎。正如亞當·斯密所言,仁愛是為鄰里而存在的,它適用的是熟人;而正義則可以適用于陌生人;仁愛涉及私人關懷,是具體行為問題,而正義則要處理的是公眾利益問題、普遍法則問題;而仁愛對社會的存在來說不如正義那樣重要;以正義為核心的現代道德,能把人們引向合理追逐自身欲望與利益的自由。
現代道德是社會性的道德,是以正義為中心的。(陳赟)而正義正是法律的核心概念和價值追求。《尤士丁尼法學概論》指出:“正義是讓每個人各得其所,這樣一種始終不變的意圖……法律的戒規是:誠實地生活,不加害于他人,讓每個人各得其所。”羅爾斯《正義論》也強調道:“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者廢除。”于是,在現代,法律與道德的核心樞紐為正義,正義也就成為現代道德要求的核心價值。
不義之下蒼白的道德
在社會的調控系統中,道德、法律、文化等各自發揮著它們的作用。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線,如果法律沒有實現正義,那么一切的道德要求都顯得十分蒼白無力。而社會正義則涉及法律、分配、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道德提倡“善”,我們的道德教育通常要求無私。然而“社會將公正而不是無私作為它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它的目標是為所有人尋找機會的均等”。(尼布爾)
在我國現實中,種種原因之下,不正義廣泛存在著,正在不斷侵蝕著這個社會的價值基礎。比如在經濟上,國家在資源分配上傾重于城市,利用產品差價、戶籍制度等剝奪農民的利益,使得農村長期以來發展大大滯后于城市;在政治生活領域,農民的聲音缺失,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難以有效得到解決;尤其是近來的違法拆遷等等,不一而足。
這些種種的不正義,很多還由法律法規直接確定下來,成為法定的不正義。在公法領域,最為典型的就是歷史上農民的選舉權不均等問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曾經規定自治州、縣、自治縣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鎮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這種1/4選舉權的規定深為學界所詬病。2010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選舉法的決定,最終我國農村和城市每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比例規定為1:1,在規定上實現了選舉的正義。
另外,同樣受社會關注的還有“同命不同價”的問題。我國法院確定人身損害賠償標準的主要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通過的《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其中的第二十五條規定殘疾賠償金根據受害人喪失勞動能力程度或者傷殘等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自定殘之日起按二十年計算。第二十九條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依據這一司法解釋,農民在人身損害賠償中獲得賠償數額遠遠少于城鎮居民。
面對這種規定在實踐和法理中的困境,不少地方在它的適用上都進一步進行完善。如2006年11月1日開始實施的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安全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規定:農村受害人在發生交通事故時,已在城鎮連續居住一年以上,且有正當生活來源的,可以按照城鎮居民標準計算賠償數額。2009年12月26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17條也作出了新的規定: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但這僅適用于同一侵權行為的情形。國務院于2010年12月20日修改的《工傷保險條例》規定: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標準為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這一規定統一了各地的工亡補助金標準,在全國實現了“同命同價”,為法律的正義邁進了一大步。
對于法律正義,雖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它卻是可感知的,在法律制定和修改過程中處于弱勢、沒有話語權的農民能認同這種規定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要使一個人因為社會規范的合理性而遵從它,關鍵是要向他表明什么是公正”。(約翰·威爾遜)如果不能,在這種赤裸裸的不正義之前,一切的道德說理都是如此的蒼白無力。
法律僅僅是社會的一種治理機制,法律的不公正直接影響了法律的權威,使得公民之間難以形成現代契約社會所必需的信任的紐帶。正如中國倫理學會秘書長孫春晨所言:“整個社會彌漫著互不信任的社會心理。在經濟領域,消費者對商品和服務不信任;在政治領域,公眾對官員和政策效力不信任;在法律領域,公眾對司法不信任。最后這些不信任擴展為社會成員之間的相互不信任。這樣一來,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為,在有些人那里就成了不太可能的事——小悅悅很可能就是這樣被漠視的。”
雖然社會在不斷發展進步,很多方面在趨向正義,然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正義重建道德
正義并不是平均主義,它是以機會平等為目標的。它要求相同的情況得到相同的對待,公民不論其出生、地位、財富、性別、種族和宗教信仰等情況,能夠有平等的機會獲得社會和自然資源,不因為家庭等外部因素而失去本應該得到的機會。在政治領域,平等的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經濟領域,相應的競爭領域能夠向社會公眾公平的開放;在社會保障領域,公民的社會保障條件是一致的,不因權位而享有特權;在文化教育領域,每個公民都同等享有同等的受教育和利用文化資源的權利等等。
一旦社會的法律制度對權利、義務、資源等分配不均衡,將為社會不公提供孳生和蔓延的土壤。在一個黑白顛倒、道德淪喪的社會中,個體也難以獨善其身,而在一個正義的社會中,社會機制本身就能去濁揚清,個體的正義感也隨之增強。正義的實現,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于提高人們遵紀守法的意識,還有助于培養人們高尚的道德情操。
正是我國的制度正義遠遠落后于社會的發展,導致它非但沒能給良性的道德發展提供指引,反而破壞了當代契約社會陌生人之間最應該具有的信任,導致道德的滑坡。“見死不救”的冷漠傳染病可怕,“見義勇為”以后英雄流血又流淚更是令人恐懼,因為它扼殺了本來就很脆弱的為善之心。姑且不論南京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等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隱情和它們的法律邏輯,這些都給社會公眾強烈的暗示:小心見義勇為會惹火燒身。在趨利避害的本性驅動下,見義勇為在此背景下難上加難。近期報道的數起市民花費不少時間精力和金錢舉報稅務違法行為時,卻只得到幾元或者十幾元的獎勵,還要舉報者申請行政復議和起訴,其中一個案件法院還判令舉報人將其獲得的1.5元巨獎中的0.5元返還國稅局。國家機關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行為和規定實在扼殺了公民與種種“惡”作斗爭的“善”心。
因此,與其空洞的道德說教,還不如盡力修補社會的不公之處,并且用制度來引導人們行善。完善每個人的正當權利能夠得到保障的制度規范體系,使其能有效調節人的善惡行為,保護人的“正當的行為”,懲罰人的“失當的行為”,提倡和鼓勵人的“崇高的行為”。因此,我們必須完善制度保護見義勇為者,才能讓更多的人敢于挺身而出,就像很多國家通過各種制度保護證人一樣,讓舉證犯罪的人無后顧之憂;還可以考慮建立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民事損害時的責任豁免或者自身造成損害時向獲利方求償的法律制度;再比如建立撿獲失物上交的獎勵制度,對拾金不昧者,按一定的比例進行獎勵,沒法找到失主時,獎勵幅度更大,或者直接將全部失物都作為獎勵……此等良法將更能引導人們行善。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發展迅猛,但同時價值觀的迷失、道德失范在很多領域都存在。“在社會轉型時期,道德建設應該與法律規范相協調,其協調的紐帶是公正。而建立在公正基礎上的法制,理所當然被視為社會美德的生長點”。正義正是填補道德空白的最主要基石,唯有以正義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道德體系才能經風歷雨而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