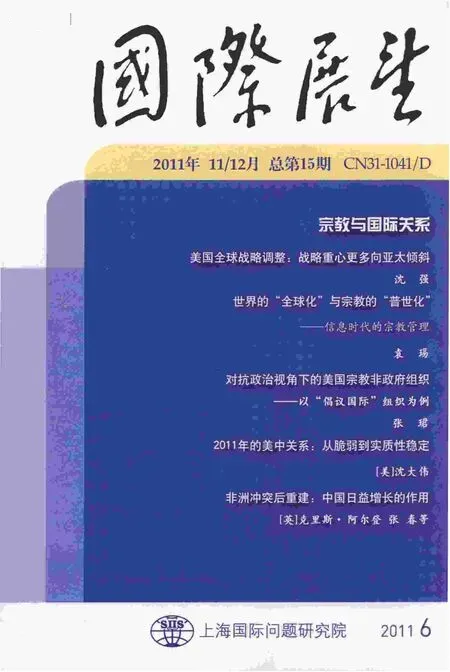世界的“全球化”與宗教的“普世化”——信息時代的宗教管理
袁 瑒
世界的“全球化”與宗教的“普世化”
——信息時代的宗教管理
袁 瑒
本文旨在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用新自由主義學者約瑟夫·奈所提出的復合型相互依存為理論框架,來探討信息時代世界全球化與宗教普世化的關系。筆者嘗試運用“網絡封建主義”、“散居共同體政治”、“散”“合”同步性、從“廣播”到“窄播”、“豐富的悖論”等概念對影響國際關系的網絡宗教現象加以剖析,從而認為單純的“技術決定論”無法解釋復雜的宗教、政治、技術之間的互動關系,學界需要運用多元方法論視角以及跨學科知識結構所構成的學術整合能力。
全球化 宗教管理 網絡政治
如果說,相互依存是 20世紀70年代的流行語(buzzword),后現代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的流行語,那么全球化便是20世紀90年代的流行語。時近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之末,全球化并未停止其席卷全球的腳步,而是以一種更深刻、更微妙的形式滲透在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的觸角不僅影響了人類包括經濟、軍事、環境、健康在內的物質生活,也影響到了人類包括思想、文化、信仰、宗教在內的精神生活。各種社會科學開始對全球化這一現象展開系統的思考與研究,一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論或理論系統,另一方面也提出不同的研究對象或課題。其中,宗教全球化問題吸引了社會學家、心理學家、人類學家、神學家、比較宗教學家、公共政策學家等各類學者的注意力,并逐漸進入國際政治學領域。
早在1985年,羅蘭·羅伯遜(Roland Robertson)便在和瓊·奇里克(JoAnn Chirico)合著的論文中,將基要主義的復興、各國政教關系的沖突和新興宗教的繁生,列為在全球范圍內普遍發生的、具有政治意味的三大宗教現象。①Roland Robertson & JoAnn Chirico, “Human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wide Religious Resurgence: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Sociological Analysis, Vol. 46, No. 3, 1985, pp.219-242.21年后,提摩太·沙恩(Timothy Samuel Shah)和莫妮卡·托夫特(Monica Duffy Toft)在以《神何以勝出?》為題的文論中更是直言,“全球政治越來越帶有或可稱之為先知性政治(prophetic politics)的印記” 。②Timothy Samuel Shah & Monica Duffy Toft, “Why God is Winning?” Foreign Policy,July/August 2006, p. 39.除了眾所周知的“9·11事件”、巴以沖突和科索沃沖突外,兩位學者列舉了一系列影響國際政治議程的宗教運動,或具有普世宗教意味的政治事件:伊朗革命、阿富汗塔利班的崛起、戰后伊拉克的什葉派復興、南非由大主教領導的反對種族隔離運動、穆罕默德的卡通風波、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伊斯蘭抵抗運動、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核試驗、美國福音派對美國選舉與外交的影響等。難怪有學者認為,不深悉宗教就無法完全理解國際關系。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探討國際關系中的宗教問題,在國內學術界尚不多見,但已有幾位資深學者從不同的方法論進路作出了可貴的嘗試。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卓新平所長所撰一系列論著《“全球化”與當代宗教》、③卓新平:“‘全球化’與當代宗教”,《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④卓新平:《“全球化”的宗教與當代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另同名論文發表于2009年4月的《中國宗教》。和《“全球化”與當代中國宗教》,①將世界范圍內的宗教問題與中國境內的宗教發展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復旦大學的徐以驊教授近年亦發表了很多以全球化為視野的論著,包括《當前國際關系中的“宗教回歸”》、②徐以驊:“當前國際關系中的‘宗教回歸’(代序)”,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宗教與國際關系》(第四輯),時事出版社,2007年。《當代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③徐以驊:“當代傳教運動研究的‘四個跨越’”,《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1 期。④ 徐以驊:“宗教與當代國際關系”,《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第2期。《宗教與當代國際關系》等。④而將全球化、宗教、國際政治、信息時代加以綜合考察的學術性論著則更為罕見,復旦大學碩士生謝潔與黃平合撰的《網絡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系——兼論美國宗教的傳播對國際關系的影響》⑤謝潔、黃平:“網絡時代的宗教與國際關系——兼論美國宗教的傳播對國際關系的影響”,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多元一體的美國宗教》(第二輯),時事出版社,2004年。一文做了可貴的嘗試。2005年,復旦大學舉辦了“網絡時代的宗教”學術研討會,其中與美國宗教和國際關系有關的論文被收入《宗教與美國社會》第三輯,⑥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網絡時代的宗教》(第三輯),時事出版社,2005年。這本論文集可以說是國內這一領域當前階段性的成果。在該論文集代序中,作者指出,“網絡社會是一個沒有中心坐標,沒有空間區隔,沒有上下權力關系,但又充滿無限橫向聯系的超文本,這種網絡特性造就了相應的宗教”。⑦徐以驊、謝潔:“‘網絡時代的宗教’學術討論會會議綜述(代序)”,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網絡時代的宗教》(第三輯),第1頁。該研討會從三大方面展開討論。第一,網絡對宗教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宗教的個人化與自由化,宗教多元主義以及宗教社區的虛擬化。第二,與會學者從多學科角度來剖析網絡宗教現象。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網絡一方面增強了原有宗教組織的政治影響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普通信徒的平等主義和民主特性。從國際政治學的角度而言,網絡既有助于建構超宗派、跨國界的宗教性認同,也可以成為以“宗教自由”的名義攻擊他國人權狀況的技術工具。而網絡言論自由的無限擴大,也引發了倫理學方面的爭議。第三,研討會也涉及了網絡時代的宗教引發的一系列現實問題,包括網絡宗教管制、世界各地不平衡狀態的宗教網絡化以及對國際安全的挑戰。①徐以驊、謝潔:“‘網絡時代的宗教’學術討論會會議綜述(代序)”,第2-5頁。
從某種意義而言,宗教普世價值觀導致了宗教全球化的必然性。宗教的普世性體現在兩大方面:功能性的和地理性的。首先,作為一種世界觀,宗教可以定義并指導人類生活與社會有關的一切,包括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教育、福利、醫療、倫理、文化、傳媒、娛樂、家庭等方方面面。因此,在前現代(pre-modern)時期不存在宗教與非宗教領域的劃分。現代化所帶來的社會分化導致宗教功能日益邊緣化,退縮到只能處理主流系統殘留的或由主流系統造成而沒有解決的問題。自啟蒙主義以來,現代主義的神話一直宣稱,宗教將因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私人化(privatization)而走向衰亡。然而,繼現代性而來的全球化過程反而引發了宗教復興和宗教虔敬(religiosity),恰恰與現代主義的預言相反,宗教開始走向國內和國際政治的前沿。羅伯遜最初在和奇里克合撰的論文里提到神學與宗教的政治化以及政治的神學化,②Roland Robertson & JoAnn Chirico, Humanity, Globalization, and Worldwide Religious Resurgence, pp.224-239.繼而在《全球化、政治和宗教》一文中用更為精煉的語詞表述兩大相互促進的現象:政治的宗教化(religionization of politics)和宗教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religion)。前者指現代國家如何逐步卷入人類生活中原來只由宗教處理的深層問題,并在不同層次上成為崇敬和“深層”認同的目標。后者則指宗教團體(尤以在全球范圍內興起的基要主義為典型)對政府問題關注的升溫,以及宗教群體和世俗意識形態打破“圣”“俗”之分在利益合作上的膨脹。③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James A. Beckford &Thomas Luckmann (eds.), Changing Face of Religion, London: Sage, 1989, pp.11-14.與其說這是一個新現象,不如說后現代時期(post-modern)的宗教正在恢復其前現代時期的整合性或普世性。與其說宗教開始變得“政治化”和“公共化”,不如說宗教傳統的“再政治化”和“再公共化”。
第二,宗教的普世性還體現在其在全球范圍內的跨國流動。幾乎所有傳統宗教都具備“世界主義”的教義基因,并各有一部前現代時期跨國、跨海或者跨洲傳播史。當前的全球化進程更使其外延性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僅體現在西方主導宗教之南下與東方主導宗教之北上的互相交叉,還體現在傳統東方宗教信徒的西方化與傳統西方宗教信徒的非西方化。亞非拉國家中基督徒人數的飛速增長和各類佛教分支在歐美影響日隆都是典型案例。不論是基督宗教“傳到地極”的使命、伊斯蘭教的“泛突厥主義”,還是佛教“走出亞洲,走向世界”,都呈現出一種宗教無疆界的態勢。很多新興宗教(如巴哈伊教)從一開始便強調其非民族性、非地域性,甚至在教義上也采取了一種“拿來主義”的開放態度。綜上所述,世界全球化和宗教普世化是一對具有天然親和力的佳偶,而全球化處境下的宗教普世化,無論是功能性的還是地理性的,都對各國的內政外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雖然信息革命與全球主義的緊密關系已成為學者共識,但目前國內結合 “世界全球化”與“宗教普世化”的相關研究仍未將信息技術的因素納入主要學術關懷。而這一蹣跚起步的課題若要漸入佳境,仍需比較成熟的理論框架提供更為明晰的路線圖,本文嘗試運用國際關系大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復合型相互依存、全球化以及信息革命三者之間關系的剖析,演繹信息時代的全球化進程對宗教的影響,以及全球化世界視角下宗教對國際關系和國家內部宗教事務的挑戰,希望對推進這一課題的系統研究有所助益。
全球化進程不僅關系到人類的每一個個體,也改變了包括國內、國際不同層面的社會群體的運作。國際關系領域首次系統地建構全球化理論,肇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并以國際政治經濟學為主要進路。諸多西方國際關系學者中,約瑟夫·奈對全球化的探討超越了政經當家的套路,既具有前瞻性,也更展示了學術拓展潛力。奈與基歐漢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存》一書于 1977年初版時,雖已提出復合型相互依存(complex interdependence)這一概念,但尚未與當時隱而未顯的全球化聯系在一起,而在該書2001年第三版時,則增加了包含兩章內容的第五部分“全球主義和信息時代”(Glob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約瑟夫·奈獨立撰寫的《理解國際沖突:理論與歷史》這一教材性著作中, 也將“全球化和相互依存”(Globalization and Interdependence)獨立列為一章內容,以顯示這一命題的重要性,其內容與《權力與相互依存》既有重疊的部分,也有新發展的例證。
基歐漢和奈將“相互依存”界定為“以國家之間或不同國家的行為體之間互惠性效應為特征的態勢”,①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3rd. ed., Pearson Education, 2001,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影印版,p.7。并進一步提出“復合型相互依存”必須符合三大條件:軍事力量屈居次位;進入國家間議事日程的各類問題之間不具等級性;不同社會之間存在多渠道聯系。②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21.在界定“全球化”之前,兩位學者先引出“全球主義”(globalism)的概念,并界定其為相互依存的形式之一,以多個大陸之間網絡型連接為特征。③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 229.如果說全球主義是一種既可增加也可減少的狀態,全球化便是一種逐步增強的發展過程。橫向而言,兩位學者將全球主義劃分為四大方面④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231-232.:1)經濟全球主義;2)軍事全球主義;3)環境全球主義;4)社會及文化全球主義。宗教顯然可以被歸入第四類。縱向而言,宗教傳播可謂伴隨著人類歷史全過程,也是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約瑟夫·奈認為,當前的全球化與 20世紀之前的全球化的不同之處體現在其“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s)與“體系效應”(system effects),換言之,網絡之間的聯系產生了巨大的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s),以至于一個地方出現的問題,會引起整個體系的連鎖反應。①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240-241; Joseph S.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5th ed.,Pearson Education, 2004,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影印版,p.194.
從政治學的角度,約瑟夫·奈很自然地將信息革命和權力聯系在了一起,并深入剖析了科技發展的政治性后果,尤其是對國際關系的影響。他剖析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時所原創或借用的一些概念,也非常適用于對全球化視野下宗教發展的認識。如果說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蒸汽機的發明引發了第一次工業革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電、合成品、內燃發動機的使用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那么,20世紀末以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在全球范圍內引發的社會變革,可以被稱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無獨有偶,從宗教學的角度,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現代印刷術帶來了“第一次宗教改革”,網絡與信息帶來了“第二次宗教改革”。②也有學者認為“靈恩運動”(Pentecostal movement)是“第二次宗教改革”。溝通成本的降低和機制速度③機制速度(institutional velocity)是相對于信息速度(message velocity)而言的一個概念,前者指一個系統或系統之內各單元之間變化的速度,后者指某一特定溝通過程的速度。的加快戲劇性地加快了宗教傳播的速度。歷史上的基督宗教自小亞細亞,經歐美傳到東方,耗時近兩千年;而當代新興宗教傳遍全球可能只需要 20年,任何地方性宗教都具有搖身躍為全球性宗教的技術性潛能。
技術、金融以及宗教信息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或“多元化”(pluralization)④技術、金融、信息“民主化”的概念是奈引用一位叫弗里德曼(Friedman)的學者之用語,但未注明出處。“多元化”則是奈原創的概念,參見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p.195。也促使更多的人進入各種形式的跨國參與,包括宗教組織,并導致了傳統政治行為體(尤其是主權國家的)的權力分散。隨著國際網絡日趨復雜,宗教性跨國行為體和經濟領域的跨國公司、軍事領域的跨國聯盟一樣,具有越來越不可預測的影響力。在“深度全球主義”(thick globalism)①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195.的語境下,“國際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框架顯然已不敷用,需要“世界政治”(global politics)的概念來替代,②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21.而世界宗教在世界政治中正占據著越來越不可忽視的地位。
在世界政治的理論框架下,約瑟夫·奈提出“網絡封建主義”(cyber-feudalism)的概念,來形容“公民具有多重認同和效忠對象的共同體與管轄權相重疊之現象”。③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21.正如封建主義的中世紀的歐洲人同時效忠于地方領主、公爵、國王和教宗一樣,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醫科留學生,可能同時對醫藥聯會、學生會、東道國、母國、國際穆斯林組織、地方清真寺團體等不同權威機構或政體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忠誠。能覆蓋更遠距離、提供更快速度、載送更直接接觸的網絡,使得宗教信徒可以越過神職人員、地方社團、政府機構等中介(intermediaries)與遠程及分散的個體與群體溝通聯系。
繼信息時代主權與控制的命題之后,約瑟夫·奈還提出“散居共同體政治”(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communities)的概念,來形容“利用互聯網施加軟權力”的現象。④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24.約瑟夫·奈引用了戴維·博里爾(David Bollier)的話:“互聯網……使得那些數量很多和享有共同的歷史,但在地理上相互隔絕的人們,可以組成大的虛擬共同體”。⑤David Bollier, “The rise of Netpolitik,” The Aspen Institute, 2003, http://www.aspen inst.org/AspenInstitute/files/CCLIBRARYFILES/FILENAME/0000000077/netpolitik.pdf, p p.21-24.而散居在世界各地卻擁有同樣信仰的眾多宗教信徒恰好是典型案例。世界上大部分宗教社團都具有普世聚合的傳統,天主教的圣統制、基督教新教的宗派制、猶太教的錫安主義便是典型的案例。當地理性和技術性的障礙被網絡攻破之后,這些宗教性散居共同體便很自然地在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凝聚力。
然而,網絡帶來的全球化并非單向的凝聚,約瑟夫·奈進一步借用詹姆斯·羅西瑙(James Rosenau)原創的語詞“散合”(Fragmegration),①“Fragmegration”一詞是fragmentation和integration兩詞截拼而成。奈引用時未注明出處。來形容較大認同體的整合過程(integration)與較小團體的分裂過程(fragmentation)同時出現的悖論現象。②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25.在當代宗教運動中,隨處可見相反作用矛盾式的并存與同步。例如,網上教會與遠程神學院的涌現,一方面形成了新的虛擬共同體,另一方面也破壞了原有地方教會的組織形態或忠誠度,導致了宗教團體的權力分散。獲取新潮神學思想的便捷度,既是對傳統建制教會(established church)的錦上添花,也是對新興膜拜團體或弱勢宗教團體的雪中送炭;既有助于教派合一,也會導致教派分裂。當然,網絡對宗教的影響力仍有待實證考量,由于退出和加入虛擬社團的社會成本都很低,“網上宗教團體”遠比實體宗教團體更為聚散無常。此外,建立在網際溝通的宗教生活也不能完全替代神職人員與信徒的人際溝通或個性對話,因而不宜不加界定地夸大網絡的功用。
基于網絡的被瓜分和信息的被操縱,約瑟夫·奈將全球化視野下的信息傳遞分為天女散花式的“廣播”(broadcasting)套路與量體裁衣式的“窄播”(narrowcasting)套路。③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236, 247;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 224.原則上,人人都能從網絡上瀏覽免費信息,但在實踐中所有網站的建設只針對特定的目標受眾。由眾多“各為其主、互不相擾”的“網絡專柜”構成的虛擬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現實世界中原有的認同與分化的延伸:基督徒通常只搜索基督教網站,佛教徒只搜索佛教網站,只有改宗傾向的宗教信徒才會嘗試“跨教上網”。從技術接觸面而言,網絡屬于廣播,但從社會功能性而言,網絡卻是窄播。為了吸引更多的受眾,各類宗教或同一宗教中的各類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商業營銷手段,使得網絡宗教“商品化”的趨勢日趨明顯,連上網本身也已形成了心理學所說的“網絡拜物教”之類的“準宗教”。
由“廣”至“窄”的大眾傳播反映了信息分類日趨細化甚至剩余的現象。信息曾一度是稀缺資源,冷戰結束后,政治開發與技術革命的結合使得大部分人所接觸到的信息量陡增,導致注意力的分散,使得注意力取代信息成為稀缺資源,這即是約瑟夫·奈所強調的全球化時代之“豐富的悖論”(paradox of plenty)。①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33;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 219, 223.因此,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有能力將“信息”從“噪音”中區分開的人擁有了某種權力。約瑟夫·奈進一步認為,信息時代的全球化進程使可信度(credibility)成為軟權力的重要來源;國與國之間除了軍事或經濟實力方面的競爭之外,還可以通過創建和破壞可信度進行明爭暗斗。②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234;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223.人權外交中對別國宗教自由的攻擊便屬于貶損對手國際形象的手段之一,而圍繞宗教自由的政治爭辯,可能最終取決于哪一方的故事更動人或哪一方的信息更可靠。國際體制內各種行為體也常常利用宗教的道德權威建立可信度,成為其合法性來源之一。
約瑟夫·奈由以上觀察得出結論,信息時代的全球化進程所帶來的分散化(decentralizing)和平均化(leveling)并不等同于國際關系均等,③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31.在以下四個方面,全球化并未縮小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差距,甚至還導致了強國越強,弱國越弱。首先,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市場壁壘(barriers of entry)以及網絡效應有利于本已物阜民豐的大國。④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3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 221.新興宗教雖然風起云涌,但要與傳統宗教競爭地盤和信徒而躍為世界性宗教仍有待時日。其次,信息作為一種公共產品,其傳播費用雖已大幅降低,但收集、過濾、綜合的過程所需之大量投資,仍令小國望而生畏。①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p.23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221-222.以“世界人權警察”自居的美國政府,投入巨額資源“監督”世界各國的宗教自由,并發布年度報告作為其人權外交的根據。中國自2000年起便被列為所謂“特別關注國”(Countries of Particular Concern)之一,但和大部分“被監督”的發展中國家一樣,仍然缺乏相應的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物力與人才資本進行反控。再次,制定信息系統標準和結構的首創者往往來自科技發達的大國,并因此擁有話語權。②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232;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222.科技領域如此,包括宗教在內的其他領域也是如此。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之類的 “認知共同體”(epistemic communities),③指由意向相近的專家組成的跨國網絡,參見Peter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Winter 1992, pp. 1-36。大多成立于西方大國,不僅確立了“人權”、“自由”、“民主”甚至“宗教”等概念的定義,也積累了相關的專業傳統,使受批判的非西方的國家很難推翻已經被奠定為“國際標準”的西方理念。最后,約瑟夫·奈認為美國所擁有的將“不同系統結合成一個系統”的能力將使其軍事力量仍保持世界第一,④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33; Robert O. Keohane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222.而這一觀點也完全適用于美國在宗教領域(尤其是基督教新教方面)的領導地位。其他國家即便擁有更多的信徒、更大的教會、更強烈的宗教熱情、更濃厚的宗教氣氛、更密切的政教關系,仍無法超越美國在宗派傳承、神學研究、政治參與、立法執法、教會管理、文宣營銷、差傳財力、人道救援各方面加起來的“宗教綜合實力”。
約瑟夫·奈還指出,化約式(reductionist)的“技術決定論”(technology determinism)往往忽視與人類和社會有關的非科技因素。他從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歷史經驗中觀察到,社會機制變革往往滯后于技術變革的速度,①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219.信息時代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導致了主權國家管理體系的相對落后,使其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控制本國信息的權力。作為人口最多、疆域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公共事務管理法規早已不足以應對全球化進程中的信息流通,既難以控制所謂“宗教迫害”的流言之傳出,也難以防止“外國宗教勢力”之滲入。然而在另一方面,信息塑造者(information shaper)“上傳”(upload)的任何信息,在具體信息接受者(information taker)的“下載”(download)過程中,都經過了該國文化差異和國內政治兩方面的過濾,而內政制度也可以引導其對全球化變革的回應方向。②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 225, 253-254.
如上所述,雖然國內宗教研究者的很多觀點和焦點與約瑟夫·奈的學術關懷遙相呼應,但大部分學者似乎都未借鑒其有關信息革命、國際關系和相互依存的理論建構。例如,《互聯網時代:宗教間對話的重要契機》③李仕權:“互聯網時代:宗教間對話的重要契機——從傳播學視角看互聯網時代的宗教傳播”,徐以驊主編:《宗教與美國社會——網絡時代的宗教》(第三輯)。一文的作者,從傳播學的角度,以“媒介·社會·文化”為背景進行考量,從而認為互聯網會給同一宗教內部和不同宗教之間帶來單面向的自由、平等、寬容和真誠。但若作者能夠借鑒國際政治學的思維進路,將“權力”概念引入“媒介·社會·文化”的組合后,便能更全面、深入、立體地剖析信息時代的宗教現象。基歐漢和奈針對“技術決定論”提醒讀者,信息并非在真空中傳播,而是在已被占有的政治性空間傳播。過去四個世紀中建立起來的主權國家世界體系,便是信息革命所處的宏觀政治性空間。信息流動需要跨越的不僅是技術障礙,還包括政治性結構下的邊界,包括早已存在的政治處境以及持續性的軍事張力與沖突。④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pp.217-218.
如表一所示,如果說現實主義認為國家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是主權國家,以武力為主要手段達到安全的目標,以約瑟夫·奈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在全球化與信息化的時代,重組國際關系的主要行為體應當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等跨國行為體,經濟、環保等國際機制也相應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手段,最終達到增進福利的目的。在反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宗教性或具宗教意識形態的行為體也會在國際關系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文化傳播或構建身份認同的手段達到和平演變的目的,取代或補充武力或財力在傳統國際格局中的作用。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宗教議程有時甚至超過軍事、經濟問題躍居首位。可以說,繼國際政治經濟學崛起之后,宗教問題對現實主義“高級政治”和“低級政治”的固定分類法形成再一次挑戰。

表一:宗 教
約瑟夫·奈指出,過去只有天主教教會或跨國公司之類的巨型官僚式組織才有能力發展覆蓋全球的網絡體系,現在,組建網絡團體的低門檻與低成本造就了大量跨國行為體,包括具有宗教背景的傳教組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NGO)。這些跨國行為體的出現,一方面導致國家、政府、主權的權力分散,甚至改變了主權國家的中心地位和功能;但另一方面,國家管理的復雜化又不能簡單等同于主權受到侵害,各國政府完全具備在適應信息時代全球化的過程中,逐漸調整其對主權管轄和控制含義的能力。①Joseph S.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221-222.
世界全球化的過程,也正是宗教普世化的過程,兩者既是冤家,又是佳偶,既相互抵觸,又相互契合。如果說經濟全球化、軍事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刺激了全球范圍內宗教功能性的普世化,信息技術全球化則促進了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而這兩種進程都可以在中國的宗教事務管理中找到縮影:體制外宗教團體從私域走向公共空間,宗教團體參與公益事業可以說都是宗教功能性普世化的體現,而不同宗教在非傳統地區的擴展(例如:穆斯林的南下、基督教的西進、藏傳佛教之東傳)則是宗教地理性的普世化。從學理上而言,“全球化”、“信息革命”和“宗教現象”本來就是可以由不同學術進路和方法論加以剖析的研究對象,不存在“信息學”或“宗教學”之類的門戶劃分。國際關系、信息管理和宗教研究在國內都是方興未艾的熱門學科,但是一般而言,國際關系學者固守“宗教無用論”,信息專家執拗于“技術決定論”,宗教研究者則缺乏政治學和信息科技方面的知識結構,因而中國學界尚不具備約瑟夫·奈所說的“將不同系統結合成一個系統”的學術整合能力。雖然約瑟夫·奈并非從事宗教研究的專家,但作為國際關系大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網絡封建主義”、“散居共同體政治”、“散”“合”同步性、從“廣播”到“窄播”,“豐富的悖論”等,都有助于我們在剖析信息時代國際關系以及國家內政中的宗教因素時,測試其理論的解釋力。
s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Universalisation of Religions – Managing Religions in an Information Era
YUAN Yang (18)
新西蘭籍留學生,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neo-liberalist Joseph Ny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universalization of religions in the information era from the angle of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use conceptual tools such as “cyber-feudalism”, “the politics of diaspora communities”, “fragmegration”, “from broadcasting to narrowcasting”, and“the paradox of plenty” to analyze cyberspace religious phenomena thatGlobal Review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imple technology determinism is incapable of explaining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religions, politics and technologies. Multipl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nd cross-section disciplinary training are needed for a more integrated scholarly inqui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