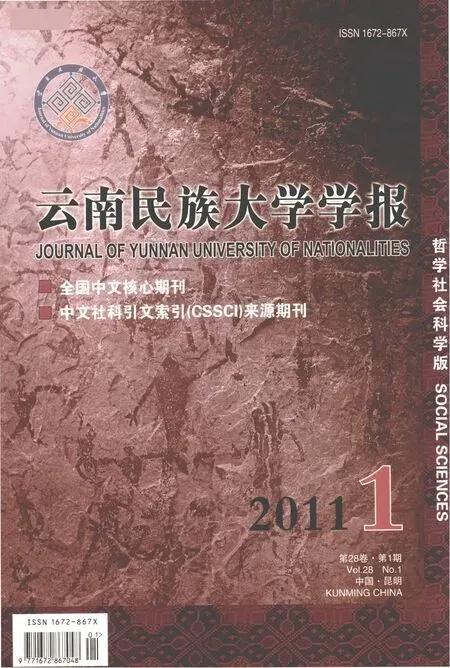論南詔入犯安南對唐代國家安全的影響
陳國保
(中山大學歷史系,廣東 廣州 510275)
唐代晚期,南詔趁唐朝國勢日衰和其南疆邊備空虛之際,出兵入侵安南。持續十余年的戰爭,對嶺南地區乃至整個唐朝,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國學術界對于南詔侵犯唐安南都護府的戰事,較早就有涉及,并一直備受越南古代史、南詔大理史、云南地方史等相關領域研究學者的關注。如黎正甫先生的《郡縣時代之安南》、呂士朋先生的《北屬時期的越南》、張秀民先生的《立功安南偉人傳》、尤中先生的《云南民族史》、陸韌教授的《云南對外交通史》等,都在相關章節或專題中論及唐朝與南詔在安南都護府的爭戰。方國瑜先生就南詔與唐朝、吐蕃之間或敵或友的歷史關系做過較為深入詳實的考察。[1]烏小花、李大龍的《有關安南都護府的幾個問題》一文,以編年的形式闡述了安南都護府的興衰歷程,討論了南詔對安南都護府的爭奪,略及南詔占領安南都護府后對唐朝在這一地區的統治所構成的威脅。但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南詔兵犯安南的戰事梳理或戰爭過程的描述,且視野往往拘泥于南疆一隅,而談到南詔所發動的這場戰爭,則多著墨于南詔的擴張性,忽視了從晚唐國家所面臨的內外形勢以及唐帝國邊疆防務策略的角度來進行審視和檢討,尤其是對戰爭影響到的唐代國家全局問題的認識,則更顯不足。西方學者雖在這方面有所突破,如英國學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即看到了南詔占領安南都護府后對整個唐代形勢的影響,頗具見地。然受所掌握的中國歷史文獻的局限,所以論證單薄;又因缺乏對中國疆域形成歷史的全面了解,故其觀點又難免有失偏頗。
一、內外交困的晚唐時勢與南詔伺機內犯
緣于邊疆與內地不可分割的整體聯結,邊疆安危往往與國家形勢緊密相關。以唐朝國勢的盛衰演變來說,表現在邊疆形勢上即為治與亂的交替更迭。安史之亂以后,唐朝由盛轉衰,中央集權大為削弱,逐漸形成藩鎮林立的局面,“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后可以戡定其禍亂,而其后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2]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升安南管內經略使為節度使;唐德宗貞元七年(791年),置柔遠軍于安南都護府;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又升安南都護為靜海軍節度使。唐王朝本欲以此南疆方鎮“鎮遏夷僚”,但據張國剛先生所劃分的唐代藩鎮的四種類型:河朔割據型、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東南財源型,安南都護府屬第三類[3](P81),“供饋不足與藩帥苛刻是邊疆型(即邊疆御邊型)藩鎮的共同特點,由此而引發的兵亂是藩鎮動亂的主要內容”[3](P98)。所以,唐代后期的安南都護府也同樣發生了政府駐軍的叛亂。駐兵之亂,本已損及唐王朝在南部邊疆的統治,而晚唐王朝所面臨的內憂外患的復雜局面,又進一步削弱了唐帝國在安南都護府的軍事部署力量。
就其內部軍事局面而言,盡管唐王朝為達到有效抑制藩鎮割據而殫精竭慮,但迫于無奈,玄宗以后的李唐統治者,基于緩和地方形勢的考慮,多對藩鎮勢力采取姑息之策,“方鎮相望于內地,大者連州十余,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愈俱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并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故兵之始重于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代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1]”尤其如唐穆宗,“上于馭軍之道,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故即位之初,傾府庫頒賞之,長行所獲,人至鉅萬,非時賜與,不可勝紀。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弛,戰則不克,國祚日危。[2]”
而其外部邊疆形勢,“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綱,戎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3]特別是西南邊疆的吐蕃,趁安史之亂唐朝國力大為消耗之際,從西域、云南、河隴三面全線出擊,進犯唐土,直接威脅到大唐帝國的生死存亡。曾經唐王朝為改變“外重內輕”的被動軍事形勢,加強中央集權,“國家自祿山構亂、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于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余年”。”[4]本是出于良好愿望,但卻正中吐蕃下懷,更給了其可乘之機。窮于備戰的唐王朝,為守住李唐江山的根本,“猛將精兵,皆聚于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5]
在這種內憂外患交織困擾的復雜形勢下,疲于應付的唐王朝根本無力顧及南部邊疆的邊防問題,從而導致了南疆邊備的空虛。其實,并非南疆如此,自唐中期以后,整個國家的邊防問題都很嚴重,如元和八年(813年)宰相李絳就曾言于憲宗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幸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6]。若以南疆而言,“交州,漢之故封,其外瀕海諸蠻,無廣土堅城可以居守,故中國兵未嘗至。及唐稍弱,西原、黃洞繼為邊害,垂百余年。”[7]雖稍有言過其實,但也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后期南部邊疆防務的松弛,而這正好給了地鄰安南的南詔可乘之機。所以說,南詔對安南的騷擾,除因其自身力量壯大而致擴張欲望膨脹的因素外,亦與唐朝國力衰落及其南疆邊防的空虛等外部客觀環境不無關系。
雄踞于唐帝國西南的南詔是唐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地方民族政權,“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云南是也”[4]。周旋于唐與吐蕃之間的南詔,利用唐與吐蕃長期爭戰而致彼此損耗的時機,逐漸發展壯大,如陳寅恪先生言:南詔“強盛之原因則緣吐蕃及中國既衰,其鄰接諸國俱無力足與為敵之故,此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也。”[5](P347)方國瑜先生亦曰:“(南詔)雖然受唐朝寵渥,但是'開門節度,閉門天子',非服服帖帖地聽命于唐朝,利用唐朝與吐蕃的矛盾,日益強大起來。”[1]隨著南詔勢力的迅速強大,其擴張野心自然也更加膨脹。因此在天寶戰爭大敗唐朝之后,南詔便在頻繁侵擾唐境劍南西川的同時,亦將目光盯上了唐帝國的南部邊疆。
元和十一年(816年)六月,南詔出兵襲擊安南都護府,開始了對唐朝南部邊疆的侵擾。不過,在憲宗、穆宗二帝當政期間,南詔雖趁安南防備相對空虛及嶺南局勢動蕩之際,零星騷擾唐朝南境,但尚不敢公然與唐為敵,姑且維持著對唐帝國貌合神離的臣屬關系,“是時,黃洞蠻屢叛,邕管間連歲被兵,嵯巔乘釁,遂東寇安南,然朝貢猶每歲不絕”[6](P136)。其實,當時南詔覬覦唐土的野心,重點仍在西川一線。太和三年(829年)冬,南詔命王嵯顛大舉進兵西川,輕易地攻陷了巂、戎等州,次年一月攻破成都,在大肆擄掠之后撤離。南詔的突襲,敲響了唐朝西南邊防的警鐘。太和四年(830年)十月,唐以李德裕為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云南安撫使。李德裕到任后,致力于西川邊防的鞏固和提高,使唐帝國西南邊疆的防御能力不斷加強,并在形勢上與安南都護府架構成唐帝國西南、南部邊疆的兩大軍事防御屏障,由此對南詔的北上或南下的擴張之路形成阻擋之勢。更令南詔坐臥不安的是它擔心唐朝借此以安南和西川作為反擊的基地,對其形成鉗制之勢。為改變這一不利的被動局面,南詔再度出兵入犯安南,“南詔知蜀強,故襲安南”。[7]雖然當時安南的邊備相對薄弱,但唐朝尚未因“蒼洱之盟”后二者結成的盟友關系而完全松懈南疆一線對南詔的防范,尤其是憑借維系在唐帝國邊疆秩序之中的安南都護府轄下散布于南疆西北沿邊之羈縻州形成對南詔的天然屏障。《舊唐書》卷17《文宗紀》即有記載云:“太和七年三月己酉,安南奏:蠻寇當管金龍州,當管生僚國、赤珠落國同出兵擊蠻,敗之。”為突破這一防線,南詔試圖招誘安南羈縻州部落首領的歸向,策劃安南內應。開成三年(838年),安南都護馬植奏稱:“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自固,或為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南詔的企圖引起了馬植的警覺,也使他意識到了這一邊疆隱患,故“自到鎮以來,曉以逆順。今諸首領愿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為州,以首領為刺史。”[8]以此提升南部邊疆的防衛能力。在此時期,南詔雖間或寇犯安南,但因唐朝尚有一定的防備,其入侵陰謀屢屢未能得逞。
然自大中七年(853年)以后,形勢發生了根本轉變。當時以行賄權僚得以出任安南都護的李琢,為政貪暴,苛刻逾求,導致安南土著居民的反叛。史云:“大中時,李琢為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李琢“貪于貨賄,虐賦夷僚”而導致的安南內亂已使南疆呈現離心之象,而其又錯誤的裁撤南疆邊防,更加重了安南都護府的危機。《云南志》卷4《名類》載:“南蠻去安南峰州林西原(即林西州)界二十二日程。自大中八年,安南都護府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遭侵軼。罪在督護失招討之職,乖經略之任。”又曰:“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為境上戍卒,每年亦納賦稅。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琢),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來真登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柘(拓)東節度使書信,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自此之后,七綰洞悉為蠻收管。”[9](33~34,45)李琢不顧當時唐與南詔對立的邊境實際,聽信峰州刺史一面之詞,盲目撤銷唐在安南都護府西北邊境一線駐扎的主要用來防備南詔的政府駐軍,僅僅依靠當地部族兵力防守,致其首領李由獨孤立無援而生棄唐之心,加之南詔百般誘引,并與之結成姻親之家,李由獨因此背唐而投奔南詔,從安南都護府的前衛將帥變成南詔侵犯安南的先鋒。唐朝的南部邊疆藩籬盡撤,堂奧洞開,南詔勢力不斷推進。所以黎正甫先生說:“南詔攻陷安南,李琢先撤去防守,實啟其門”。[10](P107)自此以后,南詔對唐帝國在南部邊疆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雙方兵爭不斷,直至咸通七年(866年)十月,高駢擊敗南詔,收復安南,戰火綿延十余年。唐與南詔在安南的爭奪,雖最終以唐帝國收復安南而結束,但唐王朝卻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連年戰爭,不僅對其南疆社會造成極大破壞,同時也使已是強弩之末的唐帝國遭受沉重的創傷并由此導致唐代整個社會的嚴重危機。
二、安南殘破,南疆離心
南詔趁唐與吐蕃衰落之際,不顧吐蕃的威脅,與唐為敵,頻繁發動對唐朝安南、西川的侵犯,雖屢有得逞,但也因此困乏,最終導致滅亡。而唐朝的南部、西南邊疆亦因南詔的寇擾變得殘破不堪,“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厲,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心!”楊收言:“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南詔在安南的肆擾,導致當地居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民生極度凋敝,以致無力承擔國家的賦稅義務,當地社會矛盾亦隨之激化。為穩定唐帝國在南疆的統治,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不得不頒布《救恤安南流人制》,“安南寇陷之初,流人多寄溪洞。其安南將吏官健走至海門者人數不少,宜令宋戎、李良瑍察訪人數,量事救恤。安南管內被蠻賊驅劫處,本戶兩稅、丁錢等量放二年,候收復后別有指揮。其安南溪洞首領,素推誠節,雖蠻寇竊據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聞溪洞之間,悉藉嶺北茶藥,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廉州珠池,與人共利。近聞本道禁斷,遂絕通商,宜令本州任百姓采取,不得止約。”[11]《新唐書》卷222中《南蠻傳中·南詔下》也云:“安南之陷,將吏遺人多客伏溪洞,詔所在招還救恤之,免安南賦入二年。”
長期的戰亂也導致了安南交州港的衰落。交州自漢代以來便擔當了古代中國海外貿易不可或缺的中轉角色,成為中原王朝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舊唐書》卷41《地理志四》說:“交州(安南)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幡,道里不可詳知。自漢武以來,朝貢皆由交趾道。”所謂朝貢,實則是經濟貿易的一種政治表現形式。[12]隋唐時期的交州、廣州已逐漸發展成為當時兩個繁榮的海外貿易基地。尤其是“唐代中葉以后,海外貿易逐漸興起,與唐朝發生貿易的國家逐漸增多,給交州港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交州港的對外貿易達到了鼎盛。當時同唐朝聯系最為頻繁的海外國家和地區是阿拉伯、波斯灣各國,南亞天竺、獅子國,東南亞沿海國家蒲甘、昆侖、扶南、真臘、占城等等。到唐代后期這些國家幾乎都通過海道,起帆波斯灣,取道馬六甲,或直接從東南亞沿海北上交州、廣州,同中國進行貿易。”[13](P118)不過,交州的繁榮顯然離不開當地和平的社會環境。唐王朝通過安南都護府,對南疆地區實施著有效的行政管理和強有力的軍事控制,既維護了安南都護府與今兩廣及內地傳統水陸交通線的暢通無阻,也為唐帝國南海海上交通線路的穩定與拓展提供了保障。于是交州憑借它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和地處水陸交通要津之地的區位優勢,不但在唐帝國的海洋貿易中占據特有的商業發展優勢,為唐王朝南海交通和貿易的門戶,而且對于唐帝國的整體經濟利益存在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這或許也是后來唐朝與南詔在安南展開長期爭奪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即如西方學者所認為:南詔進攻安南,給唐朝提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四川,朝廷關心的是可能失去一個與朝廷有密切政治聯系的富饒地區。在安南,關心的性質則全然不同,它更多是為了威信,特別是貿易。因為南部港口是通過繁榮的海岸貿易而和長江下游港口聯系起來的國際海運貿易的中心。中國對經過中亞通往西方的陸上交通的控制仍很不穩定,朝廷對喪失南方的任何可能性都不得不予以認真考慮”。而南詔對安南的頻繁騷擾,則使得交州港在唐代中國海外貿易中的地位急劇下降。自“李琢失政,交趾陷沒十年。蠻軍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13](P123),戰亂“嚴重地損害了交州港的正常秩序和外貿環境,自咸通四年,南詔攻陷安南后,原來在安南從事貿易的客商和外地人,多轉移到廣西沿海,或寓寄于當地少數民族之中。戰爭還阻斷了安南經云南與內地的陸路交通,交州港失去了南詔和西南內地市場。從此交州的海外貿易一蹶不振。”
唐朝雖擊退了南詔,收復了安南,但因戰爭的消耗,中央王朝對南疆的控制力度卻漸趨微弱。我們知道,唐為維護和加強中央王朝對南部邊疆民族地區的有效控制,在安南都護府境,既置十二正州管理交通沿線地區,又于沿邊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廣泛設置數十羈縻州,以此實現對歸附少數民族的統轄。唐代所推行的這種酌依其俗、靈活制宜的羈縻政策,并不強行國家權威在嶺南邊隅的一蹴而就,而是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旨在通過羈縻州制漸進式的推進國家秩序在南部邊疆的滲透,無疑有利于州縣制度在南部邊疆的貫徹實行,有助于實現中央王朝對它的有效牽制,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在南部邊疆的鞏固和發展。但它的消極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由于保留了當地部族土長“自治”的特權,也就等于削弱了中央王朝委派在南疆最高軍政長官安南都護等“流官”在當地的實際控制權,由此埋下了地方勢力與國家權威之間矛盾沖突的隱患。
于是,在唐代國家盛衰演變與南疆土流勢力消長變化的連環效應下,中唐以后安南都護府境內的土族大長的勢力獲得了迅速發展。以耿慧玲教授等人所著《唐貞元安南〈青梅社鐘〉銘文考釋》及毛漢光先生的《中晚唐南疆安南羈縻關系之研究》兩文的分析,根據在越南河西省(今已并入河內市)青威縣青梅社所發現的立于唐貞元十四年(798年)的《青梅社鐘》銘文,記錄了當地青梅社民242人,其中最大的姓是杜氏,有65人;其次郭氏,42人;黃氏,22人;高氏,21人;阮氏,14人;王氏11人;陳氏,9人;李氏,7人;其余鄭、呂、楊、蘇、江、魏、張、馮、黎、僧、周、吳等姓氏或不過5人,或僅有1人。若將官職與姓氏作比較,則擁有各類官銜者總計有65人,結果大致與姓氏分布相似,以杜郭二氏最強,超過半數39人。若再以所任官職之層級觀察,刺史及刺史以上職務,杜氏3人,他姓皆無;其下較重要之職位為左廂兵馬使,則為姓氏排序甚低的楊氏。至于各級中下級文武官職,大致與姓氏分布相當,以杜、郭、黃三姓居多。[14](P282)當時安南地方勢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時入晚唐,因隨國勢的衰微和南詔的入犯,南部邊疆的地方勢力應機而興,更為壯大,“五管為南詔蠻所擾,天下征兵,時有龐勛之亂,不暇邊事。……,北兵寡弱,夷僚棼然”。①《舊唐書》卷158《鄭余慶傳》。按:鄭從讜,余慶之孫,咸通六年出任嶺南節度使。安南都護府的離心力亦由之更加增強。盡管咸通七年(866年)收復安南后,出于主觀愿望的唐王朝為恢復南疆地方秩序,加強國家對安南的控制,提高南部邊疆的軍事防御能力,升安南都護為靜海軍節度使,但“靜海軍”,不過空有名號而已。如乾符四年(877年),當南詔新主隆舜提出與唐和親時,朝臣盧攜為說服唐僖宗答應南詔的和親之請,即以對南疆邊防的憂慮為說詞,“今朝廷財匱兵少,安南客戍單寡,鈔冬寇禍可虞,誠命使臨報,縱未稱臣,且伐其謀,外以縻服蠻夷,內得蜀休息也。”可謂實情。所以安南都護府也并未因為名義上的軍事升格,而避免動亂的發生,僖宗廣明元年(880),安南軍亂再起。
自唐懿宗時期起,唐王朝內外矛盾重重,危機四伏。尤其是唐僖宗乾符元年中原內地爆發王仙芝、黃巢起義以后,既要固本又須安邊的唐帝國應付嚴重的內憂外患已是捉襟見肘,因此無力亦無能顧及南部邊疆,甚至授命的安南都護(靜海軍節度使),亦幾乎是徒有虛名,未能到任。如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任命獨孤損為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其實就根本沒有到達安南。這樣,遠離帝國中心的安南都護府便因淡出國家的視野,而致實際控制權逐漸旁落于地方豪族大長手中,成為后來安南脫離中國地理版圖的直接原因,“隨著中國中央對于地方控制力的逐漸轉弱,唐末五代,越南原本在中國政治力摶合下的政治集團,也逐漸開始淡化在中國的中央體制中,被中國行政制度強化了的地方政治集團,失去中央的強力控制后,開始嘗試爭取各個地方勢力的獨立權力,客觀的情勢使得越南地區得以游離出中國的政治統治圈”。如《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前編》卷5“屬唐昭宣帝天祐三年”條載:“春正月,唐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氏,洪州人,世為巨族,承裕寬和愛人,為眾所推,因亂以土豪自稱節度使,請命于唐,唐因授之。”唐中央王朝被迫承認安南土長在南部邊疆的最高軍政地位,致使自秦漢以來即為中國王朝直接管理下的地方行政轄區,初現由郡縣統治走向藩屬冊封的端倪。故曲承裕死后,其子曲顥“據州稱節度使。顥憑舊業,據羅城稱使,分定各處路、府、州、社,置令、長、正、佐,均田租,蠲力役,造戶籍,編記姓名、鄉貫、甲長之帥,政尚寬簡,民獲蘇息,辰梁以廣州節度使劉隱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據番禺,顥據州稱使,志在相圖。”[15]如方國瑜先生言:唐與南詔的十年爭擾,“雖(南詔)主力被高駢擊破,但(安南)地方勢力當更發展,唐朝衰替已無能挽回。唐亡,南漢并有交州,但州人楊廷藝、矯公羨、吳權、楊主將、吳昌文,遁相爭自立,以致丁部領稱南越王,宋時,南越只為朝貢之國了。”[1]西方學者亦云:“公元9世紀,因越南地方勢力的復興,不斷沖擊著唐朝的最高統治,并與唐朝展開了長期的沖突,盡管沖突最終得到了有利于唐朝方面的解決,但此時的唐王朝已日趨衰弱,越南地方勢力趁機將安南引向獨立發展的時代。”[16](PP209)
三、邕州被擾,殃及五嶺
安南都護府與同為嶺南五管之一的邕州都督府是互為維衛、共同筑建在唐帝國南部邊疆的重要軍事防線,“唐設安南都護,以邕州為支柱,……。邕州與安南互為犄角,唐兵守安南,當加強邕州,南詔占安南,也要進取邕州。從安南事件發生,邕州即受威脅,安南事定,邕州始告安全。”[1]所以說,安南與邕州同樣是矗立在唐代南部邊疆唇齒相依,存亡相連的邊疆防御系統。安南固然以邕州為支柱,震懾南疆,邕州乃至嶺南也以安南為藩籬,安南為邕州以及整個嶺南的穩定提供軍事地利上的保證。因此當南詔占領安南都護府后,揮師東北、兵犯邕州時,波及五嶺,形勢更為嚴峻。
早在咸通元年(860年),南詔首度攻陷安南都護府時,即已舉兵進犯邕州。 《資治通鑒》卷250《唐紀六十六》“懿宗咸通二年”條:“七月,南蠻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才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盜。”邊鎮戍卒向招募的轉變和唐廷對邊情的無知,被藩帥的私欲所利用,致使嶺南邊防空虛,南詔趁此長驅直入,攻陷邕州達二十余日方才撤出,“城邑居人,什不存一”,邕州幾乎被焚劫一空。
邕州雖失而復得,但其因此而遭受的巨大創傷和造成的危急形勢,也迫使唐廷意識到加強邕管防守,對于堵截南詔擴張之勢、控扼五嶺、固衛疆垂以及屏藩內地的重要性。基于此,唐王朝吸取邕州疏于防守輕易喪之敵手的教訓,決定實行嶺南道東西分治的治邊策略。唐懿宗咸通三年十月《分嶺南為東西道敕》云:“敕:嶺南分為五管,誠已多年,居常之時,同資御捍,有事之際,要別改張。邕州西接南蠻,深據黃洞,投兩江之獷俗,居數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輕,軍威不振。境連內地,不并海南,宜分嶺南為東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廣州為嶺南東道,邕州為嶺南西道,別擇良吏,付以節旄。”[17]唐王朝試圖通過此舉加強邕州的邊防軍政要位,并對赴任嶺南西道的封疆大吏寄以厚望,委以重托。如以鄭愚為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而作《授鄭愚嶺南節度使制》曰:“朕以郎寧地分零、桂,共控夷蠻,將以重城鎮于兩江,壯服嶺于西道,俾崇旄節,用固疆陲。……(爾)既懋師節,仍長憲臺,勉承顧遇之榮,佇觀緝柔之績。”又《授蔡京嶺南西道節度使制》云:“濱海而南,邕為重地,城臨甌駱,俗本剽輕。居常則委經略之權,有事則付節制之任。是用改其舊號,建以新軍,一時之革,千古無對。爾其頒惠養以馭眾,亦寬嚴以訓兵,濟活鄉閭,保安谿洞。”然本是一劑治世良方的改弦更張,邕、廣分治不僅沒有給彌留之際的李唐王朝帶來一絲慰藉,相反卻成了地方官員張揚權勢、抑壓同僚的尚方寶劍,防守之誡不過一紙空文。所以咸通五年,南詔再度輕易兵臨邕州之境,只因其“知邊人困甚,剽略無有,不(復)入寇”,由此更可見邕州所受蹂躪之深。但南詔此勢已非僅僅危及邕州,而是直接威脅內地,嶺南諸州,“一有不靖,湖南且亂”,南疆一隅已不再只是邊疆失與守的問題,而成為關涉唐王朝國家存亡的全局性的戰略問題,如顧祖禹言:南寧府“內撫溪峒,外控蠻荒,南服有事,此為噤喉重地。唐置邕管于此,為廣南唇齒之勢。……蓋地居沖要,勢所必爭也。”[18]所以一時唐廷上下慌亂,調兵遣將,御敵深入,力圖收復嶺南。如此,南疆邊吏的授任是否得人便成為能否讓唐朝重新獲得對南疆主動權的制約瓶頸。所以因夏侯孜的力薦,驍衛將軍高駢被任命為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率兵抗擊南詔的侵犯。臨危受命的高駢不負重托,取得勝利。
唐朝為反擊南詔的入犯,連年用兵嶺南,戰爭不僅直接摧毀了嶺南居民的家園,而且國家軍隊的給養也成為了當地百姓的沉重負擔。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云:“關要之外,聲教至遙,每念疲人,尤多橫役。訪問五嶺諸郡,修補廨舍城池,材石人工,并配百姓,至于糧用,皆自赍持。既不折稅錢,又全無優恤,永言凋瘵,實可憫傷。……(交戰)累載已來,亦頗校科征納,主持軍將十余輩,攤保累數百家,或科決不輕,或資財蕩盡。典男鬻女,力竭計窮,盡虛掛簿書,徒為羈縶。”當然,南詔陷沒交趾,北寇邕容的軍事擴張,非但導致了嶺南地區的民不聊生,同時也給其相鄰地帶乃至唐代全國的社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破壞。如高駢《回云南牒》言:“云南,頃者求合六詔,并為一藩,與開道途,得接邛蜀。……復窮兵再犯朗寧,重陷交阯,兩俘邛蜀,一劫黔巫。城池皆為灰燼,士庶盡為幽冤。”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嶺南用兵德音》曰:“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系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準此例與置本錢。”又《咸通七年大赦》云:“應三道(安南、邕州、西川)兵士,經過累路州縣,供應頓遞,征配里閭,水程船夫,陸路車役,勞弊斯甚,疲瘵可哀。其岳州、湖南、桂管、邕管、容管內,沿路州縣,今年二月二日德音,已蠲放今年夏秋兩稅各一半,尚恐鄉村未悉,更要加恩。宜于今年夏稅正錢,每貫量放三百文,沿路州縣,亦甚凋傷,先未霑恩,今須優假,宜于來年夏稅正錢,量放一半。”可見,安南戰事,地方經濟遭受巨創的地區首當其沖的是嶺南內部及相鄰的今湖南、湖北、江西、貴州等地,同時損及全國,“累歲以來,嶺南用兵,多支戶部錢物”,“自從近歲,頗欠豐年,百姓凋殘,四方空竭。邕、交防戍,邛蜀征行,租賦罄于東南,衣糧耗于西北。”嶺南用兵對于唐代全國經濟的沉重打擊由此不言而喻矣。
四、神州震蕩,唐室殘喘
唐與南詔爭奪安南的戰爭,其破壞并不局限南疆一隅,這在上文的論述已有體現。范祖禹《唐鑒》卷21《論高駢破南詔》云:“唐室之衰,宦官蠹其內,南詔援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唐摭言》載:“時屬南蠻騷動,諸道征兵,自是聯翩,寇亂中土。”[19](P21)南詔之犯,不僅危及唐帝國南部邊疆的安全,也波及全國,造成中原內地的局勢動蕩,加速了唐朝的滅亡。盡管南詔攻破安南、兵犯邕州的囂張氣焰,因高駢的大兵壓境而稍有抑制,但迫于嚴峻形勢,為防止南詔再度突破嶺南邕州防線并北上寇擾內地,咸通三年唐調徐、泗戍兵鎮守桂林,防備南詔。唐懿宗咸通三年(862)五月《嶺南用兵德音》云:“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強,比以制馭乖方,頻致騷擾,近者再置使額,卻領四州,勞逸既均,人心甚泰。但聞比因罷節之日,或有避罪奔逃,雖朝廷頻下詔書,并令一切不問,猶恐尚懷疑懼,未悉招攜。結聚山林,終成詿誤。況邊方未靜,深藉人才,宜令徐泗團練使,選揀如募官健三千人,赴邕管防城,待嶺外事寧之后,即與替代歸還”。此即為《舊唐書》卷177《崔慎由傳》所說的:咸通“六(當作三)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桂州,即桂林,為嶺南隘口,亦是嶺南西道通向內地的要沖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桂林府,府奠五嶺之表,聯兩越之交,屏蔽荊、衡,鎮懾交、海,枕山帶江,控制數千里,誠西南之會府,用兵遣將之樞機也。……隋唐之初,皆置軍府于此,蓋天下新定,嶺南險遠,倘有不虞,燎原是懼,故保固嶺口,使奸雄無所覬覦也。”這實際也是當時唐分兵戍守桂林的原因所在。
依唐代的軍事制度,戍卒鎮守邊疆三年一換,那么咸通七年唐收復安南后,鎮邊四載的徐、泗戍兵當被輪替,但因戰爭剛剛結束,擔心南詔利用唐嶺南換兵之機,趁虛再犯,而此時的唐朝實已無兵可調,所以要求嶺南戍兵尚且嚴守封疆,待形勢完全好轉以后,再作打算。同時為穩定軍心,又許以種種承諾,“安南、邕管、西川三道軍士,皆逾山越海,擐甲荷戈,志切勤王,誠深報國,固內侵之封域,收已失之城池,盡欲捐軀,咸思賈勇,險阻數歷,終始一心,言念忠勤,誠用嘉嘆。今南蠻已加招撫,冀就弭寧。日下但嚴守封疆,且備要害。雖未用更圖攻討,亦未可便絕訓齊。其將士等義感風云,志諧金石,屯營既久,立效已多,大功將成,懇節無奪。俟其歸款,別有指揮。……其赴府三道行營兵,有親老及妻子在家者,各委本道切加存恤,勿使凍餒恓惶,俾無回顧之憂,以勵當鋒之志。其諸將士勇敢用命,當鋒歿身,義節可嘉,孤弱是念,并委本道節度使,據所申報,各須安存。如血屬單弱,不能自存者,即厚加給恤。遺骸在野,深可憫嗟,今春已降德音,盡令優給收葬,尚慮暴露,未契幽陰,今更舉明,用慰泉壤。宜令所在長吏,訪尋收殮,如法瘞藏,仍以酒醪殷勤奠酹。”然當時已是滿目瘡痍的唐帝國,根本無法兌現這些承諾,所謂“恩宥”,不過徒托空言,這從后來的龐勛事件即可充分說明。咸通九年(868年),已經鎮守南疆六年的徐、泗戍卒仍不得返籍,故請求替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為都將。……時亡命者歸賊如市。……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八日,龐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鎮守嶺南之徐、泗兵卒的軍餉及返鄉補給國家尚且難以籌措,又何能安撫存恤戍卒在家親老妻兒?“勿使凍餒恓惶,俾無回顧之憂”無疑只是冠冕之言,而“戍卒家人飛書桂林”,其內容當為苦訴家鄉窘境之情。正是在這樣一種回家無望、軍餉無期、親人顧盼的多重因素的刺激下,進退無路的徐、泗戍卒舉兵起義,并推龐勛為將,倒戈反唐,震動江淮。起義雖被鎮壓,但它卻發黃巢起義之先聲,成為導致唐朝滅亡的直接誘因之一。甚至宋代的修史者總結唐亡的教訓云:“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畔,南詔內侮,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兇渠殲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無備。……唐亡于黃巢,而禍基于桂林。”桂林之禍的根源即在于安南被擾,可見南詔侵奪安南對于唐朝全局的深遠影響。故西方學者認為:“868年以后這個偏遠的南方安靜下來了,但是這個和平是花了很高的代價才獲得的。……唐王朝這時正被許多內部叛亂所困擾,而且不久又經歷了由一個名為龐勛的軍官所領導的兵變的柔躪——他嚴重的擾亂了長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區。另外,王仙芝-黃巢的大叛亂僅在5年以后也開始了。”從此,李唐王朝的局勢更趨窮蹙,日薄西山的晚唐帝國在風雨飄搖中做茍延殘喘的最后掙扎。
綜上所述,我們看到了安南都護府對于維護唐代國家安全所具有的突出地位和作用。作為唐朝設置在南部邊疆的重要管理機構,安南都護府的主要職責是“撫尉諸蕃,輯寧外寇,覘候奸譎,征討攜貳。”因此,它不僅是唐王朝實現南部邊疆穩定、鞏固南部邊疆統治的最高軍政機關,也是防御外敵、鎮重邊陲的重要軍事屏障。依持設置在南部邊疆的安南都護府,唐王朝有效穩定了南部邊疆的社會秩序,鞏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邊疆的統治;憑借安南都護府及其互為犄角的邕州都督府與矗立在帝國西南邊疆的南寧州都督府共同構建的唐帝國南部、西南邊疆相互維衛的邊疆防御體系,則又為唐帝國統治在南部邊疆的不斷深入提供了保障。如果說唐代前期以南寧州都督府作為經略安南的據點,亦以安南作為經營西南的基地的話,那么當南詔坐大,與唐為敵,安南都護府則為唐朝用以對付南詔的前沿陣地。故云安南都護府既是唐王朝用以經略西南邊疆的軍事基地,也是防范南詔內犯的邊塞鐵籬。然而正因為唐朝南疆治策乖違,邊吏貪暴,土酋倒戈,致使唐帝國南門洞開,南詔趁機而入,戰火兵燹綿延十余載,安南遭劫,嶺南涂炭,大唐國勢益受虛耗。南詔的興起使安南都護府失去其西北的屏藩,唐朝的南部、西南邊疆也因此無法保持彼此制約的平衡。而南詔對安南的頻頻進犯,則直接擊潰了自唐初以來帝國精心構建的邊疆防御體系。所以就在南疆戰火的烽煙尚未完全淡去的時候,駐扎在桂林防備南詔的徐、泗戍兵因久不得更代,而發生龐勛起義,騷動江淮,內憂外患頻仍相繼,帝國震蕩,國勢日危。安南失陷,成為加速唐朝走向盡頭的催化劑。
[1]方國瑜.南詔與唐朝、吐蕃之和戰,方國瑜文集(第二輯)[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宋]王讜撰,周勛初校證.唐語林校證卷8《補遺》[M].北京:中華書局,1987.
[3]張國剛.唐代藩鎮研究[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4][宋]王應麟.玉海卷25《地理·議邊》[M].廣陵書社,2003.
[5]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 [M].上海:三聯書店,2001.
[6][清]馮甦撰,李孝友,徐文德釋.滇考校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7][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329《四裔考六·南詔》[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8][宋]王溥.唐會要卷73《安南都護府》 [M].北京:中華書局,1955.
[9]云南史料叢刊卷2[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
[10]黎正甫.郡縣時代之安南[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5.
[11]希泌.唐大詔令集補編卷20《仁政·賑恤》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周偉洲.唐朝與南海諸國通貢關系研究[J].中國史研究,2002,(3).
[13]陸韌.云南對外交通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
[14][臺]耿慧玲.七至十四世紀越南國家意識的形成、越南史論——金石資料之歷史文化比較研究[M].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15][越]潘清簡,等.欽定越史通鑒綱目·前編 [J].“唐天祐四年”條,越南建福元年1884,5.
[16]Keith Weller Taylor.The Birth of Vietnam[J].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17][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卷99《政事·建易州縣》[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8][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10《廣西五》[M].北京:中華書局,2005.
[19][清]王定保.唐摭言卷3《散序》[A].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740冊[C].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