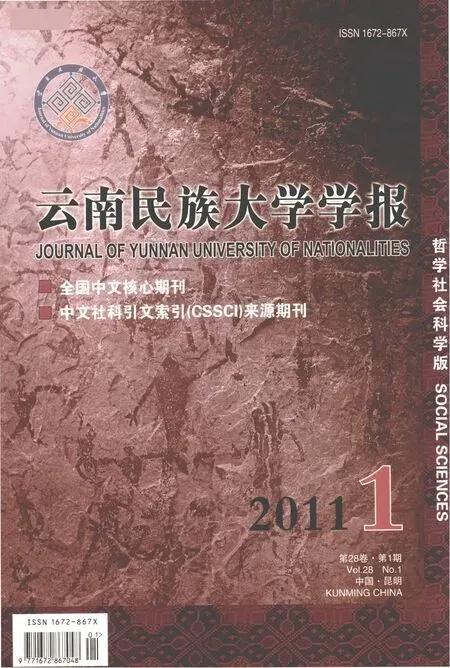高原意識與女性意識的堅守者— —論白族女作家景宜及其創作
黃 玲
(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31)
高原意識與女性意識的堅守者— —論白族女作家景宜及其創作
黃 玲
(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31)
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寫作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延伸到現在,從中短篇小說到報告文學,再到影視作品的寫作,她一直堅持對精神理想的追求。并超越了單一的民族視野,關注邊疆多民族的生存境遇,在發掘民族文化最深層的精華中,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做出貢獻上進行了有益探索,其作品中鮮明的高原意識和女性特色也為她的寫作增添了獨特的魅力。
白族作家;景宜;寫作追求;精神理想
白族女作家景宜的寫作從20世紀80年代一直延伸到現在,從中短篇小說到報告文學,再到影視作品的寫作,她一直堅持對精神理想的追求,并超越了單一的民族視野,關注邊疆多民族的生存境遇,在發掘民族文化最深層的精華中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做出貢獻上進行了有益探索,其作品中鮮明的高原意識和女性特色也為她的寫作增添了獨特的魅力。
一、小說寫作中的精神理想追求
上個世紀80年代,白族女作家景宜開始小說寫作。她的中篇小說《誰有美麗的紅指甲》曾獲全國“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優秀中篇小說一等獎”,在文壇引起很大反響。同一時期創作的中短篇小說還有《騎魚的女人》、 《雪》、 《岸上的秋天》等,比較集中于對當代白族婦女生活的表現。她的小說一反以往文學作品中農村婦女的表現模式,以新的面貌和姿態凸現出當代白族婦女的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
在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學中,我們看到很多內容是表現各民族婦女承受的苦難和在落后生產力下得到解放的過程。而居住在洱海之畔的白族,從社會形態和歷史、文化發展來看,都處于比較進步的行列。所以,作為白族第一代女作家,景宜的寫作并沒有從歷史深處去追尋婦女解放的足跡,而是從生活的當下直接切入,進入對當代生活中白族婦女精神和心靈世界的表現。
景宜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是生活在蒼山下洱海畔的年青的白族婦女,她們聰明、勤勞、美麗,都有一顆孤傲而不甘沉寂的心,不甘于按傳統規定好的模式去做人。這在20世紀80年代,是一種大膽的文學追求,也正好切合和那個時代流行的人文啟蒙精神。但這種精神追求體現在一群鄉間婦女身上,卻是作家對女性生命的大膽贊美,也是其理想精神的體現。作家讓筆下的女性形象們站得比普通婦女更高,執著地尋找著自己做人的價值和意義,她們雖然不可能像城里的知識婦女那樣大聲疾呼女性的獨立和權利,卻憑著本能,覺出人生不應該只是“這樣”,還應該有別樣選擇的可能,為此不惜與傳統規范進行大膽抗爭。
《誰有美麗的紅指甲》是這些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說圍繞鄉村衛生員白姐的婚姻愛情展開故事。美麗的白姐有著讓周圍女人羨慕的家庭,丈夫是中學同學,醫學院畢業做了城里的醫生,有工作有文化,而且白凈漂亮。可是倆人之間卻缺少心靈的默契和溝通,白姐從丈夫身上得不到自己需要的愛情。白姐不愿意在他的俯視與隔膜中生活下去,轉而對在鄉下從事漁業生產的同學阿黑產生愛情,并且大膽向丈夫提出離婚,準備和阿黑結合。這在傳統規范制約下的鄉村,無疑是個大膽而又前衛的行動,同時也把自己置于一個尷尬的境地,成為人們攻擊、嘲笑的對象。這篇小說的題記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是火把節染不紅指甲的女人,她將被視為不潔貞”。白姐的行為顯然是對傳統道德的大膽挑戰,所以她面對的將是強大的傳統力量。
白姐這個人物在當代民族題材小說中,是不多見的有著明確人生目標和精神要求的女性。支撐她的精神來源,或者說使她和其她白族婦女區別開來的原因是她對精神的需求,和對這種需求的大膽表露。小說中交代,白姐擁有文化知識,是村里的計劃生育衛生員,她看過電影《五朵金花》,對愛情有詩意的向往,這一切都是她精神追求的動力和源頭。景宜在白族文化傳統的觀照下,為小說注入現代意識,使人物的精神追求成為一個新的亮點。
二、報告文學及影視寫作中的高原意識
20世紀80年代,景宜離開云南到北京工作。因為環境和工作性質的改變,她的寫作雖轉向影視和報告文學領域,但沒有改變的是她對民族生活題材的關注。
2000年來,她創作出版了民族題材的報告文學三部曲《金色喜馬拉雅》、《節日與生存》、《東方大峽谷》,為當代文壇奉獻了新的審美內涵,也使自己的寫作境界不斷提升,表現視野更加開闊了。《東方大峽谷》描寫的是云南傈僳族、怒族、獨龍族的生活現實和歷史發展,以20世紀90年代云南獨龍江公路建設為主要線索,寫出了將近10年中各民族人民為這條特殊公路的修建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從而結束了獨龍江作為“我國惟一不通公路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特殊歷史。作家的創作意圖是希望通過這個歷史性的事件,揭示出在中國這個民族團結的大家庭中,各民族共同發展、共同進步的主題。
2000年,景宜創作出版表現納西族東巴文化的長篇報告文學《節日與生存》,該書以“1999年中國麗江國際東巴文化藝術節”為主線,記錄了古老的納西民族的歷史、文化及生活場景。有評論稱這部報告文學“通過對云南麗江少數民族群體的生命體驗和精神追求的描述,探討了傳統文化在少數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和意義,呼喚人類對共同的精神家園的關愛與堅守。”[1]書中景宜對民族節日的性質和意義作了詩性的升華:“如果沒有節日,就沒有民族文化的大集中、大傳承、大擴散。如果沒有節日,就沒有生存與夢想,就沒有創造與升華。”體現出作家視野的高度與開闊。
2001年,為紀念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景宜又創作了我國第一部全面描述藏醫藏藥發展成就的長篇報告文學《金色喜馬拉雅》。中國作協少數民族委員會、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和作家出版社專門在人民大會堂西藏廳聯合為該書出版舉行了首發式暨研討會。該書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藏醫藏藥題材,上升到對人類共同問題的關注的探討。正如作家在本書的開頭所說的:“我舉著潔白的哈達向你走來,請告訴我——什么是宇宙、人、生命的智慧之光?”書中以藏醫藏藥為起點,對漢藏文化的交流、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人類物質與精神的關系等問題都有獨到的認識和思考。
這三部長篇報告文學體現了景宜寫作中視點的轉移。特別是后兩部,在文學界了產生了很大影響,獲得讀者和評論界的一致好評。作家已經從最初寫單純的白族生活題材上升到對各民族文化交融的關注上,體現出超越和宏闊的人文視野。對導致寫作中這一轉變的緣由,景宜自己曾經有一番闡釋:因為工作關系有一段時間她被派駐中央電視臺,負責“中華民族”欄目的制作,“這種經歷下,我的創作主題從單一白族生活轉向多民族的大視野,開始從一個大概念的民族文化的交融、民族的發展與進步這樣一個層面上去思考。我開始從大理家鄉為主題的這樣一個文化土壤進入到一個更開闊的擁有56個民族的遼闊疆域。①景宜接受記者采訪時的回答 (發表于“華夏文化網”,題目:《我為故鄉而寫作》,作者辛向東)。景宜的視野中對民族和高原情有獨鐘,她的三部報告文學選擇的都是以西部高原的少數民族文化、歷史為表現內容。這和作家的文化之根和民族心理素質有著密切關系。
Anti-inflammatory, hemostasia and injury-repairing effects of toothpaste with sea buckthorn oil 1 28
景宜報告文學中的高原意識首先體現在對題材的特殊關注上。無論自己離開故鄉多遠,景宜一向是以“蒼山洱海的女兒”②2004年12月,景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多少年來,我故鄉的山水、親人,洱海中的老木船,那些給我過最初啟蒙的民間藝術家、和我一起工作過的文藝工作者常常出現在我的記憶里。我是蒼山洱海的女兒!”(采訪見于“華夏文化網”,題目:《我為故鄉而寫作》,作者辛向東)自居,從沒有忘記自己的根之所在。白族聚居的大理、下關一帶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驛站,有兩條非常重要的通道,一條通往緬甸,是“南方絲綢之路”;一條通往西藏,是有名的“茶馬古道”。各民族在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交往有著悠久的歷史。各民族間互相依存,共榮共生的傳統對促進民族的團結、進步起著重要作用。景宜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之根的基礎上,對其他民族的文化、生存發展給予人文關懷,也使自己的寫作視野得到大的提升。
其次,景宜的報告文學超越了一般民族風情的介紹,上升到對民族文化內涵甚至是人類精神的開掘,體現出作家在寫作上全新的精神追求。
民族題材的作品,容易出現的問題之一就是對民族風情的把握。因為文化、歷史、地理環境等因素造成了少數民族和漢族生活上的許多差異,在一些人眼中,少數民族幾乎等同于“異類”,于是喜歡用獵奇的眼光去了解他們的生活。一些民族生活的題材,也容易流于膚淺和表面化,或者寫成配合旅游的宣傳介紹。但景宜的身份不同,她自己首先是少數民族中的一員,其次還是一位有一定思想深度和文化品格的寫作者。而且隨著人生經歷的豐富,作家的文化品格和思想修養也得到更大的提升。體現在寫作中,就是對民族文化內涵的拓展與重視。比如在《節日與生存》中,納西族的文化、民族風情有很多可以表現的內容,但景宜選擇的是以“99中國麗江國際東巴藝術節”這一中心事件和藝術節上表演的《東巴魂》為軸心,展開對納西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敘事。通過對納西東巴、學者、藝術家、領導者、普通民眾等不同類別和群體的采訪,一步步為讀者展現東巴文化對待生死、生存、發展、進步等重大問題的態度和價值取向。《金色喜馬拉雅》中藏醫藏藥只是作家寫作的切入點,真正傳達的卻是精神層面的思考和追求。作品中還塑造了一批有著鮮明民族特色的人物,如西藏醫學院院長強巴赤列、嘎藏根登老師、賽倫活佛、多識活佛等。他們代表著藏族文化的某種精神亮點,生活得達觀而又自信。對這些人物內在精神的把握,也是對藏族文化內涵的深入開掘。
這幾部報告文學奠定了景宜新時期寫作的追求和目標:超越民族作家的視野,關注多民族的文化歷程和生存境遇,發掘民族文化最深層的精華,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做出貢獻。她已經把這一點自覺當成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
正是基于思想境界的提高和寫作上的鋪墊,所以才會有影視作品《茶馬古道》的問世。作為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的獻禮片,23集大型民族題材電視連續劇《茶馬古道》于2005年9月18日在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黃金時段播出。媒體稱“《茶馬古道》是云南與大西南各民族人民譜寫的一部傳奇史詩,一曲愛國主義頌歌。”
而作為長篇小說的《茶馬古道》是于2005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的。故事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緬甸淪陷,滇緬公路也被迫中斷,援華物質無法從緬甸進入中國。茶馬古道成了惟一的通道,一支由多民族組成的民間馬幫商隊義不容辭地踏上這條古老的山道,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和內地與川、滇、藏政治、經濟的聯系……作家為我們鋪展了一幅壯麗神奇的史詩般的歷史畫卷。小說以主人公木石羅、花依、格桑加措的愛情糾葛為中心敘事線,圍繞著麗江馬幫首領木家、三江土司格桑家、大理茶王楊家、拉薩巨商尼瑪家4家的恩怨情仇展開故事。通過藏、白、回、漢、彝、納西、傈僳、普米、珞巴等9個民族人物的命運,歌頌了偉大的民族團結和愛國主義精神。景宜在作品中保持了對云南高原民族文化的關注和內涵的開掘,表現了各民族之間多元共存、血脈相連的生存關系,對云南特有的東巴文化、佛教文化也有生動展示。在這部作品中,她具有多重身份,既是編劇、制片人,又是作家、民族學家。前者讓她能引入新的電視元素和手段來探索民族題材的表現,后者則使她的作品有與眾不同的視角和深度。而“蒼山洱海的女兒”這一身份,則使作品飄溢著濃重的高原氣息和對故鄉人深切的愛意。 《茶馬古道》為當代民族題材的表現,以及民族精神的開掘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同時出版的《茶馬古道和一個白族女人》,是一部文化散文,作者將創作《茶馬古道》電視劇的緣起,重訪茶馬古道中的感人故事以及電視劇拍攝過程中的有趣花絮,用圖文并茂的形式展現給讀者。
從題材到思想情感,景宜的這些報告文學和影視作品,都透露出濃厚的高原意識,這是作家的生命成長和文化記憶在寫作中的體現。紅土高原養育了她,也給了她寫作的靈性和源泉。
三、近期寫作中女性意識的鮮明呈現
景宜是一個在明確的女性意識觀照下從事寫作的作家,她從來沒有避諱過自己的性別和視角,而是堅持以理性精神對女性的生存進行思考和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人風格。無論是她前期還是近期的寫作中,其中經常出現的幾個詞是“白族”“女人”,表明了作家對自己寫作身份和文化立場的自覺認同。民族,是她成長的精神搖籃;女人,則是她審視、表現世界的眼光和視角。
步入文壇之初,景宜就以敏銳的眼光注意到了歷史和現實的不平等給白族婦女帶來的阻礙,讓她們對這些不平等進行抗爭,和傳統規范之間作較量,以爭得自己做人的權利。從這些文學人物身上,可以感受到20世紀80年代文學中人文主義啟蒙精神對作家的影響。與其說那些洱海邊的白族女人在爭取做人的權利,不如說是作家主體意識的覺醒使她能站到一定高度去審視女人現實的生存境遇,并為之發出聲音。她借小說中蜜婉這個人物的口說出:“我該做什么還做什么,要不照我想的不白做個人了么!”“照我想的做”,這是一種充滿現代意識的精神。很多女人在歷史和現實中其實都是在“照別人想的去做”,按照傳統規范好的模式做人。“不白做個人”則是一種人性化的樸素的人生看似底線實則要求很高的目標,體現了女性對人生價值的肯定和追求。
當一些作家還在從政治層面表現女性解放的主題時,景宜就已經以敏銳獨特的女性視角切入到女性的精神追求這一比較超前的文學命題中,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她不僅表現女性在與傳統對峙中要強、進取的一面,更以細膩的筆觸揭示出她們性格中的軟弱與彷徨,寫出了女性群體內在精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現實的尷尬是:少數民族婦女覺醒了,渴望有獨立的人格和自我價值的實現,渴望去參與社會的創造,按自己的意愿望去改變生活,但是社會卻還沒有為她們準備好適合新角色生存的土壤,傳統的社會結構并沒有及時調整好規范,遵循的還是舊有的價值尺度和道德標準。所以,那些婦女在生活的碰撞中總會感覺到迷惘、困惑和痛苦。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痛苦已經不再是“婦女受壓迫,渴望被解放”式的痛苦,而是人在自我價值實現過程中所產生的精神沖突和掙扎。
同時,景宜還賦予筆下的女性內在的自信和自傲,這是支撐她們在生活中跋涉的重要動力。她們對自己的性別都有清醒的認知,并沒有因為傳統的壓力而對自身生出自卑感和壓抑感,這是作家女性意識的閃光點。女性的性別是導致人物困境的原因,但同時也是人物自信心的源泉。著名作家馮牧曾經這樣評價說:“景宜小說的突出特點在于它強烈的女性色彩。當然這不僅僅是她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女性的緣故,而是在那一組組錯綜復雜的矛盾事件和一個個性格迥異的婦女形象背后所浸透的女性意識——女性對于這個世界的獨特的認識方式。”[2]正是在女性意識的觀照下,作家生動展示了白族婦女生命的進步歷程,并以前衛的姿態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對女性意識作了成功的實踐和探索。
景宜此時期的寫作中一直保持著女性視角對世界的認知和感悟,這是一種文化語境,也體現了作家對性別的認知在不斷提高和升華之中。如果說她前期小說中的女性意識顯得比較前衛和激進,主要集中表現女性與文化傳統的對立,以及女性生命意識的覺醒,那么到近期寫作中,這種女性意識則因為作家人生經歷和思想境界的提升,多了些博大、包容的色彩。景宜的創作既在民族上超越了對單純白族生活的表現,也從性別角度超越單純的女性生活上升到對多民族命運的關注,上升到女性對世界人類的關愛與博大情懷。
[1]梁若冰. “節日與生存”受關注 [N].光明日報,2000-04-26.
[2]馮牧文集:第 3卷 [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
Abstract:Jin Yi,a woman writer of the Bai nationality,has engaged herself in literary creation since the 1980s and maintained her pursuit of ideals.She has transcended the narrow ethnic vision and focused on the existence of the ethnic groups in the borderlands.Her highland attachment and female consciousness help reveal the essence of the ethnic cultur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a Bai writer;Jing Yi;pursuit in creation;ideal
(責任編輯 丁立平)
The Bai Writer Jing Yi and her Literary Creation
HUANG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Kunming 650031,China)
I294
A
1672-867X(2011)01-0143-04
2010-09-27
黃玲(1959-),女 (彝族),云南民族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