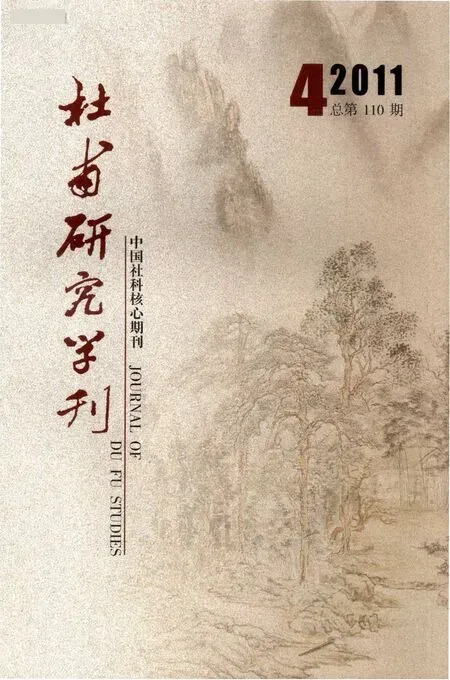杜甫戰(zhàn)事詩的藝術特點初探
周鴻彥
杜詩給讀者的審美感受是獨特而強烈的。其獨特的藝術個性在戰(zhàn)事詩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在反映“戰(zhàn)事”這一重大歷史題材時,杜甫置身于時政的劇變,關心國計民生并將其所歷、所聞、所感俱反映于詩歌當中。杜甫的戰(zhàn)事詩發(fā)展并創(chuàng)新了詩歌體裁與表現(xiàn)方法,以大氣磅礴的藝術概括力兼細致入微的筆觸,本著史家實錄精神,以悲憫憂憤的情感,在沉重的人世感悟中去展現(xiàn)個人、民族、社會的劇變。
一、戰(zhàn)事詩的文體創(chuàng)新
(一)創(chuàng)新古體詩
根據(jù)《錢注杜詩》對杜甫古體與近體詩的分類統(tǒng)計,杜詩中古體詩約四百一十五首,近體詩約一千零二十七首,杜詩中的古體詩約占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而杜詩為詩之“集大成”者,其近體詩廣為后世重視,而古體詩的重視則相對較少。以古體寫時事,受限制較少,筆者愧于學識淺陋,于杜律難有發(fā)明,就杜甫描寫戰(zhàn)事題材的古體詩論述一二。
時代劇變后社會的動蕩不安、顛沛流離的生活境遇,使詩人感時傷亂,心情沉重。要表現(xiàn)這樣重大的題材,非長篇大作,則容納不下。杜詩中多用五古表現(xiàn)戰(zhàn)事題材,如《北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羌村三首》、《昔游》、《遣懷》、《留花門》、《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草堂》、《塞蘆子》、“三吏”、“三別”等等。杜甫辭去華州司功參軍后,自陜西經(jīng)秦州,過同谷,在入蜀途中約有一百二十首隴右詩作,除《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外,全是五言詩,其中五古詩居多。五言古詩,押韻與平仄不受太大限制,既便于敘事、寫實,也適宜抒情、議論,杜甫將這種詩體的特長發(fā)揮到了極致,全面地對戰(zhàn)亂進行寫實和抒懷。從“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北征》)頗具史家風范的鄭重與嚴肅,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羌村三首》其一)久別重逢的百感交集。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到“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 “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這種對社會貧富差距的高度概括及個人沉痛現(xiàn)實遭遇的細致入微的描寫,在五古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杜甫擅長五古長篇,不僅使古體詩自然樸質,而且?guī)в新苫捻嵨丁O鄬τ谄吖诺暮婪牛骞泡^沉著、謹嚴。施補華說到杜詩五古的成就:“少陵五言古千變萬化,盡有漢、魏以來之長而改其面目。敘述身世,眷念友朋,議論古今,刻劃山水,深心寄托,真氣坌涌。頌之典則,雅之正大,小雅之哀傷,國風之情深文明長于諷喻,息息相通,未嘗不簡質渾厚,而此例不足以盡之。故于唐以前為變體,于唐以后為大宗,于三百篇為嫡支正派。”①
錢木菴在《唐音審體》中說:“七言始于漢歌行,盛于梁……,歌行本出于樂府,然指事詠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分樂府、歌行為二。”②以《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體、又有五言古體的敘事詩,這一類詩實際是古代樂府民歌的流變,但杜甫打破慣例,不用樂府古題而“即事名篇”,這樣就更能夠直接全面地反映現(xiàn)實,更具有史實價值。關于杜詩七古成就,施補華也有卓見:“少陵七古,學問才力性情,俱臻絕頂,為自有七古以來之極盛。故五古以少陵為變體,七古以少陵為正宗。”③杜詩的七古縱橫馳騁,骎骎獨上,顯示出嶄新的格調。除去以山水、書法、繪畫、舞蹈等入題的七古詩外,以戰(zhàn)亂時事入題為七古的詩作也占很大比重。如《秋雨嘆》、《曲江三章》、《洗兵行》、《憶昔二首》、《釋悶》、《歲晏行》、《蠶谷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等等。胡應麟對“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洗兵行》)評價云:“以和平端雅之調,寓憤郁悽悷之思,古今言壯句者難及此。”④杜詩七古反映現(xiàn)實,抒發(fā)議論,歷來皆受到高度評價。《大麥行》、《去秋行》、《負薪行》、《虎牙行》、《歲晏行》、《蠶谷行》、《兵車行》、《麗人行》等等反映社會戰(zhàn)亂現(xiàn)實的詩歌,也多用歌行、七古表現(xiàn)。“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歲晏行》)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工異曲。杜詩的七古既有繼承初唐以來換韻鋪寫的長處,如《洗兵行》,又有不轉韻而一韻到底一氣呵成的長篇敘寫,如《麗人行》、《歲晏行》。杜詩反映戰(zhàn)事的七古更表現(xiàn)出變化多端,以復雜的音調、自由的句式、豐富多變的用韻,突破了七言終篇的格局。使得七古節(jié)奏更加鮮明、音調更加鏗鏘,更具有豐富的表現(xiàn)力。
(二)創(chuàng)新樂府
唐代的樂府詩,在杜甫以前的作品,大都沿襲舊題,而杜甫則自創(chuàng)新題,創(chuàng)新樂府。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說》中稱:“樂府體裁,歷代不同,唐以前每借舊題發(fā)揮已意,太白亦復如是,其短長篇什,各自成調,原非一定音節(jié)。杜老知其然,乃竟自創(chuàng)名目,更不借徑前人,如《洗兵馬》、《新婚別》等皆是也。”⑤錢木菴也認為:“近代唯杜甫《哀江頭》、《悲陳陶》、《兵車行》、《麗人行》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⑥杜甫突破古體句式整齊劃一的慣例,在整齊的七言基礎上雜以少量雜言,這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古體。以“歌”、 “行”、 “嘆”等命題的七言詩,保留樂府的音樂標志,但又不必附屬于音樂,更以新題和新意入詩,是所謂的“新樂府”。杜詩以樂府詩描寫戰(zhàn)亂現(xiàn)實,一方面以傳統(tǒng)的邊塞題材的古樂府入詩,如《前出塞》、《后出塞》等,另一方面以新事入詩,即名新題,如“三吏”、“三別”、《洗兵行》、《麗人行》、《哀王孫》等。杜甫以五、七言創(chuàng)作即事名篇的樂府,自創(chuàng)新題,對后世影響極大。杜甫新樂府中仍保持著樂府詩的諷喻精神,并把這種諷喻精神深刻化,如“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麗人行》)與“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哀江頭》),一寫繁華,一寫悲慘,對照極為鮮明。杜詩中的樂府詩指陳時弊,描寫社會戰(zhàn)亂,大膽“諫君之失”,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這種批判精神在這種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體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
(三)善作定格聯(lián)章組詩
杜甫戰(zhàn)事詩中多定格聯(lián)章組詩。所謂定格,指詩的體裁相同、格式相同;聯(lián)章即指在篇章上有繼承關系,在意義上相聯(lián),有共同的主題的組詩形式。其淵源可追溯到荀子的《成相篇》。杜詩的聯(lián)章組詩多反映戰(zhàn)亂現(xiàn)實。五古如《八哀詩》、《羌村三首》、《遣興五首》;七古如《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五律如《收京三首》、《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秦州雜詩二十首》;七律如《諸將五首》等等。除此之外,樂府詩中也有聯(lián)章如古題樂府《前出塞九首》、《后出塞五首》;而《悲陳陶》、《悲青坂》、《哀王孫》、《哀江頭》以及“三吏”、“三別”也是實質上的各自標題而共有主題的新樂府聯(lián)章組詩。
杜詩在表現(xiàn)社會現(xiàn)實、戰(zhàn)亂傷懷的重大題材時,筆觸極深。除了用五古長篇《北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來表現(xiàn)社會時事外,善于精心選材、別具匠心的組織,以組詩這種形式,在變化和發(fā)展中來關注時政。如《羌村三首》,三首詩反映了作者回到家的驚喜交加的場面: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與“父老四五人”交談情況,設身處地地描寫了社會底層人們的生存情況。在《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中,詩人對自己身處絕境的悲憤。隨著詩歌數(shù)量的疊加,情感的層層積累,形成了一唱三嘆回腸蕩氣之勢。楊倫的《杜詩鏡銓》引朱熹語:“豪宕奇崛,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諸調而變化出之,遂成創(chuàng)體。”⑦樂府組詩《前出塞》描寫了在府兵制下,自備兵刃器杖,被迫去西方邊塞戍守的士兵;《后出塞》則寫自愿去北方邊塞,打算尋求出路,希望在異域立功的小軍官;二者背景的差別、思想行為的迥異,為我們展示了安史之亂之前拓邊戰(zhàn)爭與邊鎮(zhèn)重兵的軍事形勢,也為后來“安史之亂”爆發(fā)的原因埋下伏筆。以古體寫時事,較少受限制,杜甫多數(shù)寫時事的詩都是古體;用律詩寫時事,字數(shù)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他這部分寫時事的律詩,較少敘述而較多抒情與議論,如《秋笛》、《即事》(“聞道花門破”)、《王命》、《征夫》等。為擴大律詩的表現(xiàn)力,他以組詩的形式,細致深刻地表現(xiàn)了廣泛和豐富的社會現(xiàn)實內容。五律和七律中都有這樣的組詩。五律中的《秦州雜詩二十首》是一例。杜甫以七律寫組詩的,如《諸將五首》,《諸將五首》作于安史亂平后,杜甫指責諸將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平亂,造成養(yǎng)虎遺患的后果;不屯田務農,解決軍需;不效忠國家只享受高爵厚祿等種種弊端。這在一首詩中是很難完成的。杜詩以獨具匠心的組詩形式,表現(xiàn)了對國家前途與民族命運的擔憂。
二、鋪陳敘事 ,以文為詩,開宋詩先河
元稹在談到杜詩藝術特點時說:“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shù)百。”(《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杜詩善鋪陳事實,在戰(zhàn)事題材中尤多用此手法。杜甫提倡“別裁偽體親風雅”(《戲為六絕句》),但“比興”影子般的諷刺實難為杜詩戰(zhàn)亂寫實之需要,加之詩人的感傷亂離、耳目所及,因此不拘囿于“比興”的溫柔敦厚傳統(tǒng),而大量采用賦筆手法,鋪排盡致社會的方方面面,以述情切事為快。
早在天寶六載,杜甫便向玄宗進獻了《雕賦》、“三大禮賦”、《封西岳賦》。“三大禮賦”受到玄宗重視,杜甫也因此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壯游》)“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莫相疑行》)這樣難忘的殊遇。可見杜甫是運用賦體的大手筆。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賦也,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在運用賦的手法寫詩時,杜甫并沒有像漢賦那樣巨細無遺地堆砌鋪排,以顯示其典雅板重、僻詞奧義。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說》中對杜詩賦筆作了高度評價:“作詩善用賦筆,惟杜老為然。其間微婉頓挫,總非平直,須善學始得。其他名手,未有不比、興兼之。”⑧運用鋪陳手法容易散漫,但杜詩“賦”的手法,卻能把概括性的敘述與細致入微的描寫結合在一起。《洗兵行》歌頌中興,憶及三年來與安史叛軍的艱苦戰(zhàn)斗,“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僅用十四個字高度概括地寫出了戰(zhàn)爭帶來的創(chuàng)傷。笛咽關山,兵驚草木,人民飽受亂離的痛苦形象都準確地概括了出來。而賦筆所到之處,包融了社會方方面面,全方位地展示了社會各階層:上至民族軍事之爭,宮闈之秘,中及達官顯赫、詞人隱士,下及田家望雨,城南思婦,都在杜詩筆下一一呈現(xiàn),顯示出詩人“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賦家之心,從細致廣闊到凝煉深遂的筆法表現(xiàn)出杜甫乃至整個社會的人民對太平中興的強烈向往。
以賦筆寫詩,最忌平板滯直,缺少變化。杜甫卻能從布局謀篇,安排層次,節(jié)奏及用韻等方面,顯示其卓絕的才能。在敘述中,杜詩并不簡單地局限于順敘中,而兼倒敘、插敘、追敘于一體,巧妙地剪接,通過不同時間、方式來敘述事件。如《述懷》詩,“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自寄一封書,今己十月后。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詩中希望、憂慮、擔心、焦慮等各種情感交織在一起,曲折起伏。“寄書問三川”此插敘,再倒敘“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后”,再正敘“反畏消息來”,沒有這種變化,不能反映詩人之焦慮心態(tài),“反畏消息來”,更讓人覺得驚心動魄,杜詩賦筆入詩可謂爐火純青。
杜甫擅賦筆入詩,如長篇巨制《北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稍短篇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九日寄岑參》等。杜詩雖多用賦的手法,但敘述時事和間發(fā)議論都是在情感激發(fā)的情況下進行,融入整篇的詩中,不僅不破壞詩的抒情自然氣氛和形象完整,反而更增加抒情氣氛,形象更為豐富、厚重。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夾敘夾議,邊敘邊議,有時大段發(fā)表議論:“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圣人筐篚恩,實愿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zhàn)栗”。又如《北征》詩,從敘述他不忍離開朝庭以及在旅途中的個人恍惚狀態(tài),從“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轉入對朝廷的擔憂,對馬嵬驛事件的敘述后,更接以大段的議論:“不聞夏殷衰,中自誅妹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杜甫把議論納入詩篇,不這樣似乎不能把他的思想感情充分發(fā)揮出來,而其敘事、抒情、議論又水乳交融。杜甫晚年所作的《壯游》、《昔游》、《遣懷》等詩或闡發(fā)人生哲理、或總結國家盛衰經(jīng)驗,結合自己的生世遭遇,皆運用敘述的手法,甚至用敘述來代替議論:“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shù)玖弧?《壯游》)。此四句敘述統(tǒng)治者的荒唐腐朽,與議論的效果一樣。杜詩融敘事、抒情、寫景、議論于一體,打破詩與文的界限,被后人稱為“以文為詩”,直接影響了中唐的韓愈等人,并開宋詩之先河。
南宋嚴羽在評價北宋詩歌時說:“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于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⑨嚴羽對宋人散文化、議論化傾向的詩風頗有微辭。杜甫不僅豐富完善了詩歌體制,而且也創(chuàng)新了詩歌的表現(xiàn)形式,但后人卻強調其形式,忽略了杜詩反映社會現(xiàn)實,以真情實感來抒情、議論的根本。杜甫戰(zhàn)事詩的議論不是某種哲理的演繹或刻板的道理闡發(fā),而是從廣闊的社會生活中概括出來的至理名言,往往能和人們的心靈產生強烈的共鳴。如“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詩句千古傳誦。宋人在杜詩的啟發(fā)下,又從另一個角度開啟了宋詩的另一條道路,即由唐詩的主“興象”轉為宋詩的主“理致”,也是詩歌創(chuàng)作的另一種收獲。
三、憂憫悲憤的情感與沉郁詩風
“安史之亂”后,杜甫的大半生是在坎坷不遇,顛沛流離中度過的。作為有“奉儒守官 ,未墜素業(yè)”家族傳統(tǒng)的杜甫,他早年自稱“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然而卻生不逢時,當他滿懷信心投身報國時,盛唐已走下坡路。兩度科考失敗,投賦薦待詔集賢院后,又被冷落了很久,最后得一小官。然而安史之亂又爆發(fā),杜甫難以在仕途上實現(xiàn)他的抱負。雖然后來在唐肅宗身邊做了一個拾遺,但在“房琯事件”中觸怒肅宗,還差點被殺,終于迫使他離開長安。當杜甫在顛沛流離中一步步走向社會底層,就更深入地了解了普通平民的生活。動蕩時代的背景,個人的身世遭遇,已奠立了杜甫戰(zhàn)事詩獨特的情感體驗與詩歌風格。
杜甫早年在《進雕賦表》有這樣一段話:“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jīng),先鳴數(shù)子,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后人因以“沉郁頓挫”為杜甫詩歌的風格特征。“沉郁”含有沉悶抑郁之意,許多論者引申為“悲慨”,與杜甫的憂國憂民感情聯(lián)系起來。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認為:“‘沉郁’主要表現(xiàn)為意境開闊壯大,感情深沉蒼涼。”袁行霈、羅宗強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則云:“杜詩的主要風格是沉郁頓挫,沉郁頓挫風格的感情基調是悲慨。……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壯大深厚。”事實上,杜甫天寶九載以前的大多數(shù)詩歌并不具備沉郁的風格,但是如果從安史之亂后去歸納杜甫詩歌的風格,應是恰當?shù)摹6鸥Υ罅康膽?zhàn)事詩已是形成這種“沉郁”風格的重要因素。
時局的動蕩,戰(zhàn)爭的災禍,人民的苦難,自己和同流們的遭遇,浸透在杜甫的詩歌當中。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當他從長安到奉先回家后,迎接他的卻是:“入門聞號啕,幼子餓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短短十個字中蘊涵了多少愧為人父的辛酸與悲痛!小兒子被餓死,對杜甫不啻是個重大打擊,但杜甫并未直接傾瀉心中的悲痛悲憤之情,因為早在自京赴奉先的路上杜甫已親眼看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場面,對善于推己及人的杜甫來說,目睹百姓蒼生已使其哀痛不已,親歷自己兒子餓死,哀痛、悲憤之情已無法述說,欲哭無淚,慘淡的十個字,卻字字酸楚,句句含淚。“默思失業(yè)徒,因念遠戍卒”,在痛定思痛后,杜甫推己及人想到了“失業(yè)徒”,自己“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都尚且如此,那么那些失去田業(yè)流離逃亡的人們以及遠征戍邊的士兵生死又何以堪?這種深沉、痛楚、郁結的情緒已經(jīng)迥然于同時代的其他詩人,漸漸形成杜甫獨特的詩歌風格。杜甫寓居草堂,當他住的茅屋被秋風刮破后,處境極為窘困:“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jīng)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但他卻想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甚至“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甫一生雖多經(jīng)患難,更多的是把萬方多難的時代與個人坎坷遭遇緊密結合在一起,推己及人,憂國憂民,在感悟戰(zhàn)亂時世的沉重中透出深厚的憂憫悲憤情懷。
魯迅說:“悲劇就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屈原在“舉世皆濁獨我清”的混沌時世中不愿同流合污,投江自殺;司馬遷受極刑后,毅然完成《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杜甫終生堅守“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儒家志向,最終恓惶一生。杜甫一生,顛沛流離,貧病交困,但杜甫在此種境況之中,始終不折不撓,無論“窮、達”都要兼濟天下,這種精神使憂憫悲憤具有了氣力充沛,持重悲壯,使悲劇具有了崇高與悲壯的精神指向。因此,杜甫在戰(zhàn)亂面前,以天下為己任,堅守“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表現(xiàn)出憂國憫民、悲壯深沉的情感特質:“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jiān)李賓客一百韻》)、“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幽薊余蛇豕,乾坤尚虎狼”(《有感五首 其二》)、“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面對戰(zhàn)亂中的嗷嗷百姓,“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壯游》),這便是杜甫的宏大胸襟與悲憫情懷。他的憂憫,上憂國家社稷,下憫百姓蒼生。《洗兵行》從諸將破胡,回紇駐擾至郭相深謀、肅宗問寢、張公籌策……對“二三豪志”整頓乾坤的期待,同時兼顧“田家望望惜雨干”,“城南思婦愁多夢”等平民百姓、蕓蕓眾生,這既是憂國憂民的封建士大夫的拳拳之心,又是一位心存天下老者的悲憫情懷。
當安史叛軍長驅直入,唐軍節(jié)節(jié)敗退,潼關失守,陳陶戰(zhàn)敗,鄴城失利“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別》),“哀哉桃林戰(zhàn),百萬化為魚”(《潼關吏》),“野曠天清無戰(zhàn)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這樣慘痛的教訓使杜甫忍悲含憤寄希望“日夜更望官軍至”,然而青坂又戰(zhàn)敗,杜甫不得不再次“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悲青坂》)、“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憶昔其二》)這便是杜甫在悲憤中的沉重。面對國家危難,哀哀蒼生,杜甫仍然充滿著濟時之愿:“再光中興業(yè),一洗蒼生憂”(《鳳凰臺》)、“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歲暮》)、“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徒步歸行》)、“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shù)公”(《收京》)、“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為了國家的中興,杜甫在悲憤中奮起,在憂憫中期待。故杜詩的沉郁,正如蕭滌非先生所指出的——雄沉勃郁,即杜甫沉郁風格的實質。這種風格的形成,既是現(xiàn)實的,又是歷史的,既是個人的,又是社會的。杜甫的戰(zhàn)事詩感情憂憫悲憤,深沉悲壯,勃郁凝重,成為形成沉郁詩風的主要因素。
注釋:
① 施補華《峴傭說詩》,見王夫之《清詩話》(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②⑥ 錢木菴《唐音審體》,見王夫之《清詩話》(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③ 施補華《峴傭說詩》,見王夫之《清詩話》(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④ 胡應麟《詩藪》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⑤⑧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見王夫之《清詩話》(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⑦ 楊倫《杜詩鏡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 嚴羽《滄浪詩話》,見何文煥《歷代詩話》(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