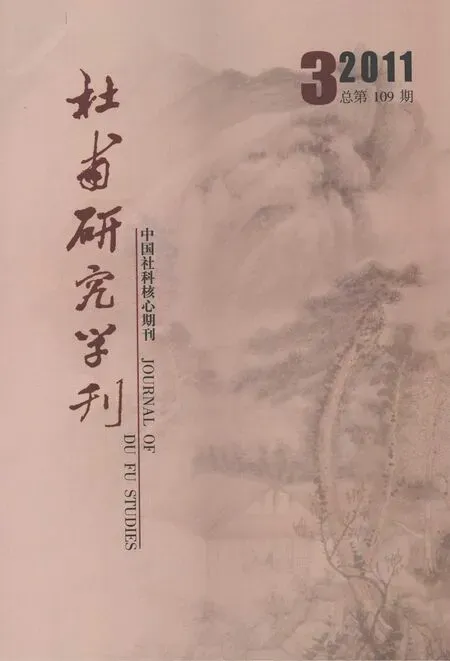論浦起龍《讀杜心解》之緣起、編次及其“心解”法
張家壯
一、《讀杜心解》之緣起
浦起龍(1679—1762)①《讀杜心解》(以下簡稱《心解》)開始撰述的時間是康熙六十年(1721),書成于雍正二年(1724)(見《讀杜心解·發(fā)凡》,以下簡稱《發(fā)凡》)②。這是浦起龍人生最黯淡的一個時期。在寫于雍正七年(1729)的《題己酉科藍筆闈卷后》③,浦氏自言年五十一方為諸生、三十二年間歷場屋十二科,這期間他一直在鄉(xiāng)里坐館④。到了雍正八年(1730),浦起龍才以第二甲第十六名中進士⑤。浦起龍撰述《心解》的時候,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送窮不去”,“久盼顯擢之音,幾為眼穿”(《致陸龍岡》)⑥的時候,在《致同年王蓼原先生》一札中,浦起龍道:
弟自顧顛毛半白,曳尾泥中,偶借案頭杜老一破牢愁,每有會心,書眉剳記,不自意遂成一書也。⑦
又《啟臬臺鳳巢族兄》曰:
夫心思才力不專于當世之制舉而憊于千年之老杜,計亦左矣!自惟十蹶場屋,進取已灰……惟少陵一書于古今世宙之故靡所不包,而自宋以還,箋疏百家罕有得其肯綮者,遂奮然援筆,舉其廿年之學而托諸一家之書,開古人之生面、寄畢生之苦心,如是而已。⑧
自來意有所郁結(jié)而不能夠通行其道者,多借著書立說發(fā)抒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浦起龍這里所袒露的正是“發(fā)憤著書”的精神傳統(tǒng)。借助上面引述的幾通短札,我們不僅清晰地把握了浦氏在《發(fā)凡》里“十蹶霜蹄,雙凋鬢雪”等話語中的詳細所指,更由此得以明白浦起龍在“進取已灰”之際借杜詩以為“送窮”之方正是《心解》撰述的最初起因。
但過去我們只是注意到《心解》的撰述是浦起龍在時代學術課題感召下的一次應戰(zhàn),即所謂“杜之禍,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世之解,《心解》之所為,不得已于作也”(《發(fā)凡》),而對《心解》成稿前作者個人的生涯以及撰述《心解》的心理動因,或略而不述,或僅作膚泛之介紹,罕有認真加以檢討。這既對我們了解《心解》的某些取向不利,也對探尋《心解》作為清初杜詩學結(jié)穴時期所表現(xiàn)出的時代特征造成困難。故而,在討論《心解》的種種表現(xiàn)之前,對于它的由來稍加追索,或許不算辭費。
二、舉業(yè)、庠塾教師與《讀杜心解》的編次
《心解》是浦起龍十蹶場屋之后撰述的第一部著作⑨。此書面世之初,頗遭譏彈,據(jù)咸豐時周有壬《梁溪文鈔》所載,其時同鄉(xiāng)華玉淳的駁論甚至讓浦起龍難以接應:“浦起龍《讀杜心解》成,玉淳致書多所辯駁,起龍無以難也。”⑩浦起龍自己在《上云貴制軍尹大人》中也說是“一時評騭未窺子美藩籬”?。這“一時評騭”,如《四庫全書總目》云:
自昔注杜詩者,或分體,或編年。起龍是編,則于分體之中,又各自編年,殊為繁碎。如《江頭五詠》,以二首編入五言古詩,三首編入五言律詩,尤割裂失倫。……又詮釋之中,每參以評語,近于點論時文,彌為雜糅。與所撰《史通通釋》評與注釋夾雜成文者,同一有乖體例。殆好學深思之士,而不善用所長者歟??
《心解》在詮釋方式(即“以文法律詩法”)上的問題,當時可謂深受訾議,在翁方綱《石洲詩話》、沈日霖《晉人麈》中都有與上引提要極為類似的論調(diào)。翁方綱《石洲詩話》曰:
近日有《讀杜心解》一書,……所解誠有意味,然苦于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蓋知文而不知詩也。?
又沈日霖《晉人麈》曰:
浦二田《讀杜心解》,固足為注杜者屈一指,然屑屑焉于起承轉(zhuǎn)合間求之,以文法律詩法,若老杜得力全從八股中來,正如紫陽(朱熹)葉《詩經(jīng)》韻,必以沈約韻律古人也。?
翁方綱對浦氏解杜“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的譏刺,至清末時也還有人在響應?。而浦氏既分體又編年的編次法,則迄今之論者仍覺其繁碎、紊亂?。
諸家的批駁自有其道理,這里暫不討論。事實上對《心解》編撰的“有乖體例”處,浦起龍自己并非毫無所感,《發(fā)凡》云:
書有圈點勾勒,始自前明中葉選刻時文陋習。然行間字里,觸眼特為爽豁,故仿而用之。但鉤勒只可施之長古、長排,彼八句亦截者,非法也。又如轉(zhuǎn)韻古風,自宜依韻分截,節(jié)族天然,否則使讀者縮腳停聲,攔腰換調(diào),多少不自在。
視圈點勾勒為陋習,足以見出浦氏的自知之明。對于分體編次所帶來的割裂,浦氏乃于卷首另列編年詩目譜一冊(也可參看《發(fā)凡》“詩雖編年,體各分見”條),更顯示了其補偏救弊的努力。問題在于,浦起龍既明知其中的弊端,何以仍要那么做呢?還是引浦氏在《發(fā)凡》中的原話作證。在說明杜詩的詮釋標準以及《心解》何以取分體編次法時,浦氏道:
其詩詞明了,初學悉能通曉,則不贅一語。
忽古,忽近,忽五言,忽七言,初學觀詩每苦之。今統(tǒng)分六卷:一,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排律;六,絕句。
出發(fā)點均在便于“初學”。至于浦起龍之借用時文圈點勾勒法分析杜詩,其實也是為此計。眾所周知,評點是明清時期一種極為流行的文學批評方式?,而此際善用評點之法者,如金圣嘆、徐增等人,他們的撰著,均明確表示了“務求有裨于初學”的宗旨義例?。正是預設的接受對象,潛在地影響了著者的研究思路。如上關于評點的言論與實例,所在多有,頗能幫助我們觀察到浦起龍的用心所在。如果我們再縱覽一下浦氏學術的整體脈絡,其心思則更可昭然若揭。在武進費念慈為浦起龍《釀蜜集》所作序言中,有云:
先生在康、雍間以文學教授鄉(xiāng)里,著書滿家,……茲編……殆為家熟(塾)讀書之階梯,開示學僮,道以徑路……?
康、雍間,亦即浦氏撰述《心解》之際。這里,費念慈指出的正是浦氏著述對有裨初學的看重。雍正八年浦氏進士及第后,先后出任云南五華書院山長、蘇州府學教授,所從事之業(yè)與其未第時之“教授鄉(xiāng)里”實無甚差別。這期間,浦氏又有《古文眉詮》一編?。所謂“眉詮”,也系用的評點鉤鎖之法“詮于簡之額”?,亦為生徒指示徑路之作。這些都在表明,浦氏學術研究的某些取向,頗與其平生的志業(yè)——他的教授生涯相關。《讀杜心解》的編次體例、以文法律詩法即生于此一脈絡中。面對其“割裂”、“強綴”與“雜糅”諸端,倘不能由這個角度來觀察,即或能發(fā)現(xiàn)《心解》別有所長,也還是要漫視其書的,前舉翁方綱、沈日霖就是如此。今人洪業(yè)云:
起龍書中注解評論與錢、朱、盧、仇輩立異之處甚多,雖未必處處的確可依,要為熟于考證者心得之作,未可嫌其編次體例之怪,而遽輕其書也。?
洪業(yè)從詮釋的新異這方面去推崇浦起龍,固然可以說是獨具只眼,但他對浦氏《心解》的編次方式還是缺乏同情之了解,故只是示以寬容罷了。此后談及《心解》,論者多取洪氏之說。這樣一來,不但對其編次體例中所寄寓的苦心仍無法理會,亦已在無形中將編次體例的各個層面與他的“心解”模式完全隔閡分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事實上,無論是分體編年還是隨詩附文,種種編次方式均統(tǒng)攝于浦氏的“心解”模式里,是“心解”杜詩的一種精心結(jié)撰。下文圍繞《心解》的“心解”路向所展開的討論,將就我們所知適時地對此進行相應的疏通。
三、“心解”之傳統(tǒng)淵源
《心解》開篇《題辭》云:
吾讀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詮釋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攝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悶悶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來,邂逅于無何有之鄉(xiāng),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離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數(shù)存焉于期間。吾還杜以詩,吾還杜之詩以心,吾敢謂信心之非師心與,第懸吾解焉,請自今與天下萬世之心乎杜者潔齊(齋)相見,命曰《讀杜心解》,別為發(fā)凡以系之。?
這是《心解》流傳最廣的一段話,討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乃至接受理論者頗多引及。他們往往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fā),將浦氏的“心解”方式徑歸于“以意逆志”的說詩體系里?,固是。但這恰像我們問某某為哪里人,答曰“中國人”一般,不免是一種訴之太大、過于籠統(tǒng)的解釋,忽略了“以意逆志”法的階段性發(fā)展與個體性表現(xiàn)——體現(xiàn)在浦起龍這里的,是它處處可以尋出老莊、禪學思想的脈絡?。
今人周裕鍇評浦氏《心解·題辭》云:
說得非常玄乎,影響仿佛近乎評點者的口吻,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鐘惺、譚元春有關讀者和作者之間的精神對接的論述。?
豈止鐘惺、譚元春,即杜詩學畛域內(nèi)那些白文本編選者“但存本義,不載群解,又可撤障耳目”?、“不從注腳盤旋,細為諷譯,直尋本旨”?種種之謂,都與浦氏《題辭》所主張的反悟自心、并不外索的闡釋路向差近似之,而萬歷進士龔道立所撰的《杜詩心解》一書?,其內(nèi)容今天雖無從了解,但從命名上說,也算得上是浦起龍《讀杜心解》的前身。周裕鍇先生的評說實際上正是將浦氏“心解”說推源到了以心學、禪學言意觀為背景的明代評點學?。從理論發(fā)展的時間脈絡看,的確如此。但在浦起龍,其根源卻可能還包括甚至主要是此前更早的宋代程朱理學的闡釋態(tài)度。
以清學為宋明理學之反動的梁啟超嘗云:
王學反動,其第一步則返于程朱,自然之數(shù)也。因為幾百年來好談性理之學風,不可猝易,而王學末流之敝,又已為時代心理所厭,矯放縱之敝則尚持守,矯空疏之敝則尊博習,而程朱學派,比較的路數(shù)相近而毛病稍輕。?
這是從內(nèi)在理路上說。而在外緣上,隨著滿清政權的日漸鞏固,一度歸于沉寂的程朱之學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與倡揚,被視為官方之“正學”,再度高踞于廟堂之上?。當此之際,始終盼望“顯擢”、躋身廟堂的浦起龍,其為學之宗程朱是再自然不過的。康熙五十三年,浦氏即在崇祀朱子的紫陽書院讀書?,而為浦氏《釀蜜集》作序的費念慈亦在序中云:
先生之學無所不窺,而一以程朱為歸,故雖泛濫百家,篤信謹守,粹然一出于正,……?
《釀蜜集》為浦氏論學之合集,其中論經(jīng)、史之文最多,如《通鑒綱目》、《十三經(jīng)異同》、《復見天心解》、《老孟論》等等,不一而足,讀后便知浦氏之學確乎像費序所言是“一以程朱為歸”,費氏以“篤信謹守”概之,絕不虛妄。
我們知道,宋儒雖然辟佛甚力,但也頗得力于此,他們對經(jīng)典的解釋往往雜襲老、釋之言,戴震就認為程朱學說是“借階于老、莊、釋氏”?,“借階”一說無疑深切理學與老、釋關系之肯綮。我們不難想見,浦起龍《題辭》中借階老、釋的言述方式其遠源實在于此。浦起龍這一言述方式在其解詩過程中仍時有表現(xiàn),僅舉數(shù)例以明其余:
(一)卷二之一《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深山大澤龍蛇遠”,浦解:
“山澤龍蛇”,雖用《左》語,實暗用《老子》猶龍意,見此等人,定應遠引也。
(二)卷二之三《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浦解:
提出“心”字,是禪定主腦。
(三)卷四之一《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浦解:
詠物至此,乃如十地菩薩,未許聲聞、辟支問徑。
(四)卷四之二《燕子來舟中作》:“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貼水益霑巾。”浦解:
結(jié)聯(lián)方專就燕子寫其若舍若戀之情,而以十一字貼燕,旋以三字打入自心中。不知燕子之為子美歟?子美之為燕歟?吾將叩之漆園。
當然,我們之所以要對浦氏的“心解”作如上一番溯源的努力,除了尋繹“心解”說的理論資源外,更為了掘發(fā)此理論資源背后潛藏著的“道問學”的學術背景,也就是上引梁啟超所謂的“矯空疏之敝”的“尊博習”。清初儒學“道問學”之新動向的興起,治學術史者著論已多,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最可參讀,這里不再贅錄。我們只節(jié)引浦氏本人所作《朱陸異同》一文之大要以見浦氏當日也確曾預于此新動向中。其言曰:
要之,朱、陸不同者,朱務于實,陸涉于虛。故陸……又云“‘涵養(yǎng)’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其意但欲專務虛靜完養(yǎng)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若朱子之學則主敬,涵養(yǎng)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羞并進,此朱子之定說也。虛實不同,議論自不得強合。說者乃謂陸子專務尊德性,而朱子專言道問學。豈知德性不本于問學則德性俱虛,而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宗朱而不及,猶不失拘謹之儒,宗陸而不及,弊將入于禪悟而不覺。?
此番辨析可再次印證浦氏對朱子的尊崇,而由其中關于“尊德性”、“道問學”的意見推之,浦氏為學之走程、朱由“道問學”而入于“尊德性”的路也就無須懷疑了,誠如《釀蜜集》陳開驥序所云,“(先生)于考據(jù)致精微,于誼理宗純正……洵乎考據(jù)誼理兼而具之”。?
回到《心解》上來說。若單就《題辭》看,浦起龍的“心解”還真是“入于禪悟”,但倘若深入到《心解》一書之本文,可知浦氏不但有得于“百氏詮釋之杜”,亦且憑借對大唐安史之亂前后“三十余年的事勢”、“公所至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薊,肅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沒之松、維、邠、靈,藩鎮(zhèn)之河北一帶地形”爛熟于胸的知識優(yōu)勢,使自己對杜詩的理解“思過半矣”(見《發(fā)凡》),《心解》也因此在“考訂年月、印證時事”上得到了四庫館臣的贊許?。顯然,浦氏正是通過考證為其“心解”保駕護航,也就是用“道問學”的精神來從事杜詩之“心解”。
四、《讀杜心解》的由博返約
“道問學”方式下的“心解”其實并不唯“心”,毋寧說它的起點正是在對已被《題辭》“否定”了的“百氏詮釋之杜”的泛觀博覽上。《心解》撰述之初,浦起龍曾多方裒搜諸家注本,《不是集·致丁紉庵》云:
弟進取已灰,長夏病目,兩月未復。近來繙閱杜詩,獨闕長孺箋本,顓力乞之寶笈中,想不靳也。
所謂“長孺箋本”即指朱鶴齡的《杜工部詩集輯注》。由此所引,我們雖然無從獲知浦氏究竟萃集了多少杜詩注本,但“獨闕”云云,數(shù)量恐亦不在少數(shù)。同時,憑借錢謙益、朱鶴齡等前輩杜詩學者的基業(yè),尤其是仇兆鰲《杜詩詳注》對唐宋以來所有杜注與詩話的搜羅匯集,提供給他以極為豐富的資料,浦起龍于杜詩自宋以還的箋疏百家亦可謂是“無所不窺”了。
以見于《心解》箋釋中的歷代杜詩注解評論言,計有80種,茲羅列其名目如次:
王洙、蘇黃門、黃魯直、范元實、葉石林、鮑欽止、趙子櫟、蔡興宗《正異》、薛夢符、趙次公、陸游《入蜀記》、《誠齋詩話》、朱子、樓鑰、魯訔、偽蘇注、吳若、王十朋、洪容齋、吳曾《漫錄》、杜田、蔡絛、郭知達、師古、《詩說雋永》、黃希、黃鶴、蔡夢弼、真德秀、劉克莊、羅大經(jīng)、王應麟、劉辰翁、方回、張綖、《演義》、張璁、周珽、楊慎、單復、王維楨、邵寶、趙滂、趙大綱、郝敬、陸時雍、唐汝詢、鐘惺、譚元春、胡應麟、胡震亨、胡夏客、楊德周、陶開虞、王嗣奭、顧炎武、申涵光、盧世氵隺、潘檉章、潘鴻、劉逴、錢謙益、程嘉燧、朱鶴齡、俞玚、潘耒、顧宸、吳見思、盧元昌、黃生、洪仲、張溍、陳廷敬、張遠、邵長蘅、朱瀚、毛奇齡、吳山民、仇兆鰲、沈德潛
基本涵括了宋以來杜集文本研究的主要成果。經(jīng)過統(tǒng)計可知,《心解》引述如上所列杜詩文獻累計達1650余條(這里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系據(jù)《心解》所引述有具體姓氏或書名者,另有不少通稱“舊注”、“舊解”、“坊本”者未計入),其中引述在百條以上的有四種:黃鶴120條,錢謙益104條,朱鶴齡336條,仇兆鰲434條,引述在數(shù)十條的還有四種:趙次公66條,王嗣奭89條,黃生75條,顧宸49條。《心解》作為非集注本,對比于這個時期的同類杜集如盧元昌《杜詩闡》、黃生《杜詩說》、張遠《杜詩會粹》等,就其涉獵釋杜文獻的豐富廣博而言,毫無疑問是最為突出的。
經(jīng)過上面的考釋,可知“心解”確乎與“百氏詮釋之杜”有著廣泛的關聯(lián),緊接下來,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浦起龍是如何使用這些杜詩詮釋文獻的?
為了具體地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先看一下浦起龍的如下箋釋:《小寒食舟中作》:
小寒食,……首點節(jié),次貼身。三、四,俱承次句寫出。朱瀚謂分承上二,非也。“娟娟蝶”,卻似蒙花。“片片鷗”,卻似蒙水。瀚又云:蝶鷗自在,而云山空望,所以對景生愁,首尾又暗相照應。此解卻得。其曰首尾暗應者,“云白山青”應“佳辰”,“愁看直北”應“隱幾”也。三、四、第七,與沈云卿詩偶相類,固非蹈襲,亦非有意損益也。黃魯直、范元實輩,斤斤辯之。前人詩話,多著相處,勿為所惑。
《登岳陽樓》:
黃生云:寫景如此闊大,自敘如此落寞,詩境闊狹頓異,結(jié)語湊泊極難,轉(zhuǎn)出“戎馬”五字,胸襟氣象,一等相稱。愚按:不闊則狹處不苦,能狹則闊境愈空。然玩三、四,亦已暗逗遼遠漂流之象。趙滂曰:公此詩,同時惟孟浩然足以相敵。孟詩云:“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云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圣明。坐看垂釣者,徒有羨魚情。”愚按:孟詩結(jié)語似遜。
筆者有《〈讀杜心解〉所用杜集文獻來源考實》一文,具體考察浦起龍對歷代杜詩注釋、評解的征引、轉(zhuǎn)述情況。考證表明,浦氏《心解》之成書頗依托于仇注,他所引述有宋以來的杜詩文獻多自仇注轉(zhuǎn)錄而出,即令錢箋、朱注等案頭就有的杜注,浦氏有時也沒有翻檢原書,而直接由仇注錄入。以上隨舉二例所見朱瀚、黃魯直、范元實、黃生、趙滂之說亦無一例外由仇注中出。然則,浦氏所引往往加以裁擇刪節(jié),較仇氏已大為簡略,如《小寒食舟中作》一箋所引朱瀚條,仇氏《詳注》原作:
朱瀚曰:頷聯(lián)分承上二。時逢寒食,故春水盈江。老景蕭條,故看花目暗。須于了無蹊徑處,尋其草蛇灰線之妙。腹聯(lián)興起下二。戲蝶輕鷗,往來自在,而云山萬里空望長安,所以對景而生愁也。首尾又暗相照應,與‘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參看。?
對比之下,浦起龍所引不但更為簡約,還隨其所需地將朱瀚的箋語一分為二。而黃魯直、范元實“斤斤辯之”的原話,浦氏則略去。諸如此類與《杜詩詳注》有著鮮明對比的例子在《心解》中觸眼即是。《杜律啟蒙》的作者邊連寶認為仇氏《杜詩詳注》“所取太博,時或短于抉擇”?,今人蔣寅也批評仇注“對繁富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是以冗濫為代價的”,且往往“不下按斷,不加分析,令人不知注者何取”?。
仇注之失,正是浦起龍《心解》所長。我們從上面所引《小寒食舟中作》、《登岳陽樓》兩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杜詩詮釋文獻的兩種取向,或質(zhì)辯舊說之反者,或采摭舊說之合者,要在借賓定主,在舊說中涵養(yǎng)自己的見解。浦起龍對“宋人之注”、“近世之解”的使用,與其所歸依的朱子有異曲同工之處,朱熹讀書法有云:
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說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
在博參的基礎上進行深思、明辯,進而由博返約,使其會歸于自家的心靈。朱子講這些,原是教人如何把知識學習與心性修養(yǎng)打通,我們以此來說浦起龍的“心解”,未免淺乎用之,但那著實可以說是“心解”得力的地方,誠如他在《致同年王蓼原先生》一札中與王蓼原談讀杜詩時所云:“取舊本互勘,攝意靜思,或當有賞奇析疑之嘆焉!”?浦起龍正是憑借仇注博取繁富,在比勘抉擇中重新熔鑄“宋人之注”、“近世之解”,從而折中去隙,會歸己意。
從歷史的角度看,《心解》的“由博返約”其實是對杜詩詮釋“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世之解”的彌縫與反撥。然而也正是在《心解》的這種“折衷去取”里,已隱然包含了注杜式微的危機。洪業(yè)《杜詩引得·序》在介紹《心解》之后即說道:“此后注杜之風殺矣!”?何以這么說?讓我們借浦起龍談十三經(jīng)注疏之學走向沒落的一段極具啟發(fā)意義的話來對此試作回答,其《十三經(jīng)異同》一文曰:
自宋儒出而為注為傳為章句,其于漢唐之注疏,博取而會其歸,折衷而去其隙,學者便之,而古學亦因以荒矣。……要而論之,古注詳核,各有師承,然多駁而未醇,宋儒刊落眾家之煩蕪,取便學者之誦讀,而學者因其便易遂不復考其源流,由是經(jīng)學日荒,求如漢儒之專門名家者無有也,亦可惜矣。有志之士宜博稽而詳究之,即朱傳所以折衷去取之故亦于是而可考焉。?
“學者便之”則注疏之學日荒,此真可謂是一語破的的解釋。“刊落眾家之煩蕪”、“博取而會其歸,折衷而去其隙”都算得上是《心解》的特點(且不論這種“折衷”是否像梁啟超說的那樣,在“別人看來不過多一重聚訟的公案”),而它的取便學者也是客觀的事實,清代杜詩批點本中以《心解》為底本者,算來就有十余家之多?。事實上,《心解》自己便是取便于仇注的繁富,“遂不復考其源流”,因而頗沿襲仇注之誤的。從這個角度上說,杜注衰殺的根苗,毋寧說在仇氏《詳注》中就已經(jīng)種下了。
(本文為福建省教育廳A類項目,編號為JA10091S,課題名稱為“浦起龍與《讀杜心解》”)
注釋:
①浦起龍之生年,《史通通釋·自敘》已言明,而其卒年則向無確說,嚴文郁《清儒傳略》(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79年)以其卒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不知何據(jù)。筆者閱讀浦氏《釀蜜集》(光緒二十七年孟春工竣板藏靜寄東軒家塾本,下文所引均見此本),卷首有浦氏族侄浦霖所作《宗老山傖公傳》,中曰:“矧公歿之年為壬午”,“壬午”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據(jù)此可知浦起龍卒于1762年無疑。
②本文所引《讀杜心解》內(nèi)容,除特別說明,均據(jù)中華書局1961年王志庚點校本,不再另注。
③⑥⑦⑧??浦起龍《不是集》不分卷,燕京大學圖書館中華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④《釀蜜集》費念慈序曰:“先生在康、雍間以文學教授鄉(xiāng)里。”
⑤見《釀蜜集》。王志庚《讀杜心解·點校說明》、周采泉《杜集書錄》均以浦起龍為“雍正二年進士”,誤。
⑨《不是集·上同年淮揚鹽道吳公》云:“某樸學寡侶,著有《讀杜心解》二十四卷、《古文眉詮》八十卷,前后問世,……近又成《史通通釋》一書……”,另浦起龍有《釀蜜集》、《不是集》,均為浦氏歿后,由其后人編輯刊刻而成。
⑩周有壬輯《梁溪文鈔》卷三十四,民國三年活字印本。
?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
?轉(zhuǎn)引自胡玉縉撰、王欣夫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
???轉(zhuǎn)引自周采泉《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如楊鐘羲《雪橋詩話續(xù)集》曰:“蘇齋(翁方綱號)議其解杜索摘文句,太頭巾酸氣,亦切中其病。”見《清詩紀事·雍正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
?如廖仲安文《杜詩學(下)——杜詩學發(fā)展的幾個時期》,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莫礪鋒《杜甫詩歌講演錄·杜詩的清代注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二者的關系,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第六章“評點論”亦有論及,可參看。中華書局2002年版。
?參看吳宏一《清代文學批評論集》,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8年版。
?????《釀蜜集》,光緒二十七年孟春工竣板藏靜寄東軒家塾本。
?《古文眉詮》完成于乾隆九年,而浦氏于乾隆十年由蘇州府學教授、紫陽書院主講任上去職。
?見《古文眉詮·緣起》。此書今存本尚多,筆者所見為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所藏光緒戊戌年嶺南良產(chǎn)書屋重校刊本。
??洪業(yè)《杜詩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卷首《題辭》獨具意義,中華書局1961年排印本將之闌入《發(fā)凡》中,與雍正乙巳年無錫浦氏靜寄軒原刊本不符,當從原刊本為是。
?如謝思煒《杜詩解釋史概述》,《文學遺產(chǎn)》1991年第3期;劉月新《“出入”說——中國古代的接受理論》,《名作欣賞》1997年第1期;鄧新華《“以意逆志”論——中國傳統(tǒng)文學釋義方式的現(xiàn)代審視》,《北京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關于這一點,也有論者已經(jīng)注意到,將之視為“頓悟式批評”的實例來看。見胡家祥、劉贊愛《藝術批評的性質(zhì)、標準和基本模式——藝術批評學論綱》,《湖北民族學院學報》1998年第5期。
??周裕鍇《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此書清光緒《武進陽湖縣志·藝文志》著錄,《志》中謂此書尚存(見周采泉《杜集書錄》,第706頁)。浦起龍與龔氏同為蘇州人,浦氏極有可能聽說甚至見到此書。此并未有直接可靠的證據(jù),聊備一說而已。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關于程朱理學之為官方青睞,可參看陳居淵《清代樸學與中國文學》第一章的相關論述,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浦起龍《舊游》詩自注云:“書院崇祀朱子”,自序又云:“甲午之夏,龍往赴檄征,讀書其地,凡三越月。”見錢仲聯(lián)《清詩紀事》雍正朝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卷中,中華書局1982年版。
?此文收入余氏《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現(xiàn)代詮釋》一書,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
?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
?見韓成武等點校《杜律啟蒙·凡例》,齊魯書社2005年版。
?蔣寅《〈杜詩詳注〉與古典詩歌注釋學之得失》,《杜甫研究學刊》1995年第二期。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十,中華書局1983年版。
?參見《杜集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