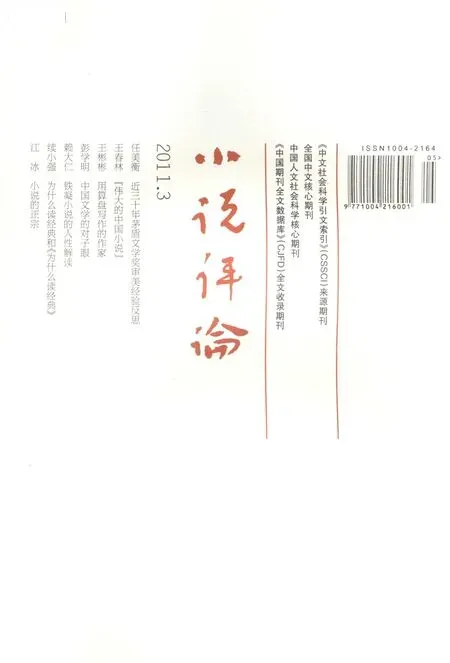為什么讀經典和《為什么讀經典》
續小強
為什么讀經典和《為什么讀經典》
續小強
一個怪異的人,一個制造迷戀的寫手,一個在叛逆中不斷回歸原點的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在他五十八歲的時候,寫了一篇《為什么讀經典》的文章。
“1981年”,中文譯本的末尾如此標注。這,是不是有一點“輕率”呢?盡管重復,時間卻并不是不重要。從語句的猶疑與徘徊不定去探測,那可能是1981年秋日的一個深夜,繁復的秋雨調子,擾亂了一個老年人的夢境,他起來,靠在床頭上,用自己“獨一無二”“復雜精致”的大腦演算了一道近似于數學的題目:經典的定義。
一個后來變得無效的前提
文章不長,讀過之后,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他老了,如此簡單的“數學題”,根本無須如此復雜的“定義”;更何況,他所給出的十四個定義,全然沒有個定義的樣子,近似囈語,模糊、晦暗,甚至潮濕得泛著霉氣。
我想這有可能是他刻意制造的意外,就像他的小說一樣,催眠術屢試不爽,我們便每每被俘:你認為他失敗了,他卻以一個勝利者的姿態恬然睡去。
直到確立了第十一個定義時,他感覺我們對他邏輯漏洞的懷疑必須作出適當的說明了,可他的說明卻是如此的斬釘截鐵:“我相信我不需要為使用‘經典’這個名稱辯解,我這里不按照古老性、風格性或權威性來區分。”語氣多么不容置疑,他有這個資格,當然,這也是他的需要:面對“經典就是經典”的無限反復,他只能描述,哪怕是一種帶有理論色彩的抽象的描述。這是他一個職業小說家的職責。
從始到終,在考慮經典的定義以及思慮如何對定義作出分解和描述的同時,我相信他一直有一個深重的困惑:他在給誰說這樣的話,他的定義對什么樣的讀者是有效的。我為有這樣的發現感到欣喜:在過去很長很長一段時間里,相信如我一樣的很多人,一直以為“經典”是具有普遍性的,對每一個人(大多數人)都應該是有效的。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笑了:其實不然;這實際上還是那句口頭禪“經典就是經典”在作怪。
在文章的最初,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雖然不會自戀到承認自己就是那個“博學的人”,但他還是清晰地指出:它(指他給經典下的第一個定義:經典是那些你經常聽人說“我正在重讀……”而不是“我正在讀……”的書)不適用于年輕人;緊接著,他又作出了特意的強調:“代表反復的‘重’,放在動詞‘讀’之前……”他當然不是對年輕人有“不讀書”的成見,事實上,盡管他開篇即點明“不適用于年輕人”,但后來我們慢慢就會發現,他的主要想法除了和“成年人”一道溫習一下自己多年對“經典”認識外,更多的還是想要給年輕人布布道的。只是這個“年輕人”前面需要有定語的修飾。按他的說法,這個修飾,應該是讀過一些而不是讀過一點書(經典)的年輕人。
于是,所有的十四個對于經典的定義,首先不僅是從“讀”而且是從“重讀”開始的。讀,準確一點講,重讀,是經典成立的前提;沒有這兩個必要的帶有勞作色彩的動作,經典有如僵尸并不存在,談論經典的定義以及其他種種,便無任何一丁點的意義,而且,顯得無知而荒唐可笑的。
寫這篇文章時,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已經五十八歲了,他平和了許多,已不像早年那么氣勢逼人了,他慈眉善目、循循善誘,他或許注意到了如此“絕對”的前提會傷害到他人,至少會影響到有更多的人進入到可談論經典的行列,于是他才說了這樣的話:“一個人在完全成年時首次讀一部偉大作品(注意:他沒有用“經典”一詞),是一種極大的樂趣,這種樂趣跟青少年時代非常不同。”讀到這句話,我就為自己仍沒有讀完《紅樓夢》而心稍安慰了。“而在成熟的年齡,一個人會(或者說應該欣賞)更多的細節、層次和含義”,這樣的話,對于一直讀經典的、親愛的你們,我想是一個莫大的鼓勵。
經驗的特殊效力
在“重復”、“重讀”的前提下,他以對“經典作品”的描述,初步給出了一個關于“經典”的大概的輪廓:“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對讀過并喜愛它們的人構成一種寶貴的經驗;但是對那些保留這個機會,等到享受它們的最佳狀態來臨時才閱讀它們的人,它們也仍然是一種豐富的經驗。”
是的,這位有點絮叨的老先生,仍是那么的寬厚,總要給人以必要的情面。對第一種情況,他有多少信心不得而知,他的重點,或者說,玄機之處,仍在于后一句。這有點像望梅止渴的故事,它多少帶有那么一點蠱惑人心的味道。在現實的文化生活內,拋除機械的強硬的灌輸式的經典教育,其實,我們最容易習慣于日常的荒蕪流轉,而停滯于閱讀和無理由的虛無等待。所以,對他“保留這個機會”的寬容或期許,我們應該有一種必要的自我暗示和警惕。
他當然有過青少年時期的閱讀經歷,要不然,習慣于準確描摹的他,不會就簡單地認定“我們年輕時所讀的東西,往往價值不大”。他認為“價值不大”的原因,不在于經典作品,而在于“我們沒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閱讀技能,或因為我們缺乏人生經驗。”
再往后面,越說越好,但在節奏上講,似乎和前面有些矛盾。他一方面確證無疑地指出青少年時期閱讀的不牢靠,另一方面,卻因了自己閱讀生涯和寫作生涯的經驗,用一種近乎和青年人商量的語氣說:“這種青少年時期的閱讀,可能(也許同時)具有形成性格的實際作用,原因是它賦予我們未來的經驗一種形式或形狀,為這些經驗提供模式,提供處理這些經驗的手段,比較的措辭,把這些經驗加以歸類的方法、價值的衡量標準,美的范式。”
如果有人想扮演經典閱讀專家或教父一類的角色,我想這一段話,應該成為他隨時隨地脫口而出的經典語錄。回想我們自身的閱讀生活,這真是太準確不過的,經典之于生活經驗的表述。
這段話中我特別注意的,是“形成性格的實際作用”。即便我們可以承認黃燦然先生翻譯的精準,但我更樂意于將“性格”作“人格”的偷換。我還沒有去找必要的資料去印證,這位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在專注于小說的虛擬世界之外,是否還有對現實社會公民政治的熱情。如此的偷換詞語,或者即便我們沒有這個略顯多余的想法,單純地把這句話拿出來、放大,還是有足夠驚人的效果。在歷史書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經典,在其成為經典的路途上,是經過無數的大坎坷的,這其中,最為“顯赫”的行徑,便是查禁、篡改,乃至文字獄,乃至焚書坑儒。它同時,似乎半遮半掩地告訴我們,什么樣的經典閱讀教育,便有可能造就什么樣的公民社會。
也許,這位老先生不屑于如此的發揮,他經常性地表現出一種輕逸的姿態,他似乎并沒有越軌的打算,回到經典的定義,他再次強調:“在我們成熟時期重讀這本書,我們就會重現那些已構成我們內部機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盡管我們已回憶不起它們從哪里來。”說到這,他覺得還不夠“小說”,于是有了下面這句讓人無限回味的話:“這種作品有一種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卻,卻把種子留在了我們身上。”
順著經驗之繩的引導,他提出第三個——第六個定義。這四個定義,都是對“經驗”的進一步發揮,有一點同義反復,但指涉的重點卻又不盡相同:第三個定義講經典作品的“印記”性、“隱藏”性;第四個定義說“重讀都像初讀”;第五個定義更進一步,說“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第六個定義則有些過高地拔舉了“經驗”的作用:對于讀者,經典作品,“永不會耗盡”。
到此,我想這應該是這篇《為什么讀經典》的第二部分。在開端左顧右盼地談論“讀”與“重讀”的重要性之后,他深入了經典的內部,轉悠了好半天,他實際上一直想說出的是:經典即經驗;我們的經驗即是經典的一部分延伸。所以,他才會說:“我們用動詞‘讀’或動詞‘重讀’也不真的那么重要。”毫無疑問,在一開始受到必須“讀”或“重讀”的驚嚇之后,我們又一次釋然了。或許,還會有人要大做驚恐狀,呵,不必讀,我即經典吶。
對批評話語的無奈
老實說,從閱讀的一開始,我對這位伊塔洛·卡爾維諾老先生,總有特別的擔心。這道數學題,大概是最不嚴謹的一道數學題,一個年邁的老者,何必糾纏于此,為一個經典的定義而失眠傷神、耗費腦細胞。這與寫作一篇小說的奇妙、歡快之旅,有太大的不同。總的來說,第二部分,雖然還是有一點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小說家氣質,但總歸解得還算順暢,他與我們的想象式的對話,也較為和氣,以“經驗”作結,大家都不至于很難堪。
第七個定義——第八個定義屬于一類,據他說,這是第五個定義所隱含的“更復雜的表述”。這確實有一點危言聳聽了,但我們已經習慣這位垂垂老矣者在這篇文章中的慣用語氣。
“更復雜的表述”之下,多少是有些對經典作品傳播與流轉的無奈。
第七個定義: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著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后拖著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只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跡。不愧是經典的小說家,如果把“經典作品”換做一個古老的名字,就不是有點而是十足的像一部短篇小說的開頭了。對此定義的描述,同樣,他抖出了一個小說家的經典武器庫,以荷馬、卡夫卡、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閱讀為例,他試圖讓我們相信這句話的無比正確性:我不能不懷疑這些意味究竟是隱含于原著文本中,還是后來逐漸增添、變形或擴充的。他在思索,或者說他告訴我們我們也應該思考:這些書中的人物是如何一路轉世投胎,一直到我們這個時代。
他再一次陷入彷徨,取消“讀”或“重讀”的前提還是有一點那么不太合適:讀一部經典作品也一定會令我們感到意外;我們還是應該“盡量避免二手書目、評論和其他解釋”;“中學和大學都應該加強這樣一個理念,即任何一本討論另一本的書,所說的都永遠比不上被討論的書”。所以第八個定義,他準確地說,是“下結論”: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不斷在它周圍制造批評話語的塵云,卻也總是把那些微粒抖掉。這話說得很奇怪,“經典作品”果真能夠自己抖掉那些批評的微粒嗎?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不值得,他認為重要的是,我們怎么也沒有料到“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是那個經典文本首先說出來的”。但是我們還要問,我們怎么就能知道我們所知道的那個東西就一定是那個經典文本首先說出來的呢?他說這需要“發現”,而且他說“這種發現同時也是非常令人滿足的意外”。那么他所說的“發現”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可以肯定的,一定不是經典作品的“教導”,而是第一部分強調的“讀”、“重讀”,以及第二部分四個定義強調的“經驗”。
于是,他帶著我們又一次回到了問題的原點:面對經典作品“廣泛存在著的價值逆轉”,煙幕不會自行散去,我們只得相信我們自己的判斷。于是,剛剛有一個不必讀的正當借口,我們卻又一次垂頭喪氣了。
確立自己
曾經有一個人和我說,他有大把大把的時間,他也想去閱讀,卻不知道該讀什么樣的書才好。我的回答是,問你爺爺或父親,但不要問我。這句話有點插科打諢,實際上它潛在的意思是:從老書讀起,或者說,讀老人們寫的書。
我們總莫名的擔心老人們的啰嗦、同義反復,乃至時空倏忽跨越般的囈語,甚至某種刻意的遮蔽——這是有根據的,對此,我也害怕。但我唯一不害怕的,是這些老人出自老人本能的對未來的善良的期許,或者毫無顧忌的帶有矯正意味的教誨。
《為什么讀經典》的第四部分,則由第九、第十、第十一三個定義組成。
第十個定義,說“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個名稱,它用于形容任何一本表現整個宇宙的書,一本與古代護身符不相上下的書。”說得很神奇,似乎在為“經典”作出蓋棺定論,而實際上,如此馬拉美夢想已久的那種書,只是一個理想的存在,說它虛幻也不為過。他沒有在此基礎上展開,那才是小說需要做的事情。所以,這個定義,就只能作為陪襯或反面的論據存在。
這一部分,處處是這位老先生無限善意的教誨。只有他認為經典作品的最終價值是確立一個人的自己時,他才會這么強調經典和個人的關系。
鑒于老先生如此懇切,我想我們應該好好考慮一下他所提供的建議:
必要的姿態:“出于職責或敬意讀經典作品是沒用的,我們只應僅僅因為喜愛而讀它們。”
需要堅持:“只有在非強制的閱讀史中,你才會碰到將成為‘你的’書的書。”
厭惡感:“但是一部經典作品也同樣可以建立一種不是認同而是反對或對立的強有力關系”,以盧梭為例,他抗拒、批評、與其辯論,甚至有不去讀他的想法,但最終,他坦率地承認:“我不能不把他看成我的作者之一。”
可以欣慰的意義:“一部經典作品的特別之處,也許僅僅是我們從一部在文化延續性中有自己的位置的、不管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作品那里所感受到的某種共鳴。”
當然,還有一句看似與主題無關卻至為重要的:“只有那些你在學校教育之后或之外選擇的東西才有價值。”
經典和時代
最后三個定義,事關經典作品和時代的關系。
首先,不能擱置的關鍵問題是,是讀經典作品,還是讀那些不是經典的如洪水般的印刷品。
讀到這里時,我有種看戲的快感。每一個人,對于自己所面對的置身其中的時代,總是有種迷離的錯位感。換一句話說,談論過去的歷史是容易的,而面對當下,我們常常無語,找不到恰切的詞匯、語句去描述它。我們曾自以為是地找到了,實際卻是云里霧里,走不出來,越說越困惑,甚至,越說越疼,這真有點像拿著鋒利的刀子,割自己的肉。
伊塔洛·卡爾維諾老先生對此也是避重就輕,他說:“當代世界也許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遠是一個脈絡,我們必須置身其中,才能夠顧后或瞻前。”前半句,大概是沒錯的,可是后半句,卻很別扭,難道我們必須親自去體驗一下腐敗官員的生活,我們才能夠寫小說、才能夠評論如此這類的小說嗎?我可能有一點過分的發揮,他所說的“置身其中”,在他看來,或許只是對“經典作品”才有效的。如果這么說,“置身其中”,便又是“讀”或“重讀”的同義詞了。不管如何,我非常認同老先生如此的判斷:
“閱讀經典作品,你就得確定自己是從哪一個‘位置’閱讀的,否則無論是讀者或文本都會很容易漂進無始無終的迷霧里。因此,我們可以說,從閱讀經典中獲取最大益處的人,往往是那種善于交替閱讀經典和大量標準化的當代材料的人。”
必須有比較,才可有“位置”感的存在。這需要勇氣和付出:我們是否能夠擺脫學術考評機制的壓力?我們是否能夠消除作為一個職業寫手的生存壓力與欲望?我們是否能夠回避作為一個讀物生產鏈條中一環的存在?
而“獲取最大益處的人”,一定是最辛勞的人。這樣的辛勞一定就有必要和價值?以長篇小說為例,據說一年有近三千部長篇產生,我們的批評家如何選定自己的“位置”,如何走出這“無始無終的迷霧”?
老先生開起了玩笑話,他認為“把現在當做我們窗外的噪音來聽”大概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案了,我想他還是太過自信了。一個老年人,從生理和精神上,對于外界的聲音當然是不敏感的,但對于他一再放不下的青年人(甚至中年人),如此的假設,未免一廂情愿:時代的喧囂,絕大多數人是無法抵抗也抵抗不了的。
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一個執迷不悟的人,到最后了,還是那么可愛的堅持,叫人不得不給予十分的崇敬:
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它把現在的噪音調成一種背景輕音,而這種背景輕音對經典作品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第十三個定義);一部經典作品是這樣一部作品,哪怕與它格格不入的現在占統治地位,它也堅持至少成為一種背景噪音(第十四個定義)。
寫到最后,伊塔洛·卡爾維諾先生對自己的解答充滿了深深的懷疑,以致他一再表明自己要必要重寫這篇文章。他終歸沒有這么做。他甚至都沒得及把《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寫完,1985年,他飄然而逝。
文章的最后,他引了一個不太令人提得起興趣的段子:
當毒藥在準備中的時候,蘇格拉底正在用長笛練習一首曲子。這有什么用呢?有人問他。“至少我死之前可以學習這首曲子。”
這能說明什么呢,有多少人愿意步蘇格拉底的后塵?就像你在引出這個段子之前所說的:讀經典總比不讀好。盡管,這是“唯一可以列舉出來討他們歡心的理由”,但誰能夠做到呢。
續小強 《名作欣賞》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