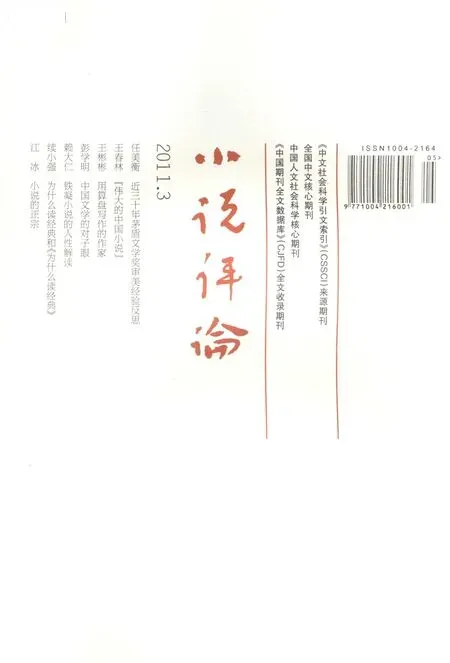何英的鋒芒與視野
雷達
何英的鋒芒與視野
雷達
新疆年輕的女批評家何英,其尖銳鮮明的批評姿態,冷靜出色的判斷力,幽默潑辣的話語方式,連同支撐著她的扎實的理論根柢,以及善于學習,默默耕耘的勤奮品質,使她的出現被看作一個奇跡,一簇閃光。
的確,除了偶爾進京到魯院學習過一回,何英很少拋頭露面,一直堅守在新疆。熟悉她的人覺得,作為一個出生在新疆的異鄉人,一個由兵團子弟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她過著普普通通的日子,以相夫教子為樂,安靜,踏實,沒有怎么顯出“學者相”和爭辯欲。她的樣子更像是一位勞動婦女。可是,你真要把她當作一個北疆的農婦,那就大錯特錯了,她早就在磨“自己的劍”,貌似質樸,內藏刀鋒。她一旦寫起文章來,能熟練地運用整套的概念工具和理論新語,她可以對全國一些重大文學問題和重要現象作出令人驚訝的評判,她尤善于感受和渲染文壇變幻莫測的氣象,對一些風頭正健,躊躇滿志的作家,她發出的質疑往往是直指根本的,絕非扮酷。她的聲音是內行的,富于學理的,打中要害的,卻又布滿了芒剌。人們會奇怪,她是在什么時候掌握了那么豐富的信息,暗藏了那么多絕妙的、尖利的、有趣的想法。
我以為,在今天的文壇上,出現何英這樣人物的機率仍然是比較小的:現在固然信息發達多了,但地域——不但是空間上的,卻也是心理上的間隔,還是制造著困難,何況是遙遠的新疆;現在固然早已是男女平權的社會了,可是,作為一個女性,要在邊地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哲學研究一類行當,又不在高校,要堅持下來,委實不容易——既要跨入“全國的”言說競技場,又要逾越“女性的”身份和心理障礙。
然而,何英并不是以一種即興式的、印象式的寫法嶄露頭角,也不是以一種小聰慧偶露崢嶸。她的從事文學批評,理論準備相對充分,充分得出人意外。在《理論的過剩與敘事的消融》、《當代文學的十個詞組》等綜合論述當代文學發展的批評文章中,她能站在當代學術的前沿,以一個處于文化研究中心位置者的自信和從容談問題。其實,這些文章都寫于新疆。這些文章在《小說評論》《文學自由談》發表后立即引起反響,前者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后者被多家網站、雜志轉發。她的另一論文《王安憶與阿加莎克里斯蒂》則得到了苛刻的上海批評家們的稱賞。《文學自由談》一度是她的主要園地,她在那里臧否人物作品,時有鋒銳之見。在那里,她是繼李美皆之后,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女批評家。
批評家之間在深度與廣度上,差異其實是很大的,我們并不缺少就事論事的評判者,缺的是能發人之所未發,能打通現當代或中與外,能抓住問題的實質,視野比較廣闊的人。對于何英,我最欣賞的,首先還是她對時代與文學之關系的某些深度思考。她能清晰地提出一些比較新穎的看法,有些看得還相當準。比如,她剖析了所謂“理論過剩”現象。她說,我們的理論果真到了過剩的境地了嗎,事實是,現代中國還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理論,過剩只不過是引進、運用西方理論的過剩。當代文學在理論的引進和運用上的過剩實際上反映出自身理論的饑渴與貧乏。引進的理論正在脫離本土經驗而顯現出意義踏空的理論游戲化。這是當代中國理論的特征之一。
在她看來,當理論與作品不能相互融會,相互激發時,理論往往呈現出意義的虛無。她發現,現在理論本身已成為某些理論家的象征資本,這個象征包含著一些確定的頭銜、某所著名的大學、某領域的學科帶頭人等等,這些資本如期貨一樣在市場里以貨幣的形式流通,某種程度上說,現今最活躍的某些理論家正在充分利用自己的象征資本,貌似科學嚴謹地制造出一批批理論商品,而這些商品也正顯出過剩、浮躁甚至狂躁的癥狀來。
這些話比較尖刻,卻并非無理,于是,她看到了某些莊嚴事象背后的可笑之處,有如戳穿皇帝的新衣。她并不反對“現代性”這個術語,但卻指出:“現代性”這個詞兒,剛出來的時候滿天飛舞,好像什么都可以套上現代性,魯迅自然是現代性的了,那么沈從文就是反現代性,張愛玲則可以是被壓抑的現代性那一路,總之學界的論文一派現代性,后來出了幾位“后主派”,一意高揚后現代,宣稱現代性的終結,現代性也便有退出歷史舞臺的意思。沒想到哈貝馬斯一句:現代性遠遠還沒有終結,又被哈貝馬斯專家們發掘出來大大地發揚了一番,于是現代性又復辟了。現在關于這個詞的言說也仍然一派混亂各說各的,連大學中文系文藝學教授都難以說清到底什么是現代性,考博要是出了這個題目,考生只有詛咒出題的人了。
再比如,她對以“后”的集體稱謂方式來劃分作家代際的命名方式的批評,也是尖銳的。在她看來,這種代際劃分法一下子深入人心且大有正式演變成文學史言說方式的架式,仔細想想十分滑稽。文學畢竟還是一個靠作品說話的領域;這種集體化的分期也不會是作家所愿,哪個作家愿意跟別人放在一個集團里來討論評價,抹殺忽視創作個性不說,誰又會和誰的寫作真的那么類似?因而她判斷,這種稱謂法必將是速朽的。她不無調侃地說,自“80后”新聞化、娛樂化之后,這一稱謂移用漫延到各個領域,成為可以任意使用的媒體符號之一。70后作家在這樣影響的焦慮之下,還要面對80后市場媒體雙受寵的新局面,他們要在哪里找到自己?不由人不替他們嘆惋:前面的輝煌讓先鋒占盡,后面的風頭讓80后出光,兩大光團之間的黯淡卻屬于他們。然而,真實情況果真如此嗎?她問的好!當我看到今天的文壇上,人們仍然以“后”為言說的重要依據,討論得十分莊嚴,甚至已經溢出了代際劃分所本有的那么一點點認識價值時,我并不認為何英顯得多么孤單無助,相反,我覺得她有可能是一個真正的清醒者。
何英對萬花筒般急遽變化的當代文壇現狀的描繪,是富有幽默感的,讀來常使人忍俊不禁。也許她有一種天生的善于捕捉、描述和概括的才能。她自創的“十個詞組”,什么“空虛時代”、“突然沉默”、“道德正確”、“追新至死”啦等等,俏皮尖刻,嬉笑怒罵,往往能說到點子上。談到文壇風景,她的出語總是清新。比如,“我們在學人家的時候,把自己丟得太干凈。血液里靈魂里的東西都漸漸忘了,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我們就成功地將自己蛻變異化成一種亞西方文化的產物,其間的幾次斷裂都堪稱前無古人,每斷裂一次,我們新變一次,也丟掉一次。”。又如,“一切可資利用的都在被轉化為商品,作為商品的文學不再能擺出高高在上的貴族派頭,大家最終的去向都是市場;而日益邊緣化的文學在這個浮躁甚至狂躁的時代也早已失去耐心,短、頻、快的出書策略既是作家的主觀選擇,也是讀者喜新厭舊的接受條件使然。這是一個讀者主導口味的時代,讀者有時候被出版商的炒作忽悠,被眾多的冒牌排行榜欺騙”。此類話頗為精彩,與我的觀察不謀而合。我在機場、火車站,鬧市等人口流動最大的地方的書店里,常看到正被碼成垛兒大肆推銷的圖書,許多是并無道理可言的,卻占住了高地,人們就只好買他的書。孟子里的“壟斷”一詞就是這個意思。總之,這些地方的進貨渠道完全被人壟斷了,他給你吃什么,你就得吃什么。這些人實際上左右著今天大眾的讀書趣味。
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人情社會,面子文化、人情文化無所不在,即使最桀傲的人,也沒法抵抗它的束縛,有的人正在痛斥別人講人情,可一陷入具體情境,他同樣擺不脫人情的控制,形成五十步笑百步的尷尬。何英似乎找到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空間,一個隔離層,使她很少顧及批評對象,能發出相對自由的、銳利的聲音。作為批評家,何英有自己堅守的衡文尺度,而這尺度是變動不居的,具有現實感的,有活力的。例如,她很強調如何確立小說敘述的“信”,一個“信”字是她最看重的,但也并非事實的真實之謂。她說,那些學來的現代、后現代敘事,學得再好,短期內也不可能轉化生成為純粹中國的敘事。它們沒有根基,即使生出一些根須,也不牢實不壯大,這也是為什么先鋒文學演變成了一場小說的語言革命,而實質上的革命內容卻被忘記或丟棄了,后面沒有自然附著上精神與靈魂的語言游戲自然難以真正打動人心。所以她認為,到《生死疲勞》為止,我們看到的莫言小說,不論他怎么動用中國元素玩地道的中國故事,實際上還是一種西方小說框架里的敘事結構和形態。總之,她對莫言,賈平凹,王安憶,蘇童,閆連科,殘雪等人的批評,各各不同,卻也不無參考價值。
密切關注新疆當代文學的發展與變化,及時給予總體性評價與總結,并能客觀解析幾個典型作家,是何英近年來寫作勞績的一個重要方面。她對趙光鳴的抒情性的辨析,對董立勃的悲情敘述和簡約風格,劉亮程的新疆時空觀,對新秀李娟的散文,都有切實的解析,但對他們各自的問題卻毫不容情,態度是冷靜而客觀的,沒有發生對外酷評,對內諛評的自我分裂。她在《當代新疆小說的敘事困境》中的一段話,深得我心,不妨一引:“新疆的當下與全國一樣,現實生活前所未有地復雜多樣,既有土得掉渣的民粹的內容,也有洋得跟內地沿海無甚區別的全球化,還有不洋不土的縣城生活,有既傳統又不乏現代的牧區生活、還有全國惟一的兵團農墾生活……。面對這些現實生活,作家已不可能躲在家里想像編造一些符合內地人心理的新疆、或原始荒蠻的與現實脫節的新疆,如何表達出現時態的真實、而不是夸張的傳奇,是新疆新一代作家努力要上的臺階。在邊地傳奇、荒蠻落后的詠嘆調或牧歌式作品的絕對數量中,是否也應該有大量城市題材或其它類型小說的出現,追求小說種類的多樣化的同時,提升純文學、嚴肅文學的形式品質。”
邊地新疆出現了何英這樣有生氣、銳氣、才氣的青年女批評家是令人高興的。任何人都只能是自己塑造自己,誰都難以越俎代皰,要求她以后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何況在今天,做一個批評家是很難的。從這部書稿來看,何英的評論實踐涉及面較廣,既有宏觀批評,也有個案細讀,既有建構性的解讀,也有解構型的批評,對當代女作家研究和新疆文學研究似乎占去了更多的篇幅,但她又一度沉迷于《紅樓夢》人物論的寫作。我看,不管今后她的興趣在哪里,只要像她自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理論家應該是有膽識的,批判精神應該是他的第一性。這是一個理論家本應持有的最基本的專業道德。倘能一直堅持下去,可以無憾矣。
雷達 中國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