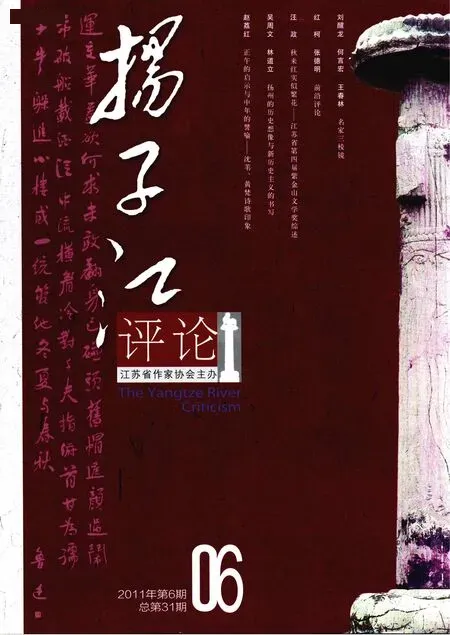論新世紀小說“西藏敘事”的幾個問題
雷 鳴
“西藏”①遠離中原大地與中心都市地帶,地理上屬于邊遠之地,但文學上卻成為了“要塞中心”。在當代文學的不同時段,“西藏題材”熱總是一波接續一波,從未表現出衰萎之趨。可以說,西藏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想象和詩性建構空間,宛若磁石與鐵,持久地吸引著漢、藏族作家或其他民族作家的想象和思考,不斷地激起他們書寫的欲望。就以新世紀以來的小說為例,西藏敘事是集約式的“井噴”,如馬麗華的《如意高地》,范穩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憫大地》《大地雅歌》),阿來的《空山》、《格薩爾王》,寧肯的《天·藏》,楊志軍的《藏獒》三部曲、《伏藏》、《敲響人頭鼓》,何馬的《藏地密碼》,安妮寶貝的《蓮花》,嚴歌苓的小說《愛犬顆勒》,曾哲的《美麗日斑》,喬薩的《雪域情殤》,黨益民的《一路格桑花》,七堇年的長篇小說《大地之燈》……綜觀這些文本,盡管有些小說已臻很高的藝術水準,但它們的西藏敘事呈現出幾個問題,需要引起我們的注意。
一、奇觀化依賴:日常生活譜系的遮蔽
西藏有著煢煢孑立的地理位置,雪域高原的旖旎風光,神秘蠻荒的宗教民俗,相對于中原與沿海地區而言,其灼人的魅力直接表現為她所流溢出來獨有的“異域情調”(Exoticsim)。法國詩人謝閣蘭認為,異域情調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或庸俗的觀察家們看到的萬花筒式的景象,而是一個強大的個體在面對客體時感受到的距離,和體驗到的新鮮生動的沖擊。它是在觀察主體清楚地認識到這種不可磨滅的文化差異的同時,還能體驗這種差異。②正是因為異域情調體現的是對文化差異的關注,具有神秘色彩的西藏便成為了一個巨大的文化“場”,吸引了許多人在描述西藏時,往往依托各自不同的源出文化,去恣肆鋪陳其中的差異因素,從而向描述的接受者提供有效的異域暗示。正是基于此,很多作家“西藏書寫”的挖掘取向與讀者的閱讀期待,差不多都框定在一個雙方默契的定勢和共識之中了——對西藏進行奇觀化展示,專注于炫耀“異域風情”。于是飛揚飄動的經幡,虔誠地匍匐前行的朝圣者,哈達、酥油茶、糌粑團、轉經輪、唐卡、天葬、藏獒,似乎是西藏的全部。歷史的民俗典故,奇特的自然風光,永遠是被津津樂道和描述的景觀。西藏儼然成了沒有人間煙火氣,唯有宗教天籟氤氳的神秘圣地。這種西藏書寫的奇觀化,當年的先鋒作家馬原、扎西達娃等是先驅。正如學者陳曉明所說的那樣:馬原“一直是運用了大量的上等的填充物填補他的‘敘述圈套’,諸如天葬、狩獵、偷情、亂倫、麻風、神秘和虛無等等”③。確然,馬原借助敘述圈套的迷宮,將西藏的諸多表征符號與奇聞異事,嫁接在一起,將西藏的奇觀化發揮得淋漓盡致。
新世紀小說的西藏書寫,依然接過了“奇觀化”西藏這根接力棒。雖然大多數小說不再設置敘述圈套,但卻是穿新鞋走老路,神秘、魔幻仍然是這些作品的最大賣點,對西藏的書寫還是以“奇觀化”作為小說成功的命門。他們要么以史詩情結,記敘西藏歷史風云人物的異類傳奇;要么以宗教情緒,把西藏獨特地域文化的神秘,演繹到極致。文本中唯獨沒有當下西藏的日常生活狀態,沒有真實的充滿血肉和肌理的西藏城市和鄉土,沒有普通藏族老百姓的喜怒哀樂,很少去挖掘新世紀的西藏人在社會轉型期的豐富的內心世界與精神變遷,很少去呈現西藏當代社會前行與嬗變的蛩蛩足音。總而言之,它們所呈現的西藏匱缺時代的面容和表情,一如既往地披著神秘、玄奧的外衣,騰云駕霧,高居仙境,而非一個實實在在、切切可觸的真實西藏。
就以好評如潮的范穩的作品為例,《水乳大地》被譽為“中國的《百年孤獨》”④,這部小說以飛騰的想象力、神奇詭異的文字,寫出了滇藏交界的一百多年的歷史變遷,重構了一種本土文化的絢麗與神奇。但是我們發現,作者那樣一種無法完全融入于表現對象之中的文化獵奇目光的存在還是相當明顯的。作品主要的篇幅和重要關節還是描繪了藏地“奇觀化”的生活,其中有著太多的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魔幻和空靈的場景,比如死而復生的凱瑟琳,騎著羊皮鼓飛行的敦根桑布喇嘛,滾動的有知覺的頭顱,手接響雷的人,顏色變幻的鹽田等。這里,我不能不說,寫作者在體現一定精神厚度的同時,也在倚靠自己作為文化學者掌握史籍的稀罕與神秘而炫奇斗艷,倚靠宗教生活的怪異場景而取悅讀者。在將西藏“魔幻化”、“奇觀化”的同時,也遮蔽了西藏一百多年歷史變遷中的日常生活本來面目。他的另一部小說《悲憫大地》描寫的生活則更顯單向度,只是專注對藏族生活一個維度,亦即宗教生活的描述,正如該書封面所寫的一樣,“這部作品主要講述的是一個藏人(阿拉西)的成佛史。”小說塑造了一個義無反顧的朝圣求佛的佛界英雄形象。阿拉西只有出家做喇嘛,以磕長頭的方式去拉薩朝圣,求得“佛、法、僧”這“佛三寶”,才能斬斷家族仇恨紛爭的種子和輪回,所以小說重點就講述了在漫長的轉經朝佛路上,阿拉西歷經艱辛和災難,終成正果的故事。文本寫了阿拉西大量不同凡人的奇異故事,如剛生出時的哭喊聲像寺廟里那些喇嘛們的念經聲,能聽懂動物的語言等等,同時作品還不時穿插斗法斗術的宗教奇觀。小說依然未能擺脫迎合“他者”的好奇心與窺視癖之窠臼。在“藏地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大地雅歌》中,作者希望“寫信仰對一場凄美愛情的拯救,以及信仰對人生命運的改變,還想謳歌愛情的守望與堅韌”。然而作為一部描寫藏地文化的作品,《大地雅歌》通篇都沒能向我們呈示出那種源于藏地本身的鮮活淋漓的異質感和綿密感,依舊憑借對藏地獨有修辭習慣的挪用,人為構造出一個符號化的藏地情境來置放故事的發生。作者敘述的扎西嘉措(史蒂文)、央金瑪(瑪麗亞)與格桑多吉(奧古斯丁)三人間看似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其背后并無明顯的藏地文化背景或獨特信仰予以支撐,如果我們把故事發生的場景做一個調換,這場纏綿悱惻、風花雪月的愛情劇似乎在世界各地皆可上演。
還有楊志軍的《藏獒》三部曲,我以為,其實就是一部藏地“靈獸”的傳奇,作者將動物的雄性、神性高揚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筆下的藏獒,可以說是“欲狀其智而近妖”。與藏獒勾連的西藏文化的神秘性悉數展露,而在這塊土地上人的生活,僅僅作為“藏獒大俠”行走江湖的舞臺布景。盡管有很多論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寓言,即便如此,這種文化寓言,也是通過奇觀化的景觀完成的,因為“藏獒”在許多人眼里,已然成為了西藏神秘光環的一道弧光和套語符號。《藏獒》三部曲之后的《伏藏》將西藏奇觀化,似乎又“更上一層樓”,伏藏、掘藏、倉央嘉措情歌、七度母之門、隱身人血咒殿堂、光透文字……所有你能想到或未想到的西藏神秘符號,都能在他這本書中看到。再加上懸念重巒疊嶂的非常《達·芬奇密碼》的故事套路——伏藏與掘藏、逃亡與追殺、歷史與現實的回溯與呼應,宗教歷史中的黑暗與血腥、倉央嘉措伏藏內容的懸而未知……懸念層層推進,奇觀化效果也愈益疊加。何馬的《藏地密碼》,120萬字的超長篇幅,依托的仍然是具有神秘感的西藏文化與西藏的地理。其神秘配方,無不外乎人們認知西藏的習慣性三味藥:藏傳佛教的歷史與傳說;藏獒的知識與傳說;青藏地理及探險。小說的標題冠有“密碼”二字,密碼本身就是難解的、神秘的,明眼人一眼可以看出,除了搭《達·芬奇密碼》的“順風車”營銷策略外,還清晰地傳達出了增強西藏文化的神秘之感的意圖。可以說,何馬“奇觀化”西藏也是司馬昭之心。
有人會說,藏地本身富含著諸多的神秘文化,這本身就是“奇觀”,就是西藏的本來面目,如果不表現這些神秘奇觀,與寫其他地方的題材又有何異?我要回答的是,如果總是以某種單一形態和單一語義的夸張化具象,去傳達或建構西藏的一種基本的、原始的、第一和最終的形象,是一種對文化和精神的驚人“省略”,是片面而膚淺的。海德格爾說得好:“自由空閑的好奇操勞于看,卻不是為了領會所見的東西,也就是說,不是為了進入一種向著所見之事的存在,而僅止為了看。它貪新騖奇,僅止為了從一新奇重新跳到另一新奇上去。這種看之操心不是為了把捉,不是為了有所知地在真相中存在,而只是為了放縱自己于世界。所以好奇的特征恰恰是不逗留于切近的事物。所以,好奇也不尋求閑暇以便有所逗留考察,而是通過不斷翻新的東西、通過照面者的變異尋求著不安和激動。”⑤由此,我覺得,一些西藏書寫的小說,以一種夸大其詞甚至無中生有的方式,去濃墨重彩渲染西藏神秘的一個側面,而侵吞和遮蔽西藏的其他維度,實際上就是以海德格爾的“閑言”方式制造事端,進而吸引大眾的獵奇心理。
一切文化的深層支撐無不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人類精神的原生態,具有本原意義,正如盧卡奇所認為的那樣,“我們對存在的追問必須從日常生活出發,如果不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最簡單的事實當中去尋找對社會存在進行本體論考察的第一出發點,那就不可能進行這樣的考察。”⑥因此,要想獲得對西藏全整而切實的認識,我們必須經過對西藏日常生活的描繪和分析,從日常生活這條長河中推導出西藏文化的特殊范疇和結構,唯其如此,我們對西藏的認知,才能是一個真實的西藏,一個生活的西藏。尼瑪潘多的《紫青稞》則給我們以耳目一新的正面啟迪,這部25萬字的作品就摒棄了“奇觀化”西藏的時髦寫法,作者以地處喜馬拉雅山脈附近的偏僻村莊——普村為切入點,展示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外部世界的巨大變革給普村帶來的沖擊,易于接受新鮮事物的普村年輕人,懷著或好奇、或向往、或懷疑的心情,以各種方式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來到山外闖世界。曲宗阿媽的幾個女兒性格各異,但在走出大山闖世界的熱潮中,她們有的自覺、有的被迫來到山外的世界,她們秉承了普村人吃苦耐勞的精神,以普村人的韌性,在“陌生”的城市找尋自己的位置。小說觸摸著當下西藏鄉村生活的真實與質感:用青稞換錄像、糌粑清茶、春耕儀式、借來衣服過節、鄰里忽遠忽近的人情關系、茶館里生活場景、藏族年輕人那份投入生活改變命運的期盼……照相式記錄,老老實實地描繪出了當下西藏農村的日常狀態,直接地、毫不借助神秘光環,還原了一個與時代發生緊密沖撞的真實的西藏。作者也展示了很多西藏的地域文化和風俗,但非抽象處理,而是被放回到了生活的原生態,按生活自身的邏輯運動,讓生活本身敘述、解釋這些地域文化風俗在當下西藏鄉土社會留存的印記。總之,用作者的話說:“在很多媒介中,西藏已經符號化了,或是神秘的,或是艱險的。我想做的就是剝去西藏的神秘與玄奧的外衣,以普通藏族人的真實生活展現跨越民族界限的、人類共通的真實情感。”⑦由斯而言,筆者不得不說,只可惜這樣切入生活、貼近藏族百姓,充滿時代氣息和人文關懷的“西藏書寫”的作品太少了,過多的是主觀渲染和盲目輕浮的抒情,要么追求獵奇和神秘,要么卡通化式地表現民俗民情。
二、詩意化潔癖: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失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持續變革,尤其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及其相伴而生的價值觀念的現實推動,中國進入消費社會或準消費社會。國人的生活質量不斷躍升,但都市激烈的職場競爭及生活物化的快節奏帶來的如精神空虛、價值顛覆、人類生存意義虛無等諸多弊端亦隨之產生。可以說,在中國大地上,尤其是在文化與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帶,躲避崇高、英雄隱退、道德淪喪等共同構成了一個精神貶值的文化景觀。而與之不同的是,西藏由于獨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歷史,相比于內地風行的那種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它所呈現出來的精神景觀則要純凈、明朗許多,加之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許多主動放棄可能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離開故鄉父母、兒女親人來到西藏工作的內地人,他們扎根邊疆、建設西藏的甘于清貧、耐于寂寞的無私奉獻精神,在這個理想失落、崇高隱退的時代情境下,顯出了難能可貴的崇高精神“飛地”效應。事實上,這種一直延續至今的“老西藏精神”也感動了幾代人。
麥克盧漢在《機器新娘——工業人的民俗》一書中,曾深刻地論述美國西部片中的邊疆生活,為何令美國人著迷:“機械化常規把我們搞得污穢滿身,經濟和家庭的復雜變革把我們搞得稀里糊涂,這個幻想中的西部給我們提供了騎士的沖勁,提供了生機勃勃、沒有顧忌的個人主義。昔日的敵人是狡詐的封建貴族;新興的敵人是聰明而獨立的機器。對于被宏大的工業搞得暈頭轉向的人而言,幻想中的西部恢復了人性的尺度。”⑧從麥氏的論述中,可以明白一點,美國的西部邊疆,為當時處于工業社會的美國人提供了一種深深的懷舊情緒,一種精神補償意義上的心理治療。與此類似,如同當時處于工業社會的美國人對西部邊疆的向往一樣,此時的西藏,恰如上述與內地不同的特點,正好為在漢族都市中的人群提供了一種“恢復人性的尺度”的心理治療,成為一個心靈舒緩凈化的有效通道。于是,處于內地都市地帶的人們,在初涉西藏或粗走西藏時,隨著感情的浸潤其中而產生震驚體驗,不由地借助西藏來澆自己胸中的塊壘,把西藏看做一個可以慰藉心靈創傷的圣地,是比喧囂紛亂物欲高蹈相對寧靜的純潔之地,正如作家藍訊所說的一樣:“在內地,理想逐漸被人拋棄;西藏卻成了理想主義者的漫游之地。我想到了一條被攪渾了水的河,魚們都游到河邊,游向有野草和清水的地方,張大嘴巴呼吸著沒有被攪渾的河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西藏被人們譽為中國的最后一片凈土。”⑨
正是基于心靈救贖的需要,許多作家筆下的西藏寫作,從不去建構一種認知西藏的典型標本和權威體系,而總是把西藏想象成一種形而上的存在,一種沒有任何丑陋、污穢與負面的完美空間,一個凈化、純化、非人間化的詩意棲居地,對西藏是一種單純的理想熱愛,有關西藏的傳說甚至惡劣的氣候、苦難的人生都是那么具有魅惑力和吸引力。寧肯的《天·藏》雖然內容豐盈,但對寧肯的敘述來說,西藏也只是一種詩、哲學、宗教的象征力量,是脫離了一切世俗世界軌道的終極之地,每個人在這里的存在,更多地呈現為非世俗、非時間的一面。小說中的王摩詰,為了追尋生活的意義,作為志愿者來到西藏,成為了拉薩附近一所中學的教員。在西藏,他存在的方式,就是思考,靜思成為每天的生活內容。他認為西藏就是一個讓人靜思的地方,別人問他“……每天都干什么?”,他回答:“沒事,就是待著。”另一個人物馬丁格,來自法國,一次假期的喜馬拉雅山之行,改變了他的價值取向,使他轉向了東方的佛教,他更是一個安詳、平靜、雕塑般的沉思者,時常與父親進行著宗教與哲學的對話。很顯然,這部小說所要表現的西藏并非一個實體的西藏,而只是一種形而上的存在,一種宗教、哲學的終極形式,正如作者自己所說:“西藏給人的感覺,更多時候像音樂一樣,是抽象的,訴諸感覺的,非敘事的。兩者概括起來可稱為‘存在與音樂’。這對我是兩個關鍵性的東西,它們涉及我對西藏總體概括。”⑩但我不得不指出,把西藏敘述為一種只是形而上的存在,西藏反而顯得很貧瘠、蒼白,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西藏,亦失去了形而上思索的現實支撐,而成為了一種哲學理論話語的推演。安妮寶貝的《蓮花》中的西藏墨脫,在作者筆下被建構成了指引人從黑暗走向光亮的心靈圣地,在這里,人與自然詩意棲居,人們精神相契相融,充滿著彼岸性的光輝。作品中寫了三個人物,一個是事業如日中天,但內心卻不斷掙扎的男子善生;一個身患精神疾病的女子慶昭;還有一個命途多舛的女子蘇內河。為了擺脫內心的創傷,去尋找生命的本相,三人殊途同歸地踏上了墨脫之旅,遠離都市的喧囂,在蔥山綠水茂林藍天下,他們獲得新的生命感悟。馬麗華的《如意高地》則把筆伸向西藏歷史深處,挖掘延衍出一段冰清玉潔的愛情絕唱,作品敘述了清末民初由川進藏的軍隊統領陳渠珍一生與一位西藏女性的愛情故事。在陳渠珍進藏之后不久,新娶了藏族妻子西原。此后,無論陳渠珍面臨難關和遭遇危難,她都會及時現身排憂解難。一直忙于政務和軍務的陳渠珍沒有認真體察到這種以“戰友”方式表現出來的摯情與深愛,而當他走出戰亂的藏區,遠離危難,西原突然得了絕癥之后,他才醒悟過來,痛惜起來,但一切為時已晚。他只能萬分愧疚地感嘆“我欠了你一生的幸福”,并時時陷入“不知魂歸何處”的無盡思念。惟有藏地才能產生這樣彌足珍貴的愛情童話,當中心地帶的我們把愛情附麗于對寶馬香車、豪宅別墅、金錢財富的追逐時,這個至純至真至情的西原,宛若在欲望功利的滾滾熱浪中蕩來一陣怡人的清風。在作者看來,雪域高原才是盛產真正愛情的地方。黨益民的《一路格桑花》中的西藏,具有著“涅槃”或再生的意味。小說中的都市白領郭紅懷疑丈夫有外遇,憤然離婚去了西藏,年輕女記者安寧懷著忐忑要把自己嫁給遠在天邊的男友……到西藏后,女人們看到了駐藏官兵,這些人的人生如格桑花般絢麗而寂寞——這是一個冰雪般澄澈的世界、一個絲毫沒有受到污染的綠色群體,女人們震撼了。
不難看出,這些文本著迷于詩意化、浪漫化“西藏”,表達的重點在于西藏的“超凡脫俗”,在于作家自己曾經從游歷西藏中得到的助益于人生的感悟、收獲,更多的只是切割傳統的西藏文明中能為內地或中心城市輸出精神資源的一個側面,而非為藏民族的未來、西藏的生存、發展、建設等宏大問題去思索。正是由于作家對西藏的詩意化潔癖,他們沒有審慎地剖析西藏在時代變革中新舊文化的碰撞,特別是舊文化精神的重重簾幕;沒有透析世代生于西藏長于西藏的子民們因受制思想和文化的局限而面對世界的新變化時的艱難蛻變和求索;沒有描繪西藏文明中具有傳統影響力的封閉意識、小農思想和心態,對于現代文明的種種節制和消解;沒有思考與追問西藏在存留傳統文化的精華因子的同時,如何急迫地選擇新文化精神。總而言之,這種把西藏詩意化潔癖的寫作路向,缺乏對西藏精神文化的缺陷和負價值的審視,沒有從不同文化的精神扭擊中張揚“新生”而抨擊“方死”,而想法單純地把西藏文化的一切都作為一種詩意之美,加以濃烈渲染。也正是基于作品中這種理性批判精神的缺席,他們筆下的西藏也仍然是一個非真實、扭曲的西藏。這正如馬麗華所說:“詩化和美意構筑的感性世界,也使它的真實性多少被打了折扣——在中國,異文化進入者的邊疆作品不約而同的困難所在。”?還有西藏作家色波在《遙遠的記憶——答姚新勇博士》一文中寫道:“將藏區詩意化,正是內地人寫作的一種偏見,好像藏區就沒有切切實實的日常生活一樣。”?這句話恰切地道破了內地漢族作家書寫西藏的特點和缺失,亦即一種過度美化和簡單處理的慣用套路。
如何擺脫對西藏的詩意浪漫“誤讀”,打破人們對西藏的固定印象和想象方式,讓我們真正進入那個遠離漢文化中心的邊疆生活的細部。阿來所說的這番話,或許對我們有所啟示:“藏族并不是另類人生。歡樂與悲傷,幸福與痛苦,獲得與失落,所有這些需要,從他們讓感情承載的重荷來看,生活在此處與別處,生活在此時與彼時并無太大區別……因為故事里面的角色與我們大家有同樣的名字:人。”?事實上,阿來也是這樣進行創作實踐的,他的六卷本長篇《空山》以綿密的細節與鄉村瑣碎的日常生活敘事,展現了自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川藏邊地一個藏民居住的地方機村的命運變遷。作者沒有對藏文化作單向度的詩化處理,而是呈示出藏地豐富多維的表情。小說中的機村人不是其他西藏書寫所展現的那般“超凡脫俗”,他們既容納著仇恨、嫉妒和殘暴;也棲息著憐愛、寬容和善良,比如他們對私生子格拉的蔑視,在對桑丹和格拉肆意施暴,把他們母子趕走之后,他們的羞愧和悔恨又涌上心頭。小說既展露了現代性對藏文化的破壞和傷人的一面,如砍伐森林的電鋸,炸毀神湖的炸藥,又真切地描繪了“新社會”伴隨著大量的“新事物”如水電站、脫粒機、馬車、喇叭,給機村人帶來驚奇、興奮與惶惑。在現代性的沖擊下,藏族文化中遵循的看重義理、講究誠實的精神疏遠了人們的生活,舊有信仰和傳統倫理遭到了摒棄,作者對此流露出悲切地哀挽;同時又對機村人暴露出來的無知、人性蒙昧表示出了強烈的譏諷和義憤。如此走出那種慣常的詩意“共名”的方式,不以陳腐的浪漫來稀釋當代藏地生活的真切性,而以多焦的視點與多重的變奏,理性而全面地審視生活西藏、文化西藏,我以為,這應該成為小說“西藏書寫”的未來與方向。
三、原生態崇拜:“東方主義”話語的復制
在許多西方人眼中,西藏幾百年的黑暗的、殘酷的農奴制度,都被有意識地遺忘或抹煞掉,西藏以其高原險遠、原始風情、宗教信仰的迷惑、神秘的雪域文化……而被看做是一塊離天堂最近的地方,是一片人間的至樂之地。對后現代的西方人來說,他們似乎總是期盼著看到一個“原生態”的西藏,一個所謂“時間停滯的香格里拉”,一個靜態的理想社會,正如穆倫在《美國占領藏傳佛教》一書所論:仍然幻想從自然和人文方面保持西藏的純潔性,實際上是要滿足其身心的需求:信仰、探險、旅游、休閑、健身,以緩解競爭壓力,慰藉空虛的心靈。?
為何后現代的西方人要如此鐘情“原生態”的西藏?可以借用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觀點為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薩義德指出:“在西方文化中,“東方并非一種自然的存在”;“作為一個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歷史的——實體,‘東方’和‘西方’這樣的地方和地理區域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的。”?當然,東方并非僅僅出自想象,“西方與東方之間存在著一種權力關系,支配關系,霸權關系”?。這就是說,西方視角中的西藏形象和西藏話語,是西方所建構的關于非西方的“文化他者”的話語,這種西藏形象作為一種權力話語,是西方文化對西藏的皈化利用與自助性地建構。我們知道,20世紀中葉以來,進入“后工業化”和“后現代化”的西方開始反思現代性,當意識到正是價值理性的衰落和工業主義的過度擴張導致種種災難時,一些西方人將目光投向了東方文明和宗教,尤其是注重精神,帶有原生態的前現代色彩的西藏文明和藏傳佛教,他們出于“自助”的心靈需要,制造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香格里拉神話”、“最后一塊凈土”,以此寄托著他們的夢想和懷舊之情,于是神秘的中國西藏,又成為了西方懷舊的故鄉,或者后現代的烏托邦。
在東方主義視野的規約下,西方人總是大量描述和評價1959年以前的所謂“原生態”西藏,縱情想象西藏未受任何現代文明的污染。在看待西藏文化時,只要求保持其多樣性,不愿看到西藏文化的發展和適應現代化。由此,他們過分沉溺于陳舊的幻想,而忽視西藏普通民眾的發展;熱衷于藏文化保持恒久原生態的神圣意義,卻淡漠文化承載者的歷史與現實生活狀況;糾纏于孤立、虛構的歷史,卻置幾十年來西藏改革與發展的成就而不顧。
遺憾的是,我們有些作家也東施效顰,承襲了這種西方中心觀的東方主義邏輯,并將之置換為一種“內部東方主義”的思維路向,亦即習慣性地從主體性文明出發,把民族國家內部從屬性文明,書寫成一種原生態“牧歌”,以此作為對過去懷念的對象,從而反思主體性現代文明。于是作家們通常預設一種“現代與傳統的沖突”的陳詞濫調般的主題,對西藏原始的民俗風習、人情世態與落后的封閉意識、傳統的思想惰力,不加辨析地頌贊謳歌;對西藏自然的本真狀態抱持偏執式迷戀,以所謂小布爾喬亞分子的格調,沉溺于“欣賞”和“艷羨”西藏的原始風景;對西藏的新生活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惶悚與疑惑,有意無意地漏掉西藏現實中發展變化的另一面。比如白瑪娜珍的《拉薩紅塵》就流露出期翼拉薩繼續現狀或回歸更古老的過去的強烈心緒:“從前的拉薩像一場久遠的夢,……葉瓣恍若雨滴飄落到我的雙肩,滑落到潮濕的泥土里。樹林里天籟搖曳,一陣清脆悠長的銅鈴聲由遠而至,一對潔白的小羊兒從林子深處走來,滿地淺黃淡綠的落葉在羊兒輕巧的步履下翻涌著,爭先綻放,仿佛一朵朵靈光閃耀的圣蓮……”“以雪山和草原為背景,自由的情侶本該騎在馬背上奔馳,在沉靜的家園里私語,在古老的床板上熱烈的地相愛,擁有祖輩們曾經的好時光……”然而現在,“所謂的老城區危房改建工程令一些人發了一筆橫財,但改建后的老城區面貌全非,人們的居住空間變得擁擠、嘈雜和更加混亂。……沒有了甘洌的水井、白色的桑爐,也沒有了友善的老鄰居……”“牧人們從雪地迢迢而至,但拉薩——他們的家變了,甚至穿過一條馬路,也要冒生命的危險。家園沒有了安全感,只有無情的車輛、高樓和緊閉的門……”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作者對當代拉薩的憂思,但在面對急遽前行的時代巨輪時,如果排拒任何新變,只是一味如條件反射地認同現代與傳統之間的張力與裂縫,不去尋找它們之間的平衡與彌合點,則將這個問題簡單化了。郭阿利的《走進草原的兩種方式》中的北京人李輝生長在北京城,向往自然生態,來藏北草原就是尋找夢中的香巴拉。文本中借李輝之口,不時流露出對科學技術進入草原的失望情緒:“看著眼前一排排鋼筋水泥結構的小樓,再看那趾高氣揚的所長心里就不舒服,憑感覺爹就知道,這里除了比北京小以外,其它一定和北京區別不大,爹不希望剛走出現代化的北京城就又進了現代化的草原。”草原上為牛羊采取人工受精的新生產方式,這樣每年都會按規定的數量生產出優質的牛羊,既提高了牛羊肉的產量,也調節了草場的生態平衡。可是作者借小說中的人物作如此議論:“抹殺了人的本性還不夠,現在連牛羊也不放過了,多么殘忍的現代科學技術呀。”還有楊金花的《天堂高度》、摩卡的《情斷西藏》、七堇年的《大地之燈》等文本也是極力渲染西藏原生態風景的美好,似乎只有一片蠻荒的、未經開化的西藏,才是真正產生純美愛情,或升華精神格調的天堂,才是美好、豐富、純潔、神圣、充滿著浪漫氣息和脫俗氣質的“香格里拉”。質言之,這些小說癡迷原生態的西藏,反映出他們對西藏的共同理解或者期待:西藏本應該就是“永遠的香巴拉”,不屬于也不應該屬于這個正在現代化的世界,西藏的任何現代性新變,都只能被看做是一種異己力量,并成為破壞藏文化純潔的象征,任何傳統的衰微,都隱喻著藏文化的危機。這樣自以為是的想象方式,完全抹殺了現代化發展對西藏的積極意義。
其實,對于現代化有些膩味的所謂城市“中產階級”或“白領”來說,要明白一個淺顯的道理:地球上的任何族群都有權利分享人類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和現代化帶來的成果,這是“天賦人權”。當我們一方面在中心地帶受益于現代化所提供的一切時,另一方面卻為了滿足我們自己所謂懷舊夢境的想象,而要求西藏是永遠靜止的、原生態的,這是極不人道的,是一種普世意義上的人文精神的缺失。西藏的現代性追求也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或者說其現代性即當下性和現實性,正如作家書云所說:“對西藏普通的百姓而言,他們需要對過去燦爛歷史文化的記憶,但更需要在變化中追求現代化的美好未來。他們渴望享受現代化的生活,不希望被當作古老的文物加以收藏和展示,更不希望把他們當作虛擬中的‘香格里拉’或‘香巴拉’讓人觀摩,被人誤解、誤會”。?誠哉斯言,真切的西藏完全不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的,而是進步與問題并存,在巨大變化中延續著古老的傳統。
總之,我以為,雖然在這個特定時期和一些特定群體中,西藏已經成為了某種前鋒或受到強烈的關注,但是西藏是無言的,言說的只是我們自己。因此,對于西藏敘事的主體來說,我們在以各自的方式感受西藏的時候,要尋找到真正抵達人類心靈的精神和感動,真正產生開發、建設、保護、發展西藏的緊迫性和憂患意識。由之,藏族作家央珍的創作談可作為我們的鏡鑒:“我……力求闡明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單一視為的‘凈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單一的‘落后’和‘野蠻’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燦爛微笑’的人們,更不是電影《農奴》中的強巴們。它的形象的確是獨特的,這種獨特就在于文明與野蠻、信仰與褻瀆、皈依與反叛、生靈與自然的交織相容;它的美與丑準確地說不在那塊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塊土地上的人們的心靈里。”?
【注釋】
①本文所說的“西藏”,并非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不是單指解放后建立的西藏自治區,更多的是文化意義上的“西藏”,它標示著一種歷史文化空間,在這個空間里,藏民作為生活的主體民族,在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生活等方面迥異于內地中原。
②張隆溪:《異域情調之美》,李博婷譯,《外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2期。
③陳曉明:《無邊的挑戰》,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頁。
④孟繁華:《紅塵不能淹沒的文學——2006上半年的長篇小說》,《中國圖書評論》2006年第9期。
⑤[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200頁。
⑥[匈]盧卡奇、[德]本澤勒:《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上卷),白錫堃、張西本、李秋零譯,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頁。
⑦中國作家網:http://www.chinawriter.com.cn/news/2010/2010-03-16/83583.html。
⑧[加]馬歇爾·麥克盧漢:《機器新娘——工業人的民俗》,何道寬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頁。
⑨藍訊:《西藏片羽》,史小溪編《中國西部散文·下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71頁。
⑩寧肯:《為什么不同》,《長篇小說選刊》2011年第1期。
?馬麗華:《西行阿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頁。
?色波:《遙遠的記憶——答姚新勇博士》,《西藏文學》2006年第1期。
?阿來:《落不定的塵埃》,《小說選刊·長篇小說增刊》1997 年第 2 期。
?轉引自杜永彬《西方對西藏的誤讀及其原因》,《當代世界》2009年第4期。
??[美]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書店 2007 年版,第 6-8頁。
?卜昌偉:《旅英華人作家書云用〈西藏一年〉記錄藏民尋常生活》,《京華時報》2009年7月24日。
?央珍:《走進西藏》,《文藝報》1996 年 2 月 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