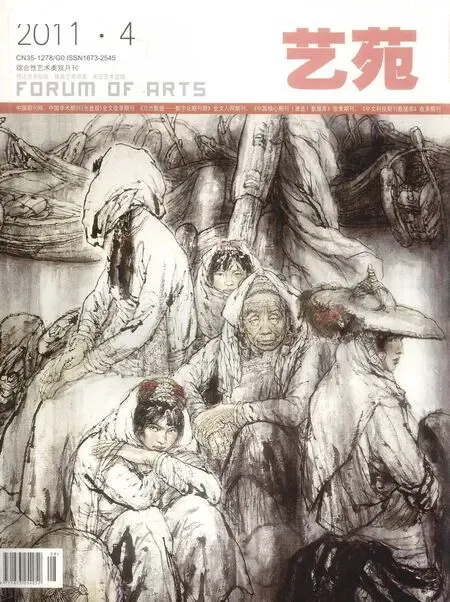人性化的視角——評(píng)電視連續(xù)劇《保衛(wèi)延安》
文/張文諾
近幾年來,一系列“紅色經(jīng)典”被改編為電視連續(xù)劇,如《小兵張嘎》、《苦菜花》、《敵后武工隊(duì)》、《鐵道游擊隊(duì)》、《烈火金剛》、《閃閃的紅星》、《地道戰(zhàn)》、《沙家浜》等。“紅色經(jīng)典”被改編為電視連續(xù)劇已經(jīng)成為電視劇創(chuàng)作的熱點(diǎn)現(xiàn)象,當(dāng)代的編劇、導(dǎo)演乃至演員在改編、拍攝、表演過程中都力圖還原“紅色經(jīng)典”所缺失的人性內(nèi)容,力圖把不食人間煙火、神化的英雄還原為具有七情六欲的人化的英雄。這一努力值得稱道,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獲得了觀眾的認(rèn)可。但由于過多地考慮票房、收視率的影響,“紅色經(jīng)典”在改編、重拍過程中又出現(xiàn)了故意填塞英雄感情戲的“濫情”傾向,這樣塑造出來的英雄同樣成為另一種假英雄,令人啼笑皆非。真正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chǎng)上、從人性的視角在英雄的“偉大性”與“真實(shí)性”之間保持一種平衡是影視劇編劇、導(dǎo)演乃至演員必須注意的首要問題。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從人性化的視角表現(xiàn)了發(fā)生于半個(gè)世紀(jì)前的延安保衛(wèi)戰(zhàn)的復(fù)雜性、艱巨性,揭示了決定戰(zhàn)爭(zhēng)勝負(fù)的復(fù)雜因素,同時(shí)又塑造了許多個(gè)性鮮明的人物形象,表現(xiàn)了編劇、導(dǎo)演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對(duì)英雄、對(duì)人性的深刻理解。
一
發(fā)生于1947年的延安保衛(wèi)戰(zhàn)在解放戰(zhàn)爭(zhēng)時(shí)期的國共兩黨領(lǐng)導(dǎo)高層中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延安保衛(wèi)戰(zhàn)的勝負(fù)直接關(guān)系著國共兩黨在其后戰(zhàn)局中的主動(dòng)權(quán),直接關(guān)系著國共兩黨軍事、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zhǎng)。國共雙方都委派了精銳力量在茫茫的陜北高原展開了殊死較量,如此重要的戰(zhàn)役并非像歷史教科書中所敘述的“我西北野戰(zhàn)軍經(jīng)過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zhèn)、沙家店等五次戰(zhàn)斗便取得勝利”那樣容易。電視劇真實(shí)生動(dòng)地揭示了戰(zhàn)爭(zhēng)的艱難和曲折,我們看到:成千上萬的交戰(zhàn)雙方士兵被戰(zhàn)爭(zhēng)、被饑餓奪取了寶貴的生命,邊區(qū)群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jià)和犧牲。電視劇用了一系列鏡頭刻畫了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和無情,揭示了戰(zhàn)爭(zhēng)和人的對(duì)立,李老漢的小孫子栓牛壯烈犧牲,改花的父親被飛機(jī)炸死,李老漢的妻子為掩護(hù)野戰(zhàn)軍戰(zhàn)士被打死,苗真和張玉峰純真、美好的愛情被埋葬于戰(zhàn)爭(zhēng)的火海。

更為重要的是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在揭示決定戰(zhàn)爭(zhēng)勝負(fù)因素時(shí)處處突出了人民群眾和普通戰(zhàn)士的作用。當(dāng)然,電視劇也沒有否定我軍領(lǐng)袖運(yùn)籌帷幄的智慧和英明,毛澤東同志根據(jù)敵我雙方形勢(shì)制定了放棄延安、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標(biāo)的戰(zhàn)略決策,彭德懷將軍根據(jù)戰(zhàn)場(chǎng)態(tài)勢(shì)靈活指揮、聲東擊西,這些無疑都是戰(zhàn)爭(zhēng)勝利的關(guān)鍵因素。但電視劇卻著重突出了人民群眾和普通戰(zhàn)士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勝利所起的決定性作用。邊區(qū)群眾不但為野戰(zhàn)軍戰(zhàn)士提供了大量的糧食、衣服和軍需物質(zhì);而且他們奮不顧身地抬擔(dān)架、搞運(yùn)輸,為軍隊(duì)提供情報(bào),直接支援了戰(zhàn)爭(zhēng)。在青化砭伏擊戰(zhàn)時(shí),如果不是李老漢和孫子栓牛引開國民黨軍隊(duì)的巡邏隊(duì),這場(chǎng)伏擊戰(zhàn)有可能很難實(shí)施,后來也只有七八歲的栓牛壯烈犧牲。劇作多次借普通戰(zhàn)士、基層指戰(zhàn)員和中央領(lǐng)導(dǎo)對(duì)李老漢一家的贊揚(yáng)與評(píng)價(jià)突出了人民群眾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巨大作用。普通戰(zhàn)士作為戰(zhàn)爭(zhēng)的直接執(zhí)行者,他們的戰(zhàn)斗力、創(chuàng)造性對(duì)戰(zhàn)爭(zhēng)勝負(fù)的影響可以說是決定性的,因?yàn)樵俑叱膽?zhàn)略戰(zhàn)術(shù)也要靠他們?nèi)?zhí)行。在打蟠龍攻堅(jiān)戰(zhàn)時(shí),戰(zhàn)事一度不順,正是由于基層戰(zhàn)士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對(duì)壕作戰(zhàn)”戰(zhàn)術(shù),才攻下了蟠龍鎮(zhèn)。彭德懷將軍在戰(zhàn)斗結(jié)束時(shí)說:“你們說我能打仗會(huì)打仗,其實(shí)最會(huì)打仗的是這些戰(zhàn)士和你們最基層的指揮員。”劇作還多次出現(xiàn)彭總站在山上沉思的鏡頭,打完蟠龍以后,他語氣低沉地對(duì)王政柱說:“每到黃昏的時(shí)候,我都站在山頂上看一看,想一想。三戰(zhàn)三捷,我們打了勝仗,但我們時(shí)刻不能忘記那些為了革命流血犧牲的戰(zhàn)士們,……因?yàn)榻裉斓膭倮撬麄冇醚忤T成的。”此外,劇作還寫出了個(gè)體生命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感受。劇作對(duì)李大旺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感受寫得真實(shí)生動(dòng),他在激烈戰(zhàn)斗期間也不能忘記他的改花,當(dāng)聽到改花的父親犧牲時(shí),他難過得直哭起來,非要去看看他的改花不可,哪怕是看一眼也行。戰(zhàn)斗英雄也是人,他們也有愛情和親情,也有軟弱的一面,甚至也會(huì)哭鼻子。正是在這些真實(shí)細(xì)膩的感受中,英雄才成為活生生的、真實(shí)的、可敬可親的英雄。“雖然戰(zhàn)爭(zhēng)是人的戰(zhàn)爭(zhēng),文學(xué)作品應(yīng)該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中的豐富性、復(fù)雜性,在審美意義上表現(xiàn)出戰(zhàn)爭(zhēng)與人的深刻矛盾,才能把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認(rèn)識(shí)推進(jìn)到深刻的層次上去。”[1](P5)以往的“紅色經(jīng)典”主要是表現(xiàn)無產(chǎn)階級(jí)革命領(lǐng)袖的作用,在他們正確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的指導(dǎo)下,我軍不費(fèi)吹灰之力就戰(zhàn)勝了敵人。這部電視劇用了大量的鏡頭表現(xiàn)人民群眾、普通戰(zhàn)士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作用以及個(gè)體生命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感受,對(duì)于深化戰(zhàn)爭(zhēng)小說的內(nèi)容和主題有重要的開拓意義。
更為動(dòng)情的是這部電視劇熱情謳歌了人道主義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地位和價(jià)值,艾特馬托夫說:“任何東西都不像戰(zhàn)爭(zhēng)那樣最強(qiáng)烈地顯現(xiàn)出作為人類的永恒的、始終存在著的美德和同情心。”[2](P322)戰(zhàn) 爭(zhēng)是關(guān)系著作戰(zhàn)雙方你死我活的斗爭(zhēng),最能體現(xiàn)人的思想和心靈,最能坦露和揭示人的本質(zhì)。人道主義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表現(xiàn)是一個(gè)復(fù)雜的問題,人道主義不是投降主義,也不是無條件的和平主義。這部電視劇揭示出對(duì)于交戰(zhàn)雙方來說,人道主義是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當(dāng)謝芳苓披著紅十字會(huì)旗去解救那個(gè)孩子時(shí),國民黨軍官命令士兵停止了射擊,說她披著紅十字會(huì)旗;當(dāng)周大勇率領(lǐng)戰(zhàn)士們攻克碉堡時(shí),他們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張玉峰;謝芳苓、小成子和野戰(zhàn)醫(yī)院領(lǐng)導(dǎo)以極大的耐心精心救治、護(hù)理心靈受傷的苗真;彭德懷將軍命令戰(zhàn)士們?yōu)樽詺⒌膰顸h中將軍長(zhǎng)劉戡凈衣凈身成殮;國民黨士兵拒絕開槍射殺老百姓……這些表現(xiàn)人道主義的場(chǎng)面在以往的影視劇中非常罕見,這些場(chǎng)面既寫出了戰(zhàn)爭(zhēng)過程本身的復(fù)雜性,也寫出了人道主義的可貴。《保衛(wèi)延安》這部電視劇表現(xiàn)了導(dǎo)演對(duì)人道主義的理解:在戰(zhàn)爭(zhēng)中,敵人不放下武器就是敵人,敵人放下武器就不是敵人,我們就應(yīng)該對(duì)他們實(shí)施人道主義幫助和救助,這是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在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中的人道主義所做出的最大開拓。人道主義的復(fù)歸,是人的觀念的全面覺醒。它不僅僅表現(xiàn)在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chǎng)上對(duì)正義戰(zhàn)爭(zhēng)一方深切地同情與理解,也表現(xiàn)在對(duì)非正義一方,能從人的視點(diǎn)上挖掘出其人性的一面。“戰(zhàn)爭(zhēng)中普通人的人性美,在以往的戰(zhàn)爭(zhēng)小說中并不少見,但大多數(shù)是從階級(jí)論的觀點(diǎn)上去表現(xiàn)的。”[3](P837、900)電視劇對(duì)普通戰(zhàn)士人性美的表現(xiàn),有利于塑造更真實(shí)、更生動(dòng)的英雄形象,有利于揭示戰(zhàn)爭(zhēng)勝利的根本原因,有利于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的殘酷性和復(fù)雜性。
二
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從人性化的視角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描寫人物,一改以往革命戰(zhàn)爭(zhēng)影視劇中以我為主、以我方的視點(diǎn)去觀照戰(zhàn)爭(zhēng)的傳統(tǒng),將單向觀察戰(zhàn)爭(zhēng)的角度轉(zhuǎn)換成雙向的角度,對(duì)敵我雙方將領(lǐng)同時(shí)進(jìn)行表現(xiàn),為多角度反映戰(zhàn)爭(zhēng)提供了可能。在劇中,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胡宗南、陳誠、劉戡、董釗等都得到了正面表現(xiàn),為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再像以往影視劇中那樣屬于道德缺陷或人格低下之人,他們不但重視友情、愛情和親情,也具有高深的軍事戰(zhàn)略修養(yǎng)、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蔣介石老謀深算,對(duì)戰(zhàn)局的判斷非常準(zhǔn)確,和我方的部署往往不謀而合;他雖然發(fā)動(dòng)了內(nèi)戰(zhàn),不得民心,但又能堅(jiān)持民族大義,在戰(zhàn)局不利時(shí)也絕不動(dòng)用英美軍艦。胡宗南英俊灑脫、高大魁梧,作為國軍高級(jí)指揮員,有很強(qiáng)的指揮才能;對(duì)自己的未婚妻一往情深;對(duì)自己的秘書懷有父子般的感情,在他身上表現(xiàn)了極大的人格魅力。劉戡頭腦清醒,敢于堅(jiān)持自己的獨(dú)立見解,對(duì)國共雙方的優(yōu)劣成竹于胸;董釗對(duì)自己的部下很是體貼和寬容。電視劇從人性的視角表現(xiàn)我軍的對(duì)手,大膽表現(xiàn)他們的智慧和才干,更能揭示戰(zhàn)爭(zhēng)的復(fù)雜性和艱巨性,更能表現(xiàn)我軍的英勇善戰(zhàn)和我方指戰(zhàn)員高超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電視劇對(duì)我方人物的塑造也有很大的開拓,毛澤東同志的運(yùn)籌帷幄、聲東擊西自不用說,他的倔強(qiáng)、不受約束給人印象更為深刻。彭德懷將軍用兵靈活、大膽、不拘兵法、奇正相間、聲東擊西等,顯示了我軍高級(jí)指揮員的高超素質(zhì);劇作同時(shí)又表現(xiàn)了他作為普通人的一面,當(dāng)他看到戰(zhàn)士們?cè)诖髴?zhàn)前夕在戰(zhàn)壕里爭(zhēng)奪荷包時(shí),他嚴(yán)厲地批評(píng)了他們;當(dāng)看到李大個(gè)子光榮犧牲、荷包被落在戰(zhàn)壕里,他陷入了深深的內(nèi)疚之中。當(dāng)戰(zhàn)局不順時(shí)他容易急躁、愛發(fā)脾氣,在打蟠龍鎮(zhèn)時(shí),我軍攻擊受阻,形勢(shì)萬分危急,王政柱參謀長(zhǎng)建議是否暫緩進(jìn)攻時(shí),他抓住王政柱的衣領(lǐng)說:“你給我聽好了,你再敢動(dòng)搖我的決戰(zhàn)決心,我就槍斃你。”看到戰(zhàn)士們一批一批地犧牲,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他又能知錯(cuò)就改,體貼部下,事后,他對(duì)王政柱說:“我本想找一個(gè)正式的場(chǎng)合向你道歉,當(dāng)時(shí)我不該那么粗暴地對(duì)你,十多年了,我這壞脾氣就是改不了。”王政柱說:“彭總,你發(fā)脾氣,我們都習(xí)慣了,你不發(fā)脾氣,我們反倒不習(xí)慣,……彭總,我們懂您的心。”這短短幾句對(duì)話寫出了彭總的真誠、坦蕩、可親、可敬的人格魅力。
劇作對(duì)基層指戰(zhàn)員和普通戰(zhàn)士的塑造也非常個(gè)性化,周大勇、謝芳苓、王成德、小成子、苗真、李大旺、改花、李大爺、王老虎、馬全有等都深具個(gè)性。周大勇是我軍一個(gè)基層指戰(zhàn)員,他沒有多少文化知識(shí),在和從總部下來的文化水平較高的王成德相處時(shí),生怕自己吃虧,所以自己可以偷看別人的東西,不許別人看自己的東西;在談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看法時(shí),他總讓王成德先說,生怕他占自己的便宜;他目光不夠長(zhǎng)遠(yuǎn),對(duì)總部的作戰(zhàn)意圖理解不如王成德到位;他有自己的私心,頭腦不夠靈活,對(duì)“解放戰(zhàn)士”報(bào)有成見,喜歡自己帶出來的老兵,固執(zhí)地運(yùn)用自己的土辦法對(duì)待犯錯(cuò)的“新兵”,差點(diǎn)釀成大錯(cuò);他作風(fēng)粗豪,不善于做戰(zhàn)士們的思想工作,動(dòng)輒就對(duì)戰(zhàn)士們吹胡子瞪眼;在愛情問題上有自己的“小九九”,生怕別人和自己搶謝護(hù)士;但他豪爽、無私、待人真誠、作戰(zhàn)勇敢、知錯(cuò)就改,所以又深受部下?lián)碜o(hù),這是一個(gè)具有復(fù)雜性格的真實(shí)的英雄形象。此外,像謝芳苓的勇敢、美麗,王成德的敢于較真、頭腦靈活,小成子的天真、單純,苗真的愛情至上,李大旺、改花的癡情,李大爺?shù)纳蠲鞔罅x,馬全有的喜歡傳播消息等無不躍然紙上、栩栩如生。“表現(xiàn)英雄人物的難點(diǎn),就在于把握英雄性格的偉大性和真實(shí)性(平常性)的臨界線,把兩種特性都表現(xiàn)出來。英雄的偉大性如果孤立地按單一化方向發(fā)展,不斷突出,以至排斥平常性,就會(huì)變得虛假,從而失去英雄的美感效應(yīng)。而真實(shí)性(平常性)如果不適當(dāng)?shù)貜?qiáng)調(diào),以至排斥英雄的某種超常性,就會(huì)變得庸俗和渺小,也同樣會(huì)失去英雄的美感效應(yīng)。”[4](P123)如果說“紅色經(jīng)典”因過于強(qiáng)調(diào)英雄的“偉大性”而變得虛假,那么近幾年的戰(zhàn)斗英雄塑造又過于突出英雄的“真實(shí)性”同樣變得虛假。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在英雄的“偉大性”和“真實(shí)性”之間達(dá)到了一種平衡,從而塑造出了真實(shí)、可信的英雄形象。

三
在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或者影視劇中,愛情描寫,尤其是戰(zhàn)斗英雄的愛情是要堅(jiān)決予以回避的。愛情描寫勢(shì)必要和人的身體、欲望相聯(lián)系,對(duì)身體、欲望的描寫會(huì)影響無產(chǎn)階級(jí)戰(zhàn)斗英雄的純粹和高大,這和當(dāng)時(shí)的主流意識(shí)對(duì)英雄的理解與規(guī)范相違背,于是,愛情從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和影視劇中退場(chǎng)了。“我們認(rèn)為在某種程度上每一個(gè)文學(xué)文本都涉及欲望。然而,提出這一問題并不是說文學(xué)處處都充滿了欲望。”[5](P172)因此,文學(xué)作品處處充滿欲望固然不當(dāng),但是欲望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缺席也使得文學(xué)成為非文學(xué)和假文學(xué),無產(chǎn)階級(jí)英雄成為只有革命性、階級(jí)性而沒有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間煙火的政治符號(hào)。戰(zhàn)斗英雄們既具有普通人的情感又具有普通人所沒有的生活經(jīng)歷和思想品質(zhì),他們的愛情生活會(huì)更令人回腸蕩氣,更能表現(xiàn)愛情的美好和英雄的性格特征。
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大膽反映了三對(duì)戀人的愛情生活。周大勇和謝芳苓、李大旺和改花、苗真和張玉峰這三對(duì)戀人的愛情生活模式和內(nèi)容雖然各不相同,但同樣表現(xiàn)了青年人愛情的美好和純真。苗真和張玉峰都是高材生,二人門當(dāng)戶對(duì)、情投意合。二人原來準(zhǔn)備去美國留學(xué),只是家長(zhǎng)想讓張玉峰積累一下更多的資本才參軍到了西北戰(zhàn)場(chǎng),最后張玉峰犧牲在黃土高原。劇作生動(dòng)地刻畫了二人之間純真、浪漫、幸福的愛情生活,兩人的愛情悲劇揭示了內(nèi)戰(zhàn)給參戰(zhàn)雙方都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令人唏噓不已。劇作還揭示了美好、純真的愛情生活對(duì)英雄們事業(yè)的激勵(lì)與促進(jìn)。周大勇對(duì)謝芳苓是單相思,周大勇最初討厭謝芳苓,認(rèn)為她拖行軍的后退,后來很敬佩她,最后愛上了她。李大旺和改花二人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李大旺作戰(zhàn)勇敢頑強(qiáng)、不怕犧牲固然是黨教導(dǎo)的作用,但改花在背后的激勵(lì)和期待是他奮勇殺敵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個(gè)人對(duì)世俗幸福的懷想、對(duì)和平生活的渴望同樣可以成為戰(zhàn)場(chǎng)上頑強(qiáng)殺敵的動(dòng)力。”[6](P89)劇作用了很多篇幅表現(xiàn)世俗幸福、和平生活對(duì)人的激勵(lì)作用。如彭總拿著荷包對(duì)著茫茫的黃土高原遠(yuǎn)望,他說:“這是他們心里最想得到的美好生活,為了這美好生活,奔赴戰(zhàn)場(chǎng),他獻(xiàn)出了年輕的生命,……為了這和平生活,我們共產(chǎn)黨人不怕困難,不怕挫折,不怕流血和犧牲,為之奮斗了二十多年。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能完成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建設(shè)一個(gè)新中國,讓所有的像大個(gè)子的年輕人都過上男耕女織的和平生活。”這些場(chǎng)景與語言表現(xiàn)了戰(zhàn)士們對(duì)和平生活與世俗幸福的向往,寫出了戰(zhàn)士們心靈的豐饒與美好和人性的真實(shí),稀釋了戰(zhàn)爭(zhēng)的單調(diào)和殘酷。劇作還用大量的鏡頭來反映戰(zhàn)爭(zhēng)之外的生活,如野戰(zhàn)醫(yī)院、后方生活的場(chǎng)景,愛情生活的場(chǎng)景等,這樣使對(duì)戰(zhàn)爭(zhēng)的敘述更加豐富生動(dòng),一方面使劇作鏡頭有張有弛,快慢協(xié)調(diào),使觀眾獲得一種欣賞的愉悅感;另一方面,這些舒緩明朗的生活場(chǎng)景是對(duì)和平生活的向往和美好人性的呼喚,增強(qiáng)了劇作的藝術(shù)魅力。
更具現(xiàn)代審美意義的是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從人性的角度反映了愛情的復(fù)雜性,在表現(xiàn)硝煙彌漫的戰(zhàn)爭(zhēng)的同時(shí)賦與愛情生活以很大的獨(dú)立地位。以往的“紅色經(jīng)典”小說或者影視劇要么回避愛情描寫,要么把愛情簡(jiǎn)單地處理為“美女愛英雄”的模式。只要是戰(zhàn)斗英雄,那么他就很容易獲得愛情,根本不考慮雙方在家庭背景、知識(shí)修養(yǎng)、情趣、氣質(zhì)等方面的差異。周大勇愛上了謝芳苓,這事只有周大勇一人相信,王成德說二人根本不般配,豪爽的王老虎說沒有這回事,全團(tuán)戰(zhàn)士都不信,都認(rèn)為二人不合適。周大勇在戰(zhàn)場(chǎng)上風(fēng)風(fēng)火火、斬釘截鐵,可是面對(duì)各方面都比自己優(yōu)越的謝芳苓,他不敢表白自己的愛慕之情,吞吞吐吐,說不出話來。王成德告訴他既然說不出來,就把感情埋在心底吧。謝芳苓明白周大勇的心思而委婉地拒絕了他。這樣的愛情描寫角度新穎、不落俗套,既有利于刻畫出戰(zhàn)斗英雄感情的細(xì)膩、性格的復(fù)雜、人性的美好,又?jǐn)[脫了把英雄庸俗化、低俗化的傾向。兩性之間的愛情是復(fù)雜的,雙方的階級(jí)立場(chǎng)相同、階級(jí)利益一致并不一定就能產(chǎn)生感情的吸引,雙方的外貌、情趣、修養(yǎng)、氣質(zhì)等是兩性之間產(chǎn)生感情的重要因素,在這種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愛情才是真實(shí)的。“在階級(jí)社會(huì)里,愛情固然與政治相聯(lián)系,有時(shí)甚至聯(lián)系得相當(dāng)緊密,但從整體上看,這種聯(lián)系僅僅折射出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和文化的發(fā)展變化,它不可能具體到在每一個(gè)愛情故事中都能找到與當(dāng)下政治一一對(duì)應(yīng)的關(guān)系。換而言之,同一政治集團(tuán)里的男女未必會(huì)發(fā)生愛情,不同政治集團(tuán)的男女未必不會(huì)發(fā)生愛情。”[3](P837、900)
《保衛(wèi)延安》作為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代表作之一,是“在既定的意識(shí)形態(tài)的規(guī)限內(nèi),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dá)成既定的意識(shí)形態(tài)目的。”[7](P2)雖然《保衛(wèi)延安》被看作是當(dāng)代戰(zhàn)爭(zhēng)小說的一個(gè)重要收獲,但是,它帶有那一代作家的思維特征,缺乏“哲學(xué)之思的意義層面上的人文關(guān)懷和作為現(xiàn)代哲學(xué)的基本問題的‘人’的自覺意識(shí)。”[8](P59)“如果用今天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來看,幼稚與粗糙也在所難免。”[9](P3)因此,對(duì)小說《保衛(wèi)延安》的改編與超越是完全必要的,當(dāng)然,小說本身也為改編和超越提供了很大的空間。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的成功之處是編者、導(dǎo)演真正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chǎng)上,從人性的視角來表現(xiàn)戰(zhàn)爭(zhēng)、塑造英雄。劇作既反映了波瀾壯闊、規(guī)模宏大的大兵團(tuán)作戰(zhàn),也反映了溫馨、浪漫又不乏緊張的后方生活;既表現(xiàn)了戰(zhàn)斗英雄作為普通人的一面,也揭示出英雄所具有的普通人沒有的堅(jiān)強(qiáng)品格;既表現(xiàn)了我軍指戰(zhàn)員以及普通戰(zhàn)士們的豐富、美好的內(nèi)心世界和私人感情,也大膽寫出了敵軍人員的復(fù)雜的精神世界。電視劇《保衛(wèi)延安》在諸多方面做出的探索與超越對(duì)于今后的“紅色經(jīng)典”的改編或者戰(zhàn)爭(zhēng)小說的創(chuàng)作都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1]潘先偉.論中蘇戰(zhàn)爭(zhēng)小說審美的趨同性和差異性[J].嘉應(y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7(5).
[2](前蘇聯(lián))作者未知.當(dāng)代文學(xué)中的偉大的衛(wèi)國戰(zhàn)爭(zhēng)[M].莫斯科,1982.
[3]許志英,丁帆,等.中國新時(shí)期文學(xué)主潮[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2.
[4]劉再復(fù),性格組合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5](英)安德魯·本尼特,尼古拉·羅伊爾,等.關(guān)鍵詞:文學(xué)、批評(píng)與理論導(dǎo)論[M].汪正龍,李永新,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7.
[6]董健等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新稿[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
[7]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前言[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8]陳思和.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教程[M].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2006.
[9]關(guān)培顯.紅色經(jīng)典創(chuàng)作得失再評(píng)價(jià)[J].湖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