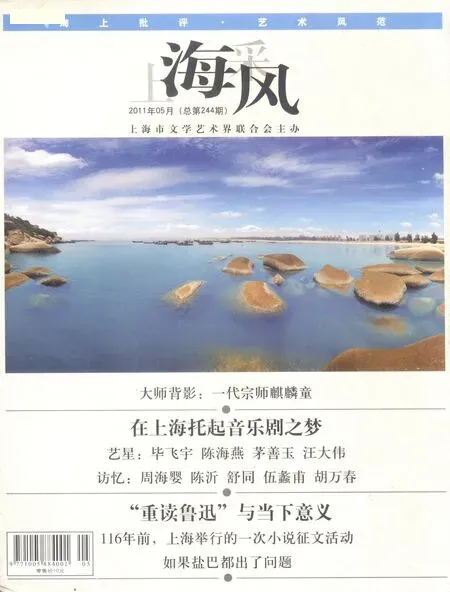數碼復制時代的著作權危機
文/張 閎
數碼復制時代的著作權危機
文/張 閎

張閎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批評家
三月十五日是所謂“國際消費者權益日”。每年的這個日子,都會有許多的消費者權益受損的事件被公諸于眾。今年的這一天,互聯網上卻出現了一份由國內50位作家和出版人聯署的名為《三一五中國作家討百度書——這是我們的權利》的宣言書,這些作家聯名控訴百度網的“百度文庫”侵犯了他們的著作權。宣言書聲稱:“百度文庫收錄了我們幾乎全部的作品,并對用戶免費開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載閱讀,但它卻沒有取得我們任何人的授權。不告而取謂之偷,百度已經徹底墮落成了一個竊賊公司,它偷走了我們的作品,偷走了我們的權利,偷走了我們的財物,把百度文庫變成了一個賊贓市場……如果放任百度繼續侵害我們的權益,我們將無法憑此生活,只能放棄我們的寫作事業。”
文化產品的生產者也要求維護自己的權益,“國際消費者權益日”同時也戲劇性地成了“中國生產者權益日”。這一事件首先表明的是,在一個缺乏個體主權意識的社會里,法律都不能為公民提供保護傘,每一個人的權利都可能受到隨意的侵犯,無論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每一個人都是受害者。
除了表現出普遍性的法律弊端之外,這一次的作家維權事件還有其特殊性。這份公布于互聯網上的檄文,盡管文人氣濃重,而且措辭有些夸張,但卻揭示了互聯網時代的文化所面臨的新的困局。
數碼復制時代的文化生產和傳播,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博爾赫斯曾經虛構過這樣一種場景:整個宇宙就是一個巨大的巴別圖書館,一個有著無數的六面體回廊的建筑,每一層的高度正好超過一個普通圖書館員的身高。萬物在其間井然有序地排列,如同一套剛剛整理好的“百科全書”。在他看來,世界就是一本打開的書,知識、資訊在其間自由流通。這樣一個“資訊烏托邦”,將使公民的閱讀成為一種隨機選擇的愛好和快樂,資訊傳播和文化記憶成為每一個公民自己的權利和責任,而不是通過外部壟斷性權力的扭曲和強制。更重要的是,在博爾赫斯看來它還是“我們人類能夠得到幸福的手段之一”。沒有閱讀,人不會有真正的快樂;而一個剝奪他人閱讀權利的人,也不會幸福。國際互聯網的出現,等于是提供了一個巨大無邊的資訊共享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長期以來權力對資訊壟斷的局面,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博爾赫斯的“巴別圖書館”的夢想。于是,在互聯網空間里,出現了一種或可被稱之為“互聯網共產主義”的壯麗景觀。似乎只要鼠標一點,知識和資訊的大門就訇然洞開,人人都可以無條件地盡情享用任何文化饗宴而無須支付任何資本。
毫無疑問,互聯網的資訊傳播原則就是免費自由共享,這被認為是互聯網精神的核心所在,是互聯網傳播與傳統傳播的根本差異。而今天,這種自由享用知識和資訊的美好圖景,卻陷入了一個個人權利的困局。在互聯網這個資訊烏托邦里,傳統的版權觀念被摧毀,人人都可以免費享用各種資訊,無論其來自哪個方面。互聯網精神的捍衛者,一直在不斷地挑戰傳統的版權觀念。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所帶來的閱讀革命,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與著作權相關的法律難題。首先是文化生產的主體出現了認同危機。事實上這種危機在機械復制時代已經出現,傳統的紙本出版物可以大量被復制,作者所創造的作品的唯一性不復存在,對于作品版權的實在性和唯一性的確認,已相當困難。但作品復制的依據依然有一個母本——原作(手稿)。而數碼復制幾乎無法確認母本,在互聯網空間中自我增殖和無可阻遏地蔓延。也就是說,在數碼虛擬空間中,表達者本身也是一種虛擬的存在,其權利也在一定程度上虛擬化了。作家維權宣言書,凸顯了互聯網的資訊自由共享的原則與市場法規之間的沖突。
但無論如何,互聯網資源共享原則,并不能替百度的慷他人之慨的不義行徑辯護。在中國,著作權保護意識本就很淡薄,而在互聯網自由共享的情況下,侵權事件也就更是屢見不鮮。在許多人看來,這已經成為一種常態。首先,文化產品也可以是一種商品,尤其是當該產品已經明確地以其他方式確定為商品的時候。如作家與平面出版機構簽署有版權契約的公開出版物,顯然已經被確認為是一種商品。另一方面,互聯網空間也并不只是純粹的資源共享平臺,它同時也可以是一個市場。網站可以通過它進行商業活動,文化生產者可以將其視作文化產品的銷售市場。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無條件自由共享的原則就不適用。未經著作權持有人的授權,擅自將他人的作品公開共享,等于是公眾以共享名義,將他人的財產隨意拿走,并置于公共場合隨意享用。作家們的維權宣言書將百度文庫不合法的共享文獻稱之為“贓物”,似乎有些夸張,但百度為這種被隨意挪用的財物提供了共享平臺,這也在某種程度上鼓勵了這種不法行為。如果說公眾對相關侵權行為并不知情,百度這種專業的互聯網機構恐怕很難為自己開脫。百度網站本身也并非純粹的公益網站。這一類的網站雖然往往在其頁面的下方提供了一份效用可疑的“免責聲明”,但實際上它并不能排除其與商業利益之間的密切關聯。
作家維權事件剛剛發生,它究竟向何處發展,尚不得而知。如何在不違背互聯網資訊自由原則的前提下,保護文化生產者的合法權益,仍是當下的一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