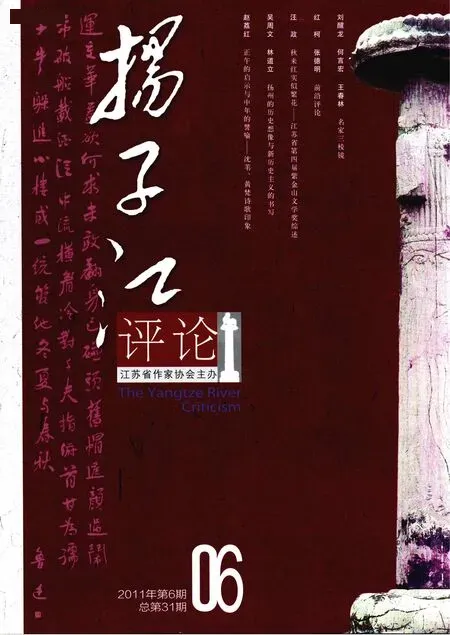語言的功能與詩歌的本性
李心釋
一
語言用來指稱世界,通常人們會想當然認同。而在這無疑處有缺口,世界并非先在,世界是被語言構筑出來的,我們所言說的,所能理解的,則是語言預先給了我們這種可能性。但是經驗依然這樣不可抗拒的原因在哪里?也許是我們太自以為是,把自己看做世界的中心,錯誤地以為為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就一定是我們的附屬品,而我們自己才是自主的。世界也并非是神秘到超乎人力而被預設,也不過是唯物主義教導的結果。語言用來指稱世界這一工具論經典看法,具有極強的現代性,如今現代性內部的裂痕已充分顯現,我們應該來反思語言的功能。
雅柯布森的語言六功能說拓寬了語言工具論的內涵,同時又導致了工具論的動搖,其中表情功能可歸入廣義的指稱功能,因與狹義指稱只有指內與指外之別,呼吁功能與寒喧功能多少有些原始,似乎是對動物發聲功能的強化,也有較強的外向指稱性。然而,詩學功能與元語言功能卻跟人對語言的工具性使用目的格格不入,元語言功能體現了語言自身的生產性,自我設定,自我繁殖,恰恰是語言借助人來進行自身的生產與擴張,而詩學功能則完全跟世界無涉,只展現語言自身的美學原則,如同音樂之音符、繪畫之色彩,對世界的指稱變得可有可無。詩學功能不獨在詩歌里,也不獨在文本里,小說里、日常話語里亦可見,一句話里亦可見,其與語言的其它功能往往糾纏在一起,但這個poetic function,正是從poetry(詩歌)里得到最充分的展現。筆者認為,工具論動搖之后的語言功能觀一分為二,即語言自主論和語言指稱論,前者包括詩學功能和元語言功能,后者包括雅氏的其它四種語言功能。
語言自主論可以參照列維納斯的他者學說來理解。從笛卡爾開始,現代人對待世界的態度是絕對的自我,一切不同于自我的他者要么被吸納,要么被排斥出去,兩者實質一樣,如列維納斯所言,過去文明的歷史就是“將他者縮減為自我”的歷史,存在屈從于概念,現實屈從于理性的安排,這本質上是一種暴力與統治。列維納斯主張顛覆西方的這種“自我學說”,認為他者絕非自我的投影或投影屏幕,也不是跟自我不相關的自給自足之物對自我的襯托,我們僅僅因為他者是他者自身而去接受它。語言自主論說的就是,語言也是一種他者存在,對于語言,我們不可用工具論來控制它、同化它,而排斥語言中的神秘力量。我們要獲得與語言的相處之道,對語言的理解首先不在闡釋、研究,而是維護、接受語言作為他者的地位,在人與語言之間的關系中達到理解。
二
我們不能容忍任何無意義的語言,而意義為何物?自古至今哲學家們并未弄清楚,雖然常識一再被懷疑,意義與指稱的聯系也變得脆弱了。對意義的追尋有原子方向與宇宙方向兩條路徑。原子方向就是切分語言,把語言往最小的可能單位切分,像索緒爾、葉爾姆斯列夫等語言學家所做的那樣,所指與能指的區分揭示了語言意義產生的條件決不可能來自世界,而是來自語言系統內部,當然也就不可能來自于人,人的意圖意義僅僅處于意義的外圈,是附加性質的,語言學家甚至不屑于去研究它。后來無論是福柯的“人(主體)死了”、羅蘭巴特的“零度寫作”還是德里達對形而上學的批判,都深深刻下索緒爾語言學的印跡。宇宙方向則引進人類學的語境概念,意義是一種語境效果,而語境既是百科全書似的,也是瞬息萬變的,對語境的把握極易退回到人類中心的位置上,每一個語言符號都是一個雙面的圖示,即標記與被標記,而我們經常忘掉其被標記的一面,也就忘掉了它以標志一個在它自身之外的“存在”為基礎,即試圖說出它所缺乏的東西。語言就是這樣在無休無止的差異系統中傳達意義,德里達極大地強化了索緒爾的聲音,大聲疾呼意義永遠不在場!但那又如何解釋我們日常經驗中的意義感?德里達給出幾種可能的解釋:一,意義是無根據的差異活動的第二位效果,來自于各個標記之間的“空白”(符號學家艾柯亦作如是觀),這一“空白”可以用羅蘭·巴特的“滿足”來解釋,即“被標記者從一個外殼逃進另一個外殼……人們得到了滿足——標記的領域”(《符號王國》法蘭克福1981,P65),對照人們在下棋等游戲活動中所得到的意義感,這一“滿足說”是有說服力的;二,符號的這一特性使得意義不可能是一種關聯所涉及的東西,即所謂的指稱,而是一種區分的關系,是區分的力量導致意義;三,德里達在《繪畫的真理》里所提出來的,如同畫圖時先確定邊框,然后才能確定畫作的內在空間,一種解釋或文本模式就是提供了這樣的邊框,意義在其“論證”過程中呈現。
嚴格地說,任何文學文本都能為語言特性所決定的這一意義呈現面貌。現實主義傳統文學的強指稱傾向和后現代文本中的“能指滑動”分別是兩種極端的語言功能觀標志。事實上,強指稱論文學到頭來還是語言如來佛手掌中的孫悟空,其文學價值并不在于它們對世界的介入有多強或多深,而在于隱匿于背后的語言符號區分活動所建立的可能意義圖景,作者的努力提供了意義創建的外部動力;所謂“能指滑動”,也決不是無意義的語言符號能指的漂移,因為不存在脫離所指的能指,如同人作為能夠領會“存在”的存在者,人在“能指滑動”中傾聽語言,這是后現代作家的語言功能自主觀的典型反映,是人祛除自身魅力的一個手段和過程,雖然過分地強調了語言作為他者的力量(語言的存在方式與人的聯系如此緊密,具體的言語作品不可能是一個與人無關的單純的他者力量顯現場所),但似乎還不足以徹底改變文學中的語言工具論傾向。
三
從語言工具論角度看,對于詩歌的介入問題是很好理解的,世界在語言之外,寫作若需要一種道義,則必然介入世界。從目前公認的寫作倫理看,詩歌的介入性問題甚至是個偽問題,并沒有文學寫作不具有介入性。然而,這是一個為自我中心者所繪制的表面圖像,將道義凌駕于寫作之上的圖像。
我們不妨先從薩特的問題開始。“介入”語義無論在中文還是在西文里都是個動詞與之對應,起碼聯系兩個論元,即介入什么和誰介入。關于介入什么,原始情境是薩特指小說、散文等作者通過文學文本對社會公共生活的介入,“介入”指的是有意、有目的地產生影響。所以“介入”一詞還隱含其它論元,如拿什么介入,以什么方式介入。詩歌作為介入方式無可厚非,詩歌作為介入工具的歷史由來已久,古代的“詩教”即是。
在所謂“介入文學”的始作俑者薩特那里,有沒有“介入的詩歌”是一個業已了結的問題。薩特在闡釋“介入文學”的含義時,明確地將“介入性”賦予了散文(主要是小說),散文藝術的“讀/寫”關系,差不多就等同于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建構了一種公共交往關系。因而,散文的寫作機制關涉到社會公共生活的制度。這樣,“介入文學”也就是要求寫作者參與到某種公共生活制度(在薩特看來,應該是民主化的生活制度)的建設過程中去。薩特寫道:“散文藝術與民主制度休戚相關,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保有一個意義。”
如果薩特真的聲稱,正是因為自己熱愛詩歌,才不愿意讓詩歌過早地“介入”也許是“骯臟的”現實生活(正如薩特在《骯臟的手》中所認為的那樣),這是荒唐的,詩歌的介入性與非介入性并不由某個人的提倡而改變,更不是因人而異。如果是這樣,薩特也不必在這里談詩歌的非介入性了。“介入”這個詞本身包含了不介入的可能性,而不介入,對于一個從現實中產生出來的事物,又是永遠不可能的。
薩特說:“因此,當我說話時,我通過我要改變的某個處境的謀劃本身去揭露這個處境;我向我自己也向其他人揭露它,以便改變它;……通過我說出的每一個詞,我都使我進一步介入世界,同時我也進一步從世界里呈現出來,既然我向著未來超越它。因此,散文作家是選擇了某種次要行動方式的人,人們可以把這種方式稱為通過揭露而行動。”注意,這里談的是“我說話”,但詩歌決不是人在說話。他說“文學是一面批評的鏡子。顯示,證明,表現:這就是介入”。詩歌同樣不處于“顯示、證明、表現”的鏈條之中。所有“說話、顯示、證明、表現”都是以語言為工具而非以語言為自身目的的寫作,當語言指向世界、作者與世界的關系時,就必然是介入性的。然而,從語言自主功能角度看,詩歌有一種本性跟其它文學文本不同,在詩歌里,語言不是作為工具去證明或闡述某種與世界相關的東西,而是以語言自身的美學原則為目標,就像一段旋律與畫面,至少它首先指向的是自身的可能性與完美性,所以我們會說“詩歌的語言有一種自足性”。就詩歌的接受與詩所展現的語言面貌來看,其與音樂、繪畫等同質,你很難再用日常語言描述詩歌,而很容易用日常語言描述小說或散文,兩者旨趣不同。我們必須記住,語言意義的來源并非那個與現實世界相聯系的環節,那不過是個外部環節或意義的錯覺。站在符號無限差異的點上,詩歌的本性就是語言的本性,“自足性”的意義來自差異系統本身,與世界無涉。
四
問題是語言跟人脫不了干系,人與語言的關系并非日常語言經驗所呈示的那種樣子,直到索緒爾、維特根斯坦出來了,人們才真的認識到語言限定了人,限定了人的世界,不管這語言是不是上帝恩賜的他者,人都必須面對語言、傾聽語言。日常語言更多的像是人的理性暴力對語言駕馭的結果,人在其中得意幾千年,終究開始敬畏起語言。詩歌所葆有的就是這一語言力量,它以呈現語言的詩性為己任,決不是日常語言功能延伸之地。那種闡釋古詩的一貫口吻如“這首詩表現了詩人懷才不遇、寂寞無聊的情緒”,外行得多么可笑,一旦闡釋,我們前面的東西已非詩歌,而是運用來做什么的東西。所以,小說、散文等可闡釋,只因為它們本身就歸屬運用語言做什么之列,而詩歌、音樂等不可闡釋,屬于“是其所是”之物,屬于他者,對待他者,我們可以建立交流關系,卻不可威逼其就范。
我們對事物的理解通常有兩種模式:日常語言的模式和藝術欣賞的模式。由于實用研究與娛樂文化造成時代精神的極度淺薄,對文學的理解即便在大學里,也是籠罩在日常語言模式之下,其典型征兆是庸俗圖解與過度闡釋,桑塔格反對闡釋的呼聲值得當代人深思。因為詩歌是語言藝術,一個對語言特性領悟不深的人,很容易陷入前一模式的轍痕里。不否認詩歌中的符號有一定的指向性,但它無不是“含蓄意指”(具體內涵參見羅蘭巴特《符號學原理》)的結果,離日常語言已遠。一個平庸的詩人會用日常語言的闡釋法對之進行二度符號化,這樣“詩歌”當然可以完全地解讀,如一些諷喻詩、政治詩、歌功頌德的詩、提倡某種立場的詩,但已變成前面所說的運用詩的形式做出的東西,跟詩歌相距已遠。日常語言最大的特征是它對世界的強指稱性,若不落實到它所指向的世界,就無法滿足人們理解的欲望。藝術欣賞模式與此相反,它反對指稱,只在對象自身的美學法則里去感受,達到領會與理解。人們若問“這首曲子你聽懂了嗎?”這會讓人無法回答,音樂不可能是通過日常語言模式的“懂”而被理解的,只要你被感動就一定是懂了,但你只能說“喜歡”什么,而非“懂”。
詩歌是語言意義的差異游戲,是語言聲音、節奏、語調等的美學游戲,這一游戲展現的是語言的可能景觀,亦即世界的可能景觀。如果語言完全是人所控制的,那么這種游戲就沒有什么意義與嚴肅性,如果我們尊重語言是一個他者,一個嚴重影響并介入我們生命的他者,那么這一游戲就會顯得意義重大。因此,一個詩人如何對待語言,語言也將如何對待他的詩歌,如果寫詩者以語言工具觀作詩,很可能到頭來他的詩歌僅僅是無意義的語言游戲,如許多極其嚴肅的為革命而寫的詩歌在今日看來竟相當可笑;當代大多數詩人持詩歌技術論,他們把語言玩得團團轉,把詩歌寫得很像詩歌,或很先鋒,不時有得意之作,也終將為語言所唾棄。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壇的確迎來了語言的覺醒,但是,遠未走出語言工具論,識得語言的力量,卻試圖據為己有,此乃技藝論者,當代有多少所謂的優秀詩人都位列其中,而真正尊重語言這位他者、聆聽語言的詩人,還羞答答地蹲在角落里。
技術(藝)論者最喜歡引的例子是繪畫藝術,在不可闡釋的特性上詩與畫有可比之處,但語言絕非色彩、線條可比,語詞本身有生命,不止在詩內,它們不是詩人降伏的對象,語詞的面貌迫使詩人對它們作出回應,學會跟它們相處。在我們如此言說時,實際上在不斷重復老掉牙的意思,看看第二語言學習者們,就知道什么是陳詞濫調。為詩所維護的語言本身是詩,是創造和創造的痕跡,它召喚人的加入,并立這個人為人。故此,只存在解除日常語言束縛的技巧,卻沒有所謂詩歌寫作的技巧。
五
那么詩人與詩歌究竟會是怎樣的關系?我們不必拿腔拿調引用巴特的“作者死了”或福柯的“人死了”來貶低詩人的存在,它們都不過是索緒爾語言觀的引申物,談的不是關系,而是指出過去被侵蝕掉的他者。詩人與人既可以置換,又不可以,詩人是人的理想狀態;詩歌與語言也可以轉換,但現實中的語言不是詩歌,詩歌是語言的理想狀態。在古希臘,言與道同,邏各斯是言,也是道,在老莊這里,言與道有間隙,言永遠言不了道;兩者的“言”不同,前者指本原態的言,后者指沉淪了的言,故而“道”是理想的“言”。在理想狀態下,人、言、道的關系是一而三、三而一,然而在現實中,人要駕馭語言,言恰恰遠離“道”,語言為我們所說時,實際上并沒能說出什么。詩人保持人的理想,與理想的語言打交道。有兩位德國精神病醫生說,人的原罪即在對立思維里。對立思維在于“自我”的確立與執著。現實里的人要駕馭語言也是對立思維的產生,是“自我”使然,只有祛除“自我”之病,人與言才可能重歸于好。老子教我們的是“致虛靜、守靜篤”,那是他拋棄“自我”執著的方法,在這一狀態里,人有了“道”的體會,與“道”有了來往。禪宗的偈語則以“不”,以現實語言合理性的否定,達到去“自我”之迷障,“道”恰恰就在禪宗的言說中尋跡而來。后現代思想家們的法寶也是這個“不”,以“不是”為“是”,把語言從證明中拯救出來。無論是不立言而立言,或以反語言的姿態說語言,都是以悖論的日常語言形式試圖超越日常語言。在語言中反語言也是語言世界所能夠提供的景觀,如同在日常語言中描述日常語言,但人們很難用詩歌來描述詩歌,如很難用音樂來描述音樂、用繪畫來描述繪畫。
詩是原初的言,是道,是立詩人為人者,詩人在詩歌面前是極其謙卑的,詩人傾聽內心,忠實于自己的內心,并不是那個“自我”的內心,而正是在聆聽語言。托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在詩學上以“非個性化”主張而著名,其言曰“詩不是放縱情感,而是避卻情感,詩不是表達個性,而是避卻個性”,太多沒有詩歌實踐的理論家們都聯系詩學歷史概念來闡釋這一背離詩歌常識之宏論,殊不知這只是艾略特立足于詩人的位置所獲得的樸素啟示,情感與個性是“自我”張揚的產物,與詩歌之言存在根本的沖突,在“自我”膨脹之時,詩歌必然隱退,這就是艾略特后面這句話之含義:“只是具有個性和情感的人們才懂得想要脫離情感是什么意思。”
詩人在擺脫駕馭語言及其技巧的圖謀之后,人們也許會擔心詩歌將僅僅是無聊的、無意義的語言游戲。可“道”是如此奇妙,也許就因為言與道的分離,人以言來“表情達意”注定失效,反之,去揣摩語言對當下的你會說些什么,才有真意浮現,“夫唯不居,是以不去”,詩人并不會因此丟失任何可辨別性,詩歌的語言就像蘑菇,什么樣的木材上長什么樣的蘑菇。當把語言當工具來調遣時,表面上嚴肅,實質上反而是語言游戲,如同我們社會的一些制度和道德話語,嚴肅而滑稽,甚至荒唐。大家或許對達達主義的詩歌和繪畫心存芥蒂,但是若懂點精神分析心理學,就會明白“自動化寫作”不僅不是對語言的尊重,反而是污辱,自動化寫作放棄的是自我,進入的是無意識中太多的大眾意識的渣滓和語詞碎片。
今年中國人民大學多多詩歌朗讀會上,多多還在不厭其煩地講著詩歌的常識:“詩歌應該是什么?欣賞,進入語言,詩歌實際就是一種語言,建構語言的存在,它什么也不是。……詩歌就是欣賞語言,進入詞語。怎樣進入它,這才是對讀者的考驗。”估計在場者沒有幾個真的能理解“詩歌實際就是一種語言”。
六
這又得回到介入性問題上來。文學的救世觀念或“文以載道”觀念在中國人頭腦里嵌入如此之深,或者并不是,只是語言指稱世界的日常語言經驗,是那樣的不可抗拒而已,詩歌不能只是語言,詩歌必須與現實世界相聯系,否則詩人怎可能成為社會上受尊重的一類人,詩人的稱號理應包括道義的光輝。
詩歌并不介入,介入的詩歌根本不是詩歌,只為介入而寫作的詩人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詩人,歷代如此,但詩人可以寫作介入的詩歌,詩歌可以被解讀成介入的詩歌,也可以作為一種語言的功能來介入社會政治生活。大量的被解讀成介入的詩歌誘導人們對詩歌的本性走向很深的誤解,古今中外具有強烈介入精神的詩人不勝枚舉,不外乎詩作內容關涉了生活現實,并反映了批判的立場,而這些正是日常語言所能闡釋的部分,與詩歌本無涉。
我們不妨換個角度看,如果將薩特關于“介入”的公共生活制度內涵擴大到整個現實生活,就沒有什么言語作品不是介入性的。像索緒爾看到的,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制度;像福柯看到的,人所說的都是話語,而話語必是權力,權力不只在制度中生存,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遍現象,那么詩歌作為一種言語作品,如何能逃脫介入的命運?現在我們可以明確地說出,詩歌之所以為詩歌,它的目標就是為了逃脫制度與權力,在墮落的語言上建立或恢復原初語言,在日常語言的夾縫沖出語言的新芽,而它的材質或內容則命定嫁接在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語言層面上。所以我們只能從是其所是之成立的一面看待詩歌,而不是從外在的內容。內容附加于成立條件之上,就像差異先于符號的內容,先于符號之間的區別,每種語言都在差異中,而每種語言的區別系統各不相同。
夜所盛放的過多,隨水流去的又太少
永不安寧的在撞擊。在撞擊中
有一些夜晚開始而沒有結束
一些河流閃耀而不能看清它們的顏色
有一些時間在強烈地反對黑夜
有一些時間,在黑夜才到來
女人遇到很乖的小動物的夜晚
語言開始,而生命離去
——多多《北方的夜》(第二節)
詩歌的語言跟詩里的“語言”形成鮮明的對照,前者是詩人謙卑聆聽的對象,后者是時刻為詩人所排斥的。這里沒有任何“表情達意”,散亂的、多向的、并列的、錯置的語詞,什么也表達不了,這里只有語言中的差異在流動,“有一些”的重復卻是用于差異的涌現,在這差異的空隙里,詩人獲得了語言對當下自己的應答。
甚至在詩人與詩歌的關系中,詩人的作用是為詩歌建立一道堤壩,抵制庸俗世界的入侵,堤壩所展示的或許正是這個詩人的獨特性和高度“自我中心”化的語調,一旦放松,語言就會被世界帶走,也就沒有了詩歌。
介入是詩歌的一個功能問題,也是語言的指稱功能問題。零度寫作、寫作的不及物性等概念,羅蘭·巴特談的都是詩歌的非介入性,而后來一轉而為“非介入”也是介入的一種形式,不過是將“內”運用于“外”罷了,并非什么自相矛盾之語。他寫道:“正是此時,作家可以被說成是充分地道義介入的,此時作家的寫作自由存于一種語言條件的內部,其局限即社會之局限,而不是一種規約或一群公眾的限制。”這個“語言條件的內部”是關鍵,作家必須以語言的方式反抗語言,詩歌或零度寫作是對已有語言條件的反抗,我們通常所使用的語言不是外部的規約,卻是無形的更強有力的社會性限制。因此,非介入的寫作對當前人類社會狀況而言,就具有了介入性。我們的文學總走在兩個極端之上,要么風花雪月(當然在政治高壓環境中,亦具有介入性),要么受強烈的介入性使命所迫,有過如人生問題小說、底層寫作、政治抒情詩等等。只有嚴肅對待詩歌的非介入性特征,才有可能對介入性有充分的道義認識,才不會為介入性所破壞。
七
那么,詩歌是否屬于介入文學是個偽問題。介入就像人要吃飯,不吃飯的人有,但一定是理想的人,是神仙,而神仙也講美食,仙界還有仙桃呢。問題在于你對吃飯看中什么,有些人把飯吃得好像飯沒有來路,天上掉下來似的,有些人則念念不忘飯的辛苦來源。偽問題在哲學上沒有意義,在文學上卻有言外之意,談介入與不介入都是有意圖的,薩特有薩特的,巴特有巴特的,有用“介入”強調文學道義的一面,有主張“不介入”強調詩歌的美學一面,實際上與介入、不介入無關。
我們注定無法舉出一首絕對“不介入”的詩歌,就像蘭波、馬拉美等人提倡的“純詩”也永遠不“純”,所以,舉出杜甫、拜倫、雨果等人詩歌的例子說明詩歌同樣是介入文學,也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現代中國的抗戰詩、朦朧詩等無不具有強介入性,甚至還能舉出強介入性的繪畫與音樂作品,這能說明詩歌本身的什么問題呢?也許,將既非有意,又無目的,更無預先的介入內容,而結果又不可避免地介入世界的介入性,定義為“非介入性”更加合適,畢竟除此之外的介入類型就跟詩歌藝術無關。
詩歌是一種反常的、天生叛逆的語言知識,詩歌具有天生的道義力量,她并不是由人賦予她的,人選擇詩歌來做道義的事件,那是人的事,不可把這從詩歌那里歸向人。杜甫可以把詩歌寫得非常介入,李白、陳子昂也可以把詩寫得一點也不見介入,郭沫若可以很有時代精神,徐志摩可以非常個人化,然而,它們能成為詩歌的都不是這樣的東西。
像芒克的《陽光中的向日葵》很容易被解讀成強介入性的詩歌: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陽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嗎
你看它,它沒有低下頭
而是把頭轉向身后
就好象是為了一口咬斷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牽在太陽手中的繩索
——芒克《陽光中的向日葵》(第一節)
這是語言對某一當下的詩人芒克的回應,跟現實生活的暗示毫不相關,這是語言的舞蹈或表演,它把當下的詩人挾裹進去,在語言的聲音與意義的起承轉合之間,詩人安頓了自己的內心。如果詩人在用漢語這一工具表情達義,那么這太陽、這向日葵都將有明確的指稱,都可以用另外的明白無誤的語詞來替換,想想看,與此類別的表達何其多,而這首詩又有多庸俗,這時,詩人不但沒有保護詩歌,反而引進世界的病毒謀殺了詩歌。
詩人在語言中的安頓可以達到像陳子昂《登幽州臺歌》里的驚心動魄,也可以是卞之琳《斷章》的意蘊悠長,它們都決不是現實中的表情達意可以說明的,陳子昂沒有苦大仇深,卞之琳亦非小女人心腸,除了漢語創造的奇跡之外,除了他們蒙受漢語幸運的眷顧之外,別無解釋。
我們必須學會分開內容與形式,甚至像葉爾姆斯列夫那樣進行四分,否則無法談清詩歌的功能與本性,像語言與人的關系,所有的語言都從人的嘴里說出,又怎么可能是語言說人?我們稱之為形式的是更抽象的內容,一般的內容則處于對語言的使用層面,任何對語言的使用必定具有介入性,使用與目的、內容等都相關。事實上,一切都存在著淪為工具的危險,后現代社會中的情形更是如此,如同“中性的”、“零度的”、“非介入的”寫作,竟可用作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抵制和逃離。當年思考詩歌本性的各種朦朧詩流派,有多少都不由自主卷入政治意識形態的斗爭之中,所謂新生代以來的詩人,當他們拒絕“政治性介入”、拒絕“為群眾寫作”成為一種姿態與立場之后,又是以政治性介入方式,替代內容為“普泛的人類命運”、某種“文化精神”、“時間”“虛無”“死亡”等哲學語匯或“圣詞”,于是又有人出來造反,反文化、反“圣詞”等,詩壇斗爭不斷,觸及詩歌本性的東西微乎其微。個人化寫作的詩歌,不幸又背叛了艾略特的遺囑,進入到無限制的自我囈語般語言狂歡的詩歌生產中。據說許多心懷天下的詩人出來聲明,以往的寫作在今日失效了,應重新去思考詩歌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對這種頑固地深陷于“介入”思維中的詩人來說,詩歌寫作成了用詩歌介入現實的方式,他們好戰,好談“介入”,寫作的可能性不過是詩歌功能的可能性,他們甚至歪曲謝默斯·希尼的話(“詩歌首先作為一種糾正方式的力量——作為宣示和糾正不公正的媒介——正不斷受到感召。但是詩人在釋放這些功能的同時,會有輕視另一項迫切性之虞,這項迫切性就是把詩歌糾正為詩歌,設置它自身的范疇,通過直接的語言手段建立詩歌的威信并對現實施加壓力”),達到對詩歌介入功能的強調。所謂的寫作方式,歐陽江河的《計劃經濟時代的愛情》、鐘鳴的《中國雜技:硬椅子》、蕭開愚的《動物園》、孫文波的《祖國之書,或其他……》等詩歌,因其跟當代中國現實的強關聯性、強介入性而被推崇,這些詩歌充斥了跟現實平行的詩句,不同的是這里有各種各樣對語詞的扭曲使用和造句的機智。
百年漢語詩歌,應該盡可能快地斬斷“介入”思維模式了,否則漢語詩歌的質量必像今日一樣徘徊不前。讓我們爆一聲:詩歌只是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