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精神康復領域的拓荒人
——記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安定醫院主任醫師、首都醫科大學精神病學教授翁永振
□文 海慧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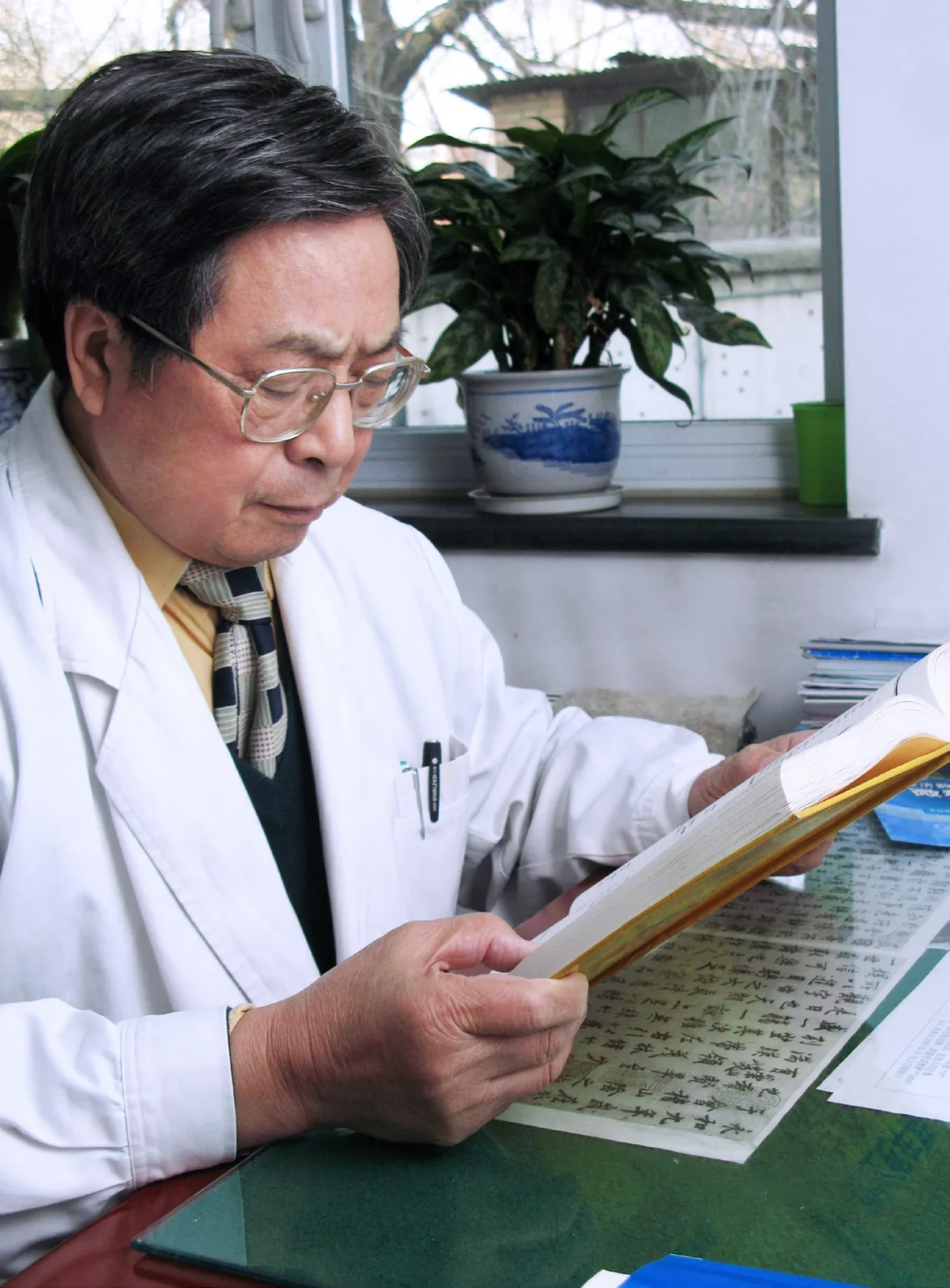
在醫院四周還架著鐵絲網,院區只有簡陋病房的50年代,他毅然選擇來到這片條件艱苦、剛剛開始拓荒的精神學科園地——首都醫科大學北京安定醫院。在我國精神病學開始突飛猛進向世界水平進軍的80年代,年過半百的他,毅然踏上精神康復研究的艱難之旅。在精神康復領域,他著有“中國利勃曼”(利勃曼為國際著名精神康復專家)之稱。從醫多年來,他將國外先進的康復技術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探索了具有我國特色的精神康復技術,并編寫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精神康復專著。他,就是我國精神康復學科領軍人、北京安定醫院原副院長、首都醫科大學精神病學教授翁永振。
初秋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筆者走進了翁永振教授的辦公室。因為上午的門診病人太多,他正在吃午飯。在他紅潤的臉上,筆者沒有看到疲憊,一說到精神康復,78歲的翁永振教授更有了興致,滔滔不絕。
青年時代的他選擇了艱苦
翁永振當年選擇精神科的經歷,印證了一代精神衛生工作者的職業精神與人生選擇。盡管當初的選擇帶有幾分好奇和迷茫,但選擇后他們無怨無悔,幾十年奮斗不息,為精神衛生事業發展夯實基礎,也親身經歷了精神衛生事業發展的巨大變革與滄桑。
1958年,翁永振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后,自愿到北京安定醫院從事精神科工作。當時同學間流傳著“金眼科、銀外科、吃不窮的婦產科”,畢業時,80%以上的同學們都忙著選擇大醫院的內、外、婦、兒科科室。而翁永振在臨床實習時發現,所有科室中,精神科最為落后,設備差,房子破,醫務人員也少。他說:“那時,其他科室的力量都已經很強了,所以我更愿意在精神科做些事情。”在傾聽我國著名精神病學家伍正誼教授的一節課后,翁永振更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丟了軀體健康,人生只是毀了一半;丟了精神健康,人生就全沒了。’伍教授對精神病患者幻覺、妄想的生動描述,深深地打動了我。我覺得那里是一片等待開墾的荒地,有我們用武的地方,我決定到精神專科醫院去工作。”他這樣說。
剛到醫院時,面對簡陋的病房、周邊的鐵絲網,一名醫生管300多名患者的狀況,翁永振沒有感到意外,更沒有改變當初的選擇,一干就是半個多世紀。北京安定醫院當時有3個分院,翁永振所在的回龍觀分院是收住病人最多的。“記得我到北京安定醫院總院報到后,便被分到當時的回龍觀分院,一輛手拉警鈴的救護車,顛簸著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回龍觀分院距城里30多里地,當時那里就是農村,四周一片農田,交通不發達,往返城里只有兩趟公交車,下車還要步行半個小時。雖然很辛苦,但我心里很充實。”
20世紀60年代至今,翁永振見證了我國精神病學發展的突飛猛進。他清晰地記得,他剛來醫院時,醫院實行全封閉管理,患者興奮躁動時,多采用胰島素休克和電休克治療。由于氯丙嗪等抗精神病藥物在國外剛研制成功,尚未在國內批量生產或應用于臨床。那時的精神病房比較混亂:90%以上的玻璃是碎的;怕被打碎而不敢掛上石英鐘,怕被撕毀而不掛日歷;開飯時要把30%~50%的患者固定在床上,不然粥桶就會“飛上天”。
但隨著抗精神病藥物的廣泛使用,精神衛生機構的面貌隨之改變,病房開始安靜有序。伴隨生物學治療時代的來臨,我國精神病學快速進步:精神衛生機構推行開放式的管理模式,各地區都開展了精神病防治工作,精神衛生工作者積極探索我國的非住院化與社區防治工作,研究逐步與國際接軌。
半百之年的他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上世紀80年代末,年過半百的翁永振踏上了研究精神康復的艱難之路。最早讓他萌生這個想法的是一個長期住院的患者。他說:“那個患者和我年紀相仿,當我剛開始工作時,他就一直在住院,治療后反復發作20多次,最后惡化致殘。我發現,單用藥物治療不能最終治愈疾病,幫助患者脫離痛苦。所以,我選擇了精神康復領域。”
如何預防精神分裂癥患者復發惡化,是精神衛生領域的熱點問題。有些老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癥的患者,紙脆泛黃的病歷比辭海還要厚。患者發病住院——治愈回家——再次發病入院,如同走入“旋轉門”。在備受煎熬中,患者的社會功能逐漸衰退,最后成為廢人。
“目前,北京市的精神衛生機構僅有6000多張病床,只能接受5%的患者住院治療,十幾萬的患者分散在社區。”面對緊缺的精神科醫療資源,翁永振憂心忡忡。他解釋說:“大部分精神病患者出院后,雖然病情穩定下來,但仍得不到社會的理解和接納,只能放棄回歸社會,甚至是逃避社會,病情往往會陷入惡性循環。因為這其中缺少一個中間地帶,即在住院治療與回歸社會之間為患者提供一個過渡平臺,使其保留社會能力,培養自信心、成就感,具備一定的生活、勞動技能,為日后融入社會打下基礎。”

▲1991年10月,翁永振(前排左一)在洛杉磯訪問美國專家

▲1983年4月,翁永振(左一)在美國兒童精神病學學術會議上發言
翁永振指出,對于精神病患者而言,回歸正常人的生活才是最好的康復治療。“早有研究證明,由家庭為患者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由經過培訓的社區醫生組織康復活動、提供醫療支持,是最理想、最省錢的康復模式。但目前,社區康復基本還是空白,在病人出院后,只有社區醫生定期訪視或送藥,沒有有計劃的康復訓練。而由患者需求催生而來的康復農場等專業康復機構,本質上也只是從住院治療到社區康復的過渡場所。”他惋惜地說:“顯然,社區康復環節的缺失,是造成精神病患者深陷‘旋轉門’的癥結所在。”
于是,探索有效的精神康復技術,使其廣泛應用于社區康復之中,成為翁永振多年來執著的事。他拜訪了國際著名的精神康復專家利勃曼(Robert P.Liberman)教授。為了汲取國際精神康復的經驗和做法,他從加拿大的溫哥華一路向東到了蒙特利爾,考察了加拿大5個城市的精神康復工作。望著精神病患者自己管理的餐廳,以及足以養活他們并帶來快樂的福利工廠,翁永振由衷地羨慕和感嘆。他深深地感受到,精神康復是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回歸家庭、自食其力、自尊自強的唯一途徑。20年來,他致力于精神康復的研究,與瑞典、美國、加拿大、日本、荷蘭、法國及中國香港、澳門的精神康復研究中心和康復機構建立了廣泛的聯系,他將國外先進的康復技術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探索了具有我國特色的精神康復技術。

▲翁永振(右)和利勃曼(左)在交流
1992年,北京安定醫院率先從美國加州大學引進“技能訓練程式”精神康復技術,17年來通過5項科研項目的資助,對其預防精神分裂癥患者復發和再住院的作用開展探討。項目負責人翁永振經過10多年的研究和實驗,編寫了一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精神康復專著,并通過實踐證明:該康復技術的應用使重性精神患者復發率顯著降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1年復發率從55%降至12%,1年再住院率從39%降至3%,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都顯著提高。
翁永振解釋說,為使精神病患者康復后能獨立生活并回歸社會,必須訓練他們的3大技能:藥物自我處置技能,即掌握抗精神病藥物作用的有關知識,正確管理和使用自己所服用的藥物,識別和處置藥物的副作用,并能與醫務人員商討和藥物有關的問題。癥狀自我控制技能,即能夠識別、控制自己病情復發的先兆癥狀,并較好地處置持續癥狀,同時用所學技能拓展社交范圍,提高防止疾病復發的技能。社區獨立生活技能,即制定回歸社會的具體計劃,學會與周圍人正常交往,并應付生活中的種種壓力。
翁永振分析,因為患者常有認知功能明顯下降,分析、綜合能力都有缺損,用通常的方法教精神病患者如何防止病情復發,一般是無效的。我們引進這套特殊的技能訓練程式,通過模擬演練、小組討論等多種形式的培訓,提高患者自我處置用藥的能力,培養其人際交往的能力和技術。病人獨立生活技能的提高,有可能降低對專業人員的依賴,早日回歸正常人的生活。此外,也節約了醫療資源,讓有限的資源為更多的病人服務。
一次國外調研的經歷令翁永振記憶猶新。他在訪問美國道瓊斯公司時,看到有很多精神病患者為公司服務。他們與普通職員一樣佩戴胸牌,忙忙碌碌,從事信息傳遞、報紙收發等基礎性工作。當詢問公司人事部門“為何敢于接受精神病患者”時,對方的答復是:“我們基于對康復技術的信任,他們在工作中也很敬業。”
“這項精神康復技術曾使歐美許多精神病患者受益。我敢預言,該項技術引入國內后,能利用現有資源為更多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務。”翁永振信心十足。
甘為精神康復事業架橋鋪路
翁永振強調,院內康復與社區康復相結合的康復模式,將有助于精神病患者走出“旋轉門”困境。但無論從資金投入、人員水平,還是發展規模、覆蓋范圍而言,我國目前精神康復事業的發展現狀都難以滿足社會需要,還要付出相當多的努力。可喜的是,國家已開始重視并關注精神康復工作,但還需更多的政策支持和保證。
此外,培養一支專業化的精神康復師隊伍也迫在眉睫。作為國內精神康復領域的權威專家,翁永振多次呼吁:國內精神康復事業處于起步階段,經驗不足,再加上當前我國還沒有精神康復師的職稱系列,人才隊伍很不穩定。他說:“我們在北京市的東城區、宣武區、平谷區、朝陽區4個區縣,開展了為期8年的社區康復項目取樣工作。這些具備城市、農村、城鄉結合部等類型特點的地區實踐,從多個角度證明了我們康復技術的科學有效,也受到患者、家屬及精神衛生工作者的一致好評。我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建立一個長效籌資機制,將技術廣泛推行下去。目前我工作的重心,是利用一切機會向外推介這項康復技術,推動其功效早日展顯現出來!”
提及對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展望,翁永振說:“我深深感受到,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精神衛生事業碩果累累,但相比綜合性醫院,精神衛生機構的實力仍然比較弱,要發展壯大,還任重道遠。我期待并堅信著,通過不斷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一定會為精神衛生事業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