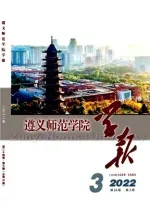雙語對兒童認知發展的影響
李文權
(遵義師范學院初等教育系,貴州遵義563002)
隨著我國逐漸與世界接軌,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對外聯系日益密切,外語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為了滿足人們對掌握外語的迫切需要,在上海、遼寧、山東、廣東、江蘇等省市的許多地區,雙語教學和雙語學校大有“燎原之勢”。一些雙語研究機構開始建立,有關雙語教學的交流和研討活動也不斷開展。短短的幾年時間,雙語教學已成為教育和社會共同關注的一個焦點[1]。有關雙語問題的爭論較多,但探討雙語對兒童心理品質發展影響的較少。這一問題的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有助于深入了解語言與思維的關系,也可為我國的少數民族雙語教學和外語教學提供心理學理論指導。
國外對雙語影響研究的主要領域之一是雙語和認知發展的關系。大量的研究試圖明確地把雙語和認知發展及學術成就聯系起來。這些研究有的支持雙語對認知發展有積極的影響,但有的卻發現相反的效果。
一、雙語在認知發展上的積極效果
皮耳和朗伯(Peal and Lambert)設計了一項研究去檢查雙語對兒童智力方面的影響,并調查雙語學生學業成績和學生對第二語言社區態度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雙語兒童比單語兒童的言語和非言語智力發展更好。在皮耳和朗伯的研究中作為被試的雙語(法語-英語)兒童,由于在兩種文化和語言中的經驗更廣,他們表現出單語兒童所不具備的一些優勢。具有兩種語言系統的經驗促進了心理靈活性、良好的概念形成和更多樣化的心智能力。另一方面,單語兒童表現出了更單一的智力結構,他們對各種智力任務都只有使用這一結構。雙語兒童在學校的表現也比單語兒童好,他們在英語學習中的成績也明顯高于同班同學。他們在學校較好的學業成就依賴于對言語的敏感性[2]。
在托蘭斯(Torrance)等人的研究中,新加坡學校3、4、5年級的單語和雙語中國人、馬來人兒童接受了托蘭斯創造性思維測驗。測驗的小冊子被翻譯成被試的本族語,所有的指導都用學校的教學語言即漢語、馬來語或英語進行。用標準的操作指導對測驗中的流暢性、靈活性和精致性進行評定記分。對獨創性記分的指導建立在新加坡文化資料基礎上,依據這個測驗美國版發展的原始評定標準相同的原理進行。[3]總體上,單語兒童在流暢性和靈活性方面比雙語兒童表現好,但獨創性和精致性卻表現出了相反的趨勢。在精致性方面總體差異明顯,但在獨創性上差異不顯著。如果對一些回答進行矯正,雙語兒童在獨創性和精致性上優于單語的趨勢會變得更加明顯。
沃爾(Worrall)設計了幾個實驗檢驗利奧波德(Leopold)對雙語和單語兒童配對的早期字音和字意分離的比較觀察。兒童對字詞的語音或意義的注意用語義語音傾向測驗(Semantic and Phonetic Preference Test)進行評價,測驗中字詞之間的相似性可以在有共同意義或聲音屬性的基礎上進行解釋。
雙語導致對物體命名關系更早的隨意性這一觀念受到了維果次基(Vygotsky)發展的提問技術的檢驗。這項技術要求對名稱進行解釋,名稱是否能互換,并解釋在游戲中名稱互換時,對象的屬性是否隨之改變。實驗結果支持了利奧波德的觀察。在4-6歲的雙語兒童中,54%的兒童一致選擇字詞間的相似性是根據語義維度來進行的[3]。
利奧波德歸納得出的結論為:在雙語環境中成長的兒童比單語同伴在語義發展方面早2到3年達到較高水平。多數雙語兒童根據字詞的象征屬性而不是聲音屬性感知到字詞間的關系。
皮亞杰思想在雙語研究中的應用也有學者探討。皮亞杰式的任務有自身獨特的優勢:這些任務便于管理和操作,可以保證任務的內容被標準化而不必是教學用的語言;實驗者也能注意確保被試理解要完成的任務。在評估小組的認知作業時,這肯定是很重要的。對這種小組進行有效、可信的評價是個難題。例如,泊得門和斯本(Paldman and Sben)開展了一項研究,證明5歲雙語兒童有預期的來自2種語言的優勢:物體恒常性、命名、句子中使用名稱。此外,還建議物體恒常性應該在命名之前發展(正如皮亞杰建議),命名應該在句子中使用名稱前發展。單語和雙語的5歲兒童還專門在完成物體恒常性、命名和句子中使用名稱這些任務中的能力接受對比。這3個任務構成語言技能的自然序列。雙語兒童比單語兒童更容易完成這些任務。這在非言語測量中非常明顯。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在句子中變換名稱時雙語兒童占優勢,而2組在名稱知識和獲得新名稱的敏捷性方面是相當的[4]。
利德克和納爾遜(Liedtke and Nelson)的研究考慮了早年雙語的經驗對心理發展的影響。他們把雙語兒童和單語兒童概念發展的某些方面進行比較。線性測量的概念測驗(Concepts of Linear MeasurementTest)成為最初的研究工具。這個測驗包括6個針對線性測量方面的分測驗:1.距離的重建關系;2.長度守恒;3.位置變換的長度守恒;4.形狀扭曲的長度守恒;5.長度測量;6.對直線繼續細分。雙語兒童在測驗中的平均成績明顯高于單語兒童,這與皮耳和朗伯的發現(雙語對智力發展有積極影響)是一致的。雙語組在這個測驗的守恒部分的平均分也顯著高于單語組。雙語兒童比同齡單語兒童顯示出對概念有更好的理解[5]。
總之,這些結果表明,雙語兒童語言和文化的經驗是一種有利條件。此外,這些結果也顯示,屬于雙語或在變成雙語會加速某些心理成分的發展。
二、.雙語在認知上的消極或模糊效果
達西(Darcy)的一項早期研究將雙語組和單語組的被試按人數、性別、社會經濟地位和差距在6個月內的年齡密切匹配。研究結果表明,雙語組被試在斯坦福-比奈智力測驗上的表現明顯不及單語組,但在阿特金斯對象擬合測驗(AtkinsObject-FittingTest)中卻顯著優于單語組。對這種雙語影響不盡一致的結果,多數專家認為達西用斯坦福-比奈測驗研究的雙語被試可能經歷了語言上的差異,因為斯坦福-比奈測驗上的作業任務要求被試有較好的英語掌握背景。一些學者(Brown,Foumier,and Moyer)發現,美國的墨西哥兒童在針對科學概念和皮亞杰的具體推理測驗的成績顯著低于相對應的英國裔美國兒童。他們的研究人群由科羅拉多州鄉村的墨西哥裔和英國裔美國5年級學生組成。墨西哥裔被試的特征是有西班牙姓氏或者在家說西班牙語。用托蘭斯創造性思維測驗檢查3年級到5年級雙語和單語學生的創造力,各年級單語被試在流暢性和靈活性方面有明顯優勢。雙語被試的成績在精致性方面顯著高于單語組,雖然在新穎性方面只達到一個年級的水平差異[6]。
巴體克和斯維恩(Batik and Swain)的一項縱向研究把參加法語計劃的學生和普通的英語計劃的學生進行對比。3個組每年用奧蒂斯-勒隆心理能力測試(Otis-Lennon Mental Ability Test)進行評價。法語計劃組學生比英語計劃組學生做得好,雖然組別間最初的差異很難歸因于語言學習或者計劃類別。另有一項研究用皮勃迪圖片詞匯測試(PPVT)和瑞文推理測驗把西班牙-英語的雙語學生和只講英語的單語學生的測驗結果進行比較。研究對象來自3個層次的完整班級(幼兒園、3年級和6年級),所有學生社會經濟地位較低。雖然兩組學生在瑞文推理測驗中沒有顯著差異,但單語學生在PPVT上的成績明顯優于雙語學生[7]。
使用皮亞杰的守恒方式測驗,樸羅斯(Pulos)等人發現只講西班牙語、只講英語的單語學生和一年級雙語學生間的測驗成績沒有顯著差異。也許可以假設,沒有發現差異可能在于雙語優勢或許發生在更早或更晚的發展階段[8]。果若爾(Gorrell)等人把2組雙語(越南語-英語、西班牙語-英語)和1組單語學生在韋氏兒童智力測驗中的積木設計分測驗和復雜性逐漸增加的3維空間角色承擔測驗(threespatialroletaking test)中的得分進行比較。他們發現雙語被試的積木設計分測驗比單語組表現好,但在空間角色承擔測驗中沒有這種優勢[9]。
三、評價與展望
在這一領域進行的一系列研究中,由于分組方法上的錯誤、對語言熟練程度的控制和雙語定義方面的問題,導致研究結果難以解釋。這包括控制語言變量的失敗,特別是缺乏使用測量或控制語言熟練程度的工具和指標。例如,費爾德門(Feldman)的研究結果因分配被試的組別標準而產生問題。雙語組的分配依據是兒童“對幾個簡單的西班牙問題的理解和在家說西班牙語的能力”。此外,沒有提供下面的信息:這些問題的種類或在家說西班牙語的能力是怎樣確定的。
同樣,在利德克和納爾遜(Liedtke and Nelson)的研究中,對雙語組分配的標準是根據教師觀察。這個組被定義為“進校前用過2種語言和家里說2種語言的兒童”,關于雙語或單語組語言熟練程度的實際水平沒有提供資料。就象費爾德門(Feldman)的研究一樣,這個研究因缺少合適的語言控制而沒有多少說服力。
一些研究存在方法上和理論上的局限,包括:取樣偏差、抽選樣本語言熟練程度控制的缺陷、測驗偏差、程序誤差。這些局限限制了對研究結果的分析、解釋。在使用皮亞杰測量和純理語言學測量的研究中,雙語占優勢是很明顯的。從理論上講,這由控制語言熟練程度這類方法上的因素、雙語環境和經驗的某些特征可以進行解釋。它包括這樣的觀察:基于皮亞杰的活動任務可能更好地顯示認知差異,因為他們對語言的依賴程度不大。現在,多數研究者認為:雙語、雙文化環境的某些特征可以促進雙語兒童在認知和學術作業方面的積極效果。此外,語言熟練程度需要達到某種水平的雙語才會對認知產生積極的影響[10]。如果雙語制的確促進了認知功能,雙語的優勢就應該在嚴密控制語言熟練程度、小心操作和定義雙語的研究中顯現出來。只有開展嚴密控制各種變量的大量研究,才能真正揭示雙語對各種認知能力發展的影響。因此,要支持熟練雙語有高級認知功能的假設,還需要進行一系列嚴密控制的實驗。
[1] 趙小雅.HELLO,雙語教學[N].中國教育報,2004-01-05.
[2] Norbert Francis.Modular perspectives on bilingualis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 alism,2002,5(3).145-156.
[3] Sotiria Tzivinikou.Developmental speech problems and bilingualism.International Education Journal,2004,5(4).466-473.
[4] Heather McLea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lingualism and the Performance of spatial tasks.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2003,6(6).423-438.
[5] Ellen Bialystok.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bilingualism at an early age and the impact on early cognitive de velopment.Encyclopedia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2006,9.1-4.
[6] Mohsen Ghadessy,Mary Nicol.Attitude change in bilin gual edu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 tion and Bilingualism,2002,5(2).113-128.
[7] Maria Teresa Sanchez,Maria Estela Brisk.Teachers' as sessment practices and understandings in a bilingual pro gram.Nabe Journal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2004,2.193-213.
[8] Anita C.Hernández.The expected and unexpected liter acy outcomes of bilingual students.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2001,25(3).251-276.
[9] Elaine Hampton,Rosaisela Rodriguez.Inquiry science in bilingual classrooms.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2001,25(4).417-434.
[10] Carlos J.Ovando.Bilingu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Issues.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2003,27(1).417-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