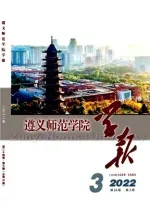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理論脈絡
曹文斌
(遵義師范學院政治經濟系,貴州遵義563002)
一、引言
動物保護倫理是當今世界頗具爭議的倫理學前沿理論,它以動物福利作為倫理起點和基礎,內容涉及科技、法律、情感甚至信仰等多方面因素,是一門關于人類應該在多大的限度和范圍內有效地保護動物的倫理學科。在中國社會里,佛教倫理、道家學說和儒學思想可喻為根植于中國民間的“三大福音”,它們匯集構成了動物保護倫理的理論脈絡。佛教倫理就包括了“眾生平等”、“大慈大悲”和“果報輪回”的教義和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民間,奠定了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重要思想基礎;道家學說主要有“慈心于物”、“道性貴生”、“善惡報應”等思想,這些思想通過后來創立的道教而傳播至中國民間,對于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思想和實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儒學思想主要有“仁愛”、“無傷”、“和諧”等動物保護理論,它們構成了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重要支柱,也是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一大道德福音。
二、佛教倫理
中國佛教倫理中的動物保護思想常常是通過“眾生平等”、“大慈大悲”、“果報輪回”等核心教義和理念以民間口碑的形式流傳至今,有時甚至是祖輩相傳,成為美談和佳話,從而奠定了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重要思想基礎。
1.眾生平等
中國佛教特別是大乘派佛教提出了眾生平等思想,在《大般涅槃經》中有較多的論述。中國佛教認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又“以佛性故等視眾生無有差別”。一切眾生,包括有生命的動植物,甚至無生命的草木山川、江河湖海等等,與人一樣,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平等機會,因此,中國佛教在道德考慮上視眾生是絕對平等的,這就是眾生平等思想的主旨。在此基礎上,中國佛教還提出了不殺生的戒律要求(戒殺),成為約束佛教徒的第一大戒。通過中國佛教在民間的活動,眾生平等思想廣泛滲透于中國普通百姓的心中,特別是中國佛教的不殺生戒律對民間的影響尤為深遠,可以說,在民間廣為人知,并常常來源于生活中耳熟能詳的話:“孩子,不要殺害小動物,它也是一條生命!”這句話雖然是很多中國普通民眾在兒時的記憶,但卻意喻著生命平等的第一要義,使民間也深入地了解到動物和人一樣,也是一條活生生的生命,不應當隨意地殺害它們。中國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民眾對待動物的態度和行為,使他們友善地對待動物,不為自己瑣碎的利益而屠殺無辜的動物。為更徹底地恪守不殺生戒,中國佛教在內在的佛經要求的基礎上,在道教影響和帝王推行的外在力量促成下,還發展出了素食的戒律要求,禁止食用一切肉食,無論是出家弟子還是在家信眾,大都遵從這一戒律而奉行素食,這是對眾生平等思想的最有力貫徹,也有效地推動了民間對于動物保護的實踐。
2.大慈大悲
所謂“大慈大悲”,是指諸佛菩薩對眾生所懷有的廣博的慈善心和憐憫心。《大智度論》卷二十七用形象的例子闡釋了大慈大悲的含義:“大慈大悲者,四無量心中已分別,今當更略說:大慈與一切眾生樂,大悲拔一切眾生苦。大慈以喜樂因緣與眾生,大悲以離苦因緣與眾生。譬如有人,諸子系在牢獄,當受大罪;其父慈惻,以若干方便,令得免苦,是大悲;得離苦已,以五所欲給與諸子,是大慈。如是等種種差別。”中國佛教認為,給與歡樂為“慈”,拔除痛苦為“悲”,合稱“慈悲”,后來又用大慈大悲來形容人的心腸慈善。諸佛菩薩心量廣大平等,救度一切眾生而不見眾生之相,故稱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又常用以稱佛,如“大慈”、“大悲”分別指稱彌勒、觀音兩尊菩薩。而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拔除眾生今現在之苦,號為“大悲菩薩”。中國佛教經籍中曾說,佛祖釋迦牟尼的前世看到行將餓斃的老虎準備吃掉小虎崽,他便舍身從山崖上跳下去喂虎充饑!足見中國佛教頌揚的菩薩心腸是何等的慈悲!中國佛教的大慈大悲思想在民間的影響突出地體現在對觀世音菩薩的信仰上,傳說中的觀世音菩薩是一位能解脫人們現實苦難,能滿足信仰者真誠愿望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善良菩薩,在我國民間流傳久遠,可以說家喻戶曉。“觀世音成為了百姓心目中救苦救難、無所不能的‘萬能神’,成為了許多普通百姓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途徑和精神寄托。”[1]到了唐代,朝廷為避太宗李世民的名諱,略去‘世’字而簡稱觀音菩薩,至今相沿成習,所以現在民間多稱觀音菩薩。中國民間普遍信仰并宣揚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思想,以普遍、平等無差別的悲心憐憫一切眾生,不舍一切眾生,救一切眾生于苦海之中,這也常常得到源于生活的印證。中國民間特別是一些虔誠的佛教信眾,正是以大慈大悲的思想和情懷來對待動物,對于動物承受的苦難給予了博大的同情和關懷,并真正擔負起關懷和愛護一切眾生的責任,這對于動物保護的實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積極影響。
3.果報輪回
中國佛教的“果報輪回”是指“因果報應論”和“六道輪回說”。中國佛教在不殺生戒律的基礎上,又以因果報應論作為反對殺生的理論支撐。中國佛教認為,如果觸犯殺戒,不論親自殺,還是使他人殺,都屬于同罪,必得惡報。這種因果報應論對于中國民間的影響也相當之大,“至晚在東晉南北朝時期,民間已普遍流傳殺生受報應之說”。[2]如果某人屠殺、虐待和折磨動物的行為被人發現,常常導致的抗議或斥責就是:你會遭到報應的!通常情況下,這種抗議或斥責的語言和方式很有威懾力。中國佛教還認為,生命體有六種不同的表現形態,從高到低分別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稱為“六道”。在這六道之內,一個生命體會按照一定的規律運動,從一種形態轉變為另一種形態,永不停頓。這種前后相續的不停運動就像車輪的不停回轉一樣,所以又稱作六道輪回。既然眾生有輪回,人和動物之間當然也就可以相互轉化:一個人如果棄惡從善,來世就可以脫離苦海、繼續做人,甚至超越輪回而涅槃成佛;而如果作惡,死后則可能墮入畜生、餓鬼、地獄之三惡道。這樣,中國佛教便把因果報應論與六道輪回說聯系起來,用果報輪回思想來警示人們眾善奉行,諸惡莫作。“這一對來世的設定和因果報應的描述,對于信徒的日常行為有極大的約束力,是佛教落實‘不殺生’的生命觀的重要理由。”[3]中國佛教的果報輪回思想在我國社會廣為流傳,在很大程度上對于民間信眾起到了強有力的震懾作用。由于擔心作惡會得惡報,因此誰都不敢隨意地殺害或傷害動物,對于動物保護的實踐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道家學說
道家學說中有許多思想關涉到生態環境方面,其中更不乏與動物保護有關的理論,主要有“慈心于物”、“道性貴生”、“善惡報應”等,這些思想通過后來創立的道教而傳播至中國民間,對于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思想和實踐具有相當大的影響。
1.慈心于物
所謂“慈心于物”,就是指將仁慈之心賦予動物和植物,從而達到保護動物和植物的目的。道家學說較早地提出了這一主張,如葛洪的《抱樸子內篇》就把保護動物和植物看作是善行:“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已及人,仁逮昆蟲。”[4]這里所講的慈心于物、仁逮昆蟲,就是要像仁愛之人那樣愛護動物及至昆蟲。由于道家學說受佛教倫理和儒學思想的影響較大,因此,慈心于物思想實質上相當于中國佛教的大慈大悲思想,即要求以慈悲和同情之心對待包括人在內的一切動物。
道家的慈心于物思想的慈心對象——“物”,并非僅僅指稱動物和植物,“道教所謂‘慈心于物’的‘物’,就自然物而言,既包括動物、植物之類有生命物,也包括大地、山川等非生命物;因此,‘慈心于物’不僅要慈善地對待動物、植物之類有生命物,而且也要慈善地對待自然界中的非生命物。”[5]這樣,由于道家學說中的慈心于物思想將非生命物也納入了道德關懷的范疇,在理論上也就有了更大的道德視域。
道家的慈心于物思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好生惡殺”實踐,這在《太平經》、《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三天內解經》等道經均有強調,道教還把好生惡殺與個人的“得道成仙”結合起來。道家的好生惡殺要求的實踐行動就是“戒殺放生”,道教為此還制定了各種戒律,涉及范圍非常廣泛,許多戒律類著作都包含有戒殺動物和植物的條文,以此來規范弟子的行為。不過,道家的好生惡殺實踐并不區分動物是有益還是有害的,即使是有害動物,也屬好生惡殺之列。道家的慈心于物思想和好生惡殺實踐,后來在道教戒律和包括《太上感應篇》在內的勸善書中被不斷加以強化,成為約束道門中人的一大戒律,亦通過各種道事活動而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民間對待動物的行為方式。
2.道性貴生
所謂“道性貴生”是指道家的眾生平等和尊重生命的思想。“道性”一詞最早指“道”的特性,是人所應當效法的,始見于《道德真經河上公章句》卷二:“道性自然,無所法也。”后來南北朝時期的道家學者受佛教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論影響,亦援佛入道,仿造佛性論的思想提出了道性論,如唐初的道經《太上妙法本相經》指出:一切眾生,悉有道性,稱之遍有;種之則生,廢之則不成。這樣,道家的道性論就為眾生皆可修道提供了理論基礎。道家還參照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提出了眾生道性平等的思想。在道性論強調眾生平等的基礎上,道家又提出了“貴生”思想,將道德關懷的對象和范圍從人和社會領域擴展到了生命和自然界,把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情懷投射到動物身上,從而形成了以一切生命和存在作為保護對象的道家倫理原則。道家的貴生在思想上首先是尊重生命,落實在行動上,就是保護生命的實踐。如《太平經》說:“夫天道惡殺而好生,蠕動之屬皆有知,無輕殺傷用之也。”[6]又如詩云:“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盼母歸。”常常被道教經書所引述。道家力倡對動物的道德情感擬人化,以極富感染力的手法表達了貴生思想。此外,道家對于動物生命的重視,還不僅表現為對活體動物的同情和關愛,甚至于對那些死去的動物也要求予以哀悼和埋葬,以表達對動物的尊重,更是道家貴生思想的獨特之處,對中國民間培養有關動物保護的良好習俗發揮了積極的影響。
3.善惡報應
道家也有類似于佛教的果報輪回思想的“善惡報應說”。道家吸收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將其變成自己的神學基礎,從而有力地支撐了自己的善惡報應說。《太上感應篇》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行善者,必有善報;行惡者,必有惡報。在道教看來,人的一切行為都要受到神明的監督和懲罰。許多道教經書以善惡報應說論述了關懷和愛護動物者必定會得到善報,而殺害和傷害動物者將得惡報的思想。道家所說的善惡報應通常有兩條途徑:一是通過自然界的變化對人進行賞罰;二是對行善者和作惡者直接進行賞罰。而善惡報應的賞罰主體就是各種神明,賞罰對象當然是這些行善者和作惡者。如《抱樸子內篇》認為,天地間以及人身上有各種鬼神,用民間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各人頭上一片天,舉頭三尺有神靈”,他們監視著人的所作所為,并且給犯有罪過的人以懲罰,根據所犯罪過的大小,減損人的壽命。道教創立后,大力推動了中國民間崇鬼拜神的封建迷信活動,對于民間的影響也相當之大。從這種意義上來講,道家的善惡報應說對于民間殘害動物的丑惡行徑顯然具有普遍約束力。在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甚至還出現了“地獄”的說法,認為那些殘害動物的作惡者會墮入地獄遭到惡報,身經“三涂”和“五苦”的折磨。所謂“三涂”即“火涂”、“血涂”、“刀涂”;所言“五苦”即刀山、劍樹、銅柱、鑊湯、溟泠之苦。這種說法更使民間對于動物尤加保護,不敢濫意殺生和虐待,起到了和佛教的果報輪回思想一樣的威懾作用。此外,《太平經》在善惡報應說的基礎上還進一步發展出“承負說”,即認為善惡報應即使沒有發生在自身,也會在子孫后代那里得到應驗,又更好地支撐了善惡報應說,用通俗的話來講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從而使道家的善惡報應說在理論上更趨完備。
四、儒學思想
儒學思想在動物保護方面的內容也非常獨特豐富,如“仁愛”、“無傷”、“和諧”等思想,它們構成了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重要理論支柱。倡導“敬畏生命”倫理學的法國哲學家、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史懷澤說:“中國倫理學的偉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動上同情動物。”[7]完全可以認為,儒學思想就是中國動物保護倫理的一大道德福音。
1.仁愛
“仁愛”是儒學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當代學者幾乎公認的儒學精華所在。早在儒學創立之初,孔子就把對待動物的態度看作是道德問題,認為人應當以一種同情的態度善待動物,即以人道的態度對待動物,這就是體現在動物保護倫理上的仁愛思想。從這種仁愛思想出發,孔子甚至還認為動物也有與人相似的道德情感,他認為有血肉靈性的動物尚且對同類的不幸遭遇具有同情之心,人類就更應當自覺地禁止傷害動物的行為,主動地同情和保護動物,所謂“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史記·孔子世家》)也正是這個道理。
孟子又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仁愛思想,將仁愛衍化為對動物的憐憫與關愛,認為人固有一種惻隱之心,這是人與動物的不同之處和區別所在。他說:“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對動物的惻隱之心典型地體現為同情和關懷動物,他把這種仁愛思想擴展到動物身上,將動物擬人化,顯然更易引起人與動物之間的感情共鳴。因此,孟子的仁愛思想是儒學在動物保護倫理中的感情和心理基礎。荀子也認為:“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后能去之也。”(《荀子·禮論》)可見,“儒家這種以鳥獸昆蟲具有與人類一樣的同情同類的道德心理,給中國古代珍愛動物、保護動物的行為以深遠的影響。”[8]
2.無傷
孟子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孟子·梁惠王上》)他從仁愛思想出發,進而得出了“無傷”的道德實踐觀,指出仁愛的核心要義就是不應該傷害生命。反推之,如果傷害生命,則不能稱之為“仁”。這種無傷的道德實踐觀,類似于佛教和道教的不殺生戒律,從因果關系上來講,“仁愛”是“無傷”的思想原因,“無傷”是“仁愛”的實踐結果。
宋朝儒者王柏說:“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殺傷也。故日天子無故不殺牛。”(《魯齋集》卷四)可見,無論動物還是植物,儒學也強調不能無故而殺之。據史載,宋朝大儒程頤一次見家人買了一大堆小魚來喂貓,于心不忍就偷偷撿了一百多條魚放生在書房的池子里,并在旁邊看了一天,當看到水中之魚的歡快,不禁油生感慨:“圣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9]顯然,程子的感嘆和內心的戚戚,正是由仁愛思想而滋生的真摯的愛物之情,它使儒者導向無傷的道德實踐觀。
很多儒者從無傷的道德實踐觀出發,呼吁世人不殺生或少殺生。明代高攀龍曾告誡家人:“少殺生命,最可養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知為彼思量。豈復有仁心乎?……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藥言》)文中所言“少殺生命,最可養心”、“省殺一命,于吾心有無限安處,積此仁心慈念,自有無限妙處。”雖然是出自人自身的養心需要,但在客觀上是以無傷思想作為動物保護的理論指導,從而很好地宣揚了不殺生或少殺生的護生思想,對于動物保護具有可操作的現實意義。
3.和諧
儒學的仁愛、無傷的護生思想既蘊涵了其博愛的胸懷,又體現了它對宇宙本質、人與自然關系的獨特思考。在儒學體系中,還不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寶貴思想創見。
在宇宙生成論上,早期儒學就強調人與萬物是同源同構的,都源出于天地,即所謂:“天地捆蘊,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周易·系辭下》)張載的“乾稱父,坤稱母”的說法也形象地喻示了人與萬物的同源性,認為人與萬物都是“天地捆蘊”的產物,都派生于天地。后來張載將這一思想發展成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即“民胞物與”思想。這是一種以擬人的手法來看待人與萬物關系的思想,即把所有人都看成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將萬物都看成是與自己同樣的生命存在物。正因為這種人與萬物的同源同構性,所以儒學又推崇“萬物一體”的思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二程遺書》卷二上)明代的儒者王陽明還說:“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霜,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木石,與人原是一體。”(《傳習錄》下)王陽明的萬物一體思想一經提出,使強調人與萬物同源同構的民胞物與思想得以推而深入并被確定下來。
儒學又由民胞物與和萬物一體思想進而推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從而奠定了儒學生態倫理的“和諧論”。在儒學看來,人與自然怎樣才能和諧相處呢?對此,孔子就曾明確提出“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意思是說人在取用自然萬物時應該注意時節。孔子十分注重對動物的永續利用,反對竭澤而漁、覆巢毀卵的行為。此外,孔子提出的“釣而不網,弋不射宿”,也明顯地體現了一種節制利用動物的思想。元朝儒者許魯齋說:“天地間為人為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許魯齋集》卷一)從而提出了一種有限度地開發和利用自然界的思想,也相當于現今的可持續發展觀。他認為人類不應該過分地向大自然索取資源,對資源的利用應該有一個限度。“文中的‘分限’說,實際上是在主張人應尊重和保護‘物’的生存權,以使人、物和諧相處。”[10]從而達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荀子也提出了取之有時、用之有度的生態保護思想:“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堪稱儒學思想中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論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中國儒學的倫理思想是以人類中心論為基調的,但儒學作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其熱愛生命、珍視動物、保護動物的思想,對于民間提倡生態道德、遵循生態規律、節約生態資源,產生了積極的意義。
[1] 陳必昌.佛教核心教義對中國民間信仰的影響[J].民俗研究,2005,(3):255-260.
[2] 吳平.中國古代佛門百態[M].北京:東方出版中心,1997.125
[3] 魏德東.論施韋澤的“敬畏生命”理念——兼與佛教“不殺生”戒比較[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8,(4):38-43.
[4] 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卷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5.126.
[5] 樂愛國.道教生態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207.
[6] 王明.太平經合校[M].北京:中華書局,1960.174.
[7] (法)史懷澤.敬畏生命[M].陳澤環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75.
[8] 佘正榮.儒家生態倫理觀及其現代出路[J].中州學刊,2001,(6):148-157.
[9] 程顥,程頤.二程集[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1.579.
[10] 胡發貴.儒家生態倫理思想芻論[J].道德與文明,2003,(4):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