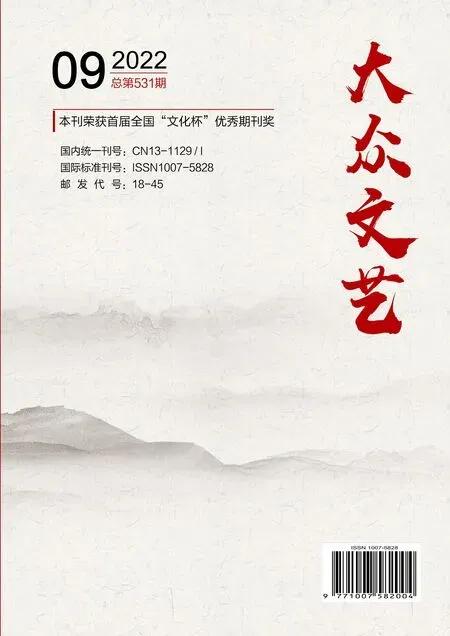勞倫斯小說中莉迪亞和康妮情節相似性的重要意義
趙曉娟 (河北建筑工程學院 外語系 河北張家口 075000)
勞倫斯小說中莉迪亞和康妮情節相似性的重要意義
趙曉娟 (河北建筑工程學院 外語系 河北張家口 075000)
勞倫斯在其小說《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對莉迪亞和康妮的情節安排有高度相似性,這反映了他對工業文明批判和他本人持有的血性哲學觀的堅持,他其實強調了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的重要性,試圖達到警世、醒世和修世的目的。
情節;相似性;工業文明批判;血性哲學觀;堅持
注:此文為河北省社科聯課題(201003084)成果
2)疏除果粒。多在落花落果終止后,果粒介于黃豆粒和花生粒大小時進行。摘除病果、小果和特大果,使果粒大小均勻。
水上鉆孔灌注樁的施工不同于陸地,施工場地受限制,大多都是搭建施工平臺,采用振動錘下埋護筒。實際開展深水鉆孔樁施工工作的過程中,由于受到水流、水深、施工平臺的制約,護筒埋設如留隱患,就可能在施工中出現護筒穿孔,形成管涌、跨孔,嚴重影響工程質量。面對護筒穿孔問題,需積極采用科學合理的方式和手段加以應對和處理。發揮雙套護筒的優勢和作用,有效處理深水鉆孔樁的穿孔問題,提升工程項目建設的總體質量。
在D.H.勞倫斯的作品中,《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同具豐富的文學和社會價值。它們有很多共同之處,都曾因性描寫被禁,后來又都成為了蜚聲國際的廣受讀者歡迎的嚴肅小說。它們都觸及了女性追求自我滿足主題。它們屬于勞倫斯不同時期的作品,有些評論分別提到了這兩部作品中的女性追求自我滿足主題并談到了女主人公莉迪亞和康妮,甚至對二人的自滿滿足追求的關聯有過些微點評。理查德?威森在“《虹》的喜劇與歷史”中認為“追求完全滿足中性愛的喜劇斗爭在勞倫斯的手中成為了提供歷史心理分析視角的非常有效的工具”(205)。他指出:莉迪亞結束于“性愛社會的短暫建立”(209)。評論家朱利安?莫納漢在《生命行動:勞倫斯的小說和故事》中分析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結構且承認最終“是接觸慢慢令查泰萊夫人得到滿足”(109)。西莫?的波娃在《第二性》中評論到,勞倫斯在康妮的經歷中描寫的是“婦女從屬于男性存在的存在”(貝克特145)。艾登?伯恩斯在《自然與文化》中質疑勞倫斯向現代人提出的像康妮(和梅勒斯)一樣通過純潔而神圣的身體滿足得到自我滿足的建議的可行性(107)。1978年,H?M?得利斯凱在《叉狀的火焰—勞倫斯研究》中寫道,《虹》發表多年后勞倫斯才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在現了湯姆和莉迪亞的“保存自我和屈從于愛人欲望的調和”(88)。1983年邁克爾?斯奎斯在《查泰來夫人的創作》中指出康妮“擺脫了意志力”:她“在教育和調節的相互作用下”尋求人“更深層的滿足”(33)。瑪麗安娜?圖哥夫尼克在她的作品“對性的敘述:《虹》”中指出,《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的性的關聯比《虹》和《戀愛中的女人》中的更多”(37)。總之,近百年的D.H.勞倫斯小說國內外研究經歷了從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讀者中心的過程,他們雖觸及了《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共同的女性追求自我滿足主題,但并未對《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有關女主人公莉迪亞和康妮情節的進行詳細比較研究。
實際上,在《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作者對兩位女主人公莉迪亞和康妮有關情節的處理有類似處,這種相似性反映了作家對工業文明批判和對本人持有的哲學觀的堅持。
一、與莉迪亞和康妮有關的情節的相似性
安娜生活的世界已見工業文明和基督教世俗文化的影響。她想通過受教育實現她的獨立人格,可女子學校的環境對她而言顯得“吝嗇”而“小氣”,對待人的工業文明的功利“標準”令她 “幻滅”和想“避開”(108)。她渴望通過宗教的洗禮來尋求自我身份,可牧師的死板的布道文令她覺得“虛假和毫無道理”,扼殺她“內心深處”的“宗教感情”(109)。異性威爾的出現令她想通過他了解和實現自我,她也確實通過和威爾的交往獲得了“新的獨立”(119)。可威爾是世俗基督教文化的代表,盲從于死板的宗教說教和外在形式,人格“抽象”(118),身心分離。雖然安娜崇拜并嫁給威爾,在愛情和婚姻中,威爾卻只想用“意志”讓安娜“永遠屬他所有”(129)。安娜在與威爾的關系中,只獲得了肉體的滿足——“無限的令人瘋狂的感官的沉醉”(249)。安娜于是在工業文明環境和與世俗基督教代表的婚姻中內心一直“不滿足”(205),后來開始回望她父母獲得的滿足,她看到“很遠處一條微微閃光的地平線,一個像拱門一樣的虹…她也必須到那里去嗎”(205)。這讓我們想起了第三章《安娜?蘭斯基的童年》的結尾處的讓她“安全”和“自由”的“拱門”,她的父母“在蒼穹的兩邊支持著它”(99)。遺憾的是,安娜沒有前行,沒有繼續探求同樣作為女性的她的母親曾經的追求和獲得的滿足,她享受著創造生命的滿足,“感到自己像大地一樣是萬事萬物的母親”(218),“心安理得的放棄了那走向不可知的冒險旅行”(206)。
通過上述情節比較,可見勞倫斯對莉迪亞和康妮有意而為之的類似的情節安排在于他對工業文明的堅持批判和對他的血性哲學觀的反復宣傳:他認為人在金錢為本的工業文明中會被剝奪個體自我,不能實現自我滿足,只有建立人與人(兩性為核心)及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社會,人才會得到個體自我的滿足,人類文明也才得以可持續發展;和諧關系是指關系雙方既保持個體自我的特異性,又實現水乳交融的同一性。
對表2 的數據進行分析歸納整理,改進企業領導人員網絡培訓的意見建議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研究和探索互聯網下,干部培訓模式變化規律和趨勢;二是加快網絡培訓平臺建設,推進移動學習平臺;三是資源共建共享(課程資源),搭建共建共享平臺;四是現代化教育培訓手段和培訓方式的應用,培訓方式方法創新,探索線上線下混合式教學;五是化解工學矛盾,滿足培訓需求。
作為現代作家,勞倫斯生活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環境中。在農業社會,人們過著平和無自我身份意識的生活。隨著工業的入侵,這種平和被干擾和打斷了。人們開始對新的生活方式感興趣,對舊的生活方式不滿并想打破它。他們希望在新生活中理解自我和找尋自我身份。然而,與此同時,他們的自我在現代文明中逐漸被異化。勞倫斯對這個問題投入了極大的關注。
厄休拉在對壓抑和扭曲人性的金錢至上的功利主義和意志主義世俗基督教文化、工業文明教育、殖民主義代表伴侶及工業社會工作“不滿足”后回望她外婆在農業泛神論的環境中(人類農業文明時期)曾經的追求與自我滿足的擁有。厄休拉的生活出現了殖民文化,她的愛人,一名愿意去他國作殖民者的軍人,與當時的社會政治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與高度功利主義殖民文明統一,個體自我極度缺失,他要靠自我意志在與厄休拉的關系中發揮作用來實現自我,他只想“占有”她,并非平等的融合……厄休拉沒有找到外婆告訴她的“發現你值得愛而愛你,并不是希望你完全聽他擺布而愛你”(273)的那個人…厄休拉試圖通過進入和“征服”(354)男性世界實現自我。她試圖通過與貌似獨立實則世俗的女權主義者英格建立關系來實現自我,可她最終發現熱衷于婦女運動的英格只有表面的獨立實則缺乏個體自我,“沒有自己的生命”(365),受利益驅使只能淪為社會制度“傳宗接代”(374)的工具。厄休拉轉而投向進入社會工作獲得獨立來實現、發展和滿足自我,可是雖然她成為了“獨立的社會人”(387),也在反抗男性權威中取得勝利,她的個體自我卻被社會異化了,她付出了“很大的一個心靈上的代價”(432),她雖然成就了社會自我,卻并沒有獲得個體自我的滿足。最終,厄休拉與外部環境和異性格格不入,她放棄戀人,放棄象征殖民和工業文明的腹中胎兒及工作,進行深深的反思。她開始回望莉迪亞的滿足,她要“極力尋找”它,充滿著渴望與希望,“她看到一條淡淡的彩虹……在遺忘之中……看到一條彩虹慢慢地自動形成了……”(529)。而且,“在那彩虹之中,她看到了大地新的結構,看到那脆弱的腐敗的房屋和工廠全被一掃而光,看到這個世界將以真理作為它的活的支架重新建立起來,巍然屹立在蒼穹之下”(這里的真理即莉迪亞也即勞倫斯建立的血性哲學觀)(529)。
在《虹》中,勞倫斯尤其安排了第一代莉迪亞的迷失與回歸為作品最重要的情節和整個作品的主旨凸顯情節,勞倫斯意欲為女性和人類探索在現代實現自我滿足的可能。在后來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他繼續探討這個問題。在新的社會發展時期,人的自我認識、實現和發展更加困難。女性找尋自我滿足比男性更難,其復雜程度遠勝于男性。然而,在勞倫斯看來,雖然現代社會中女人對自我滿足的追求在實現自我身份方面更復雜和艱難,女性始終在內心深處追求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她們不僅追求個體自我的獨立,還追求與異性及自然的同一性,這正是勞倫斯持有和反復宣揚的血性哲學觀的內容。《虹》中,莉迪亞只是在英格蘭鄉村與農人湯姆? 格蘭文步入婚姻的殿堂后才實現了自我滿足;在與革命者保羅? 蘭斯基的婚姻時段,莉迪亞未實現自我滿足。安娜與厄休拉回望代表農業文明的彩虹,代表家族第一代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及兩性關系的彩虹,代表莉迪亞的自我滿足的彩虹。安娜與厄休拉的反思是勞倫斯的安排的,是對現代文明的深刻批判,對現代讀者的嚴肅提醒,讓讀者意識到人的自我滿足在目前金錢至上和壓抑人性的文明下是不可能是實現的。人類必須反思和改變,回歸一個懷有對自然敬畏的與自然和諧相處非純功利的狀態,人的個性被尊重,人與異性和環境和諧,人的個體自我才會滿足,人和社會才得以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和勞倫斯持有的血性哲學及女性觀密不可分:女性會不懈地追求自我滿足,而這種自我滿足和男性的不同,它集中體現了勞倫斯血性哲學觀,即,感性哲學觀。
二、勞倫斯對工業文明批判和血性哲學觀的堅持
在他看來,人的自我滿足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的確很難實現,尤其是對女人。這是因為女性不得不面對既來自家庭又來自社會傳統和變化的壓力。她們對自我滿足的追求特別要應付一系列的復雜身份,比如,母親、妻子、女兒、文化存在和社會形象,其復雜程度遠勝于男性。勞倫斯試圖在小說中批判工業文明剝奪人性的一面和表達他的血性哲學觀。在他的代表作《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勞倫斯為莉迪亞和康妮安排了相類似的情節,表現在情節內容和凸顯主題的重要性上。她們最初都來自文明世界,莉迪亞來自社會革命頻發的工業文明環境,康妮來自世界大戰肆虐的工業文明環境。她們都曾在工業文明世界追求自我身份和自我滿足。莉迪亞原為一波蘭革命者的妻子,生活在華沙革命動蕩的社會環境中,在紛亂的革命洪流中,她視丈夫為主人和上帝,“追隨”他和他的革命理想,想借此找尋和實現自己的身份;康妮在故事的開篇曾熱烈地追逐著女性主義自由,她追逐著與男子同等的話語權,與男子討論哲學和發表對藝術的見解,在性關系中追求個人意志的勝利,滿足于“精神生活”。然而她們都幻滅了,并沒有獲得個體自我的滿足。莉迪亞的盲從令她“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個性”(48)她的丈夫生活在革命的“幻想”中,占有和控制她的自我,不允許她做“任何降低他身份的事”……他們夫婦疏于照顧孩子而造成兩個孩子死亡,隨后,莉迪亞生活在“離奇的深刻的恐懼”(49)中。康妮在嫁給了代表高度現代工業文明的克利福德回到拉格比大宅生活之后才真正體會到自己的不滿足,在代表工業文明的大宅的剝奪人性的生活環境中,她陷入了“不安”(21)和“恐懼”(59)。
莉迪亞和康妮此后都轉向了自然和自然人(勞倫斯安排的)回歸自我,實現自我滿足。我們在莉迪亞與湯姆? 格蘭文的鄉村婚姻時段發現了她的自信和自我滿足。在恬靜美麗的鄉間,大自然喚醒了莉迪亞,使她成為“新人”(54)。農人湯姆的出現使莉迪亞有了“安全感”(54),他/她們經歷了“脫胎換骨”的過程,成為彼此的“門”,得到完全的“自由”(98)。此后莉迪亞與湯姆生活在農業化的環境中,與自然和諧相處,身心統一,彼此尊重,性愛和諧,生兒育女,享受天倫之樂,在兩性關系中莉迪亞既保持了個性又實現了同一性,得到完整的自我滿足,一種“無法述說的滿足”(106)。對莉迪亞的情節安排為小說點睛之筆,統領和凸顯小說主題,因為勞倫斯安排她為她的后代樹立了女性在和諧的兩性關系和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中實現自我滿足的榜樣。勞倫斯安排第二代和第三代格蘭文婦女回望莉迪亞的自我滿足。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與康妮有關的情節充斥著整部小說。康妮隨克利福德來到拉格比大宅時,是1920年,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被戰爭摧殘的克利福德“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已經泯滅,某種感情已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種麻木的茫然”(2)。戰爭使克利福德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犧牲者,使他喪失了人類的感情,失去了性能力,然而他沒有反思戰爭對人的異化,卻還能“滿面紅光,精力充沛”地熱衷于煤礦的機械化進程和物質利益,并“盡可能使查泰萊家族的姓氏保持下去”(2);對康妮,他無性的渴求,也不在乎她的性福,只在乎康妮能為她的家族傳宗接代,維持現有的社會秩序,找一個和他的家族社會地位相當的男人為他生一個兒子。克利福德的朋友也一樣,他們來自上層階級,看重的是物質利益和現有的社會體系,不看重兩性的既有同一性又保持個性的和諧關系,甚至將性關系看作人類文明生活的負擔。他們認為,小孩如能不通過性交就能在容器里生成那再好不過了……見證了這一切,康妮的內心深處觸動了。康妮則在對大宅失望后,走出冰冷的大宅,走入樹林,樹林喚起了康妮的一些生命活力,在這里,康妮感受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舒適。她越是對大宅感到失望,失望于大宅機器般的冰冷和喪失人性(人只有以錢勢來定位的社會身份和相應的社會關系而喪失了感性的關系);就越迷戀于樹林,迷戀于樹林的生機與容納。如果說人與自然地關系讓康妮恢復了一些人應有的一些感覺和人性,守林人的出現則重新給康妮帶來了健康溫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該說是梅樂斯身上出現的人性的光芒喚醒了康妮內心深處某種莫名的渴望。梅樂斯熱愛自然,養雞,砍柴,與自然和諧相處,康妮喜歡梅樂斯,不知不覺與梅樂斯發生了性關系,確切的說是充滿“人性”(曾 370)的關系。是在與樹林和梅勒斯的和諧關系中,康妮回歸了自我,恢復了“靈敏的女性追求快樂的本能”(344),實現了自我滿足。康妮的迷失與回歸成了小說的主要情節也是集中凸顯主題的情節,體現了作品對工業文明的批判和對和諧的兩性關系與和諧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倡導。
一般來講,男性追求集體自我即社會自我的滿足,隨工業文明的發展追求自我中心(意志)主義;女性在內心深處追求個體自我的獨立和滿足,在和諧的兩性關系和與自然的關系中,追求個體自我的滿足。勞倫斯最后希望可以通過康妮這個女性角色為人類再次探索在工業文明時代實現真正自我滿足的道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康妮續寫著厄休拉的追索與回望。她生活的時代是厄休拉生活時代的延續,是一個高度工業化并伴隨世界大戰的時代。康妮受現代文明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這正是勞倫斯所要批判的。與厄休拉相比,她更加追求社會政治文化身份、話語權和個人意志,擁有了社會自我的身份,但未真正擁有個體自我的滿足。而代表高度功利主義的世界大戰給人帶來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勞倫斯曾說,世界上的任何戰爭都是非正義的……在勞倫斯看來,現代人類文明的發展過與強調人的意志,過與物質和功利,人類互相憎恨和殘殺是人類文明最大的悲哀;被戰爭摧殘的克利福德沒有對大戰反思,卻和拉格比大宅一起成為了機械文明的代表。大宅及工地如機器冰冷,沒有生機,丑陋不堪;來這里的朋友也都是機械文明的代表。康妮終于與克利福德和大宅水火不容了。她在這里不僅絲毫未實現自我和發展自我,還喪失了自我,她曾經的女性主義自由也顯得幼稚可笑了。
合作結構的建立,需要合理分組作為打破傳統教學方式格局,實現學生交流面擴展,營造合作學習良性氛圍,實現學生物理理論知識教學和實驗教學效果最大化.通過合作學習實現學生面對面交流,同時有均等的價值參與社會實踐,并在學生自信和交流能力上具有同步提升價值.為保證合作活動有效、公平的開展,需要師生共同制定規范約束小組成員在合作當中的行為,且需要嚴格執行.
勞倫斯認為,所謂的女性主義不過是女性與男權工業社會同流合污罷了,它是支持工業文明體系的……大宅周圍的樹林、林間小屋和守林人梅樂斯是自然的代表;來自機械文明世界的女性康妮在這里受到自然與自然人的召喚,發揮個體自我的下意識追求,回歸本我和獲得個體自我的滿足。與樹林為伴的守林人的赤裸的身體令麻木的康妮開始關注自己的身體。隨后,她受莫名渴望的牽引,不停地從大宅來到樹林。應該說是梅樂斯身上出現的人性的光芒喚醒了康妮內心深處某種莫名的渴望,這正應和了勞倫斯的血性哲學和女性觀,符合康妮的內心渴求。康妮喜歡梅樂斯,不知不覺與梅樂斯發生了性關系。勞倫斯描寫了他們之間的八次性行為,讀來并不猥褻,卻充滿了純潔、神圣與美好。康妮的身體被逐漸喚醒了。在大雨中的林間的一次性愛似乎令康妮完全找到了自我,她懷著一顆敬畏的心享受與大自然和異性和諧相處的妙處,實現了自我滿足。勞倫斯通過莉迪亞和康妮相似情節的安排反復呼吁,現代人只有受 “自然文明”的召喚,棄絕現代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重建和諧兩性關系和人與自然關系,才能獲得真正自由和滿足。情節安排的類似性反映了勞倫斯對工業文明批判的堅持,要引起世人對工業文明對人的異化問題的足夠重視,借此警示和醒世,希望用他的血性哲學觀改善社會,即,讓人和社會回歸人性和自然——人類在自身發展的同時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同時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兩性關系為根基);兩性關系須是靈與肉的結合,既有在性愛中充分尊重對方和放棄意志的充分的融合和超越,又有生活中個體獨立的保持。
總之,勞倫斯設計的有關莉迪亞和康妮的類似情節是女性在工業文明中追求自我滿足,找尋身份,試圖實現自我和發展自我,可是現代人類文明去除人性,使自我迷失,不能令她們真正的滿足,她們在上述短暫的偏離后,最終還是回歸了個體自我,下意識地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和兩性和諧獲得滿足; 此情節在《虹》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都成為最重要的主題凸顯情節,反映了勞倫斯對工業文明批判和其血性哲學觀的堅持,勞倫斯希望借此反復批判工業文明對人的異化,反復宣傳他的血性哲學觀,也是在強調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建構和諧社會對人類的重要性,他試圖讓他的寫作真正起到警世、醒世并修世的作用。
[1]勞倫斯.D.H.虹(黃雨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2]勞倫斯.D.H.性與美(黑馬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4.
[3]勞倫斯.D.H.勞倫斯散文選(馬瀾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4]勞倫斯.D.H.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趙蘇蘇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5]馮季慶.勞倫斯評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
[6]伍厚愷.尋找彩虹的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7]曾繁人主編.“勞倫斯作品中的性描寫”.20世紀歐美文學熱點問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8]趙傾國,關和鳳.“從《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看勞倫斯對二元論的解構—生態女權主義的解讀”.文教研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