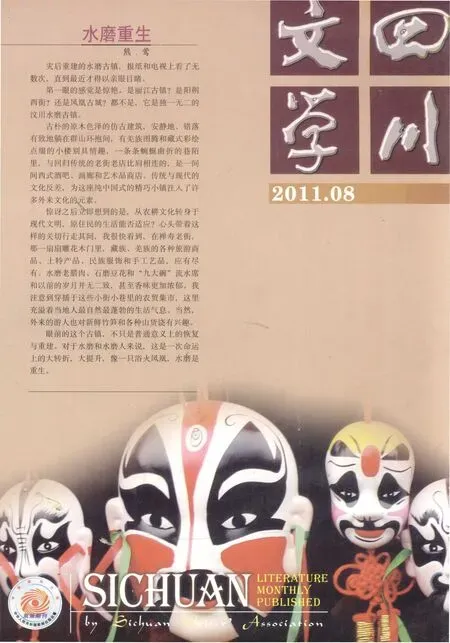回看游蹤(二題)
□鄒永前

初上竹海
現在的“蜀南竹海”已經遐邇聞名,是4A級國家風景名勝區。當年它卻不叫這個名字,而叫“萬嶺箐”。這名字出自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于明正統年間做過禮部尚書,尚書在南京為官時寫過一篇文章《箐齋說》,文中還專門解釋說,“箐”字乃蜀南一帶的方言,指竹木茂盛,故明代時這里名叫“萬嶺箐”。
我第一次到竹海不是因了旅游,而是中學生的野營拉煉。1976年的春秋時節仿佛要出大事,空氣都有些凝固一樣。共和國的領袖相繼去世,忙著爭權的新貴正積聚力量準備作最后一搏,然而學校里的師生自然不知道這些,學校要培養的是紅色接班人,要學工、學農和學軍。學工,我們學校辦有一個不大不小的鐵器廠,生產打谷機什么的。學生們一期中安排個十天半月,去翻翻砂、打打鐵,挺方便;學農也不難,本就置身于一個小縣城,從南到北不過一千來米,從東到西不過三兩百米,之外就是田地,與城邊的哪一個生產隊聯系一下,農忙時去幫幫忙也是簡單的事情。惟有學軍難點,學校沒有條件搞軍訓,就弄了一個“拉練”活動,倒也轟轟烈烈。
南方的秋冬時節是沒有多少晴朗的日子的,連綿的雨已經下了好些天了,想來學校有意要讓我們到暴風驟雨中去鍛煉,如海燕樣叫喊著,飛翔著,像黑色的閃電,箭一般地穿過烏云,翅膀掠起波浪起飛吧,就在這樣一個季節,我們開始拉練了,目的地就是“萬嶺箐”。
由我們這些十四五歲的少年組成的,三百多人的隊伍踏著泥濘出發了。每人還弄上一床被子,有的用麻繩,有的用雞腸帶(一種用棉線編織的像雞腸似的帶子,故名)捆成背包狀背上,再背上一頂草帽之類,雄赳赳,氣昂昂地踏上了野營拉練的征程。而今的學校是斷不敢組織這樣大規模的集體活動的,現在的家長哪里愿意讓自己的獨生子女去翻山越嶺、過河淌水?倘有個意外,誰又負得起這個責?而我們的父母似乎都有三、五個孩子,磕磕碰碰原本就是常有的事情,意外地死掉一個好像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娃娃命不好而已,抹掉眼淚,日子照樣過。
從縣城到萬嶺小橋有四十多里路程,那時可只有一條小道溯淯江河而上,至相公嶺,也就是現在的竹海鎮則轉而登山。雖然平時習慣跑路,但那仍是十分艱難的。開始時大家興致很高,覺得挺好玩的,待走到相公嶺的時候,大家是再也沒有了玩的興致,只盼早點到達目的地。
早上七點出發,到達萬嶺小橋已經是下午五點過,這小橋是當時萬嶺公社革命委員會所在地,也就是現在蜀南竹海風景名勝區游人集散中心所在地。當然,那時的小橋沒有今天的賓館、飯店一類,不多的民居和公社醫院、小學校、楠竹經營所,以及公社革委會辦公地點等散落于修竹茂林之中,靠著幾條土路聯系在一起。冬日的天氣原本就黑得早,加之這茂竹遮蔽,霧蒙蒙的,所以我們這個班被安排在了楠竹經營所后,吃了夜飯,便疲倦不堪地睡下了。
第二天先是去參觀公社醫院種植的中藥材,如今還隱約記得好像有三七、紅花之類;然后參觀醫院,醫院不大,一樓一底,但仍顯得空蕩蕩的。接下來的勞動就是搬運楠竹,就是把林場工人從山上放下來的楠竹搬運到一個地方集中,對我們這些十五六歲的娃娃來說,這個活兒并不輕松,一會兒有同學被楠竹上未剔盡的節疤扎傷了手,一會兒又有人在放下楠竹時被砸傷了腳。扎傷手的用口吸吸血就是,厲害點再涂點碘酒、紅藥水什么的,傷了腳的更簡單,抱著腳跳著罵幾句搭檔就過去了。想來那時的孩子真是命賤得很,一天的活兒,嘻嘻哈哈的就干過去了。
然而,萬嶺箐這地方,對我們畢竟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世界,修竹茂林,盤根錯節,層巒疊嶂,擁青瀉翠,郁郁蔥蔥。這綠色的海洋、嬌翠欲滴的竹撩撥著你、誘惑著你、親吻著你、溫潤著你,讓你恨不能把這滿世界的綠都吮吸到自己的肺腑,洗滌自己的靈魂。所以,在下午干完活之后,我和幾個哥們同學仍相約,悄悄地沿著我們駐地后山的密林小道爬上山去了。爬山,倘若是無目標,那就必然是這山望著那山高,所以,于今我早已記不得那天我們翻了幾個山頭了。這時竹海起霧了,竹海之霧捉摸不定,不知什么時候悄悄的它就浮動在你眼前,然后便包裹了你。霧,就已在你腳下的丹崖絕壁間繚繞著,并慢慢向上升騰,慢慢簇擁你、淹沒你,最后只剩下你和身旁幾棵若隱若現的修竹。
包裹了我們的霧,讓我們一下緊張了起來,于是我們轉身便拼命往山下跑去,跑了一會兒,我們突然發現問題來了,原來我們上山的路已經找不到了,而且我們是跑下一座山頭,又面對了另一個山頭,恐懼開始如霧一樣包裹了我們。
這種在自然環境中對自然的恐懼,我參加工作后在大涼山還體驗過一次。那是1982年我在涼山一所中學任教的一個星期天,我和友人相約去登山,上到山上天還好好地,玩了會兒,天突然就黑了下來,緊跟著便電閃雷鳴的,暴雨頃刻就至。我們沿著來時的路,也就是山溝里往山下跑去,跑著,我們發現大事不好,山石竟也是在洪水裹挾下沿著山溝向下沖來。
“快往山梁上跑!”這聲音提醒了我們,也讓我們在那次遇險中沒有成為大自然的犧牲品。雖然我至今不知道那警醒我們的聲音是哪兒發出來的,也不知向我們發出脫離險境呼喊的人是彝族,還是漢族,但他拯救了我們。我不能想象,倘若那天我們沿著山溝向山下跑去,不知強大的泥石流會把我們掩埋在哪里。
好在竹海的霧滯留的時間并不長,一會兒霧便散去了。霧去,青翠的竹便又疏朗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讓我們順利地找到回去的道路。
以后,讀書,在外工作,然后回到長寧工作,有了去發現和體味竹海之美的機會。如今算來我上竹海已有好幾十次,每次游到忘憂谷、墨溪、仙女湖、仙寓洞、七彩飛瀑我都不覺得厭倦,每次上去無論是與三、五文友一起采風,或是陪一些不相干的客人走馬觀花式的看景,我都很想如祥林嫂那樣對他們講講我第一次上竹海,以及在大涼山登山遇到泥石流的故事,在心中感恩那位呼喊我們“快往山梁上跑!”的陌生人。
走出大漏斗
這個大漏斗在宜賓興文石林。去石林應當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旅游。那時也就二十來歲,放寒假,幾個要好的男女同學相約,湊份子去剛起步開發的興文石林玩。
早上乘客車從長寧出發,中途轉乘宜賓開過來的客車,到達古宋已經是天都黑下來了,其實也就百十里地,不過那時的交通,百十里地已很遙遠,我們此行算是遠足了。
古宋,位于四川盆地南緣,現在是興文縣縣城所在地,但在那時還屬敘永縣管轄。是明、清以來的川南重鎮,素有“川南要沖、敘南門戶”之美稱。是成都去云貴的重要通道。去云南,西路是建昌道(南路),即從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入,渡金沙江以達云南姚州(今云南姚安縣)境。中路是石門道(北路),即從成都經嘉州(今四川省樂山市),沿岷江經敘州(今四川宜賓市)而去云南老鴉灘(今云南鹽津縣),越豆沙關(即所謂石門)以向昆明。東路是川黔道西路,即從敘州沿長江東下,經南溪、江安后,或由今之蜀南竹海到興文以去永寧(今四川省敘永縣),或繞道瀘州過納溪縣以去永寧,再穿過黔邊直去云南的曲靖。過往的客商曾經無數次走過這條道路,充軍戍邊的士卒曾經無數次走過這條道路,貶職充邊的曾經無數次走過這條道路。嘉靖三年(1521年),以“議禮”得罪,充軍云南永昌衛(今云南保山縣)的楊慎,那時也曾經走過這條道路。走在這條道上的楊慎擺脫不了驚悸,膽戰心驚地寫下了“九絲城畔都蠻哄,……千戶紐綬喪其元,六郡疲民哭之慟。遠礙近哨煙塵昏,江陽戒嚴長寧奔。”的詩句。24歲狀元及第,金榜題名,“議大禮”為首撼門哭諫的楊慎,走在這條道上曾熱切期盼嘉靖放過他,然而,留給楊慎最終是徹底絕望,半生謫戍,去來行役,“往復滇云十四回”,多次奔波在川滇黔古道上,客死異鄉的宿命。
我們來時,過往的客商、充軍戍邊的士卒,以及楊慎早已消失在歷史的煙云之中,小鎮和我們當晚投宿的旅店也許早已不完全是幾百年前的樣子,但有一古老的物種對我們的侵擾,似乎又在向我們昭示著我們那時的時代還在重復著什么。
那晚,在古宋我們投宿的是一家小客棧,從車站出來,沿石板路走上一小段路程,便有一不很顯眼的招牌,某某旅社,進門一柜臺擋在眼前,喊一聲,里邊天井走出一中年婦人,一詢問尚有房間,就決定住下。開始登記,問我們有介紹信沒有,我們說有學生證,也就可以了。拿上行李,上樓,樓板咔吱咔吱作響,進入房間,四張木床,一邊兩張相向安放著,靠門有一課桌樣大小的木桌子,放著一暖水瓶,桌下一木桶、一搪瓷臉盆。黑黑的蚊帳,發黃的床單和被褥橫陳在我們眼前。好在我們對這些東西并不陌生,視為理所當然。大家伙隨身不多的行李往鋪上一丟,高高興興去吃飯,然后在伙房舀出熱水洗臉,燙腳,坐在床鋪上聊天,累了,倒頭便睡。半夜有同學起來上廁所,驚呼:“不得了啦,蚊帳上有蟲!”叫來服務員,服務員說有什么大驚小怪的,臭蟲,捉來踩死就是。
然而,那夜卻不敢再睡了,熬了小半宿,天一亮就趕著逃離了那家旅店。
真正到達石林已經是第二天中午。我們年輕的眼睛看什么都覺得新奇有趣,天泉洞、天龍洞、迎賓石、龍牙觀瀑、二龍戲水無不讓我們歡喜快樂。景自然是樂之所在,但重要的,我們的快樂還并不完全在于景。
一行年輕人經石門雄踞、天涯望歸等景點,兩個多小時后到達大漏斗。
漏斗,即天坑,是喀斯特地質的一種特殊地型。天坑的形成,系雨水降落在石灰巖地面上,沿著巖石的裂隙滲入地下,由于石灰巖具有溶于水的特性,地下水夾雜著溶解的石灰巖質,一路溶蝕四壁,逐漸擴大,在地下形成大型的溶洞。溶洞的洞頂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斷往下崩塌,直到最后洞頂完全塌陷,形成了喀斯特漏斗。漏斗是形象的說法,其形大都上闊下窄,巨大的縫隙使再多的水注入,也無法存留,就如生活中人創造出的漏斗,你就是有一座金山銀山,也會被漏斗吞噬掉一樣。
興文石林大漏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漏斗。90度的懸崖絕壁,如刀削斧劈。石壁平整,還沒有碑刻銘文,當時意氣風發的我站在石壁下突發奇想,有一天我一定在這石壁上留點文字什么的。這個奇想至今未實現,倒是后來一位偉人來到這里,在那峭壁上留下了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天下奇觀”。那是1983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視察興文石海后的揮筆題詞。
從大漏斗旁下去便是天泉洞。天泉洞,興文石林溶洞群中最具代表性,開發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個溶洞。溶洞常見,凡喀斯特地貌不管你是否已經發現,可以說都有,其景點也不外是因了石灰巖千姿百態,與我們人的歷史中的人物、故事、傳說,生活中的方式、習俗、景象相似,于是我們的前人,以及那些功利的旅游開發者,便發揮想象力,賦予了那些沒有生命的石灰巖以生命的內涵。今天,對于我這個已經看過許多溶洞的人來說已經不奇,但對當時的我們是說不出的驚嘆。記得從后洞進去,便是一個300多米長、40米寬的地下大廳,然后往里走,一束光線從暗黑中射過來,十分奪目,導游說那是天窗……直至前洞口“穹廬廣廈”,我們又發出了驚嘆:這是一個萬余平方米的地下大廳,洞頂巖石,拱卷呈穹,中央高達40余米。本地傳說,明代僰人首領哈大王率領起義軍數千人馬,曾在此洞中揮戈操練,以待戰機,待追趕的官軍至此,哈大王率眾出擊,殲滅官軍于大漏斗中。
然而,套用一句網絡用語告訴你:別崇拜哥,哥只是一個傳說。
僰人是先秦時期就在中國西南居住的一個古老民族。明代稱都掌蠻,生活于今興文、珙縣一帶,崇尚武風,喜好銅鼓,族中有人病故,全族往往將其棺木懸掛在懸崖峭壁之上,稱為懸棺葬。雄踞云貴川三界的咽喉地帶的僰人,民風剽悍,難于馴服,因此,歷來是中央政府的心頭之患,與中央政權的沖突的歷史可證的就有五百余年,茍存于中央政權的剿與撫之間。
比如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僰人為了獲取生活必不可少的食鹽,燒毀淯井監,殺死監官。梓州路轉運使寇瑊緊急命令各州巡檢發兵,僰人潰不成軍,被迫投降。寇瑊不專以武戰勝人之兵,而以寬容與妥協服眾,僰人有了繼續存在的機會。
到了宋徽宗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年底,瀘州安撫使賈宗諒強向晏州(今興文縣)等處“夷人”攤派竹木,僰人頭人卜漏率眾起事,然而此次鬧事的僰人沒有了100年前的祖輩們那么幸運。戰爭的結果是,是年冬月,宋軍在晏州輪摶大囤(今興文縣博望山)縱火燒山,攻破輪摶大囤,幾十里山林,燒成一片火海,卜漏等酋長十余人逃走,被趙遹窮追到晏州山后俘獲,押送汴京處死。
明朝開國以后,政府為了加強對西南地區的統治,開始逐步限制僰人的利益,僰人又曾發生過兩次大的騷亂,第一次是在明成化年間,此次,因有在朝為官的蜀南長寧人周洪謨的悲憫情懷,不嗜暴力,主張對夷施行懷柔政策,反對武力征伐,僰人算是又躲過了一劫。到明神宗萬歷元年(公元1573年),到了強勢的張居正手下,中央政府在這里強行廢除了一直以來的蠻夷酋長制度,代之以漢臣,使原本緊張的對抗終于演變成一場全面反抗明朝政府的戰爭。然而,僰人永遠失去了過往的幸運。四川省巡撫曾省吾、總兵劉顯率軍征剿僰人,僰人最后滅亡于了興文縣的九絲山,消失在這石林的大漏斗中。
從天泉洞出來已是下午四點過鐘,回望天泉洞,洞上高達一百四五十米的峻嶺斷崖灰黑幽幽的,四百多年前曾有的懸棺,痕跡尚還依稀可辨,那是一個民族證明自己曾經存在的證據,也是一個弱勢的族群必然被強勢的力量吞噬的證據。
我們離開興文石林,離開大漏斗是在到達這里后的第三天,一早乘從石林發出的客車,回至古宋已經是中午,匆匆趕往車站,開往宜賓方向的客車票業已售完。于是我們決定步行,一邊走一邊想搭順風車,但從古宋到長寧的雙河,一路未能如愿,48公里的路程,我們走了整整七個小時,每人都走得精疲力竭,腳上起了血泡。
回看當年,自然之景的大漏斗,我們靠著自己的雙腳走出來了。回顧人,如今我已是知天命之年,生命之大漏斗,生活之大漏斗我能否走出?真還說不好。情場、職場、商場、官場,文壇、體壇、政壇,以及中國文化中那形形色色的怪圈,這樣那樣的場,有些我壓根走不進去,而那些我走進去了的,我還能安然地、毫發無損地走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