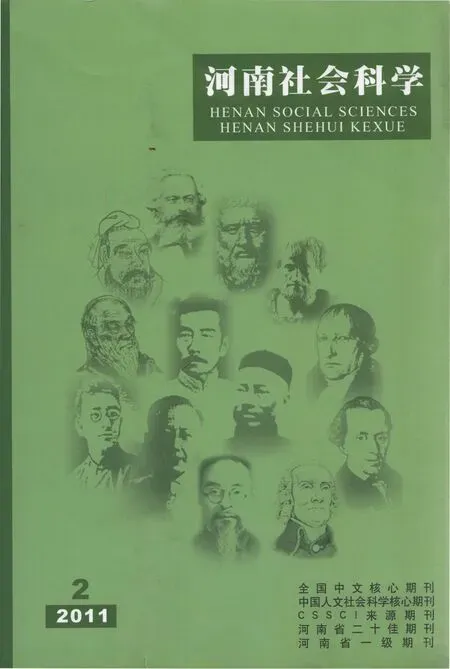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保護的經驗
——以融水苗族坡會群為例
徐贛麗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保護的經驗
——以融水苗族坡會群為例
徐贛麗
(廣西師范大學 文學院,廣西 桂林 541004)
當前我國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大多關注單項知識或技藝層面的生存狀態、社會意義、傳承價值和保護方略,不大重視社區整體內文化遺產的保護及文化對社區民眾的意義。人們在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略時,強調加強政府的資助力度;在實踐中,保護任務又交給了政府部門的文化工作者。因此,許多民俗成為“官俗”,失去了對社區民眾的意義。民眾不參與,文化遺產就有可能空殼化,于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要么成為暫時性的工作,要么已經變味。早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開始初期,周星曾提出把文化遺產保護在基層社區的意見[1],但未引起大家足夠重視,在此有重申的必要。
社區保護之說有其合理性。一方面,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特定文化空間內當地民眾創造的及文化與人相互依賴的道理,從特定區域的整體空間出發,借助文化主體的積極性和社區力量把文化遺產保護在基層社區,是較為可行的。另一方面,特定社區或文化空間本身具有文化遺產的屬性,同時又是眾多單項文化遺產的有機共生區域,這就決定了特定社區的遺產財富遠勝于單體文物或遺址,包括單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僅要保護存在于特定社區空間內的單項文化知識,更要把文化視為一個完整、功能齊全的自足系統,從空間整體和與人們生活的關系網絡中探究文化保持的方略,不僅要注重單項重要的文化遺產,而且要開展文化生態保護工作,有計劃地進行整體性動態保護。本文擬從具體案例說明社區保護的意義,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區保護是更為有效、實用和可行的。
一、融水苗族坡會概況
融水縣是廣西境內唯一的苗族自治縣,位于桂西北山區,與貴州從江縣相鄰。境內居住的苗、漢、壯、侗等民族,呈大分散小聚居狀態。苗族大都居住在縣境中部、東部和北部邊遠山區,主要分布在14個鄉鎮。坡會是融水境內以苗族為主的民間傳統節日,是一個在村外田邊、山坡或河灘舉行的交際和娛樂性節日。坡會期間,各村苗族小伙子們扛著蘆笙,姑娘們身著盛裝,男女老少皆喜氣洋洋一起趕坡。當地的坡會習俗由來已久,如良雙鄉“整依直”坡會,據歷史文獻記載在1687年就有了,至今有300多年歷史,其他坡會也大多有上百年歷史。坡會承載的苗族傳統文化內涵豐富,是苗族文化遺產的綜合體現,包括蘆笙文化、苗族音樂舞蹈、服飾文化、祭祀儀式以及打老同和蘆笙會等社會組織習俗、婚戀習俗等。融水境內十多個村寨存在時間呈連續性的系列坡會活動,從正月初三至十七日這段時間內,各地的坡會此起彼伏,連續不斷,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系列文化空間,并因其具有“序列的連續性、儀式的完整性、群眾的自發性、內涵的豐富性、文化生態空間的原生性、坡會的群體性和教育功能、多民族團結融合性的顯現”等顯著特征[2],于2006年以“融水苗族系列坡會群”之名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當地之所以會有系列坡會活動傳統,是因為當地苗族共有一些文化傳統。坡會是整個苗族地區的文化象征和文化認同標志。各個村寨的蘆笙隊在邀請和被邀請之間相互走動,使得附近相鄰苗寨村社的坡會在時間上被接續起來。目前,融水系列坡會群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其文化的保護與延續的經驗具有可借鑒性。
融水苗族坡會活動豐富多彩,既有傳統祭祀儀式,又有多種競技活動,其中以吹蘆笙踩堂為主,同時還有斗馬、賽馬、跳芒蒿舞等。以歷史悠久、影響較大的香粉古龍坡會為例,“這天,方圓數十里的男女老少身著節日盛裝,在坡上賽蘆笙,跳蘆笙舞,賽馬、斗馬、斗鳥,對歌,舞獅和鳥槍射擊比賽,盡興娛樂。古龍坡會地處苗區前沿,商品經濟較其他地方發達,坡會同時又是物資交流會,各種土特產品和民族時興商品較多,給坡會增添了節日氣氛”[3]。坡會活動的過程、內容在保持傳統的節目不缺失、傳統程序不變更的基礎上,適當結合當代生活,故有了一些新項目。總之,吹蘆笙和跳踩堂舞是坡會的主體活動,同時兼有文藝和體育競技娛樂,還有打同年等社交活動。此外,坡會也是物資交流的場所。
二、坡會的價值與功能
融水苗族坡會年年舉行,民眾為何能保持高漲的情緒?有苗族學者說:“苗族蘆笙是歡樂、喜慶和豐收的象征。苗族吹蘆笙,除了娛樂、友誼、交流和婚姻等目的外,還在于祈禱保佑,獲得風調雨順、田園豐收。因此,沒有蘆笙,不趕坡是一種不吉利,人心難得統一,生產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只有痛痛快快地娛樂,盡情地吹蘆笙,讓四面八方的朋友都來參加,增加節日的熱烈氣氛,使神靈滿意,民眾歡喜,來年生產才有精神上的保障。所以,苗族群眾心目中,蘆笙坡會規模越大越好。”[4]由此可知坡會的多種功能和坡會對于當地民眾的意義。融水坡會像許多少數民族傳統節日一樣,擁有多種功能[5],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種。
(一)男女擇偶和村寨聯誼
苗族坡會的來源有多種說法,但大多數坡會跟婚姻習俗有關。苗族傳說講到,苗族曾實行遠距離的外婚制,造成很多不便,許多年輕人因此不能成婚,于是人們就舉行蘆笙坡會號召年輕男女相聚,給他們提供一個在野外自由交往的機會[6]。趕坡范圍的逐漸擴大,也使得青年男女自由交往的面得到擴展。相當多的人的初戀都是由坡會開始,后來才走向婚姻的。
坡會上,小伙子圍繞蘆笙柱吹起蘆笙,姑娘們在外圍跳起踩堂舞,互相交流。吹蘆笙的小伙子,有的在蘆笙上插羽毛,隨著吹奏樂曲身體左右搖擺,羽毛被揮舞起來,有時會甩到姑娘臉上,吸引其注意。姑娘們都盛裝出行,展示美貌以吸引未婚男子的目光。在盛大、熱鬧的坡會上,姑娘和小伙近距離接觸,互相認識,留下美好記憶。通過年復一年的坡會,一聚再聚,年輕人就這樣結成良緣佳侶。坡會具有的這一功能使得年輕人對坡會抱有向往和期待。
打同年一般是指村與村之間整體的交流,是以村為單位的聯誼活動。邀同年要先經全村人同意。如果邀請某村打同年,就在坡會上吹起蘆笙邀請曲,圍住對方的蘆笙堂轉三圈,然后在對方的大蘆笙上貼邀請書。受邀方同意后,可在坡會散后跟著邀請方回去打同年,也有的會選擇其他合適時間受邀。打同年由村里年長的男性帶領全村小伙和姑娘前往,是為了讓兩個村的年輕人互相認識,尋找戀愛結婚的對象。打同年除了在蘆笙坪上進行蘆笙踩堂外,還有同年儀式。同年儀式在蘆笙坪上進行,主人要宰殺牛、豬等牲口款待客人。同年儀式就是把這些牲口拿到蘆笙坪上展示,主要程式是牽著還未宰殺的牛或豬,給牲口戴上大紅花、插上芭芒草,繞蘆笙坪轉三圈;同時展示的還有款待客人的米酒、糯米飯等。展示完后,經過三輪蘆笙踩堂,同年儀式就結束了。晚上,在蘆笙坪上進行同年宴會,之后,青年男女便可相邀回家或到村外對唱情歌。一般打同年進行三天,三天過后,客寨返程時,主寨要送給他們肉、糯米飯、米酒等食物,讓他們帶回給那些沒有來打同年的村民們一起吃。當客寨回到自己村子,便在本村蘆笙坪上,由全寨人集中享用帶回來的食物,會餐期間還會進行蘆笙踩堂活動。第二年,原來的主寨要到客寨打同年,客寨按照同樣的接待規格回敬。打同年的目的是為了增進兩個村寨之間的感情、消除矛盾。同時,也是為了給未婚男女提供相互認識的機會,以解決其婚姻問題。至今打同年仍是當地男女青年進行婚戀的主要方式。
(二)娛神娛人
雖然現在我們了解的坡會功能主要是為了社交或娛樂,但當地各類坡會活動的第一項都是祭祀。儀式通常是繞蘆笙柱三周,吹三曲,主事者面向東方蹲下,口念祭詞。祭祀的目的是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六畜興旺。
蘆笙踩堂是苗族民眾娛樂活動中最具普遍性的。民國《融縣志》載:“正月,侗苗則皆以男女集會,以蘆笙跳舞相賽……(蘆笙之會)蓋為男女間最大最愛之公共娛樂;集會則因人數而見笙之多少。女子衣華服,亦集為一班。每至一村,賓主各奏笙,互答三次而后作友誼之比賽,于是笙歌跳舞,聲韻抑揚。”[6]值得一提的是坡會的吹蘆笙活動中會有一位吹芒筒的人,他常扮演喜劇演員,以滑稽的動作令觀眾捧腹大笑,增加歡樂氣氛。
坡會上的娛樂還有斗馬、斗鳥、耍獅、舞龍燈等,其中以斗馬為多。斗馬的刺激、驚險會吸引許多民眾到場,其中以男性居多,圍觀人群中常傳出歡笑聲。這項競技活動深得當地人喜愛,也非常吸引外地游客或攝影愛好者。斗馬比賽的馬是專門喂養的,從不用于運輸;臨近比賽,主人要拌以黃豆粉、碎米、甜酒等喂食,使馬變得膘肥體壯,生性沖動。但斗馬本身并不能給主人帶來經濟收益,斗馬比賽的獎勵一般有村民自發捐獻和政府的資助,獎金數額不多,還有一些生活用品。當地人說:斗馬有點獎勵,但不大,這里的人就是喜歡。民眾的精神需求與自我滿足使這項活動一直傳承下來。
(三)貿易交換
坡會也有物資交流的作用。坡會的規模有大有小,大的上萬人,甚至數萬人,小的一兩千人。每年的坡會都同時形成人數多、流動量大的集市。苗族居住的村寨多分散在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區,平時貿易往來少,節日期間人們把山里、地里的產出作物帶到集市出售,商人小販也趁機運送物品來坡會進行交易,這滿足了供需兩方的需要。在商品短缺時期,坡會成為展示商品和滿足人們物質消費需求的重要場所。
(四)傳承文化和強化族群認同
坡會伴隨歷史發展一直在傳承和傳播著苗族的文化傳統。蘆笙是一種多功能的文化復合體,坡會則是苗族蘆笙文化傳承者的聚集點,分散在較大地理范圍的苗族人民相聚一起,有助于這些傳承者互相學習借鑒。在無文字的苗族社會生活中,有約定俗成的規約:到12歲的男孩必須習吹蘆笙。因為在祭祀、娛樂、求偶、婚嫁、節慶等場合都要使用蘆笙,他們主要是通過學蘆笙——念唱蘆笙歌、背記蘆笙詞,獲取知識和做人的道理。每首蘆笙詞都有明確、穩定的歌調,其內容廣泛,包括歷史傳說、生產知識、愛情婚姻、社會公德、鄉規民俗等方面[7]。現在,學校教育幾乎替代了傳統文化的教育傳承,孩子們只有在坡會期間才可比較自如地學習吹蘆笙和踩堂。盡管當地中學現已開始教授吹蘆笙,但在鄉村現實生活中,坡會期間一系列活動仍是孩子們非常珍惜的學習民族文化的機會。在蘆笙踩堂活動中,常可看到孩子們舉著蘆笙跟大人學習吹奏的場景。坡會上男孩學習吹蘆笙,女孩則在母親細心裝扮下加入蘆笙踩堂隊伍。孩子們從小在這種氛圍里生活,習得民族傳統文化,并保存共同的記憶,有利于把文化傳承下去。
坡會不僅是一個教育子孫后代學習本民族文化的場域,同時也可增強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坡會作為融水苗族人民全民參與的活動,每年重復其儀式和活動內容可起到強化認同的作用。有學者指出:“作為一種公共的文化行為,節日的最終目的并不在于娛樂或審美,而是在于社會教育和社會融合,是為了通過集體的慶祝活動和人人參與,來建立一套公共的精神信仰和價值觀念。”[8]當地政府在“申遺”材料中對坡會作為苗族文化遺產的價值是這樣歸納的:“融水坡會的意義和價值在于它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坡會鏈,正是這樣一個鏈條,可以顯示出當地苗族地區傳統的厚重、民風的淳樸,有著較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比較團結一致,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感。”
坡會是民族文化集中展現的時空。每逢坡會,當地苗族與各民族男女老少舉家舉寨前往趕坡;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覺得在城市失落或缺損了民族自尊心,也會利用春節假期積極參與。苗族同胞共同參與民族文化活動,進行村寨、群體乃至個體之間的交流,并以村寨、家庭或個人為單位開展各項比賽,以爭贏奪冠為快。共同的記憶、利益和文化特征使人們聚在一起,采取一致行動,坡會在無形中形成一種認同。總體來說,在當代,坡會的娛樂功能和尋求民族自信心、認同感的功能增強了,而其婚戀功能和信仰功能卻有所減弱。
三、坡會傳統延續至今的原因
前已述及,融水苗族坡會的文化內涵豐富,功能多樣,不同年齡、性別和有不同需求的人參與坡會都能從中獲得滿足,這就為其傳承和興旺形成了必要的條件。此外,坡會的組織者、參與者等因素也是不斷推動坡會年年相續、代代相承的重要原因。
坡會的組織者是坡會持續辦下去的主要力量。融水坡會是民間傳統的組織形式,苗族坡會的建立與廢棄都由埋巖決定。埋巖是苗族議定和執行習慣法的社會組織,遇有大事各村寨老或各村代表以至全體人民,會聚一起商討、決定處理辦法。當場要立一塊石頭讓其大半截露出地面以示決定,日后大家共同遵守。至今,融水苗族的民間組織仍發揮很大作用①。坡會的規模大小、舉辦目的、日期和場所以及坡會之間的關系、坡會的管理者等,都需要眾人商議來決定。為保證其法律效力,使大家共同遵循,要舉行埋巖儀式。一些大的坡會多經埋巖建立,未經埋巖的坡會也要經過當地父老商議,并征得村寨群眾同意才能建立。因此,坡會一旦建立便長期保留,不得更換,除非坡會建立后,年年遭災,人民生活困苦,或坡會給民眾造成過重負擔,或坡會期間傷風敗俗之事劇增,群眾憂心忡忡等。
坡會的確立有專門的民間組織負責,而坡會上吹奏蘆笙也是有組織的。坡會均為當地德高望重的人出面組織。通常每個苗寨都制作有一堂三十至五十大中小三種型號的蘆笙,每堂蘆笙都有一兩個舉足輕重的“蘆笙頭”,蘆笙頭有一定威望和社會活動能力。他們一般多為中年男子,既是蘆笙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又是苗寨的活躍分子;多數會唱古歌、說理歌、酒歌、情歌,能熟練吹奏引調、走寨、送親、踩堂、雜調、合調、留客、打同年等各類蘆笙曲,懂得各種禮儀和規則。如正月十六的古龍坡會遠近聞名,承辦該坡會的“古龍坡籌委會”是成立有一百多年的民間組織,有自己的辦公地址,有固定的人員進行組織策劃。紅水良雙坡會主要由良雙村洞寨楊氏家族主持,至今已傳十幾代人,最年輕的第13代傳人才40多歲。
既然組織者基本上是地方民眾或地方精英,那么,融水縣政府是否就僅是旁觀客呢?其實作為苗族自治縣,縣政府領導多是苗族出身,他們對本民族文化有深厚感情,也曾親自參與坡會建設。安太十三坡就是由政府出面整合周圍的小坡會重新建立的。1985年的正月十一至十八日,全國苗族學術討論會在融水縣城召開,為重振蘆笙雄風,恢復蘆笙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在時任自治區民委副主任梁彬及縣里四大班子的建議和支持下,在安太鄉建立了縣境內規模最大的蘆笙坡會,把安太一帶過去分散、時間不統一的蘆笙坡會統一起來[9]。隨后,縣直機關的干部們于1986年成立了縣蘆笙協會,每年組織蘆笙隊下鄉,參加不同地方的坡會活動。現在縣級文教機關等多個單位都有蘆笙隊。縣里成立蘆笙協會,帶動了蘆笙文化的傳承,消除了民眾顧慮。坡會組織除了民間的,有時基層政府也會出面。近年,良雙村村委漸漸介入坡會的組織,負責籌集捐款用作蘆笙比賽的獎勵和贊助每個村的踩堂隊伍。隨著村寨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以前蘆笙自我管理的傳統改變為蘆笙由村委干部負責收藏、作為公共財產管理。
但同時,政府并沒有對坡會進行過多的行政干預。政府辦節或保護文化遺產帶來的后果有可能是灌輸意識形態,使民間活動被政府征用,或成為宣傳政策的途徑,這樣往往會使當地民眾視之為政府工作或任務,從而失去參加活動的興趣和熱情。目前,融水坡會尚未出現因旅游開發帶來的民族文化資源商品化問題,旅游公司尚未接洽前來趕坡的游客,縣政府也沒有著手干涉坡會的策劃與安排,只是派出交警管制交通,以及有一些單位在坡會上擺攤宣傳政策而已。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常涉及的問題之一是經費。許多有關呼吁都提到要加大政府的資助力度,但政府財政經費有限,諸多文化遺產都需政府扶持,政府恐怕顧不過來。融水苗族坡會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坡會作為地方傳統,活動經費一向是當地苗族民眾捐助。苗族民眾人人熱心公益,都把做公益看做是盡義務。苗族民眾里修路、搭橋、建亭,都是群眾自愿完成的。遇到大型公共活動,人們踴躍捐款捐物,這是傳統的美德。坡會要用到誰家水田或旱地,主家會提前整好場地,為節日到來做準備而不要任何報酬。坡會中打同年、賽蘆笙等所有開支,都由村人共同負擔。當地苗族人民認為,年節中多一份喜慶、多一份歡樂,來年田園里將多一成豐收。在這樣的鄉俗民風里,大家對文化遺產的保護都有積極性。
許多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討論都談到“傳承”、“傳承人”是關鍵。目前,政府對傳承人的補貼確實是一項支持,但在政府作出補貼前,當地的傳承譜系也沒有中斷過。這主要是出于民族情結和文化自覺意識以及民族文化生存的危機意識。融水縣是廣西唯一的苗族自治縣,苗族本是一個不斷遷徙、歷經艱辛的民族,融水苗族主要從貴州遷來,為了不忘祖先、不忘民族文化,故特別注重以自己本民族文化來強化認同和凝聚民心。
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不只是由幾個民間藝人來傳承的,而是整個生活在這一文化空間的所有人共同繼承的財富,如果只注意保護幾個傳承者而不關心當地廣大民眾,不關心他們的文化難以傳承下來的原因,那我們想保護的就真的會成為即將過去的“遺產”,而不能達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要求的“有機地存活于共同的社區或群體之中構成非物質的生命環鏈”,對遺產的保護還“包括它由生成、傳承到創新的全部過程”[10]。
非物質文化遺產重在保護文化主體,參與者應該是社區居民,甚至是全民參與。融水坡會“申遺”時沒有使用“融水苗族坡會”的寬泛統稱,而是明確地以“融水苗族系列坡會群”為名,同時列出15個坡會,這就使各地坡會都納入保護的范疇,都有自身存在的價值。各地坡會是組成系列坡會文化鏈上的一環,盡管受到現代化的沖擊,但誰也不想從這根鏈條中脫離出來。韓國東國大學歷史系教授任敦基指出,各種遺產不應厚此薄彼,各種遺產項目有各自不同的形式,且每一個表演者都在傳播自己的版本。如果遺產中不同版本之一被列為國家的文化遺產,那就有可能在被列為遺產的版本得到傳播的同時,其他地方和藝術家的其他變種版本被排除在外。如果試圖在民間藝術的保護上具有更廣泛的多樣性,就應該考慮一種方法,使其能夠超越被列為遺產和沒有被列為遺產的民間藝術之間的關系,并能夠長久地保持民間藝術的多樣性[11]。這番話很有道理,我們應該重視。
四、非物質文化遺產社區保護之理由
古人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12]地方土壤的特殊性培育出特別的物種,當地生態環境構成相生相克的生物平衡系統,很多物種只能生存在適合自己的環境下。同理,文化也有自己的生態環境。文化遺產應該保護在其本土社區而不應懸置在社區之上或移植到與文化生態不相適應的異地。文化遺產被從原有社區抽離出,離開其生長土壤,得不到營養,遲早都會枯竭。在文化遺產產生的特定社區保存著跟遺產相關的文化記憶和情感依托,如果抽離了其原生土壤,就會導致文化脈絡的斷裂,使遺產成為歷史的碎片和化石,難以在當下民眾生活中獲得發展、產生意義。有學者指出,如果以政府政績工程的形式對待遺產保護,取代遺產傳承的主人,不但會影響到傳承人傳承文化遺產的積極性,也會影響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生態性、民間性與真實性,從而使民俗變成“官俗”[13]。文化遺產保護在基層社區,有如下理由。
(一)社區保護可以保證社區民眾的幸福和利益,促進社區進步
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社區的意義,是其保護的動力。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的條件之一,是要求這一文化須扎根于一個地方的傳統文化歷史中,能夠作為一種手段來體現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質和價值,對社會團體起到促進作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地方民眾是有價值的,前述坡會的功能就是當地民眾一直堅持的動力。當地大量青年外出打工,他們在緊張的工作中,在外地人生地不熟,也會遇到婚姻問題,這時他們仍需要回到家鄉來解決,因此,坡會的傳統功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仍然存續。日本民俗學者菅豐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就在能給當地人帶來幸福。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而獲得的利益,理所當然地應當還原給保持這種文化的普通人為主的群體。非物質文化遺產并不是其本身有價值,而是在傳承這種文化的人們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之中其價值才得以生成[14]。
(二)社區保護可以依靠地方民眾的力量,以民俗的方式進行
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在于其功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關鍵是要延續或更新其功能,包括娛樂、祭祀、認同和凝聚等。既然是文化遺產,則其對當地人就有切身的意義,它曾經滿足過人們的需求,是大家的情感寄托。社區保護可以發揮文化主體自身的積極性。只要社區成員認識到遺產的內涵和價值,就會激發他們對自己文化的認同感、自豪感,激發他們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研究者在對彝族“火把節”的研究中提出:“未來火把節在活動內容和組織形式上應首先滿足當地居民的需要,包括情感需要、文化認同需要和心理歸屬需要。”[15]社區保護便于動員地方文化精英參與,不僅能促使人們更好地保護,也可適當增加與文化遺產相關的活動,使社區民眾受益,或給他們帶來娛樂和各種機會。有人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流失原因進行過調查,結果顯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公眾保護意識不強。我國有一些傳統文化傳承至今,并沒有消亡,反而興旺起來,原因是這類文化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人們會主動保護并延續。現在有一些被列為文化遺產的對象不能跟普通民眾的生活產生關系,不能給他們帶來利益或讓其感興趣,他們覺得與己無關,這就導致了文化遺產的無意識流失。因此,不能只是簡單地強調保護,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更需要激活其功能、轉化其價值、使民眾喜好,尤其是為社區民眾所應用。
社區保護的好處很多,例如,可依靠基層自己的基金或樂捐的方式以及民間原有組織力量來落實保護,不需依賴國家,降低運作成本。依靠基層社區民眾的力量具有可行性,具體說來,不妨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推行民間社會的教育,不只依賴學校教育。二是發揮文化精英的作用。許多地方文化精英都有為家鄉的文化保護和建設出力的愿望,希望借助文化的力量增加家鄉的社會資本,尋求發展機會,而他們往往在地方社會也有較大的影響力。三是發揮民間組織的作用。年輕人外出打工,許多地方的老人協會主管著社區的傳統文化活動,老人們有時間并且保存了關于遺產的記憶,愿意為恢復和傳承文化遺產的相關活動出力。四是發揮宗教向心力和號召力的作用。民間信仰一直是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力量,利用民間信仰的相關活動,也能帶動文化遺產活動的復興和保存。五是可由單個社區逐漸擴展到周邊社區。那些有保護民俗的民風和優良的公益生活傳統的社區,常常能自覺使文化遺產得到保護[16]。如果先從這些社區著手,再形成保護區,可以帶動和促進相鄰社區的文化傳統的恢復。
(三)社區保護更有可能保證遺產的本真性
社區保護方式可以使文化遺產的內涵得到正確闡釋,因為社區民眾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遺產中最真實、有價值的部分。方李莉曾針對文化主權問題提出“誰擁有解釋文化的權利”這一問題②。瓦努阿圖國家文化委員會和瓦努阿圖文化中心主任拉爾夫·雷根瓦努認為,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鍵特征是它的動態存在,即是不斷地由承載這一文化的人重復創造,因此,應該由傳承者自己來確立他們的文化當中什么是最值得保護的,并且積極參與保護措施的決策以及這些措施的實施[11]。
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實踐中,人們常討論的一個話題是“本真性”,即要保護具有本真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本真性的追求,源于許多申遺項目其實是為了爭奪文化資源提出的。地方文化精英或政府官員的一些全新詮釋,往往缺失現實中的根基。因此,盡管有些文化項目已進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卻不被地方民眾所認可和接受。融水坡會的申報書盡管也有整理和美化痕跡,但基本符合現實。無論用多美的辭藻形容此類活動,都是為了給外人看,但對當地民眾來說,坡會有著悠久的傳統,有著多種文化內涵,苗族民眾從小就沐浴其中,誰都懂得它的內涵和意義。
(四)社區保護可以使文化遺產在原生地繼續生長
坡會的影響不僅在于增強民族認同與集體意識,它還促使后輩們在坡會氛圍中明確了屬于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坡會是集體性的,集體的共同參與強化了后代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塑造了后代將文化繼承下去的責任感。這正契合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行辦法》的要旨:“要通過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等途徑,使申報的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后繼有人,能夠繼續作為活的文化傳統在相關社區尤其是青少年當中得到繼承和發揚。”
坡會年復一年的舉行,使參與其中的廣大苗胞意識到自己的民族身份。有學者提出:“節日最大的特點是周期性復現,傳統節日在年度時間中循環,人們可以不斷地脫離日常世俗時空,回到神圣的歷史時空中,直接面對自己的祖先,反復重溫傳統、體味傳統,從中汲取新的文化力量。”[17]周星曾指出,社區保護的好處之一在于“由于社區文化生態和社區人文背景的支撐,不僅有可能使‘遺產’持久地‘活’在民眾的生活之中,而且在新的條件下,它還可能獲得‘再生產’的機會,亦即成為社區文化創造力的源泉”[1]。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僅是要保護其形態,更要延續和傳承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存在于特定群體生活之中活的內容,是發展著的傳統的行為方式,具有流動性。社區保護不僅能使遺產得到保護、傳承,還能使之發展,容納民眾的創造,并能保持其核心的價值。這才是許多學者所強調的整體保護、活態保護。
(五)社區保護可以喚醒和復興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其他文化元素
社區保護能保護好遺產生存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使其他相關的文化元素和社區及周邊居民的生活需要相關聯,使內部需求循環起來。這有利于增加社區和諧與穩定,喚醒居民的愛鄉情結,提高文化自信。坡會綜合了各種苗族文化元素,它包含的各文化成分之間有較強的內在邏輯性和關聯性。節日中吹蘆笙踩堂、穿民族服飾、斗牛、斗鳥等都與社區苗族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關。蘆笙世代傳承,苗族制作、吹奏蘆笙和聽蘆笙,已形成了生產、銷售和享用的路徑和規則;苗族服飾在這一特定場合也成為自我認同和強化認同的符號。由坡會帶動,社區保護可以連帶保存苗族的蘆笙文化、音樂、舞蹈、服飾、宗教儀式、社會組織習俗、婚戀習俗等。
總之,社區保護既必要,也可行。社區保護的關鍵是恢復和轉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社區中的功能,依靠地方民眾的自主性,并借助政府相關政策。社區保護并不排斥國家保護,當下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尚處初始階段,政府的引導、指導、監督、宣傳及財政支持都是必要的。當某些遺產項目已經失去功能和市場時,社區保護需要依靠國家給養,同時依靠遺產本身的價值,使之繼續得到延續。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所涉及的領域眾多、內容復雜、覆蓋面廣、任務艱巨,包括人員編制、經費投入等都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做支撐,而政府的力量也有限度。因此,最終仍要落實到社區才能進行持續、有效的保護。
(注:本文的部分資料來源于廣西師范大學2007級民俗學專業研究生郭悅、韋婷婷的實地調查,在此致謝。)
注釋:
①直至今日,當地的許多村民對國家法知之甚少,而熟悉本村的村規民約。絕大多數村民都認為習慣法才是管得到的“法”,只要按老傳統辦事就不會違法。
②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36567792_0_4.html。
[1]周星.民族民間文化藝術遺產保護與基層社區[J].民族藝術,2004,(2):18—24.
[2]柳州市文化局,融水苗族自治縣.非物質文化遺產·融水苗族系列坡會群申報材料匯編[C].柳州:柳州市文化局,2005.
[3]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志編撰委員會.融水縣志[M].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8.
[4]吳承德,賈曄.苗族蘆笙[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92.
[5]羅安鵠.鼓樓文化、坡會文化與現代化[J].廣西社會科學,1998,(5):108—112.
[6]丁世良,趙放.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下)[C].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7]余佳.苗族蘆笙文化的現狀及思考[J].藝術教育,2009,(9):100—103.
[8]王霄冰.節日:一種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間[A].中國民俗學會,北京民俗博物館.傳統節日與文化空間——“東岳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專輯[C].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3—15.
[9]戴民強.融水苗族[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2009.
[10]方李莉.請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擁有者[J].藝術評論,2006,(6):22—28.
[11]震剛.各國學者共論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EB/OL].http://www.china.com.cn/zhuanti2005/txt/2005-01/28/content_5771618.htm.
[12]盧守助.晏子春秋·雜下之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3]苑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主體研究[J].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09,(2):1—8.
[14]菅豐.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價值[J].文化遺產,2009,(2):106—110.
[15]李玉臻.從邊緣到中心:旅游背景下民族傳統節日轉型研究——以四川涼山彝族火把節為例[J].學術論壇,2009,(2):90—93.
[16]董曉萍.論民俗保護區的方案及其構成[J].河南社會科學,2007,(2):18—21.
[17]蕭放,廖明君.傳統節日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J].學術訪談,2009,(2):21—27.
2010-12-08
徐贛麗(1967— ),女,江西宜豐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民俗學博士,主要從事文化遺產、民俗旅游等研究。
責任編輯 宋淑芳
(E-mail:hnskss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