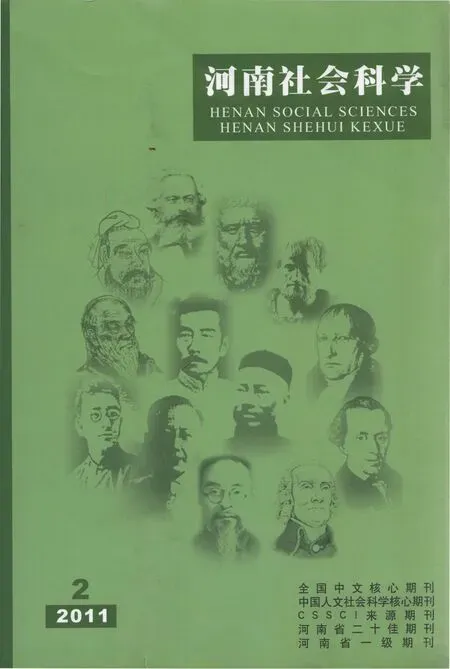文化遺產與“地域社會”
周 星
(日本愛知大學 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日本 愛知縣 441-8522)
文化遺產與“地域社會”
周 星
(日本愛知大學 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日本 愛知縣 441-8522)
近年,急劇興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極大地改變著中國的社會格局與文化生態。經由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導的《世界遺產國際公約》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國際公約》,中國全面引入了國際社會通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同時,國內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多種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既善于學習國外經驗,又堅持與實際國情相結合,充分體現了中國的主體性。鑒于現階段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面臨的新挑戰和新問題,本文擬對日本重視“地域社會”的有關經驗作一些介紹,希望為中國今后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實踐提供一些參考。
一、什么是“地域社會”
“地域社會”一詞來自日語,可以考慮將其翻譯成漢語的“地方社會”(或“鄉土社會”)及英語的local community。考慮到漢語中的“地方”主要是相對于“中央”而言的,故在介紹日本的文化遺產保護體制時,本文仍使用“地域社會”這一表述。所謂“地域社會”,主要是指基于地緣關系形成的集團、結構和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它和“地域共同體”的概念較為接近,只是后者更加突出集團這一側面。日語又有“地域社區”一詞,作為一個日英合成詞,主要是指一個地域內居民生活的場所(或空間),居民們在其中生產、勞作、消費、娛樂,同時享有教育、醫療、健身和保安之類的社區服務,人們在其中相互交流、相互幫助,共同組織和參與本地特有的節祭和藝能展演活動等。換言之,“地域社區”的概念,有時可以和“社區”(community)、“地域社會”等相置換[1]。不過,從日語使用的文脈看,“地域社會”有時還被用來指稱超越村落共同體或町(鎮、街區)等基層熟人社會而更加廣大一些的“地域”或“地方”。
日本“地域社會”的最為基本和單純的形態就是村落,經營稻作的農村、種植雜谷的山村或從事捕撈的漁村等。村落往往會有一座神社,它構成該“地域社會”里居民精神世界的中心。同一個“地域社會”里的居民,被認為無條件地就應該是本地某神社(供奉著“氏神”)的信仰者(“氏子”)。這從當今的標準看來,有可能出現干涉個人信仰自由的情形。由于經常在同一座神社參加各種神事、祭禮和民俗活動,人們彼此就會產生一種“歸屬意識”。同一“地域社會”的成員,有時會相信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或他們各自的祖先彼此之間也曾經存在著很深的連帶性。在多數情形下,同一“地域社會”里的人們往往從事著相同或類似的生計,擁有相近的價值觀和人生經驗。可見,舊時日本的“地域社會”往往就是一個具有一定封閉性的共同體,“外人”想要進入很困難。共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人們的集團,其傳統社會結構有利于抵御外部的安全威脅,也有利于共同和平均地利用周圍有限的自然資源(土地、河流、山林、海面等),但它往往會形成對個人的壓力,甚或會以犧牲個性和個人幸福為代價追求“地域社會”的整體利益。這樣的“地域社會”里固然存在某些競爭或個人的利益,但更加重要的規范則是成員之間彼此相互信賴、相互扶助、相互協作、相互救濟。一些在當今看來可能不盡合理的“人情”、“義理”和社交規范往往具有強制性,這在帶來社區連帶感的同時,有時也會對個人隱私構成威脅。這樣的“地域社會”大體上是自江戶時代以來得以形成的,到明治時代則有了民族國家的強行介入。日本一般是在“市町村”這一國家行政的地方基層機構的體系之下設立“町內會”或“自治會”①,這類民間社團往往就成為“地域社會”的代言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尤其是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及伴隨而來的社會文化的深刻變遷,促使日本各地的“地域社會”漸漸趨于瓦解。從某種意義說,“地域社會”的頹廢乃至解體,是日本現代化進程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之一。都市化進程導致農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或其近郊,在實現了全社會中產階級化的同時,日本還迅猛進入高度發達的汽車社會和IT社會,與此相應,農村、山村、漁村之類“地域社會”則出現了大面積的“過疏化”、“空洞化”、“鄰居他人化”以及“高齡化”、“少子化”等一系列深刻的社會問題。由于遷徙自由和頻繁的工作變動,持續參加“地域社會”各項傳統節祭或其他民俗活動的居民日趨減少,很多長期傳承于當地的傳統產業、傳統工藝、傳統藝能(歌謠、舞蹈)等文化形態均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承擔者(傳承人)后繼不足的窘境。
多年來,日本各地出現了旨在復興“地域社會”或使其“活性化”的種種嘗試和努力,以應對超老齡化社會因人際關系高度疏離產生的弊端。為振興“地域社會”,促使本地域內經濟、社會及文化的發展,當地基層政府與普通的居民、商工會、農協、漁協等本地社團之間密切合作,以擴大雇傭規模來遏制人口外流趨勢。振興“地域社會”,就必須強調當地的主體性。企業將其社會責任具體落實到為地方作貢獻上,積極參與社區節慶活動;大學舉辦各種市民講座;銀行、郵政等為當地居民提供多種往往超出其業務范圍的服務等。總之,產(企業)、學(大學及科研機構)、官(地方行政)、民(NGO、NPO、市民團體)相互結合,被視為振興“地域社會”的基本模式。一般民眾是地域振興之可持續發展的受益者和推動者,他們組成了許多旨在解決本社區內特定社會問題(老年人福祉、環保、教育、醫療、防災、社會保障等)的NPO組織和志愿者市民小組。與振興“地域社會”有關的文化活動,主要有:發掘具有本地文化特色的傳統產品(本地名吃、名產、社區標志、可促成“地域名牌化”的象征物和吉祥物等);擴大本地傳統節慶祭典的知名度;對本地觀光資源深度開發;建立美術館、博物館、歷史民俗資料館,保護本地歷史性建筑物等。
使用“地域社會”這一概念時,考慮到中國的情況,筆者想用它來特指超越村落共同體等鄉土熟人之基層社區的較為大面積的“地方”,把它界定為介于國家的基層區劃之“縣域”和村落之間的“地方”。大體上,其范圍可以經由“通婚圈”、“祭祀圈”和“集貿市場圈”這幾個人類學的范疇來限定。所謂“通婚圈”,主要是指婚姻成立時相互擇偶的地理空間,以某村落為例,其女子出嫁的大致范圍以及該村男子所娶妻子來自的周邊村落分布的地理空間范圍。鄉土社會多實行宗族外婚及某種程度的村落外婚,由于交通條件限制和“娘家—婆家”關系的制約,通婚圈大致就局限在人們步行當日可以往返的范圍之內。同樣,“祭祀圈”大體上是指經常前來同一座廟宇(或廟宇群)上香朝拜,或輪值參加廟會宗教活動的人們所居住的大致范圍。“集貿市場圈”則主要是指依賴于某個集貿市場(墟、集、場)或步行所及的周邊若干個集貿市場的人們分布居住的大致范圍。這三個“圈”雖然往往不能夠完全重合,但可以反映出一個“地方”的封閉性及流動性,它們所大體框定的“地方”也就相當于一個“地域社會”。顯而易見,正是在這樣的“地域社會”里,生發、容納和承載著絕大多數農耕生活時代的傳統文化形態,因此,可以說“地域社會”是文化遺產的傳承母體。
二、重視“地域社會”的文化遺產保護
日本以《文化遺產保護法》為核心的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制體系,從整體上說,具有重視“地域社會”、重視文化遺產的相關當事人(傳承者、保持者、管理者)等特點,可以說確立了中央與地方緊密協作、共同管理和保護文化遺產的行政體制[2]。例如,《文化遺產保護法》對所謂“地方公共團體”的地位和作用有詳細規定,以確保其在本地域的文化遺產保護與活用工作中承擔具體而又重要的責任。通過由國家(中央政府)、地方公共團體、文化遺產當事人、社區組織及全體國民分別承擔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從而形成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全國范圍內的系統體制[3]。
日本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出臺于1950年,此后在實際應用過程中歷經修訂而逐漸趨于完善。例如,1954年的修法,明確界定了地方公共團體在保護、活用文化遺產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強調了地方公共團體的重要性。1975年對《文化遺產保護法》進行大幅度修訂,將新設的“民俗文化遺產”(包括“有形民俗文化遺產”和“無形民俗文化遺產”)范疇納入保護對象,并創設了“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制度,以保護那些承載和銘刻著各個“地域社會”之歷史與文化傳統的村落和街區[4]。“傳統建筑物群”和周圍環境融為一體形成的歷史性風貌,被認為具有較高的歷史、學術和文化價值。該制度要求各地對傳統的建筑物群設定“保護地區”,亦即強調整體風貌的完整性保護。在日本,現代化的街區開發迅猛發展,導致傳統的村落及街區景觀迅速消失。有鑒于此,20世紀60~70年代日本各地相繼出現了由當地的市民團體組織和發起的保護運動,其成果反映在法制建設方面,就促成了由國家選定“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這一制度。
“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的選定,首先需要由各地的市、町、村教育委員會進行“保存對策調查”,制定相關的“保存條例”,并據此展開必要的維修、修景、環境整備和防災等保護工作;然后,由市、町、村向文部科學大臣提出“選定”申請,經法定的“咨問”與“答申”程序,才有可能被選定為“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一經選定,將由國家提供必要的經費補助,國稅和地方稅也都會有一些稅制優惠[5]。這個制度的最大特點是由基層地方及本地域居民來決定當地的“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保存地區內的現狀變更、維修或改善其外觀等保護事業,歸根到底都以地方為主體進行。截至2010年6月,分布在日本各地的“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共計87處。這些保存地區的選定和保護不僅使其整體的歷史環境或景觀得到有效保護,而且通過鼓勵地域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使這些地區成為富于歷史個性魅力和生命活力的新社區。
日本在2004年對《文化遺產保護法》進行再次修訂,又進一步創設了“文化景觀保護制度”。“文化景觀”主要是指不同地域因為人們的生活或生計及根植于該地“風土”形成的景觀,例如,“梯田”(水田)、“里山”②、“水渠”(灌溉系統)、花園、人工植被等。地域社區的居民利用當地獨特的氣候和風土、環境條件創造出的“景觀”,往往可直接成為觀光產業的本地資源。新創建的制度以根植于地域生活和生業的景觀為對象,促使其在當地得到保護并將其傳承給后世。它不僅促進了一般民眾對“文化景觀”的理解,也有助于“地域社會”的振興和發展,增強了景觀所在地域社區的活力。
對“重要文化景觀”的選定,基本和上述“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的選定程序相似。首先,得由各地方的基層政府,根據《景觀法》確定其景觀規劃,制定與景觀地區有關的都市規劃,展開關于文化景觀保護的調查等;其次,由地方上制定保護文化景觀所必需的條例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計劃(內容包括文化景觀的位置、范圍,保護的基本方針和保護體制,文化景觀的整修和整理);再次,由地方政府向國家提出申請,但需要征得有關所有權人的同意;最后,經過《文化遺產保護法》所規定的“咨問”、“答申”等法定程序,便可被“選定”。一經選定為“重要文化景觀”,中央政府的文化廳便發布“公示”,并通知景觀所有權人、占有者及地方政府。此后,地方上進行的有關“重要文化景觀”的維護、修景、復舊、防災等項目,均可依法獲得國家財政的經費補助,同時在地方稅的稅制方面也有優惠措施。
上文以“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和“重要文化景觀”的選定制度為例,介紹了日本文化遺產保護的法制體系比較重視基層“地域社會”和地方公共團體的作用這一特點。保護好本地域的文化遺產,既是地方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地域社會”面臨的重大課題。目前,日本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比例高達97%)均制定了適用于本地域的《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從而使本地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有了地方法規作為可靠和具體的依據。同時,地方政府還設立和經營著許多旨在保護和“公開”本地文化遺產的公共設施,如美術館、博物館、文化館、歷史民俗資料館、文化傳習館及地域社區的文化中心等,并通過多種方式動員普通市民參與,積極開展各種學習、愛護、傳承和活用本地域文化遺產的活動,其中包括以普通市民為對象的涉及文化遺產的“啟發”和“普及”活動。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全國各地均活躍著一大批致力于保護、傳習、開發和活用本地域內各種文化遺產的民間社團,這些地方性和民間性的文化遺產保護組織,在“地域社會”的文化傳承中發揮著核心、骨干和凝聚的作用[6]。例如,和歌山縣紀伊大島的“須江獅子(舞)保存會”、岐阜縣郡上市的“獅子舞保存會”、大阪市淀川區神津神社的“獅子舞保存會”、愛知縣奧三河的“花祭保存會”等。日本政府為保護其非物質文化遺產設立了“保持者”(所謂“人間國寶”)、“保持團體”的認定制度。各個地方政府的教育暨文化部門,均必須為使本地獨特的傳統工藝、手工藝或民藝的某些傳承人能夠獲得國家認定而準備許多調查資料;很多地方往往還會成立“某某人申請‘人間國寶’后援會”之類的民間社團,而一旦有某人獲得“人間國寶”的認定,他所屬的“地域社會”整體都會引以為豪[7]。除少數分布在全國范圍或局限于宮廷皇室的傳統藝能以及某些超越了“地域社會”而存續的行業性藝能技藝之外,絕大多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括藝能、技藝和民俗活動,基本上都是以“地域社會”或地域社區為依托和母體的。因此,對于它們的保存和活用,自然也就應該強調“地域社會”這一具有根本性的立足點。
三、幾個代表性案例
這里,舉幾個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利用“地域社會”的傳統習俗,維護世界文化遺產
岐阜縣的“白川鄉合掌造村落”,于1995年12月被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該村落以巨大的正三角形“合掌”式屋頂構造的農家建筑為特點,被視為日本“豪雪地帶”之山村民居的典型,其造型結構便于承重(積雪)和在屋頂閣樓內從事養蠶業等。這種民居的特點和優點很多,屋頂像人手“合掌”一般坡面陡峭,幾近60度;屋頂內的閣樓山墻開窗采光,可確保通風,冬暖而夏涼。苫蓋屋頂的材料是在當地就地取材的茅草和蒿草之類。在一片片綠色的稻田或旱地上聳立著一座座美麗的“合掌造”傳統民居,構成了一幅獨特的人文景觀,被認為是日本傳統山村的“原風景”。19世紀末,當地曾有過很多這樣的民居建筑,但到20世紀中葉以后,數量急劇減少,除修建水庫淹沒了一些之外,也存在有人嫌它住起來不方便而出售或拆毀的情形。1971年,在一些外來學者的建議下,白川鄉荻町成立了“村落自然環境守護會”,制定了“不出售、不出租、不破壞”的三條“村民憲章”,對村落進行整體性保護。1976年,當地的村落被指定為國家的“重要傳統建筑物群保存地區”。當地村民通過各種文化遺產保護活動阻止了村落人口的進一步減少,甚至有一些外出的年輕人又回到村里,對“地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
建筑一座這樣的民居,除了柱、梁、椽等骨架部分需要由專業的木工匠人承擔外,其他如建材的籌備、部分搭建工序,尤其是屋頂苫蓋茅草的作業,過去都是由全體村民通過一種叫做“結”的互助機制集體協作完成的③。采用本地建材、盡量不花或少花錢而由全體村民集體協作建成,這些都反映了山民的生活智慧。舊時白川鄉盛行大家族制度,一棟房子里一般要住幾十人,通常也不分家。人們必須通過集體互助才能夠在嚴酷的深山環境里生存。每隔30~40年,其茅草屋頂就需替換更新一次。由于房屋的規模巨大且屋頂傾斜坡度很大,僅靠一家人難以完成作業;而且,由于房屋仍在使用中,故屋頂替換作業必須在較短時間完成。更換一次屋頂,據說要準備3年之久。首先要根據屋頂斜面面積對所需茅草數量和人力予以概算;一旦擇定吉日,就向全村各家發出通知,請求大家在某一天來幫忙。事先割取必要數量的茅草,并確定參與人員的分工(男人們收集和搬運茅草、對茅草進行甄選、準備其他道具如繩子等;女人們為大家準備飯菜和作業間歇休息時的茶點,同時,也要準備作業完成時用于祝賀的禮品等)。作業一般不在兩個坡面同時展開,而是先完成一面,再接著完成另一面。通常苫蓋一面約需要2個工作日,每天需要200~300人參加,其中約有100人需要在屋頂斜面上作業,因此,其集體勞動的場面頗為壯觀和激動人心。
2001年,長瀨家的一次更換屋頂作業,就是在時隔30年之后舉行的。不僅全體村民,甚至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環境保護團體和志愿者們,共有500多人參加了這次作業。長瀨家的房屋比一般民居的房屋大一倍。僅屋頂斜面的單面就使用了12000捆茅草。當時,NHK電視臺轉播實況,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自從白川鄉的“合掌造”村落登錄為世界文化遺產之后,游客們蜂擁而至。村落人口僅有2000人,每年卻要接待來自日本全國各地的游客多達150萬人。大量游客來訪引發了很多問題,諸如交通堵塞、停車場不足、游客排泄物的處理困難、游客超出旅游路線任意進入居民家中窺探等。與此同時,村民們以游客為對象大賺其錢,價值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村落內部不但產生分化,而且間接影響到人們的互助協作精神。由于人口老齡化、山村“過疏化”及第一產業(農業)的衰退,“結”這種互助機制慢慢地就變得難以為繼。現在,通過電視影像的廣泛傳播,白川鄉“合掌造”村落通過“結”這一互助和共同作業的機制來維系地域社區的運作和認同,這在全日本都得到了較好的評價,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支持。
(二)福島縣只見町的民具保存與活用運動
日本福島縣只見町的教育委員會為編纂其《町史》的“民俗志”[8],遂在進行民俗資料調查、發掘和整理當地的民具資料(亦即有形民俗文化遺產)時,積極動員地域社區的鄉民參與其中。經過對民具的詳細整理、記錄、保存與活用(如公開展示等),使民具的科學價值得到了廣泛認可。這種通過文化遺產的保護活動促進“地域社會”文化建設的成功實踐,被譽為日本民具整理和研究的“只見方式”[9]。
從1990年起,在町教育委員會的主持下,當地一些群眾性民俗社團(“朝日鄉土研究會”、“明和民俗談論會”、“民具談話會”)、社區有識之士和民具愛好者們,組織町內幾十位老年人從事民具的整理和分類工作。伴隨著民具資料的整理和分類,又有不少民具被捐獻出來。這些老年志愿者大都七八十歲了,幾乎都曾親自使用或制作過各種民具,對鄉土民俗懷有深厚感情,希望能夠把自己有關民具的知識傳遞給子孫后代。由于舊時農家生活中尋常可見的民具無不包含著他們的心血和記憶,甚至是他們過往人生的見證,因此,老年志愿者們都覺得自己這一輩人有把它們記錄下來和保護起來的義務。他們根據年輕時的經驗和記憶,認真填寫民具卡片,同時還把民具的制作方法、使用方法及相關的民俗知識均予以說明,有的人甚至還會講述有關某件民具的故事。為把民具實際的制作和使用方法記錄清楚并傳承下去,老人們還親自作為模特進行示范,再現舊時農田耕作或紡織的動作與技藝。對某些已經絕滅但尚存記憶的民具,老人們則進行民具的復原工作。民具的整理工作瑣碎而又繁難,但老人們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終于取得了成功。他們整理出來的民具資料,從日本全國看也是非常珍貴、完整和規范的。由于達到了系統調查、認真整理、科學分類以及有固定的保存場所等標準,2003年2月,日本政府將“會津只見的生產用具和勞作服裝收藏品”(其中生產用具1917件,勞作服裝416件,合計2333件)正式指定為“國家重要有形民俗文化財”。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只見町接受捐贈和經多方收集的民具共計7500多件,其中多達2333件被指定為“國寶”,這在當地“地域社會”的編年史和文化建設方面無疑均是一件大事。
“地域社會”的民具銘刻著當地生活和生產的痕跡,反映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體驗和民間智慧,在其逐漸退出現實生活之后,又將成為人們鄉土記憶和寄托鄉愁情感的載體。民具原本分屬各個農戶或鄉民個人,但通過民具的保存與活用運動,其價值被重新認知:民具不僅是過去的遺物值得紀念,而且還內含著很多民俗知識,凝結著先民的智慧。現在,它們不僅成了“地域社會”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在被整理成民俗資料之后升格為日本國家的文化遺產。
(三)豐橋鬼祭保存會
愛知縣豐橋市有一種民間祭祀活動(祭禮),亦即號稱為“天下奇祭”的“鬼祭”,1954年被指定為愛知縣無形文化遺產,1980年更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家級的“重要無形民俗文化遺產”。“鬼祭”是豐橋市八町大街的安久美神戶神明神社(又名“豐橋神明社”)的春祭行事,每年定期在2月10~11日舉行[10]。它原本是在舊歷正月初十、十四日舉行的神事,故亦被認為是呼喚春天的祭禮,具有祈禱農作物豐收、占卜當年豐歉的性質。從1968年起,改為以建國紀念日(2月11日)為“本祭”,因前一天要做準備,亦為祭日,稱為“前夜祭”。“鬼祭”的起源可上溯至平安時代。天慶二年(939),關東發生“承平天慶”之亂,朝廷遣使到東海的伊勢神宮祈禱平定;第二年叛亂平息,被認為祈禱靈驗;天慶三年(940),當時的朱雀天皇將三河國渥美郡北部的安久美莊(今豐橋市中心一帶)寄贈給了伊勢神宮。于是,這里便成為“安久美神戶”(神的領地),并設立了神明社。神明社的規格較高,據說相當于“縣社”,其主祭之神為“天照皇大神”,配祀諸神則有“仲哀天皇”、“神功皇后”、“應神天皇”、“火產靈神”、“武甕槌神”等。
前夜祭主要是舉行很多“神事”儀式,通常要一直持續到深夜。這些“神事”儀式頗為古樸,被認為反映了日本古代神道的風格。本祭從早到晚要一整天,主要是在神社的拜殿前設置八角形舞臺,表演“田樂躍”、“鼻天”之舞等傳統藝能,其中有些是平安時代起流傳下來、以滑稽著稱的“田樂”之舞。“鬼祭”最引人注目之處是11日下午2點左右開始的“赤鬼”和“天狗”之間的相互逗趣和斗法。高天原(神界)的“天狗”(武神)試圖懲戒性格暴烈的兇神“赤鬼”,雙方斗法的結果是“赤鬼”被驅逐出“境”(神社)外。據說是有所悔悟的“赤鬼”(這時轉換成益神),在神社周邊的“地域社會”各町來回奔跑,直至深夜。“赤鬼”一路播撒白色的米粉以清洗自己的罪孽,并散發祛痰糖(一種供品)向人們表示歉意。據說此糖吃了可以避邪,而人們身上若沾有白色的米粉,則整個夏天都不會生病,因此,圍觀者爭先恐后地搶拾祛痰糖,并希望沾染一些“赤鬼”撒下的米粉。簇擁在“赤鬼”周圍的人,包括圍觀的看客、過路的行人,都會被米粉撒成白人。
神明社內的5棟建筑物(本殿、拜殿、神樂殿、神庫、手水舍)是日本國家級的“登錄有形文化遺產”。上述文物連同“鬼祭”這一無形文化遺產得以綿延傳承千年仍得以維系的原因,就在于“地域社會”人們的團結和努力。豐橋“鬼祭”在國家登錄為無形文化遺產時的“所有者及管理者”抑或“保護團體名”是“豐橋鬼祭保存會”。具體來說,正是這一“地域社會”的民間組織發揮著核心作用,主持和操辦著一年一度的“鬼祭”活動。保存會的會長和骨干都是當地出身,他們都是神明社的“氏子”④。由氏子們組成的保存會對于把“鬼祭”傳承下去有很強的責任心。繁雜和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從前一年9月份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第二年2月,“地域社會”內部要為此舉行各種座談會和全體大會,討論種種事宜。各街區的人們彼此分工合作,或者練習神樂、舞步,或者將祛痰糖事先裝袋,或者在神社內設營布置;“赤鬼”、“天狗”、“小鬼”、“青鬼”、“司天師”等在傳統藝能表演中登場的角色,事先也均由神社周圍的不同街區落實選出(有時通過抽簽儀式選出)。此外,每年還從不同街區推選出多位“神役”、“頭取”(祭禮負責人)和操持事務“諸役”。祭日來臨,“地域社會”的各街區全部出動。操持“鬼祭”活動的頭取、神役、諸役,每年都要輪換,這種每年輪值的方法可讓“地域社會”里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從而增強“地域社會”的凝聚力。每年到“鬼祭”這兩天,不少豐橋出身的外地人也會專程趕回來參加。
豐橋“鬼祭”的藝能活動中有一些由少年兒童承擔的儀式情節(兒童舞蹈)。少年兒童因為純粹、純潔而被認為是更加接近神的存在,也更加適于擔當和諸神溝通的角色。但近年由于“少子化”,要在范圍不大的街區里選出合適(本命年)的孩子已非易事。因此,有人主張公開招募,但也有人反對,認為招募來的孩子沒有氏子資格。保存會每年主辦“鬼祭”都要花心思動員豐橋市內尤其是地域社區的幼兒園、小學和中學的學生們參加。孩子們參加傳統祭禮活動和民俗藝能表演,可帶來很多活力,也會渲染氣氛。近年,豐丘高中“和鼓部”的學生們在神前“奉納”鼓樂,就很受歡迎。每年舉行“鬼祭”時,保存會還要主辦“豐橋鬼祭繪畫比賽”活動,市內的小學生、中學生和大班以上的幼兒園小朋友每年都有近900件作品參賽。孩子們的作品均以在“鬼祭”上看到的活動為題材,往往很好地表現了“天狗”和“赤鬼”的動作神態及參加祭禮的看客表情。繪畫比賽設置了很多獎項,獎項的命名均和支持“鬼祭”活動的各方有關,如“愛知縣神社廳長獎”,“安久美神戶神明社宮司獎”、“豐橋鬼祭保存會名譽會長獎”、“豐橋鬼祭保存會金獎”、“豐橋市長獎”、“豐橋市議會議長獎”、“豐橋商工會議所會頭獎”(商工會議所相當于中國的地方工商聯)、“豐橋市教育委員會獎”、“豐橋青年會議所理事長獎”、“中日新聞社獎”、“豐橋丸榮獎”等。每年都有數十位兒童和中學生的作品獲獎。頒獎式之后,獲獎作品還要在百貨商店、地方金融機構(信用金庫)等處公開展示一段時間。從獎項名稱可知,參加和支持“鬼祭”活動的除了地方政府,還有本地企業、媒體等。通過繪畫比賽,孩子們從小就知曉“鬼祭”活動的很多情節,在他們成人后,自然也會對“鬼祭”感到親切,并產生把它傳承下去的愿望。
旨在祈愿地方安泰、繁榮和民眾健康的“鬼祭”,其內涵頗為古奧,在當地市民心目中有很高的認同度。“鬼祭”現已成為豐橋市的文化資源。紀念豐橋建市100周年(2006)時,以“赤鬼”為模特推出的吉祥物“豐橋鬼”(福神),其形象就取自“赤鬼”和繁體的“豐”字。每年快到“鬼祭”舉行的時節,“豐橋鬼”就會在繁華的新干線豐橋站的大廳豎立著招呼過往客人。
四、結語
日本保護文化遺產的經驗之一,便是重視“地域社會”。其政府文化政策中很多方面均涉及振興“地域社會”,而文化遺產被認為是振興地方不可或缺的“資源”。日本政府推動的諸多文化項目,諸如“家鄉文化再興事業”、“地域藝術文化活性化事業”、“推進青少年體驗文化藝術活動”等,都不同程度地內含著活用地方文化遺產、振興傳統文化、促進地方發展的深意。2001年,日本的《文化藝術振興基本法》在國會得以通過,其“總則”也突出強調了文化對于人的意義以及“民眾”的文化主體性原則。重視“地域社會”和文化遺產當事人各方的主體性參與,其實也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自1990年以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都發表《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3年其報告的主題即為《民眾與參與》,可知民眾的參與已成為衡量發展的尺度之一。文化遺產的保護也不例外,其目標是要實現世代傳承或通過保護文化遺產以確保或增強所屬社區的活力,因此,必須重視“地域社會”或文化遺產所屬社區民眾的廣泛參與,包括讓文化遺產各相關當事人(傳承人、所有人、保護團體等)均參與到保護的具體實踐當中。
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在政府文化行政的強力主導下,已經取得了非凡的成績。在普查、申報和建立名錄體系初見成效的同時,今后更加重要的便是如何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落實到具體的基層社區。文化遺產對于“地域社會”的意義無需置疑,在重視和依托“地域社會”保護文化遺產方面,日本先行一步的經驗及案例[11],或許能夠對中國的文化遺產社區保護工作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注釋:
①“町內會”大體上相當于中國的居民委員會、社區或“街坊會”。“町內會”是指建立在村落或都市的街區(町、區),由當地居民組織的旨在維護社區親睦和推動當地共同利益的“任意團體”(亦即不具備法人權利和能力的社團)。作為一種地緣組織,它在各地的稱謂不盡相同(又有“町會”、
“自治會”、“地域振興會”、“常會”等稱謂;在有些商業街,則稱“商店會”)。雖然并非義務,但同屬一個“地域社會”的人們往往有全員參加的傾向。
②“里山”主要指環繞村落周圍、與人們生活密切相關的山地和森林。相對而言,“遠山”則是指人跡罕至的野山。
③結:日本基層村落共同體人們之間的互助組織機制或相關的習慣和規范,同時也是一種基于地緣的近鄰交往和勞動力的對等交換及共同作業的制度。一般在蓋房子等重勞動或一時需要大量人手參與作業時,便全村集體出動或相鄰之間互相幫忙。在白川鄉,運營“結”這種互助機制的組織叫做“合力”。“結”所涉及的范圍也并不局限于屋頂茅草的更換作業,它還涉及插秧、割稻、砍柴、割草及村民們的婚喪嫁娶等,可以說滲透到了山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④“氏子”:日本“地域社會”共同體所信仰的神社里奉祀的諸神,被稱作“氏神”;而該“地域社會”的全體成員都是該神社及其所祭之諸神的“氏子”。
[1]王康.社會學詞典[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
[2]色音.日本文化遺產保護制度與文化政策[A].陶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論集[C].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344—354.
[3]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遺產保護的舉國體制[J].文化遺產,2008,(1):133—143.
[4]周星,周超.日本文化遺產的分類體系及其保護制度[J].文化遺產,2007,(1):121—139.
[5]王軍.日本的文化財保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廖明君.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日本經驗——周星教授訪談錄[A].多維視野中的文化對話——中青年學者訪談錄[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268—293.
[7]劉曉峰.什么支撐著今天的日本?——寫在日本《人間國寶》周刊創刊之際[EB/OL].中國民俗學會網站,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
[8]只見町史編纂委員會.只見町史(第3卷)·民俗編[M].只見町,1993.
[9]周星.垃圾、還是“國寶”?這是一個問題——以日本福島縣只見町的民具保存與活用運動為例[A].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田野工作方法[C].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408—436.
[10]周潔.日本的祭禮[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
[11]馮彤.日本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傳統民俗文化的傳承及其對中國的啟示[D].北京師范大學博士后出站報告,2010-10.
2010-12-08
周星(1957— ),男,陜西丹鳳人,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教授,中國民俗學會顧問,中國藝術人類學學會副會長,民族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