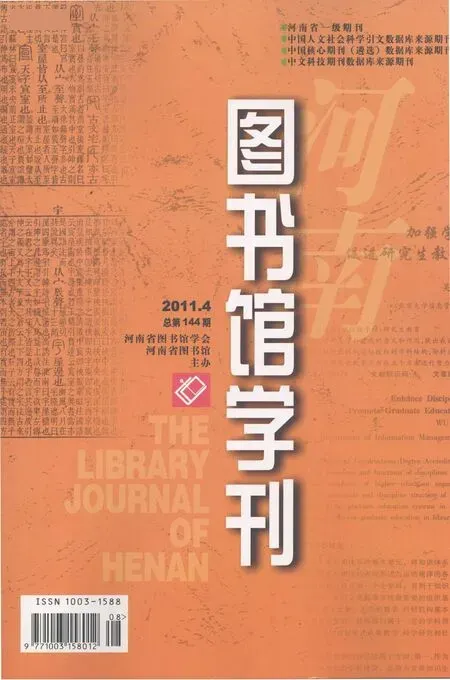阮孝緒在目錄學(xué)領(lǐng)域中的貢獻(xiàn)
關(guān)延虹
(河南商業(yè)高等專科學(xué)校圖書(shū)館,河南 鄭州 450000)
1 《七錄》以前目錄學(xué)的源流
目錄學(xué)是研究目錄工作形成和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即研究書(shū)目情報(bào)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的科學(xué)。圖書(shū)分類是目錄學(xué)研究的主要對(duì)象。中國(guó)古代圖書(shū)分類的活動(dòng)開(kāi)展比較早,在《周易·十翼》中的《序卦傳》編次匯總了六十四卦的卦名,說(shuō)明排列次序和內(nèi)在聯(lián)系。孔子刪定的“六藝”(詩(shī)、書(shū)、禮、樂(lè)、易、春秋)已初步具備了圖書(shū)分類的框架,為以后圖書(shū)分類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chǔ)。[1]自兩漢以來(lái),古代圖書(shū)分類以六分法為基本方式。西漢劉向編定成《別錄》20卷,《別錄》,即“別集眾錄”的意思。其子劉歆在《別錄》的基礎(chǔ)上編纂成我國(guó)第一部綜合性的分類圖書(shū)目錄——《七略》。《七略》是我國(guó)目錄學(xué)的開(kāi)創(chuàng)性著作,它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術(shù)思想和流派,記錄了西漢末年一代文化典籍之盛。它系統(tǒng)地組織圖書(shū)的體式,是我國(guó)最早的圖書(shū)分類法。[2]南朝梁阮孝緒在《七錄序》中記載“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shī)賦略,次兵書(shū)略,次數(shù)術(shù)略,次方技略”,故稱《七略》。為了從學(xué)術(shù)體系說(shuō)明群書(shū),按照書(shū)的內(nèi)容性質(zhì),除輯略外,分為六略(六類),六略之下分三十八種(小類),種下分六百零三家,家下列書(shū),計(jì)一萬(wàn)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可見(jiàn),《七略》是一部系統(tǒng)嚴(yán)密的圖書(shū)分類目錄,成為我國(guó)歷代編制各種圖書(shū)分類目錄的典范,對(duì)于我國(guó)目錄學(xué)的發(fā)展有深遠(yuǎn)影響。隨后東漢班固將《七略》重新剪裁、編次,散《七略》中的“輯略”,即關(guān)于該書(shū)學(xué)術(shù)源流的綜述于其他的六略中,刪去各書(shū)敘錄,門(mén)類條例一依《七略》,改寫(xiě)成《藝文志》一卷列入《漢書(shū)》。現(xiàn)在我們?nèi)匀荒軌驈摹稘h書(shū)·藝文志》窺見(jiàn)《七略》的遺風(fēng)。魏晉期間荀勖等編撰的《中經(jīng)新簿》已分四部,即《七略》的六藝略,乙部相當(dāng)《七略》的諸子、兵書(shū)、數(shù)術(shù)、方技四略,丙部系由《七略》六藝略中之春秋類目所附的歷史書(shū)籍?dāng)U大而成,丁部既《七略》的詩(shī)賦略。“荀勖又因《中經(jīng)》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shū)。”南朝齊王儉《七志》中提出九分法,經(jīng)典志即《七略》六藝略,諸子志即《七略》諸子略,文翰志即《七略》詩(shī)賦略,軍書(shū)志即《七略》兵書(shū)略,陰陽(yáng)志即《七略》數(shù)術(shù)略,術(shù)藝志即《七略》方技略,另外經(jīng)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shū)志、陰陽(yáng)志、術(shù)藝志,再加上圖語(yǔ)志、(附)道經(jīng)、佛經(jīng)三類,計(jì)九類。
2 阮孝緒《七錄》
阮孝緒(479-536),字士宗,南朝梁陳留尉氏(河南尉氏)人。[3]年十三通五經(jīng)。二十五歲,阮孝緒就具備豐富的書(shū)目知識(shí),加之對(duì)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博采宋齊以來(lái)圖書(shū),王公縉紳之館,茍能蓄集墳籍,必思致其名薄。凡在所遇,若見(jiàn)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眾家,更為新錄。即所撰《七錄》較王儉撰《七志》著錄更為豐富,分類更有條理。《七錄》十二卷,分為內(nèi)、外篇。內(nèi)篇:經(jīng)典錄、紀(jì)傳錄、兵錄、集錄、術(shù)伎錄;外篇:佛法錄、仙道錄。該書(shū)計(jì)收書(shū)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帙(量詞,用于裝套的線裝書(shū)),四萬(wàn)四千五百二十六卷。《七錄》的撰成不僅達(dá)到了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綜合性系統(tǒng)目錄的最高峰,而且也使阮孝緒成為南朝梁代杰出的目錄學(xué)家。阮氏對(duì)目錄學(xué)之貢獻(xiàn),據(jù)姚名達(dá)在《中國(guó)目錄學(xué)史》中指出“分類合理化、適應(yīng)時(shí)代環(huán)境、工作科學(xué)化。阮錄在當(dāng)時(shí)已將‘天下之遺書(shū)秘記,庶幾盡于是’,可以說(shuō)是已盡到目錄學(xué)史上編集、創(chuàng)見(jiàn)之功。”[4]
3 《七錄》與《七略》和《隋書(shū)·經(jīng)籍志》比較
3.1 《七錄》與《七略》
《七錄》的經(jīng)典錄、文集錄與《七略》的六藝略、詩(shī)賦略基本相同;子兵錄即合諸子略與兵書(shū)略,術(shù)伎略即合術(shù)數(shù)略與方伎略。只有紀(jì)傳略為《七錄》的新創(chuàng),充分地體現(xiàn)了《七略》六分法的原則。“劉(歆)王(儉)并以眾史合于春秋,劉氏之世,史書(shū)甚寡,附見(jiàn)春秋,誠(chéng)得其例。今眾家紀(jì)傳倍于經(jīng)典,猶從此志,實(shí)為繁蕪,且《七略》詩(shī)賦不從六藝詩(shī)部,蓋由其書(shū)既多,所以別為一略,今依擬斯例,分出眾史,序紀(jì)傳錄,為內(nèi)篇第二”。[5]因此,縱觀《七錄》與《七略》的分類,在存在著明顯差異的基礎(chǔ)上更存在相互繼承和發(fā)展的關(guān)系。
3.2 《七錄》與《隋書(shū)·經(jīng)籍志》
《七錄》內(nèi)篇五大類與逐漸成熟的四部分類法相近:經(jīng)典錄即經(jīng)部;紀(jì)傳錄即為史部;子兵錄改為子部,文集錄即集部;術(shù)伎錄中的大部分子目可并人子部,少數(shù)可劃入經(jīng)部、史部。實(shí)際上《七錄》、內(nèi)篇的五部采用的就是四分法。[6]眾所周知,人們以《隋書(shū)·經(jīng)籍志》為四部分類法完全形成和確立的標(biāo)志,實(shí)際上,比較成熟的四部分類法早已包涵在阮孝緒的《七錄》之中。《隋書(shū)·經(jīng)籍志》以后,仿其體例和分類方法編制的目錄成為各種公私目錄的主流,經(jīng)唐 《古今書(shū)錄》、宋《崇文總目》及晁公武《郡齋讀書(shū)志》、陳振孫《直齋書(shū)錄解題》等眾多目錄的不斷發(fā)展完善,至清乾隆間《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蔚為大觀。正如姚名達(dá)認(rèn)為:“《阮錄》最大影響,就是做《隋書(shū)·經(jīng)籍志》的范本……《阮錄》的分類,對(duì)于后世的影響,也是非常大的。如道佛的分類,一直影響到后世的目錄學(xué)家;而其將文字集略的另列,亦開(kāi)后世將類書(shū)另列的風(fēng)氣。”[7]因此,《七略》《七錄》和《隋書(shū)·經(jīng)籍志》三部目錄著作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和發(fā)展,其圖書(shū)分類法的主流由六分變?yōu)樗姆郑镀咪洝穭t在其中起到承先啟后的關(guān)鍵作用。
4 《七錄》目錄學(xué)創(chuàng)新
4.1 開(kāi)研究前人目錄之端,為私人編著目錄開(kāi)啟先河
余嘉錫認(rèn)為,阮孝緒以前的目錄“大抵為公家藏書(shū)目錄;漢楊樸、劉向之著錄,乃起于奉詔校書(shū);魏晉南北朝,則大抵為秘書(shū)監(jiān)丞職掌。其以處士而著書(shū)者,阮孝緒一人而已。”[8]阮孝緒是一個(gè)“處士”,低下的政治地位,使他沒(méi)有機(jī)會(huì)接觸皇家藏書(shū),因而著錄只能根據(jù)某些藏書(shū)家的目錄和流傳的官家藏書(shū)目錄,進(jìn)行研究編目工作。但是,由于阮孝緒繼承和吸取了前人目錄的合理成就,因此他所撰《七錄》,比“官目”更為完備,特別是擺脫了單純收錄藏書(shū)的局面。
4.2 發(fā)揚(yáng)撰寫(xiě)提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七錄》總括群書(shū)四萬(wàn)余,皆討論研核,標(biāo)判宗旨,通過(guò)提要介紹作者事跡、圖書(shū)流傳等情況。雖然有些割析辭義,淺薄不經(jīng),而遠(yuǎn)不逮劉向、劉歆,但大體上以他們?yōu)闇?zhǔn)繩,繼承他們撰寫(xiě)提要的遺風(fēng),并在體例上補(bǔ)充了王儉撰寫(xiě)提要的不足。
4.3 于分類名副其實(shí),并有所創(chuàng)新
阮孝緒通過(guò)研究,采用七分法:內(nèi)錄五篇,道經(jīng)、佛經(jīng),外兩篇,既表明佛道為附錄的含義,又確為七分,名實(shí)一致。同時(shí),從現(xiàn)實(shí)出發(fā),使史書(shū)擺脫從屬地位,而獨(dú)立成類,專立《紀(jì)傳錄》,并列十二目,加以細(xì)分,這是前所未有的。《七錄》大大推動(dòng)了圖書(shū)分類學(xué)的發(fā)展,對(duì)后世有著重要影響。
4.4 精于研究目錄學(xué)史
阮孝緒十分熟悉古代目錄學(xué),認(rèn)真研究了齊梁之前的目錄學(xué)發(fā)展過(guò)程,認(rèn)為《別錄》的成書(shū)早于《七略》:“昔劉向校書(shū),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變其訛謬,隨即奏上,皆載在本書(shū),時(shí)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旨,著為《七略》。”從而統(tǒng)一了對(duì)《別錄》、《七略》誰(shuí)先誰(shuí)后的爭(zhēng)論,并指明《漢書(shū)·藝文志》源于《七略》,盡管《七略》早軼,但通過(guò)《漢書(shū)·藝文志》可知《七略》的概貌。總之,阮孝緒在動(dòng)亂的時(shí)代和家境條件比較差的情況下,獨(dú)立完成了一部搜羅比較完備的圖書(shū)目錄,在我國(guó)目錄學(xué)發(fā)展史上,應(yīng)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七錄》雖然遺失,而《七錄·序》在《廣弘明集》中完整無(wú)缺地保存至今,成為我們研究中國(guó)古代目錄學(xué)的一篇極為重要的早期文獻(xiàn)。
4.5 自立楚辭的類別
阮孝緒編撰《七錄》,在《文集錄》中將集部之書(shū)分為四類:楚辭、別集、總集、雜文,他第一次將楚辭獨(dú)立成為圖書(shū)目錄種類,成為中國(guó)古代圖書(shū)的分類傳統(tǒng)。楚辭作為分體文學(xué)總集立于書(shū)目,《七錄》開(kāi)其先例,不僅反映了魏晉以來(lái)文學(xué)專集編撰產(chǎn)生的事實(shí),而且圖書(shū)目錄中集部的創(chuàng)立,反映了文學(xué)逐步擺脫經(jīng)學(xué)、依附學(xué)術(shù)而走向獨(dú)立發(fā)展的事實(shí)。
5 結(jié)束語(yǔ)
西漢時(shí),劉向、劉歆父子編撰《別錄》《七略》等書(shū)、東漢班固《漢書(shū)·藝文志》、魏晉荀勖等編撰的《中經(jīng)新簿》、南朝齊王儉《七志》、南朝梁阮孝緒《七錄》、唐代魏征《隋書(shū)·經(jīng)籍志》、南宋鄭樵有《通志.校讎略》,至清代章學(xué)誠(chéng)著成《校讎通義》,進(jìn)一步總結(jié)了目錄學(xué)的豐富經(jīng)驗(yàn)。而反映我國(guó)古代著述的規(guī)模最大、最全的目錄是《四庫(kù)全書(shū)總目提要》和《四庫(kù)全書(shū)簡(jiǎn)明目錄》。其間南朝梁阮孝緒《七錄》稱為七分法,對(duì)兩漢《七略》以來(lái)的六分法和魏晉以來(lái)逐漸盛行的四分法兩者都進(jìn)行了揚(yáng)棄和改造,他把兩大分類法的精華揉合起來(lái),為中國(guó)圖書(shū)目錄分類由六分到四分的轉(zhuǎn)變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1] 王重民.中國(guó)目錄學(xué)史論叢[C].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149.
[2] 來(lái)新夏.古典目錄學(xué)[M].北京:中華書(shū)局,1991:79.
[3] 申暢.中國(guó)目錄學(xué)家傳略[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45.
[4] 姚名達(dá).中國(guó)目錄學(xué)史[M].上海:上海書(shū)店,1984:5.
[6] 邱敏.略論六朝目錄中的圖書(shū)分類[J].江海學(xué)刊,2001(2):1231-133.
[7] 姚名達(dá).目錄學(xué)[M].上海:商務(wù)印書(shū)館,1934:25.
[8] 余嘉錫.目錄學(xué)發(fā)微[M].長(zhǎng)沙:岳麓書(shū)社,201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