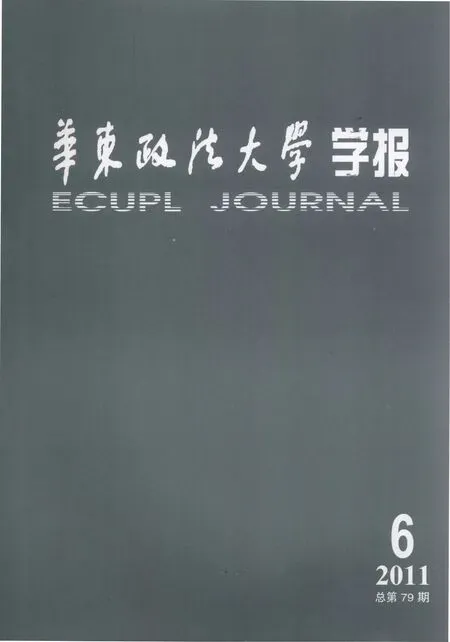論薩維尼法人擬制說的政治旨趣
仲崇玉
論薩維尼法人擬制說的政治旨趣
仲崇玉*
我國民法學界對薩維尼的擬制說存在重大誤解。在薩維尼筆下,法人僅僅意味著一種私法上的財產能力,為抽空法人概念的內涵立下基調;法人具有全然不同于其成員全體的獨立實體,為凸顯法人相對于國家的派生性埋下伏筆;羅馬法本文被有選擇地運用和再造性詮釋,成為證明法人是擬制之物的法學證據;德國倫理哲學也得到了重申和強調,引以為證明法人不具倫理性的哲學基礎。因此,薩維尼的擬制說表面上是私法理論,實質上卻是反映其政治前見的公法學說——國家擬制說。
薩維尼 法人 擬制說 政治旨趣
我國民法學界普遍認為,法人擬制說主要為德國法學家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1779-1861)所創立、闡發。〔1〕當然,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詳細論述請參見下文。近幾年來,學界有人開始懷疑作為法人本質通說的組織體說,進而轉為支持擬制說。例如,有人認為“薩維尼正是基于人道主義、民主主義的思想,繼承了羅馬法中對團體賦予人格、認為團體人格是擬制的看法”。〔2〕參見馬俊駒:《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論和立法問題探討(上)》,載《法學評論》2004年第4期。有人認為薩維尼擬制說正是堅持自然人倫理性的結果。〔3〕參見李永軍:《論權利能力的本質》,載《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2期;蔣學躍:《法人制度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204、205頁;周清林:《權利能力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提交,第165、166頁。還有人視薩維尼擬制說為反封建時代的產兒,并認為其宏揚了人文主義的法律觀。〔4〕參見蔡立東:《公司本質論綱》,載《法律與社會發展》2004年第1期。甚至還有人提出要為擬制說辯護。〔5〕參見江平、龍衛球:《法人本質及其基本構造研究——為擬制說辯護》,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3期;張駿:《關于法人本質的再思考——從擬制說出發》,載《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當然,龍衛球教授并未特指要為薩維尼的擬制說辯護,毋寧說是為我國學界所理解的擬制說而辯護,從學術旨趣上說,這種擬制說與薩維尼的擬制說已經相去甚遠。但是,筆者不能排除有人做這種理解的可能。
本文將在仔細閱讀原著的基礎上,運用詮釋學的方法,揭示薩維尼的擬制說雖然是一個私法理論,其核心線索卻是國家與社會中間組織的關系問題,它體現了薩維尼的政治前見——全能主義的國家觀念。薩氏擬制說并非基于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繼承羅馬法的法人觀念,從根本上說,也不是堅持自然人倫理性的結果,更難稱得上是反封建時代的產兒,所以我們不僅不應為之辯護,而且應當對其進行深入檢討和反省。基于此,本文將從知識譜系學的角度檢討薩維尼擬制說與德國主體倫理哲學以及羅馬法本文的真實關聯,揭示擬制說中的法學思維方法,從而引出對我們的啟示。
一、薩維尼的“前見”
(一)薩維尼的政治態度
從薩維尼的寫作背景上看,當時德國已經進入一個新的自由結社時期。〔6〕John D.Lewis,The Genossenschaft-Theory of Otto Von Gierke:A Study in Political Thought,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35,p.53.德國出現了一大批新興的市民組織,如文學社、報紙期刊社、音樂社以及各種教育協會等。〔7〕參見王紹光:《多元與統一——第三部門國際比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頁。這與當時致力于加強中央集權的政府產生了激烈的矛盾,對此,作為政治家的薩維尼不會熟視無睹,〔8〕雖然薩維尼一生的活動主要以學術及教學為主,但其政治身份也不容置疑。他于1814年后成為王儲威廉四世的老師,1817年任普魯士樞密院法律委員,1829年成為國務委員,1842年出任司法部長,直到1848年因革命而下臺。終其一生,薩氏在學界與政界的地位都極為尊崇。參見[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陳愛娥、黃建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58頁;[德]施羅德:《薩維尼的生平及其學說》,許蘭譯,載許章潤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頁;[英]威廉·格恩里:《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傳略》,程衛東、張茂譯,載許章潤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對于各種新舊社會團體,特別是具有社會、政治功能的社團以及公法法人的政治考量構成了薩氏法人學說的底色。這也決定了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2卷(以下簡稱“《體系》Ⅱ”)中,薩維尼論述的法人類型主要包括公社、村莊、城鎮、行會、城市以及宗教組織,而純粹的私法性商業組織并非薩氏考察的重點。
薩維尼的法人學說還與當時德國的諸侯政治有著密切聯系。面對諸侯并立的政治圖景,薩氏的腦海中“充滿了慈善的獨裁政府與侯國們勾心斗角造成的混亂之間的對比”,〔9〕Frederick Hallis,Corporate Personality:A Study of Jurisprudence,Aal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2.作為親身經歷過法國入侵與奴役的德意志愛國者,薩維尼親眼目睹了國家敗落、外族奴役的慘狀,中央集權式的強大國家實是其一以貫之的潛在訴求。〔10〕關于薩維尼的國家主義和集權主義問題,可參見謝鴻飛:《薩維尼的歷史主義與反歷史主義》,載許章潤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頁。因此,貫穿于薩氏法人學說始終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強化國家對各類法人組織的控制。也因此,主導擬制說的個人主義法學方法不過是一種表象,更為實質的是集體主義。還因此,在《體系》II中,團體內部生活儼然霍布斯筆下的原始狀態,薩維尼對社團自治的悲觀情緒躍然紙上。〔11〕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99 and §100.他之所以拒絕將團體人格和利益寄托于團體的成員,而是執意供奉在利維坦的祭壇上,其最深層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法國大革命以及后來的1830年7月革命的影響下,薩維尼時代的德國正處于近代革命的前夜。然而,薩維尼卻一方面“支持現存的政治宗教與秩序,維護王室、教會、社團與特權階級歷史上傳來的權利”,而且這種態度愈老彌堅;〔12〕[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陳愛娥、黃建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0頁。另一方面又對法國革命懷有一種本能的敵視,〔13〕[德]參見許章潤:《民族的自然言說》,載薩維尼:《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許章潤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譯序第4頁,正文第42頁;[德]康特羅維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載許章潤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對本國“經由公民平等來解散古老等級社會”的革命也同樣懷有深深的疑慮。〔14〕[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陳愛娥、黃建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5頁;[德]赫爾曼·康特羅維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許章潤譯,載許章潤編:《薩維尼與歷史法學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而社團的發展壯大往往會導致薩維尼所深惡痛絕的政治革命或動亂的發生,因此,薩維尼對新興社團極不信任甚至敵視。〔15〕See Frederick Hallis,Corporate Personality:A Study of Jurisprudence,Aal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4.于是,維護舊社團體系的特權與抑制新興社團發展這兩種考慮便決定了他對法人進行區別對待的理念,而區別對待的最佳辦法自然就是國家對社團進行嚴格篩選與甄別,從而既維護舊式團體的特權地位,同時又利用國家的力量對新興團體進行鉗制。
根據這種思路,在《體系》II中,薩維尼將社團組織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自然法人”,主要包括公社(communities)、市鎮(towns)、村莊(villages)等,這類法人在羅馬國家成立以前即已存在。在當時的德國,這類社團應當包括村莊、公社、自治市、教會甚至各侯邦,薩氏稱其為“自然的甚至必然的法人”(natural or even a necessary existence),它們從存在的時間上看比國家還要古老,因此其法律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它們在歷史上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特權和獨立的法律人格,對此,國家無緣置喙。〔16〕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p.180,204.薩維尼對這一類團體的論述,顯然類似實在說觀念。第二類是手工業行會(artisan guilds)及其他組織,但這類團體的地位是不穩定的,它們要么不時為公社兼并而成為其組成部分,要么就屬于第三類社團。〔17〕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180.第三類即各種廣義的社團與財團,它們的產生和存在取決于一人或多人的任意決定。在薩維尼的時代,這實際上主要指是新興的各種社會組織,薩氏稱之為“人為且意定的”法人,而這一類法人則需要國家的特許。〔18〕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p.180,204.因此,薩氏的擬制說僅僅適用于第三類社團。
當然,薩維尼的法人學說畢竟是以私法理論的面目呈現出來的,其中的政治前見還要與法學理論隼接起來。
(二)薩維尼的法學方法
薩維尼的法學方法也同樣源于康德的影響。維亞克爾認為:從康德的倫理學中已經衍生出學術性形式主義(亦即法學實證主義)的主要血脈,后者并進而將嗣后的現代運用改造成一種實證法的自主學科。〔19〕[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陳愛娥、黃建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38頁。這種方法繼承了盛行于歐洲大陸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理性法學的某些方法,但是逐漸擺脫其倫理傾向,而側重于視法律為一個自主的系統,實為形式主義化的概念法學之濫觴。
薩維尼繼承了理性法學追求體系性的特征,在他看來,體系是法律科學的基本任務,〔20〕[德]參見馮引如:《薩維尼評傳》,華東政法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提交,第31頁。他在其早期的課程《法學方法論》中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認為歷史研究為法學研究提供素材,而哲學的處理則將這些素材組織成內部體系。〔21〕[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陳愛娥、黃建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48頁。在他看來,法學研究的最高境界就在于將歷史性研究和體系性研究結合起來,“法學完整的品性就建立在這個結合的基礎之上”。〔22〕[德]薩維尼、格林:《薩維尼法學方法論講義與格林筆記》,楊代雄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74頁。薩氏認為,理論上有兩種方法可以實現法學和民法典的完備性:一是列舉一切可能的情形,以窮盡一切可能性;二是可以通過一套原則概念術語的法律邏輯構件,來建構一個嚴密的邏輯體系,使得任何特殊案件都被涵蓋在這一體系之中。他同時指出,第一種方法注定要失敗,因為社會生活不可能窮盡列舉,因此惟有第二種方法值得追求。〔23〕[德]參見徐國棟編:《中國民法典起草思路論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頁。出于構建法律科學體系的需要,薩氏必須要將法人與自然人統合起來,從而形成統一的法律主體這一最高概念。〔24〕[德]馮引如博士認為《現代羅馬法體系》標志著薩維尼私法法律科學體系的建立,參見馮引如:《薩維尼評傳》,華東政法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提交,第78頁。《現代羅馬法體系》共九卷,實際上只完成了私法的總論部分,貫穿該書的線索、同時也構成該書主體部分的內容就是法律關系理論,《體系》II實際上是法律關系理論下的第二章,其標題就是“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人”,其下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而打造法律概念的方法也來自理性法學。薩維尼認為,每個法學概念都必須符合法律現實,〔25〕[德]薩維尼、格林:《薩維尼法學方法論講義與格林筆記》,楊代雄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頁。法學概念與其所指事物之間的關聯性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其內在規定的。〔26〕[德]薩維尼、格林:《薩維尼法學方法論講義與格林筆記》,楊代雄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頁。這種概念界定方法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一直持續到薩維尼所處的德國古典哲學時代。那么根據這種方法,法律主體的本質應當是什么?
這涉及對薩維尼影響甚巨的康德倫理人格主義哲學。〔27〕[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頁。“從學術成熟期起迄至宏大的晚期釋義學巨著,薩維尼均嚴守理性法學與康德的自由倫理。”〔28〕[德]Franz Wieacker:《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發展為觀察重點》,陳愛娥、黃建輝譯,臺灣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0頁。康德認為:“沒有理性的東西只具有一種相對的價值,只能作為手段,因此叫做物;而有理性的生靈叫做‘人’”,所謂理性“不僅指人類認識可感知的事物及其規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類識別道德要求并根據道德要求處世行事的能力”。〔29〕轉引自[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頁。只有具有理性的生物人才可以成為法律主體:“人最適合于服從他給自己規定的法律——或者是給他單獨規定的,或者是給他與別人共同規定的法律”。〔3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6頁。在此基礎上,薩維尼提出了他的著名公式:“所有的法律都為保障道德的、內在于每個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關于法律上的人或權利主體的原初概念,必須與生物人的概念一致,并且可以將這二種概念的原初同一性以下列公式表述:每個個體的生物人,并且只有個體的生物人,才具有權利能力。”〔31〕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p.1-2.薩氏的這一論斷使得法人作為法律主體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法人只能是“個人主義的塵埃”。〔32〕梅特蘭語,See F.M.Maitland,Introduction,in 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0,p.xxx.但是這顯然是行不通的,因為它不僅有違于各種團體能夠實實在在地取得財產權利、承擔義務的事實,而且還有礙于法學體系的構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限制理性法學的倫理傾向。
實際上,最早做出限制的人正是康德,他已經意識到法律主體與倫理上的人的不同,他又提出:“(法律上的)人是指那些能夠以自己的意志為某一行為的主體。”〔33〕[德]康德:《〈習慣的形而上學〉之導論》,第4卷。轉引自[德]漢斯·哈騰鮑爾:《民法上的人》,孫憲忠譯,載《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第4期。法律主體這一概念的提出顯示了康德的法學實證主義傾向,此舉產生了重大影響。德國學者哈騰鮑爾認為:隨著“法律主體”替代“人”,產生了“權利能力”理論。蒂博已經初步提出這個思路,薩氏做了進一步發展。〔34〕[德]漢斯·哈騰鮑爾:《民法上的人》,孫憲忠譯,載《環球法律評論》2001年第4期。薩氏從法律關系概念出發構建了他的法律理論框架,他說:“誰可以作為法律關系的承擔者或者說法律關系的主體?這個問題涉及某種權利享有的可能性,或者說涉及權利能力……”〔35〕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Sons,1884,p.1.當然,在《現代羅馬法體系》第8卷當中,薩氏的觀念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更強調“人”這一概念的核心性,認為人的自由行為產生了或幫助產生了法律關系,法律關系甚至可以理解為是人的屬性。參見薩維尼:《法律沖突與法律規則的地域和時間范圍》,李雙元等譯,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頁。于是法律上的人之本質規定性就是權利能力,如果具有權利能力就是法律主體,反之,則不是。顯然,無論在倫理上還是法律實證上,自然人都是具有權利能力的。那么法人團體有沒有權利能力呢?
薩維尼認為他在公式中所表達的法律主體概念只是其原始的觀念或自然法上的觀念,無論是在羅馬時代,還是在當時,這一概念都要受到實在法的雙重修正,一是限制,二是擴張。他舉例說:“首先,實在法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否定某些個體生物人的權利能力;其次,實在法可以將權利能力轉而授予個人之外的某些主體,從而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人為地創造法人……”。〔36〕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在這種情況下,法人勉強有了成為民事主體的可能性,因此,在《體系》II中,薩維尼在討論完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及其諸種限制之后,接著討論了法人的權利能力問題,從而闡發了其法人擬制說。
薩維尼擬制說的內容可以根據三個“W”法則歸納為以下相互聯系的三個部分:(1)法人是什么?(2)為何擬制法人?(3)怎樣擬制法人?
二、法人是什么——法人的形式主義法律界定
在法人部分一開始,薩維尼就說:“上述法律能力(即自然人法律能力)與個體生物人觀念相符。現在,我們必須考慮法律能力延伸至通過純粹擬制而得以承認的人造主體的情形。我們稱這一主體為法人,也就是說,它是純粹出于法律目的而被設想為法律主體的人。在其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和個體生物人一樣的法律關系承擔者。”〔37〕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76.雖然薩維尼斷定法人是一個擬制產物,但是他并沒有接著分析法人是如何擬制出來的,也沒有說明為什么要擬制法人這樣一個主體,他接著討論了法人可以參加法律關系的范圍,以此來進一步界定法人的內涵。他說:“為了賦予法人這一觀念以適當的精確性,有必要仔細地劃定這種法律能力所涉及的法律關系的范圍,如果沒有這一界限,就會在論及這一問題時產生不小的混亂。”〔38〕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76.
第一個限定是,法人的人造法律能力僅僅適用于私法關系,不能運用于公法關系領域。薩氏還順便批評了將世襲君主制國家的一系列君主視為法人的獨體法人觀念。〔39〕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76.第二個限定源于法人自身的本質,即法人本身意味著一種財產能力,因此家族領域中的身份關系被排除了。在做出這兩個限定之后,薩維尼總結了適于法人參加的法律關系:所有權與他物權,債權、遺產繼承、奴隸所有權和庇護。相反,以下關系不適用于法人:婚姻、父權、親屬關系、夫對妻的權力、奴役和監護。在精確界定了法人適用于的法律關系之后,薩維尼對法人下了一個定義:“法人是一個人為假設出來的享有財產能力的主體。”〔40〕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78.
由此可見,薩維尼的法人是一個形式化的法人概念,它僅僅切割下來法人的部分特征——私法上的財產能力,而將其他特征排除在外。薩氏自己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他接著說:“但由于這里已經將法人的本質僅僅限定于財產能力這一私法屬性,所以,不能宣稱這是在實際存在的法人那里所發現的惟一屬性。相反,法人概念總是預示某一與其相獨立的客觀事物,這一事物甚至由財產能力所促進,而且,說來奇怪,這一客觀事物經常被認為比財產能力更重要。”〔41〕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78.
也就是說,薩氏實際上也承認團體組織具有其他方面的屬性,而且這些屬性往往高于其財產能力,或者說財產能力是由其他屬性所派生,但是他立即又重申法人團體的其他屬性超出了私法范圍而進入了公法領域。他以羅馬法上的市鎮為例,指出其存在的基礎“是個政治和行政上的屬性,其私法屬性,即其作為法人而存在,就其重要性而言,卻相形見絀。”〔42〕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78.由此,薩維尼放棄了將團體組織其他屬性納入法人概念的努力,而基爾克的有機體說由企圖將法人概念重塑為一個實質性工具,從而奠定包括下至私人俱樂部上至國家的全部團體組織的產生和存在基礎。
薩維尼將法人概念限定于財產能力和私法領域的主觀動因有二。其一,薩維尼將法人的權利能力限于財產方面有為進一步展開擬制說做好鋪墊的考量。法人的財產能力可以最直接、最鮮明地揭示法人區別于其單個成員甚至成員全體的法律狀態,因此,獨立于成員法律人格之外的法人的人格就只能依靠擬制才能產生。其二,它滿足了將公、私法上的各種團體組織納入到法人概念之內的需要,為構建形式主義的法人理論體系打下了基礎。聯系薩維尼時代純粹的私法人如公司尚不發達,而公法性團體卻比我們現在還要豐富且“自然法人”與“意定法人”并存的歷史事實,這種界定,至少在薩維尼自己看來,的確有助于消除法人過于紛繁復雜的個性,而直接凸顯其共性。但下文的分析將表明,這種外延上的擴張是以內涵上的稀薄為代價的,這樣的法人概念必然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概念,最終將導致法人概念學術構建價值的大大萎縮。
薩維尼雖然承認了法人的主體地位,但是同時又嚴肅地指出法人的非倫理性。為了表明法人缺少倫理基礎,薩氏還批評了法國民法中運用“道德人”(moral person)指稱法人的做法,認為“moral”(倫理的、精神的)與作為同倫理道德無關之存在的法人的本質無緣,故以之表達反倫理或者無倫理的法人人格,徒然增加混亂。〔43〕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179.同時,薩維尼還以他精心選定的羅馬法文本,來證明法人擬制性。他說:“羅馬人本身沒有法人這一總稱。當他們希望表達這類主體的法律性質時,他們僅僅說法人代替了人,這等于說法人是虛構的人。”〔44〕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179.薩維尼這一論斷等于宣布羅馬法支持了擬制說,結果引出了一場波及英美法系的世界性學術論戰,最后證明,薩氏這一論斷的證據并不充分,甚至錯誤。〔45〕詳細情形參見仲崇玉:《羅馬法中的法人人格觀念若干問題辯正》,載《東方論壇》2009年第5期。
薩氏將法人觀念囚禁于私法和財產能力的形式主義做法,使人們只是看到了自然人、法人的二元對立,從而埋下了法人理論研究向抽象的價值哲學轉變的伏筆,而他對于自然人法人倫理差異性的強調更加助長了這一趨勢。因為在每個自然人都已經是法律上的人的時代,也只有在自然人——法人的二元對立模式中,探討自然人的倫理性才具有點兒“學術”意義,特別是經過德國主體哲學思維習慣放大之后,這種對立可以反射出法人這個自然人地位的“篡奪者”并不具備倫理基礎,反襯出“自然人”的神圣與偉大。這樣,薩維尼一方面承認了法人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又與康德倫理握手言和。然而,在主體哲學那里,重要的不是活生生的法律實踐,而是法律主體的倫理名分。難怪英國學者哈里批評康德倫理哲學:“生活服從于概念的嚴格審查,道德成了邏輯信條的侍女。”〔46〕Frederick Hallis,Corporate Personality:A Study of Jurisprudence,Aal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43.這種觀念在一個半世紀之后的我國學界仍有回響,盡管二者并無知識上的傳承關系,如有人認為法人本質或法人人格問題關注的核心是自然人與法人的倫理關系,其結論自然是褒自然人而貶法人。
更嚴重的是,薩維尼的將法人概念扁平化以及凸顯自然人法人倫理差異的思路將真正的問題,即民事主體制度中的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的運作問題遮蔽起來,極大地限制了法人理論的研究視界,進而抑制了法人理論的制度說明和構建能力。因為如果將法人的非財產性權利納入法人概念,那么進入法人理論視域的必將是市民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問題,那么孕育法人的市民社會自生自發秩序自然也就擺在了我們面前,法人的財產能力與其他法律能力都是這種草根秩序的產物,這顯然會導向實在說。而基爾克的有機體說則深入細致地展現了上述場景,為法人理論開辟了新的天地。
三、為何擬制——法人的前法律分析
為什么要擬制法人這個問題涉及法人制度的前法律分析,即法社會學或法哲學意義上的分析。首先,薩維尼明確地認識到法人這一主體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在討論法人的歷史發展時,薩維尼說:“在羅馬時代,在很久遠的時代就存在許多類型的盟會,特別是宗教和產業方面的盟會,還有低級官員如侍從官聯盟。然而這些盟會的存在并未導致對法人觀念的需求。……只有在涉及非獨立團體(包括自治市和殖民地,它們是國家的擴張),法人觀念才獲得顯著應用,同時也獲得了更明確的完善。因為這些社團與自然人一樣,一方面,需要財產并且也有機會取得財產,但是,另一方面,它們具有非獨立性,這就使得其能夠被法院傳訊。”〔47〕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83.
盡管薩氏仍然從財產能力角度分析法人的歷史動因,但是必須承認,薩維尼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法人觀念產生的歷史契機,這就是自治市和殖民地的發展,導致原有的個體自然人觀念無法解釋其法律狀態,必須將其視為一種新型的法律主體——法人。
其次,薩維尼指出了法人觀念產生的社會實踐必要性。關于法人的權利,他說:“所有這些財產權利作為一個整體整個地、不可分割地歸屬于法人,從而,決不個別地歸屬于組成法人的個體成員。”〔48〕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Sons,1884,p.211.類似的表述在《體系》II中還有多處。這一觀念在羅馬法時代就已經產生,英國的布萊克斯通也曾提及,參見[英]威廉·布萊克斯通:《英國法釋義》(第1卷),游云庭、繆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522頁。薩維尼進一步發展了這種觀念。而基爾克則進一步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揭示了獨立人格產生的歷史契機。“法人所有權與法人的其他每一項權利一樣,不可分割地歸屬于作為整體的法人,其成員不能分享。”〔49〕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12.對于法人訴訟,他說:“法人的訴訟代表不是各個成員的各自的代表,而是像一個個人的代理人那樣,是作為一個整體的法人的代表人。”〔50〕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21.
再次,薩維尼總結了法人組織的外在基礎,他在對意定的法人進行歷史考察之后,總結道:在羅馬法中,意定法人被認為是城鎮的仿制品,它們和城鎮一樣有財產和自己的代表人,而財產和代表人在事實上構成了法人的特征。〔51〕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193.應當承認,這一分析指出了法人成立的兩個重要條件,二者都屬于法人的外在客觀表現,盡管薩氏關于法人的外部基礎的分析并不全面深入。
最后,薩維尼探討了法人的本質或本體問題。在《體系》II第86節,薩維尼將法人分為團體法人和機構法人兩類。對于這一分類,薩維尼分析道:“有些法人具有可見外在代表——數個個人成員,這些成員作為集合整體構成了法人;其他法人則相反,不具有這一可見的基礎,僅僅是一個更為觀念性的存在,依賴于通過它所實現的共同目的。我們可以借用一個拉丁詞語稱第一類為社團(Corporationen,Corporation),……第一類法人包括所有的公社,以及被授予法人權利的行會和社團。然而,第一類法人的本質屬性存在這一點上:權利主體并不存在于其中的個人成員(甚至也不存在于所有的成員整體),而是存在于觀念整體(Ideal Whole);由此導致的一個獨特的但特別重要的結果就是,當某一成員發生了變化,甚至全部成員都確實改變了,法人團體的本質和統一性都不會受到影響。第二類通常以通用性術語‘機構’(Anstalt,Institute)表示,其主要目的在于宗教服務(眾多的教學機構屬之)、教育和慈善。”〔52〕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181.
自然,薩氏這段話中關于機構法人的論述可以視為布林茲目的財產說的前身,我們甚至可以從中推測布氏目的財產說與薩維尼法人學說的知識譜系關系。但是,筆者在此想強調的卻是,薩維尼指出了法人的本質,在社團法人是觀念整體,而在機構法人則是目的。對于薩氏這一論述的“意義”,筆者覺得應當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闡釋。
第一,應當承認薩維尼關于團體法人和機構法人的這一分類在當時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薩萊耶斯曾表示,薩維尼是近代第一個對團體法人和機構法人概念進行澄清的學者,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53〕Saleilles,Etude sur l’histoire des sociétéen commandite,in Annales de droit commercial etindustriel,fran?ais,étranger et international,t.IX,10-26 et 49-79.1895,p.77.轉引自吳宗謀:《再訪法人論爭——一個概念的考掘》,臺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提交,第27頁。同時,該分類還有極高的學術構建價值,盡管薩氏本人似乎并沒有意識到,而基爾克則深入挖掘了這對概念的學術價值,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關于法人演進的總體矛盾運動規律——團體法人觀念與機構法人觀念的斗爭,作為其整個法人制度史和觀念史研究的中心線索。
第二,還應承認薩維尼關于二者的基礎的判斷也是正確的,因為團體法人的法律人格的確與其成員人格相獨立,而且團體人格的社會存在形態正是觀念整體,而機構法人的確因其創立者所設定的目的而產生并為服務于此目的而存續。特別是其關于觀念整體的觀點不僅隱含著重要的學術構建價值,而且還包含著潛在的制度構建價值,可以說既有理論意義也有實踐意義,〔54〕關于這些意義的初步總結,請參見[德]貢塔·托伊布納:《企業社團主義:新工業政策與法人的“本質”》,仲崇玉譯,《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6年第1期。甚至可以這樣說,法人本質的任何研究都繞不開“觀念整體”和“擬制”,關鍵問題是什么樣的觀念整體,又是怎樣擬制的,然而,限于法人制度歷史發展階段上的限制,薩維尼本人并沒有有意識地發掘這些意義。〔55〕正因如此,筆者不想在這里全面展開分析這些隱含著的意義,將另文再做系統說明。
第三,不得不指出的是,薩維尼關于團體法人整體不同于部分的認識似乎仍然停留于羅馬文獻的水平上,〔56〕參見仲崇玉:《羅馬法中的法人人格觀念若干問題辯正》,載《東方論壇》2009年第5期。他并沒有進一步分析這一觀念整體如何產生,又存在于何人的觀念之中。卻明確指出觀念整體既不同于團體成員個人,也不同于團體成員全體,“成員整體全然不同于法人團體本身”,〔57〕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10.“成員不同于法人團體本身,正如監護人不同于其被監護人一樣。”〔58〕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11.相應地,團體利益也全然不同于其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59〕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 86 & p.210.在《體系》II中,薩維尼反復強調這一羅馬法上的普遍觀念。這樣,薩維尼上述結論實際上就將所謂的觀念整體與團體成員相隔離,阻斷了由團體成員的行為來說明觀念整體的產生和存在的進路,那么順理成章的就是,法人人格的產生與存在也不能從成員的行為中說明,說到底,就是不能從法人的內部秩序中得到說明。按照這種思路,法人這個觀念整體豈不成了先驗實體?實際上,薩維尼正有這種傾向。
第四,置放于當時德國古典哲學的語境中,我們會發現薩維尼的法人擬制說與有機體說的相通之處以及其與法人否認說的真正區別所在。德國古典哲學的一個總體特征就是強調在可見的物質世界之外,存在著一個觀念或理念的世界,而且往往認為相較于前者,后者更具有終極性和本原性。這種傾向在康德那里就已經初具規模,后來典型地呈現于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它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看得見的物質世界是虛幻不定的,而看不見的、抽象的理念世界才是“實在”的。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以理解,觀念整體概念并非意味著法人在現實世界中沒有相應的實體,特別是薩氏有時還用“觀念實體”(ideal being)這一概念替代觀念整體,〔60〕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10.更能顯示所謂觀念整體的實體性。因此,筆者贊同吳宗謀先生的觀點:薩維尼筆下的“虛擬”法人其實僅意味著“觀念上的”、“精神上的”實體,而非“不存在的”實體。〔61〕吳宗謀:《再訪法人論爭——一個概念的考掘》,臺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提交,第26頁。不惟如此,在薩維尼那里,觀念實體不僅僅是個實體,而且是個與其成員一樣實在甚至更“實在”的實體,因為薩維尼還強調,當法人全部成員都改變了,法人的實體性不受影響。再聯想一下薩維尼在其早年的名著《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中對集體精神、民族精神的熱情憧憬:“設若每一階級、每一城鎮,不,每一村莊,都能創生一種特定的集體精神,則此特征鮮明而又多元紛呈的個體性,必將增益公共福利。”〔62〕[德]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許章潤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其中的“集體精神”一詞正是基爾克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說,薩維尼既開啟了將法人觀念實體化之門,也潛在地開辟了通往客觀化之途。而基爾克則正是順著這一理路,全面運用黑格爾的客觀唯心哲學論證了觀念實體乃是一種先驗的精神實體,繼薩維尼將法人觀念實體化之后,又明確地將該觀念實體客觀化,從而構建了實在說的硬磐。可能正是基于對薩維尼擬制說這種傾向的清醒認識,耶林釜底抽薪地否認了法人的實在性和客觀性,并進一步否認了法人的法律主體性,法人不過是一種法律符號,真正的主體是法人團體的成員。〔63〕Jhering,Geist des r?mischen Rechts auf den Verschiedenen Stufen einer Entwickeklung,Teil 3,Leipzig,1906,p.357.這一點構成了擬制說與受益人主體說的根本對立。再聯系前文薩維尼關于自然法人之實在人格的論述,將薩維尼視為實在說的創始人,似乎也順理成章。正因如此,我國學者吳宗謀認為將薩維尼視為擬制說的頭號代言人是一種誤解,〔64〕參見吳宗謀:《再訪法人論爭——一個概念的考掘》,臺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提交,第24-27頁。德國學者弗盧梅也認為人們將薩氏的學說稱為擬制說是出于誤解。〔65〕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頁腳注;蔣學躍:《法人制度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頁腳注。
然而,如果我們了解了薩維尼對于如何擬制法人這一問題的回答,我們就會發現,吳宗謀和弗盧梅并沒有真正觸及薩維尼心靈深處。
四、如何擬制——法人的后法律分析
既然法人人格是擬制的,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誰來擬制?如何擬制?這涉及法人的設立和終止等法律制度問題,因此屬于法人的后法律分析。當然,在我國許多學者看來,法人人格問題是個理論問題,而法人的設立和終止是具體制度問題,前者是私法問題,而后者則更是一個公法問題,二者并無內在關聯,〔66〕這正是英美法系大多數學者所堅持的,除梅特蘭、維諾格拉多夫、哈里斯、拉斯基等少數學者外。在我國,只有方流芳、王利明、劉得寬和施啟揚等為數不多的學者將這兩個問題聯系到一起。參見方流芳:《公司:國家權力與民事權利的分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論文,1992年提交,第26頁;王利明:《論法人的本質和能力》,載《民商法研究》(第3輯),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劉得寬:《民法諸問題與新展望》,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96、497頁;施啟揚:《民法總則》,臺灣1995年自刊,第117頁。因此,在教材中,它們也往往是兩個孤立的知識點,學者也習慣于抽象地、沒有語境地討論法人人格問題。但是,法人人格的產生是一個具體的法律過程,從而必然與法人的設立發生關聯,因為:(1)法人設立制度的民法意義就在于賦予法人以正式的法律人格,因此(2)法人設立和終止制度的宗旨和任務中,既有公法的因素也有私法的考量,所以(3)法人設立和終止制度也有民法上的法理基礎,而非僅僅是源于行政法,而且鑒于民法是市民社會基本法的地位,民法上的法理基礎更為根本。然而,最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此,而在于,就薩維尼本人來說,這兩個問題也是聯系在一起的。
在《體系》II第89節中,薩維尼專門討論了法人的設立和終止問題。關于法人的設立,按照薩維尼自然法人和意定法人的分類,應當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是一些特定的公社和殖民地,它們是公法法人,其本身即由國家設立,它們公法特征是私法人格的基礎;第二種是歷史久遠的公社和國庫,無論最初如何成立,都無需國家特許;第三種就是剩余的其他法人組織,它們的成立需要國家統治權力的許可。〔67〕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4.他說:“除了必然的法人之外,就其余的意定法人而言,有一條規則:法人的地位不能僅僅由多個成員的任意聯合所證成,也不能由單個設立者的意志所證成,因此,國家統治權力的許可是必不可少的,這種許可既有可能是明示授予的,也有可能是默示授予(通過有意識的容忍或實際上的承認)的。”〔68〕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4.由此可見,薩維尼否認法人的基礎在于團體成員或者機構法人創立者的用意,無非就是為國家擬制埋下伏筆,法人只能是一種擬制產物,擬制的主體也只能是國家。
但是,在薩維尼時代,法人應由國家擬制或特許的主張就已經受到諸多質疑,許多學者認為,社團法人的成立應以國家的特許為前提,這固然無可厚非,一方面是因為特定羅馬法本文就如此規定,另一方面是因為自由創立法人團體會給國家帶來危險;但對于慈善法人,卻無需特許,其理由是:(1)羅馬法允許自由設立慈善機構;(2)慈善是無害的、值得嘉許的。〔69〕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5.對此,薩維尼極不贊同,他認為即使慈善組織的設立也要取得國家的審查許可。〔70〕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6.接下來,薩維尼從三個方面駁斥了上述觀點,從而論證了自己的主張。
首先,對于羅馬法允許自由設立慈善機構的規定,薩維尼指出,羅馬法的規定無需句句遵從,一是因為羅馬法本文還沒有經過注釋,二是因為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使得羅馬法不再適用。〔71〕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6.因此,羅馬法的規定不能作為支持慈善法人自由設立說的依據。
其次,薩維尼還從政治、經濟上的考量反駁了慈善法人自由設立主義者,他以少有的嚴厲口吻說:“團體法人的危險可能性固然得到了大家的承認,但是也絕不能將上文提到的捐助基金想象成絕對有益的和不可或缺的。如果有人設立一項巨額基金用于支持傳播具有政治危險性的、反對宗教信仰的、或者是不道德的理念和書籍,國家應當容忍嗎?即使是濟貧機構也不應在任何情況下聽由私人的任意意志加以設立……此外,即使是涉及政治上無害的機構,也應注意防止出現財富過量地聚集于死手(dead hands)的問題。〔72〕指永久管業,即財產屬于法人或家庭永久占有,但不能變賣或轉讓的狀態。在這里,薩維尼關心的是大量國家財產游離于國家控制之外、無法收稅,從而削弱國家財政的問題。誠然,國家可能會發現現存的已經得到許可的捐贈也會引起這種財富聚集,但是如果個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按照其意志設立新的捐贈,那么國家對于財富聚集的監控將會完全落空。”〔73〕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p.206-207.
最后,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是,薩維尼還提供了為國家擬制或特許辯護的法理說明,而且從薩氏的行文來看,他更強調這種法理基礎。〔74〕在《體系》II中,薩維尼先進行了法理論證,然后又指出了政治和經濟考量。See 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 Sons,1884,pp.206-207.他說:“創立法人的國家許可的必要性有其正確的法理基礎,這一基礎獨立于所有的政治考量。自然人因其有形外表而天然地有法律能力,這一觀念在現在獲得了比羅馬時代更加廣泛的承認,因為在羅馬時代大量的奴隸形成這一規則的例外。通過這一外觀,其他任何人都會知道他必須尊重他人的人權,并且每個法官也會知道他必須保護這一權利。現在,如果將個人的自然權利能力通過擬制轉移給一個觀念主體,這將完全缺乏上述自然確證;只有國家最高權力的意志才可補足這一缺陷,因為國家最高權力創造了虛擬的權利主體,而且假如同樣的權力被允許由私人意志恣意運用,既使完全不考慮因不誠信地運用這一權力而可能導致的巨大濫用,無疑仍會導致法律狀況的極大不確定性。”〔75〕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6.
在這段說明中,薩維尼沿著個人主義和理性法學進路,指出社會存在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律主體是因其具有特定的內在規定性——自由,個人因具有內在自由,其成為法律主體有著自然法和倫理上的先驗基礎,但法人卻缺少這種內在自由,而國家最高權力意志則可以點石成金地、憑空補足這一基礎。正如梅特蘭嘲諷地說:如果國家沒有將法律能力這種神秘的“虛擬生命的氣息”注入法人之中,它就不可能成為法律上的人,〔76〕See F.M.Maitland,Introduction,in Gierke,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xxx.薩氏所稱的國家擬制法人的故事正是圣經里的上帝造人之虛妄傳說的翻版。這段論述說明,在薩維尼那里,法人人格這個所謂的抽象問題是與具體制度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由此,我們還可以明白,薩氏先前對于法人是個擬制主體的界定,關于羅馬法支持擬制說的論斷,將法人這一觀念整體與團體成員相隔離的價值取向,以及拒絕從法人的內部秩序說明觀念整體的研究思路,不過是為了論證國家擬制打基礎。這段論述以私法理論的面目論證了法人特許和許可制度的合理性,將法人理論納入了當時流行的政治哲學觀念之中,成為后世法人大論爭的焦點,因此,這才是擬制說的核心內容,而筆者上文所提到的吳宗謀與弗盧梅所未觸及的薩維尼的內心深處也正在此:在薩維尼那里,深層的問題不是法人的擬制還是實在,而是政治理念,是對中央集權國家的推崇和對市民社會自治的貶抑。只有在這種政治觀念統轄之下,薩維尼才可能同時容納擬制和實在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觀念,無論是擬制還是實在,都是為國家扼制法人的政治立場服務的。將薩維尼的法人人格理論稱為國家擬制說,不僅在法理上符合薩維尼的原意,而且也符合其政治立場。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其中合理的一面,正如薩氏所擔心的,如果自由創設法人,必定會導致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秩序的混亂,現代國家也普遍沒有采納自由設立主義立法模式。同時,國家對于法人的登記制度以登記程序的公示性使社會團體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承認,大大節約了團體的交易成本,因此,國家對法人的登記管理制度不可或缺。但問題似乎并不到此為止,我們還要問:在自由設立和國家特許之間,有沒有將國家權力和社會公共利益相協調的空間?可不可以采用準則制?薩維尼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無需就所有法人制定一個關于其設立條件的實定法規則。”〔77〕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4.其原因在于:多數公社與國家相比一樣古老、甚至更古老;而國家出現以后的公社總是通過政治行為而非依照私法規則設立;而國庫的設立更是個歷史問題。〔78〕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4.言外之意就是,除了國家和所謂自然法人之外,其他法人的設立行為都屬于存在于法律之外的政治行為,對此,法律無緣置喙。
關于法人的終止,薩維尼說:“法人一旦正式成立,其解散不能僅僅由現有成員的主觀意志來決定,因為法人確實獨立于現有成員而存在,但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許可也是解散法人所不可缺少的。反過來說,如果為了國家的安全與福祉而使得解散法人成為必要,只需國家的意志就可解散之,即使這有悖于其成員的意志。解散法人既可以按照法律的普遍性規則,也可以在特例中,通過超出法律定則之外的政治行為來解散。關于具有國家機構性質的捐贈法人,國家在解散它們時可以有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間;例如,解散原因不限于現有機構可能表現出危險性或邪惡性,而是僅僅因為如果建立新機構,捐贈目的可能會更成功地得到實現。”〔79〕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07.總之,可以用薩維尼自己的話來總結:“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解散法人都需要國家的許可。”〔80〕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Jural Relations:Or,The Roman Law of Persons As Subjects of Jural Relations: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Book of Savigny’s System of Modern Roman Law,translated by William Henry Rattigan,London:Wildy& Sons,1884,p.259.這就是基爾克所稱的“既不能生也不能死”的混亂觀念。〔81〕Gierke,Die Genossenschaftstheorie und die deutsche Rechtssprechung,Berlin:Weidmann,1887,S.75.
五、小結
綜觀薩維尼的擬制說,我們會發現,在薩氏筆下,法人概念僅僅意味著一種私法上的財產能力,為抽空法人概念的制度構建功能立下基調;法人具有全然不同于其成員全體的獨立實體,為凸顯法人相對于國家的派生性埋下伏筆;羅馬法本文被有選擇地運用和再造性詮釋,成為證明法人是擬制之物的法學證據;德國古典倫理哲學也得到了重申和強調,引以為證明法人不具倫理性的哲學基礎。
就這樣,在薩維尼那里,法律分析、羅馬法研究和哲學理念都被統一到當時盛行的政治理念——霍布斯、盧梭以及黑格爾的現代中央集權型全能國家觀念上來。由這種政治觀念和薩氏本人的政治傾向所決定,法人存在的基礎不在于私法范圍之內,而在于公法領域之內。在公法領域里,國家覺得有必要,就創造這些法人,如果覺得其有害,則禁止這些法人。而且對于那些經過國家批準的法人,國家仍可隨時剝奪其法律人格,法人的生死全部操于國家之手。總之,薩維尼在私法上擬制出一個團體主體的同時,卻在公法上制造出了一個團體奴隸。正因如此,法國民法學家薩萊耶斯認為擬制論不是私法理論,而是偽裝在私法概念下的公法理論。〔82〕Saleilles,De La Personnalité Juridique:Histoire et Theories,2nd edition,Paris:A.Rousseau,1922,p.366.轉引自Frederick Hallis,Corporate Personality:A Study of Jurisprudence ,Aal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0。
再回到本文開頭,可以發現,我國有關薩維尼擬制說的評價沒有深入揭示其精神實質,有失偏頗。實際上,這種情況并非個例,由于民法學術源遠流長,所以幾乎民法的每個概念和規則都會被各種各樣的“說”所包圍,特別是由于我國的民法文化和學術是從大陸法系繼受而來的,所以相當一部分學說的源頭就在國外已無人問津的黃卷枯頁之中,但是學界卻往往缺乏對這些“說”的原始文本的全面解讀和深入分析,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正本清源地梳理民法的學術基因,利用多種學科的知識,進行系統性的學說批評就有了獨立于應用研究之外的、特別重要的學術意義,因為惟有如此,方能促進民法概念和文化的本土化。
*仲崇玉,山東大學法學院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研究人員,青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山東省博士后創新項目“法律人格制度研究”(項目號20080308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陳 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