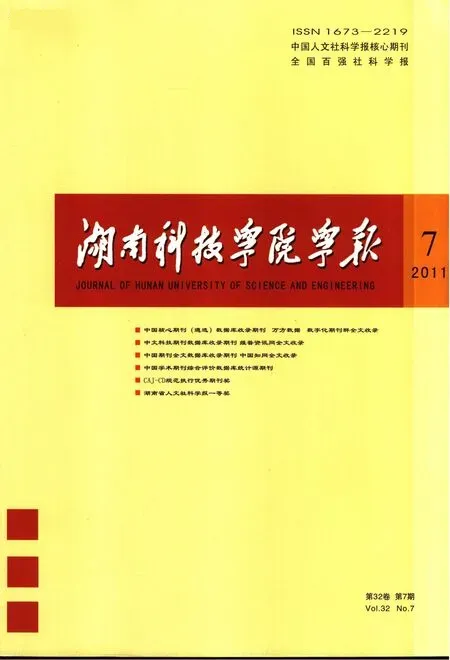其實還是士大夫問題
——高峰訪談錄(二)
高 峰
(上海市委黨校,上海 200233)
其實還是士大夫問題
——高峰訪談錄(二)
高 峰
(上海市委黨校,上海 200233)
編者按:本文為《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編輯部張京華于2010年6月赴上海所作高峰先生訪談的一部分,內容主要為學術研究的方法評論,錄音整理稿經作者審定并略有修改。
高峰;訪談錄;士大夫
一
高峰(以下簡稱高):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是蠻成問題的。陳寅恪《寒柳堂記夢》未完成稿談到在洪憲帝制的時候,士大夫那個丑態,看到這個情況,他覺得氣節是最重要的,至于是立憲還是帝制,倒是其次。
張京華(以下簡稱張):是。
高:我非常能夠體會他這種說法。有時候你看中國社會,現在哪怕你搞帝制也沒關系啊,只要社會能有秩序啊。你人稍微有點氣節,這個氣節不是說要什么“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沒到這么高的層面,就是在臺面上也給自己一點面子。現在有些學者實際上是自己不給自己面子是吧?就是你在臺面上自己給自己一點面子就可以了。實際上,像張東蓀當初講到中國文化的時候,他也蠻注意這一點,他說清朝之所以在后來一下子垮得那么厲害,武昌起義是很偶然的一件事情。清朝一下子就垮了,這只不過是清朝本身太站不住腳,而并不是因為當時革命黨勢力有多么大。那么清朝為什么會這么站不住腳,主要是因為士大夫太不像樣。
張:清朝最后的退位當時做得很容易。一開始起義的時候好像很壯烈,很艱難,結果后來退位很容易。
高:后來發現很簡單。
張:一股風就退位了。
高:可是那個時候,據國外學者研究,清朝的GDP可是世界第一啊。
張:哦,是嗎?
高:國際上的經濟課題研究說,一直到1889年,中國的GDP還是世界第一。1890年被美國取代,美國世界第一,中國世界第二。
張:1889年那還是慈禧在位啊。
高:慈禧在位。就是說鴉片戰爭時候,圓明園被燒等等事件出現時,中國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一。
張:所以當時經濟其實不是問題。
高:經濟不是問題,是中國文化有問題。我的感覺中國社會出問題一定出在內憂,而不是出在外患。只是因為內部太出問題了,外患才成為患。
張:多少年以來一說清朝就說鴉片戰爭,就說經濟。
高:還是士大夫問題,是內部問題。用現在的話說,是公務員問題。
張:晚清李鴻章、張之洞他們都在位,清流啊。
高:但是這個沒用。就是秩序垮掉了。像李鴻章,我看他也是絞盡腦汁。
張:也是硬撐。
高:要沒他撐的話,恐怕還更快點。
高:當初,好像是同治中興的時候吧,好像都認為大清了不得了。當然那時候沒有GDP的概念,但是社會經濟比較發達,那個船艦從德國買進來了,洋槍洋炮也進來了,北洋水師也建立起來了,那個造船廠也開始建立起來了。好像有一個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曾國藩的一個幕僚,他說我看大清帝國完了,不出五十年吧。他講這話過了四十六年以后,大清帝國就倒了。曾國藩當時不相信。
張:這是人的問題。
高:社會亂掉了,沒秩序。一個社會沒有一個最起碼的秩序。
張:還是吏治問題。
高:中國的問題也涉及高層。毛澤東針對這一點也有些想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有這種想法。毛澤東一度把公務員打爛,把公檢法、公務員全部打爛。
張:他說文化部是才子佳人部,教育部、衛生部是老爺部。其實發動“文革”的好多理由還是有原因的。
高:但是一打爛了呢,社會沒人管了。
張:對,他操作不好,但他理由是有的。
高:中國近代史上有兩次“公務員”被打爛了,就是官僚制被打爛了,一次是軍閥混戰的時候,一次是毛澤東的時候。這兩次時候社會都還可以,軍閥這么混戰,社會沒大亂。毛澤東時候,三年自然災害餓死幾千萬人,社會也沒大亂。因為它秩序在,秩序在的話,大家自動會跟這個秩序對位,知道自己是什么本分。
張:以前等級在的時候,那么農民知道自己這個本分,他就老老實實把田種好,他不會尋思去過錦衣玉食的貴族生活。你秩序一打掉了,那么就有人會問:你可以錦衣玉食,為什么我不能?
高:如果天下都去爭錦衣玉食,怎么辦?
張:高峰你說現在社會,先不說問題吧,問題一下說不完,那么它有一個辦法沒有?
高:我看沒辦法,至少我個人認為沒什么辦法。
張:做研究你是元老級的,應該有些想法。
高:我個人認為沒辦法。
二
高:一位上海作家來,他說要跟我談談中國文化。說到小孩讀經,我說我現在不太贊成小孩子讀經。他問我為什么不贊成,他倒是很贊成的,他要復興傳統文化。我說因為文化是一種制度性的體制,沒這種制度保障了,你要把它重興,那么社會上是怎么一回事情?經書上是怎么一回事情?你將來只有兩種可能。
張:哪兩種可能?
高:兩種可能,一種可能就是培養更多的兩皮兒、雙皮兒。
張:對。
高:現在的小孩子,你鏡頭對著他,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什么的都可以講,但是最后什么事情都干,無所不用其極。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真的相信了經書上說的東西了,那這小孩將來就苦了,你沒有給他人生的光明。
張:對。
高:我是不太贊成小孩子讀經,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他們情況不一樣。我們自己是有一個文化認同,他們既然已經生活在這個沒有文化認同的世界上,那除非這個小孩將來大起來,他自己由于某種機緣產生了這種文化認同,那么我也支持他。現在有哪個小孩子,他說他感到對社會上的一切他都看不慣?他說他覺得還是儒家文化好?
張:這種很少啊,有也可能是神經病,才會這樣看啊。韓寒可能是個特例。
高:是個特例。
張:韓寒不會是神經病,但是他不滿意現實世界。
高:對。
張:但他也是個特例,八零后的人很少會這樣看。
高:他老是要跟社會逆反一下。
張:他是八零這代的人,而且他是很有錢的。
高:他不靠你這個體制過日子。現在有很多學者,因為在體制內過日子,他會說很多話,他的人格就變得比較差勁兒。
三
高:我現在比較關注社會的行為傳統。現在問題比較復雜,過去我們是比較單一的。從清末開始,中國不管是向日本,還是向英美,還是向俄國,向西方學習這一點是不變的,我們都想向西方學習,認為西方比我們強大,所以要向西方學習。我們為什么要學習他們的代議制,并不是因為代議制本身好,是因為他比我們強大,那么代議制可能是他們強大的一個原因。我們要立憲,為什么要立憲?因為西方比我們強大,日本立憲,沒多久它就打敗了俄國,并不是因為立憲本身好。但是現在呢?最近幾十年的發展呢?你看西方金融危機出現了,看來他們的制度也有問題啊。中國的經濟發展上去了,中國的GDP現在是世界第二,我們也不比他們差。因為本身你對事物的理解就不是從目的上去理解,而是作為工具理解的,那事情就很難辦。所以我們現在,包括我個人都有這種情況,我覺得我們大部分學者現在處于一種茫然狀態,因為他們兩頭落空。
張:怎么理解呢?
高:傳統的東西呢他們扔掉了。現在四五十歲的一批學者,至少在二十年前他們還是想向西方學習的。包括像牟宗三他們這一代,向西方學習,特別在政治、在科學和民主這一點上對西方是沒有疑問的。包括在一些行政制度上、管理制度上,對西方都是沒有疑問的。
張:是的。
高:我們只是在儒家道德上,在道家境界上,在個人的心境上,可以保留我們自己的東西,其他東西學習西方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現在是西方也不過如此。可你再回過來吧,現在五十歲一代的人,這一代學術界的人能夠擔得起中國的傳統文化嗎?恐怕沒有幾個人擔得起。有很多人做經學研究,我甚至能看出他這文章就是從電子文獻上引上去的,我知道有些學者在做學術史。
張:他本來就把經學當史料,而史料俗一點說就是材料,材料那自然就是抄抄、貼貼。
高:從思想史上下降一點,我比較注重中國社會。并不是老說中國五千年文化傳統,我比較注重人的社會行為。實際上,衡量一個社會好不好,衡量中國好還是西方好,有沒有個標準,搞不大清楚,學術界的觀點很不一致。現在學術界當中民族主義勢力也蠻大,有一批學者專門研究西方的保守主義。我的看法是,在法學界里頭似乎自由主義比較多一點,政治學界和國學界里頭新左派和民族主義都不少。現在的問題是,實際上你一上來,你這個目標就不明確,你學西方并不是認為這個代議制本身有優點,而是因為代議制能帶來強大,現在我們不用代議制我們也強大,這個就比較成問題。所以,我最近一段時間是比較悲觀的,因為身體不好,我原先心里想到了很多的問題,但是很少有條件能夠自己親自去做這些課題。我看現在做學術史的無非就是幾個路數,一個路數是最下等的,就是外面搞課題的那種研究,把史料堆積起來,堆得越多越好,號稱是樸學,號稱學陳寅恪,這是最下等的。上等一點呢,注意到這里頭一些社會學層面的東西,注意文化的影響,這算是目前比較好的,能夠注意到社會思潮和學術的互動,但也僅此而已。但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就思想本身解讀思想這點沒弄清楚,這是硬件。社會跟思想互動,你把握這個思想沒有?我們說要論證康德的思想跟當時的啟蒙運動、德國社會的互動關系,前提畢竟還是以對康德思想本身的研究為基礎的,這個是硬件,其他是軟件。但這部分東西是最難做的。徐復觀老早就說過,經學這樣搞不行,老是說誰怎么說、誰怎么說,誰談誰、誰談誰,這樣不行。你得把兩漢當時的經義給說出來。比如說,兩漢公羊家有一套理論,他們是怎么說的,古文家他們是怎樣說的。但是這個東西沒人搞,這個部分是硬件。現在的學者往往圖方便,急于出成果。
張:你說硬件,其實就是一些很客觀的問題,必須得好好梳理的,不能隨便編造的。
高:對。現在學術界喜歡研究“思潮”,我承認“思潮”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就像英國劍橋學派說的那樣,就是一種思潮的興起不是突如其來的,一種學說興起之前,往往社會上已經有很多類似的說法了。然后再有某個大人物倡導,再由國家執行就產生了,在這之前,社會上已經有很多這方面的說法流行著。英國很多思潮,乃至西方近代很多學說的產生都是這樣的。但是實際上又不完全是這種情況,所以“思潮”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對某些思想當中一些邏輯脈絡的研究。用我們中國傳統說法,這種社會方式的研究是外學,而這個思想傳統本身的研究是內學。但是現在搞“內學”的人越來越少了。
張:所謂“思潮”實際上有點兒貼不上是吧?似是而非的東西多一些。
高:實際上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就都亂說。亂說的東西太多了。
張:現在許可亂說,許可任何做法。
高:后來我就發現,一些新書里頭亂說。亂說的多了,接下來還有幾個人會去自己讀《四書》《五經》?那還不是都聽你們這幾個專家學者的?
張:一代傳一代,但都是復述。
高:后來就沒辦法了,再過四五年就沒辦法講了。現在國學已經沒辦法講了,再過四五年就更沒辦法講了,這比較麻煩。所以我就覺得社會上如果不那么提倡國學,能讓一部分人自己真正對國學有認同感,或者哪怕是有忤逆感都行,讓他們自己去搞,可能還好一點。
張:那他們可能是在這個社會上得到既得利益最少的一些人。
高:差不多可以這樣說。
張:也可以說是最無私的一些人,“無欲則剛”。另一方面,事實上你想欲也欲不到啊。
高:對。
張:所以只能剛,沒辦法。你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高:是的。實際上我缺陷很多,因為很多地方借不了體制的光,但是也有一大優點,就是我看問題不受自身利益影響。
張:你說話就非常公正,沒有主觀的成見,用不著去考慮別的東西。
高:我也不考慮我跟某個學派或者某個人的關系什么的,我自己想發表什么意見我都可以發表,我只要覺得這個看法自己心里感覺比較踏實,我就可以說。本來呢,我一直不想特別掛在某個學派上,這個倒不是這兩年身體的關系,我一直有這個看法。記得德國的一個歷史學家說過,各個時代,它的發展可能有高潮有低潮,但是在上帝眼里是平等的。這個話我不敢說,因為我不知道上帝眼里看世界是什么樣的,但是我認為各種學說、各種思想,都可以在某一個層次、某一個階段上有它的一些成見,很多學說都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
張:是。
高:就是說,不必提倡哪個就必須要打倒另一個。因為我發現現在的學術界已經有這種傾向,就是無謂的黨同伐異。搞西學的也有,搞國學的也有。實際上,老實說現在學者搞黨同伐異,特別是國學,搞黨同伐異也沒這個資本。
張:現在有些不同意見在爭,國學上就誰跟誰在爭,什么觀點跟什么觀點在爭,爭得好像蠻兇的。就國學一個概念,大家的意見也大不一樣。
高:現在國學這個爭呢已經不太像樣,已經落到第二義上了。因為現在很明顯,你看關于國學的很多爭論一上來就直接跟既得利益掛鉤。
張:是。
高:有很多就是直接的利益相爭。
張:那你說得太對了。現在怎么爭其實都離不開利益。沒有學派,只有宗派。
高:一上來就是第二義。第一義,實際上真正的東西,沒幾個人關心。報紙我有時候也看,看到他們國學家在爭,我覺得一上來就是第二義。
張:是的。
G09
A
1673-2219(2011)07-0004-03
2010-06-21
高峰(1962-),男,上海人,畢業于復旦大學哲學系,任教于上海市委黨校,兼任湖南科技學院濂溪研究所特聘教授。自2000年以來居家養疴,治學不輟。出版著作《大道希夷——近現代的先秦道家研究》、《禪宗十講》、《春秋穀梁傳譯注》,編纂《十家論佛》等多種。
(責任編校:張京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