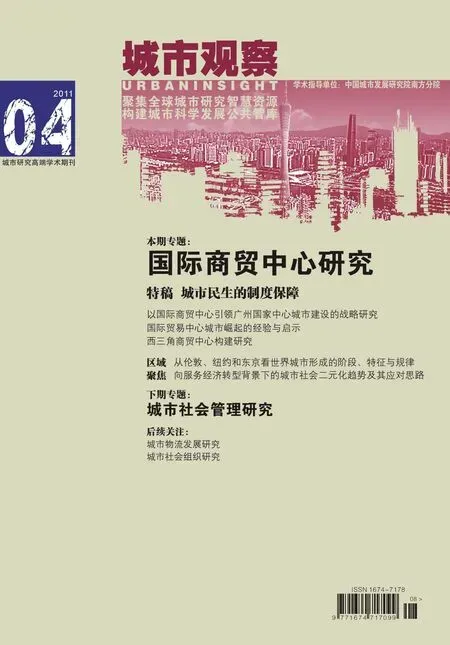城市文化建設中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
◎ 王楓云
城市文化是以城市為載體所形成的自然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結合,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統一。[1]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與城市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城市文化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是城市的靈魂所在。在21世紀,城市發展的關鍵環節是城市是否具有自己的特征,是否具有吸引人才、技術、資本的獨特性,也就是是否具有自己的城市文化。[2]因此,加強城市文化建設,推進城市吸引力與凝聚力的提升,是培育城市綜合競爭力的必然要求。而商品性文化生產作為城市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健康、有序的發展與城市文化建設的成敗密切相關。
商品性文化生產遵循發達市場經濟的必然趨勢和客觀規律,將城市文化品(社會科學作品、文學藝術作品等)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展開一系列的創作、加工、營銷以及傳播推廣活動。與物質生產一樣,在商品性文化生產中也會出現“假、冒、偽、劣”的文化產品,這些“假、冒、偽、劣”的文化產品不僅是一種虛假的文化生產能力,甚至是一種強大的社會破壞力量。因此,通過有效的政府監管,防止商品性文化生產的異化,是城市文化建設的必然要求。
但是長期以來,我國城市政府對商品性文化生產的監管主要采用的是一種“強制命令”的監管模式。在這種模式下,擁有法律授權的政府監管機關是唯一的主體,監管措施往往具有單方性、強制性的特點,監管的內容主要包括:通過地方性文化法規對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進行間接監管;通過認可和許可等各種強制性手段,對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的市場進入、退出、價格、服務的質和量以及投資、財務等方面的活動進行直接監管。這種強制性的政府監管模式帶來了一系列弊端,比如:監管目標的達成主要依靠政府監管機關憑單方意志做出的強制支配行為,被監管者沒有意見表達和行為選擇的理論支持和制度安排;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地位的不平等,嚴重挫傷了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的積極性與主動性,缺乏為實現政府監管目標而積極參與和配合的主動性與責任心,處于消極被動的地位;由于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在參與和監督的渠道上面臨諸多障礙,導致了政府監管的低效率、高成本以及在信息不完備情況下監管的盲目性;一些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為獲得高額利潤,通過合法與非法的途徑“購買政府”,引發了劣質文化品的泛濫和公共官員的尋租行為等。[3]
顯然,這種“強制命令”式的政府文化生產監管模式,在引導商品性文化生產向城市政府所期望的方向發展的進程中,往往難以完滿達到預期目的。因此,在城市文化建設中,推進政府對商品性文化生產的監管從傳統的“強制命令”式監管向“授益誘導”型監管模式轉型,就顯得很有必要。
一、商品性文化生產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內涵與特征
(一)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內涵
(二)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特征
1.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人格獨立且意志自主
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運行,不是強調文化生產主體完全聽命于政府監管主體、被動接受監管主體支配,而是強調文化生產主體的獨立人格,強調其能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動參與監管過程,文化生產主體利益需求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得到認可和尊重。
2.城市政府監管機關與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雙方地位平等
在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運行中,生產主體不僅人格獨立,而且與城市政府監管機關地位平等,監管主體不得以自己的利益否定或取代文化生產主體的利益,文化生產主體可以在規則既定的情形中與監管主體對話,并就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問題與監管主體展開協商,最終在整合雙方利益需求的基礎上形成均衡決策。
3.城市政府監管機關與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的積極互動
在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運行中,沒有監管主體強力作用的空間,城市政府監管預期目標的達成,不是監管主體單方意志決定的結果,而是城市政府監管機關與文化生產主體積極互動、相互磨合的產物,二者同向并增的理想在互動中得以實現,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在互動中得以升值。
二、商品性文化生產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類別與功能
(一)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類別
對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進行分類,有助于從不同的角度對其加以了解,揭示該模式存在領域的廣泛性和存在形式的多樣性,有助于加深對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概念和性質的認識,有助于根據不同類型授益誘導政府監管模式的特點,建構不同的制度模式。
北方設施農業及畜牧業區要防范大風降溫雨雪天氣的不利影響,做好棚舍和設施溫棚的加固保溫工作。北方冬麥區要做好冬前田間管理,墑情或苗情偏差田塊要及時灌溉、施肥,促進小麥扎根分蘗,苗情長勢過旺田塊要適時鎮壓,控旺轉壯,確保安全越冬。
從不同的角度,可以將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做如下劃分[5]:
1.權利賦予型誘導與義務減免型誘導
根據政府監管機關對文化生產主體所授予的利益,是賦予權利還是減免義務,我們可以把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分為“權利賦予型誘導”與“義務減免型誘導”。
2.過程型誘導與結果型誘導
根據政府監管機關對文化生產主體所授予的利益,是引導其實施某種政府所期望的文化生產行為,還是引導其達到某種政府所希望的文化生產結果,我們可以把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分為“過程型誘導”與“結果型誘導”。
3.物質性誘導、精神性誘導、權能性誘導、信息性誘導
按照城市政府監管主體對文化生產主體授予利益的內容,對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可作如下分類:①物質性誘導,又稱功利型誘導,是指以一定的獎金、獎品或其他實物形式作為獎勵手段,滿足文化生產主體的物質利益需要,進而引導其實施城市政府所希望的行為;②精神性誘導,指授予榮譽稱號等具有一定象征意義的符號,或對文化生產主體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予以認可、贊賞等作為引導手段,滿足文化生產主體精神方面的需要;③權能性誘導,是授予文化生產主體享有從事某種活動或獲得一定權利的資格;④信息性誘導,當今社會,信息作為一種資源的作用更為突出,為某些符合條件的文化生產主體提供其他主體所不能享用的信息,也是一種授益方式,從而可以使該文化生產主體擁有比其他主體更為優越的競爭條件。
(二)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功能
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之所以能夠影響個體行為,使文化生產主體按照城市政府監管機關的意愿積極作為,就在于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尊重并引導了文化生產個體的自利本性,在于激發了個體基于需要而產生的行為動機。一言以蔽之,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功能來源于其內在運行機制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具體而言,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功能體現在以下方面:
1.文化生產主體的行為激勵功能
充分挖掘城市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的潛在智力、財力和物力資源,最大限度地調動文化生產主體實現政府監管目標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激勵功能。實踐表明,強制與命令有助于制止違法的文化生產行為,利益誘導則有助于鼓勵和激發更為積極的文化生產行為,會實現強制和命令的監管模式所無法實現的監管目標。富含物質和精神等誘導性因素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能有效激發文化生產主體行為的動因,促使人們不斷挑戰自我、發展自我,在努力地有秩序地實現自身利益增值的同時,促進城市文化的良性發展。
2.文化生產資源的流向引導功能
引導文化資源流向是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的主要功能之一。該監管模式通過特定的利益引導商品性文化生產主體的某些行為,彰顯城市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價值偏好,為生產主體提供明確、清晰的行為導向,使生產主體在了解、認同城市政府施政意圖和充分信賴城市政府的基礎上,自覺按照政府的要求,將文化生產資源投放到城市政府鼓勵發展的領域。同時,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通過賦予生產主體實際利益,加大影響和引導生產主體的力度,使生產主體在利益機制作用下,朝著城市政府既定的目標運行,以實現政府的文化發展戰略。
3.文化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
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作用于文化生產主體的內心世界,使文化生產主體在獲得了一定的利益滿足后盡可能按照監管主體的意愿作出某種行為選擇,這是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能夠推進文化生產資源優化配置的制度原理。一般而言,接受利益、按城市政府監管機關意愿作為的文化生產主體,一般都是那些資源充裕,能在與其他主體競爭中最大化自己利益的文化生產主體。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整合了政府監管主體的行政目標和文化生產主體的行為動力,使城市社會文化生產資源得以優化配置。
三、我國城市商品性文化生產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設計時應注意的問題
在我國城市文化建設中,設計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應最大化該監管模式的激勵程度和激勵效果:
(一)根據文化生產主體的不同需要設計不同的授益形式
內容型激勵理論表明,個體需要是有差異的,即使同一個體在不同時期也會有不同的需要,因此,同一授益形式對不同的個體或不同的授益形式對同一個體的激勵效果是不同的。例如,在物質需求還是多數文化生產主體基本需求的今天,授益的形式僅僅采取精神獎勵是不夠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就是要從個體的不同心理和不同需要出發,選擇不同的獎勵形式,設計不同的激勵措施,使更多的文化生產主體的動機受到激勵、需求獲得滿足,增加為實現城市政府監管目標而積極作為的興趣與愿望。
(二)確保文化生產主體的預期目標得以實現
過程型激勵理論認為,目標實現的程度越大,可信度越高,激發能力越強。因此,在設計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時,為確保文化生產主體按照城市政府監管意圖實施其所倡導的行為,就必須有意識提高授益的效價和期望值,最大化文化生產主體的行為動機。具體表現在:一是要提高文化生產主體經努力可達到希望績效的自信。授益所賦予的各種利益必須對文化生產主體具有足夠的吸引力,能夠滿足文化生產主體的優勢需要,同時,授益所誘導的行為必須是文化生產主體經過努力后可能做出的行為。目標過高、可望而不可及,或目標過低、唾手可得,都難以產生正的效價。二是要提高達到績效后文化生產主體能獲得應有評價或獲得應有授益的信心。對付出努力、做出行為后可否獲得授益的程度,會極大地影響文化生產主體的行為動力。因此,城市政府監管主體必須堅持授益公平并講求信用的原則。三是要提高文化生產主體對“努力——績效”和“績效——授益”的關系認知度。只有在文化生產主體清楚地知曉自己的努力績效和行為結果時,授益誘導才會發揮巨大的激勵作用。
(三)理性看待商品性文化生產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存在的不足
需要說明的是,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也有其與生俱來的不足和局限,需要理性對待。首先,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在追求秩序、確保文化生產主體義務實現方面,沒有強制命令型監管模式的強大力度,這也是城市政府在文化生產監管中多種監管模式交替并用,強制型監管模式難以被授益誘導型模式完全替代的原因所在;其次,相對于強制命令型監管模式而言,授益誘導型監管模式的“柔性干預”副作用較小。但是,授益誘導型政府監管模式畢竟是城市政府調控商品性文化生產運行的手段,運用不當,同樣會影響甚至破壞商品性文化生產的市場環境。因此,在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的呼聲日益高漲的今天,城市政府對商品性文化生產的授益誘導型監管模式的運用也應審時度勢、因地制宜、有所取舍。[6]
[1]吳宏放,趙文廣.加強城市文化發展的對策思考[J].中共四川省委省級機關黨校學報,2003(4).
[2]劉文儉,馬秀貞.城市文化解析[J].中共杭州市委黨校學報,2005(2).
[3][4]郭志斌.論政府激勵性管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22,15.
[5]傅紅偉.行政獎勵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46-60.
[6]孫麗巖.授益行政行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