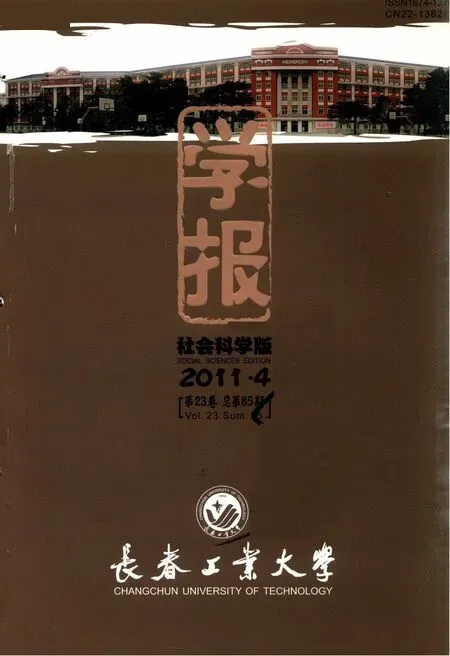賽珍珠小說觀的內涵
晏 亮
(湖北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石435002)
賽珍珠小說觀的內涵
晏 亮
(湖北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石435002)
賽珍珠的三篇演講詞《中國小說》、《東方、西方及其小說》、《中國早期小說源流》,分別從小說的發展史、地位、功能、內容以及創作技巧等方面,全方位闡釋了賽氏小說觀內涵:有著悠久發展歷史的中國小說,在它自己的國度里向來地位不高,中國小說主要是為了滿足平民的審美趣味而創作的;中國小說的功能決定了其內容也是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國小說主要采用“生活化”的結構,運用白描手法、普通人的語言以及全知視角。
賽珍珠;小說觀;內涵
賽珍珠是20世紀世界最多產的女作家之一,一生共創作了上百部作品,其中以中國題材的作品最為著名。與其豐富的小說作品相比,賽珍珠自己闡發小說理論的文章卻為數較少。1932年賽珍珠在華北語言學校分別作了題為《東方、西方及其小說》和《中國早期小說源流》的演講。在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賽珍珠以《中國小說》為題作了重要的演講,她由此也成為第一位在如此重要的國際場合給予中國小說崇高評價的西方作家。下面將以這三篇演講詞為具體討論對象,分別從小說發展的歷史和功用,小說內容以及小說創作技巧等幾個方面全面闡述賽珍珠小說觀的內涵。
一、小說的發展史、地位和功能
中國小說的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正如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總結的:遠古神話,六朝之鬼神志怪,唐宋之傳奇,宋元之話本、擬話本,元明之講史,明之神魔小說、人情小說,清之諷刺小說、狹邪小說、公案小說、清末之譴責小說等階段。在《東方、西方及其小說》中,賽珍珠通過對比中英小說發展途徑的不同,準確而客觀地指出,起源大大早于英國小說的中國小說,但是發展卻較前者緩慢得多。“中國小說自身成長、壯大,具有了生命,只是到最近幾年才受到別國文明的重大影響。”[1](P194)在《中國小說》中,賽珍珠指出:“如果漢朝是黃金時代,那么唐朝就是白銀時代”[2](P966),“到了宋代,小說的形式真正開始明確起來,而到了元朝,它便成熟繁榮,達到了頂點,此后再沒有超越,實際上只有一部小說可以與之相提并論,這就是清朝時的《紅樓夢》。”[2](P968)由此可見,具備中國小說史基本素養的賽珍珠,雖然能夠概括出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大致流程和每個階段的基本特征,但是與魯迅相比,仍然顯得稚嫩和感性。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狀態下發展和成熟,中華民族的文化也不例外。“實際上,受佛教影響頗深的六朝時期,佛教的母題似乎滲透了所有的小說,出現了許多復活再生的故事及神話傳說”[1](P194),“這幾年中,西方的影響已深深地滲透到中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1](P194)從賽珍珠以上兩段并不太深刻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她承認中國傳統文化并沒有完全排除外來文化的影響,特別是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更是全方位的,滲入到社會各個領域。這些與時下學者的主流見解是基本吻合的。
同時,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序言中所言:“中國之小說向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后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于小說仍不詳。”[3](P2)由于中西學者對中國小說史論述過少,西方讀者對中國小說基本上處于不了解的狀態,就像賽珍珠在《中國早期小說源流》中指出的那樣:“到目前為止,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小說差不多還是一無所知的。文學史里提到的大多是中國詩詞和名人語錄,就是著名的漢學家在涉及小說和故事的問題時,也是三言兩語、一帶而過。”[1](P211)
有感于此,賽珍珠憑借其特殊的雙語文化優勢,通過對中國小說源流的探究,向西方展示出一個內容十分豐富卻長期被忽略的小說傳統。
小說盡管在漢代成為一種獨立文體,但是一直到明清,其邊緣化的處境并沒有根本性轉變。在正統文人那里,小說只能是“小道”、“末技”,甚至是“邪宗”。顧炎武曾感慨:“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小說’這一教。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子弟之逸居無數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于禽獸乎!”[4](P709)可見,小說在明代雖然已經非常盛行,但是地位仍然很低。直到李贄以小說評點的創作實踐打破以小說為“末技”的傳統觀念,小說才真正獲得獨立的文學價值。在《中國早期小說源流》中,賽珍珠開篇就指出:“中國小說在它自己的國度里素來地位不高。”[1](P210)對于這個怪異的現象,賽珍珠進行了中西對比:“在西方,作者本人的名字和他的書名一樣重要,要想研究小說,其中的一個方面就是研究作家本人,他的個性,他的作品是否寫出了時代特征,他本人要表達的思想,他的個人風格,等等,一言概之,他和他的書是不可分割的。”[1](P190)可以說,賽珍珠敏銳地看出了在中國對小說的輕視所導致的小說作品著作人身份不詳的結果。在《東方、西方及其小說》中,賽珍珠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小說發展過程中很少出現大家的事實:“英國小說的花朵在文學花園里雖姍姍來遲,……,我們可以舉出兩個名字來標示這繁榮的時刻—理查森和菲爾丁,而中國小說的發展卻沒有類似的時刻”[1](P195),并認為這無疑是導致起源大大早于英國小說的中國小說到了近代發展滯后的原因。
對于中國小說的功用,賽珍珠在《中國小說》中認為:“中國小說主要是為了讓平民高興而創作的”[2](P960),因為普通的中國人根本就不在乎“詩言志”、“文以載道”等所謂的正統原則。結合中國文學史到唐宋一段的發展來看,賽珍珠的認識還是比較客觀的。長期以來,小說在大眾的觀念里,就是消閑的手段。先秦至漢魏時,小說多出自俳優,而俳優的作用主要就是給君主、貴族尋開心。到了唐代,小說無論是數量還是藝術水準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不再是一種街頭巷議,而是有意為之的一種文體。但是落到實處,唐人對待小說創作的態度,如同韓愈在《答張籍書》中自述的:“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5](P29)到了宋代,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繁榮,城鄉民眾娛樂需要的不斷發展,直接促進白話小說走向繁榮興盛。在宋詞中經常看到對市民爭聽俗講、說話情景的描述。
20世紀初,梁啟超在著名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中,開宗明義:“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6](P408),將傳統觀念中作為“末技”、“小道”的小說提到“治國安邦”的高度,這無疑是對傳統小說觀念的一個強勁的挑戰與沖擊。顯然,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賽珍珠對自明以后的小說功用觀念的轉變沒有正確的認識。這也是導致從總體上來說,她的大量中國題材作品思想藝術價值并不太高的原因之所在。
賽珍珠的家庭教師儒家文人孔先生曾經這樣教導她:“小說是為了娛樂那些游手好閑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而寫的,換句話就是說,小說為那些沒有道德和哲學知識,而且不懂得欣賞真正的文學的人而寫。”[7](P30)孔先生的這一番話自然會對處于觀念思想正在形成階段的賽珍珠產生影響,但是她仍然背著孔先生閱讀了大量中國通俗小說。在中國小說民間性和通俗性傳統的長期熏陶下,賽珍珠得出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在反映中國百姓的生活上,小說令哲學家的空洞文字望塵莫及。所以賽珍珠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否定提出了批評,對“五四”以后小說受到重視卻表示了由衷地贊揚,而她對胡適、魯迅等人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為中國小說所作的辯護。作為一位西方作家,她能從多元文化融合角度出發,不遺余力地以畢生的跨文化創作實踐,身體力行地繼承著中國的小說傳統,特別是與同時期的大部分中國現代作家主張全面西化,基本上摒棄中國傳統小說的形式和創作方法,采用西方小說的形式與創作方法相比,更可見出賽珍珠對中國文化的走向獨立思考的可貴。
二、小說內容
賽珍珠認為,中國小說扎根于人民,為了滿足平民需要而作的目的,使得中國小說的內容“凡是構成人們生活的無所不寫,不論是上層人的生活還是下層人的生活”[2](P963)。在中英小說的對比中,賽珍珠指出:“英國小說是以比較新鮮的形式寫出來的,而中國小說是人們寫了一次又一次,并且一次比一次長的情形下,先通過口頭流傳,然后寫成短篇的文字,最后才以加上了許多這樣那樣的內容的小說形式出現。”[1](P197)中國幾乎沒有一部獨立的小說巨著,它們大多是史書記載和說書人口中的朝廷更迭的故事的進一步發展,“最開始它們只是支離破碎的拼湊,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作者開始關注這些故事中某個具有中心環節作用的人物,并形成某種統一”[1](P197)。可以說,賽珍珠是比較清醒地認識到了中國小說過多依賴原始材料,因而缺乏獨創性的狀況的。同時,賽珍珠通過中英小說的比照,對中國小說缺乏獨創性的特點表現出了非常開放的包容態度:“西方,對獨創力進行大加褒揚的明確的準則,至少是自從小說誕生以來就確立了的,……,可是我們換個角度想想,我們的傳統不是中國的傳統,在中國如果照搬另一作品的格式或情節就是對那一作品的一種肯定和贊賞,幾百年以來,模仿和照搬優秀古典作品和倫理故事的內容其實也有其特殊的原因。”[1](P199)
在《中國早期小說源流》中,賽珍珠對中國小說忠于生活程度較高的原因作了很精辟的分析,她認為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不署名為小說家創造了良機,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揭示自身境遇和表達對于生活的激情。“學者們遇上無法向他人傾訴的傷心事時,就用化名寫個故事,排遣一下自己心頭的憂傷”[1](P211);再者是因為“大多數小說和故事至少從宋朝開始幾乎已經都用白話或市井語言寫成”[1](P212),這有利于小說在民間的流行和閱讀群體的擴大。作為一個西方人,對中國小說特點的認識能如此深刻,實屬不易。
三、小說的創作技巧
賽珍珠對中國小說創作技巧的歸納主要從小說的形式與結構、小說語言、寫人藝術以及敘事藝術等四個方面展開。
在《東方、西方及其小說》中,文章第二部分通過對中英小說結構與形式的比較研究,發現與在結構上具有整體性和注意整個故事情節的形式和相互銜接的英國小說不同,中國小說卻是“不僅僅沒有高潮也沒有結局。有時甚至連一個主要的情景都沒有。”[1](P200)對于這樣的結構技巧,西方評論家通常是看不明白的甚至是加以否定的。與西方小說所有情節幾乎都能用筆在紙上圖示出來不同,中國小說基本上是無法圖示的。然而正是這種在西方評論家眼里的缺憾,賽珍珠卻認為是優點。“首先,這種無格式的情形與生活有極大的相似性。生活中本來就無所謂主要情節與次要情節之分。”[1](P200)在賽珍珠眼里,中國的小說結構實際上也是中國人生活情形的真實體現。“隨著一個事件的發生與結束,人們登上舞臺,又退場,他們可能還會回來,也許永不再相見”[1](P200),從這句略帶中國哲學藝術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賽珍珠對中國小說結構的推崇。在小說的創作、構思、形式、風格等問題上,賽珍珠認為要“自然”形成,不能有意而為之。她認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或者說在中國,人們是這樣教給我的—最重要的應該是‘自然’,就是絲毫不矯揉造作,非常靈活多變,完全聽憑流過他大腦的素材的支配。他的全部責任只是把他想到的生活加以整理,在時間、空間和事件的片斷中,找出本質的內在的順序、節奏和形式。”[2](P964)其次,賽珍珠認為沒有結局的小說可以延伸讀者的思考空間,“一個人一旦習慣了中國小說的結構形式,那么閱讀西方小說對于他來說,就像是吃一種易消化的食物。”[1](P201)這句話中分明包含了賽珍珠自己鮮明的價值判斷。在演講接下來的部分,賽珍珠并沒有對中國小說的形式特征作進一步的羅列和說明,甚至幾乎沒有提及中國小說具體的創作方法,而是轉向她所熟悉的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心態。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賽珍珠雖然長期生活在中國,飽讀傳統經典,但是她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認識其實還是處于感性階段,并沒有能力真正從整體上去把握它。
對于中國小說語言的流變,賽珍珠也有自己獨到的分析。在《東方、西方及其小說》中,賽珍珠提出:“最早的小說就是用文言寫的”[1](P202),原因在于當時文言文就是口語,在普通大眾文化水平不高的情況下,讀書人成為了小說最主要的消費群體,而文言文是當時所有讀書人都能看懂的語言。在《中國小說》中,賽珍珠直接提出,真正的小說語言是普通人自己的語言,“中國的小說是用‘白話’寫的。或者說是用人們平常說的話寫的,……,而文人說這其中沒有任何表現技巧。”[2](P960)由此可見,對于中國小說的家常語言、通俗流暢、清晰易懂的風格傾向,賽珍珠是非常欣賞的。
在中國小說傳統里崛起的賽珍珠,對于中國小說特長之一的描寫人物,自然有深刻的領悟。在《中國小說》中,她認為,中國人“對小說的要求一向是人物高于一切。”[2](P961-962)賽珍珠曾經花差不多四年的時間翻譯了《水滸傳》,這本書讓她受益匪淺,“《水滸傳》被認為是中國最偉大的三部小說之一,原因并不在于它充滿了刀光劍影的情節,而是因為它生動地描繪了各不相同,每個人都有其獨特之處的一百零八個人物。”[2](P962)。通過人物的行動和語言來塑造人物性格,在動態中凸現人物形象,這正是中國小說塑造人物的看家本領和傳統習慣。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小說向來注重對人物內心的開掘,注重人物心理的細致分析,而賽珍珠本人也有過大學期間攻讀心理學并且在碩士畢業后留校教授心理學課程的經歷,雖然她有足夠的心理學知識展示在小說的人物創作中,但是她最多偶爾為之,也像中國小說家一樣在塑造人物時,注重的是人物的動作、語言,寫作手法多采取客觀敘述。
《水滸傳》和《紅樓夢》無疑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最為成功的中國古典小說。在沒有看到《紅樓夢》問世的金圣嘆看來,《水滸傳》的寫人藝術是當時任何一部小說都無法企及的。“而金圣嘆對于《水滸傳》寫人藝術的評價,也達到了中國古代小說批評在這一問題上的最高水準,大致概括為以下五個方面:人物形象的高度個性化;人物的語言、行為與性格之關系;用對比、襯托突出人物個性;典型人物的真實性;對人物塑造理論的深層認識。”[8](P77)金圣嘆在《水滸傳序三》中說:“《水滸》所言,一百八人,人各有其性情,各有其氣質,各有其形狀,各有其聲口。”[9](P213)他認為,在《水滸傳》中,梁山一百零八將,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個性。在這一點上,賽珍珠與金圣嘆是不謀而合的。在《中國早期小說源流》中,賽珍珠指出:“另一方面,人物形象塑造常常是一流的。一個詞,輕輕一筆,舉手投足之間,人物就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水滸傳》尤其是這樣。”[1](P223)中國古典小說在人物塑造上的特點,即通過人物的行動和語言來描寫人物性格,在動態中塑造人物形象。《水滸傳》自然也不例外。《水滸傳》中眾多成功的人物形象,都是通過人物的語言動作來塑造。這些從金圣嘆對其評點中可以看出。第二回中魯達對于迫于鄭屠淫威不放金翠蓮父女離去的店小二,“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落兩個當門牙齒。”[8](P81)對此,金圣嘆有一段眉批:“一路魯達文中皆用只一掌、只一拳、只一腳,寫魯達闊綽,打人亦打得闊綽。”[8](P81)而金圣嘆對于幾位好漢初見宋江所說的第一句話的評點,更是精妙:對魯達“活是魯達語,八字哭笑都有”[8](P83),對楊志“寫楊志便有舊家子弟體,便有官體,一發襯出魯達直遂闊大來”[8](P83),對李逵“稱呼不類,表表獨奇”、“卻反責之,妙絕妙絕”[8](P83)。通過金圣嘆的評點,將魯智深的古道俠腸、楊志的圓滑世故、李逵的粗莽可愛活脫脫地勾勒在讀者眼前。
賽珍珠所注意到的中國小說在人物塑造上的重要特點在金圣嘆的評點中基本上都得以體現。賽珍珠也認為人物描繪的生動逼真作為中國人對小說質量的第一要求,但這種描繪不是靠作者進行解釋,而是由人物的行為和語言來實現的。與西方小說向來注重對人物內心的開掘不同,“在描寫故事時,中俄小說作家都不喜歡西歐長篇小說中所彌漫的那種主觀性。雖然也有一些精彩的心理描寫,但是想讓作者由此再往前一步,深入挖掘一下自己的心理學知識,無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10](P244)。具有豐富西方文學知識同時又熟諳西方小說寫作技巧的賽珍珠,還有過曾經教授心理學的教學實踐,但是她接受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在中國小說里,人物的內心世界通常通過行動、語言等外在的形態來體現。
對于《水滸傳》的敘事藝術,金圣嘆也進行了頗為全面的總結。他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說:“《水滸傳》有許多文法,非他書所曾有”[9](P223),并且列舉了十五條“文法”,其中有十三條是關于敘事方法的。以“極不省法”與“極省法”為例。所謂“極不省”,就是對與中心故事相關的內容交代得比較詳細。“如要寫宋江犯罪,卻先寫招文袋金子,卻又先寫閻婆惜和張三有事,卻又先寫宋江討閻婆惜,卻又先寫宋江舍棺材等”[8](P94)。而所謂“極省”,就是對一些讀者可以理解并且無關緊要的次要情節進行最簡單的處理。“如武松迎入陽谷縣,恰遇武大也搬來,正好撞著;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魚湯后,連日破腹等是也”[8](P94)。金圣嘆對于《水滸傳》作者這種根據故事情節發展需要而決定詳略安排的手法是表示肯定的,但是賽珍珠對于這樣的敘事手法并不認同。在《中國早期小說源流》中,她直接指出,“這三部長篇(《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主要的弱點在情節方面。情節特別復雜,還有很多次要的情節處理得很槽糕。……,有時是一片混亂。”[1](P222)《水滸傳》在情節描寫方面,大都是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特點,金圣嘆是認識得很深刻的。他在第九回對店家李小二眼中事的批語:“是李小二眼中事”,“一個小二看來是軍官,一個小二看來是走卒,先看他跟著,卻又看他一齊坐下,寫得狐疑之極,妙妙。”[8](P97)與英語小說中的視角較為豐富不同,“在中國小說中,作者總是無所不知的。他們甚至可以被忽略。而故事就像是在我們面前的顯微鏡下進行的。”[1](P20)賽珍珠對中國傳統小說大多采用全知視角是非常推崇的,她的《大地三部曲》就是襲用了這種手法。當然,賽珍珠提出的視角概念是比較籠統的,她指的其實就是傳統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而并沒有進一步細分第三人稱全知視角與第三人稱限知視角的區別。在寫作實踐中,賽珍珠也沒有一直采用中國傳統白話小說中常用的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當具體寫作過程中出現與西方文化有關的現象時,賽珍珠在立足于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的同時,又會有選擇地向第三人稱限知視角轉移,從而產生“陌生化”的藝術效果,形象地再現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差異。毋庸置疑,賽珍珠這種反東方主義的敘述特征使她在能夠比較客觀地反映中國人民的思想情感的同時,也比較容易獲得西方讀者的認同和接受。
綜上所述,賽珍珠對中國小說特點的認識的確不乏偏頗之處,特別是與李贄、金圣嘆等眾多小說批評理論大家相比,可以說她對后者在小說批評理論中所表現出來的敏銳眼光和深刻思想是望塵莫及的。但是作為小說家,賽珍珠對中國小說的把握卻有獨到之處,比較全面、系統地概括了中國小說的本質,從而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小說觀:有著悠久發展歷史的中國小說,在它自己的國度里向來地位不高,中國小說主要是為了滿足平民的審美趣味而創作的;中國小說的功能決定了其內容也是反映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國小說主要采用“生活化”的結構,運用白描手法、普通人的語言以及全知視角。
[1]姚君偉.文化相對主義:賽珍珠的中西文化觀[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1.
[2]〔美〕賽珍珠.大地三部曲[M].王逢振,等譯.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插圖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清〕黃宗羲.明儒學案(第三十二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王汝梅,張羽.中國小說理論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
[6]郭紹虞,等.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美〕賽珍珠.我的中國世界[M].尚營林,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
[8]石麟.中國古代小說批評概說[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9]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匯編[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10]林語堂.中國人[M].郝志赤,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晏亮(1982-),女,碩士,湖北師范學院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