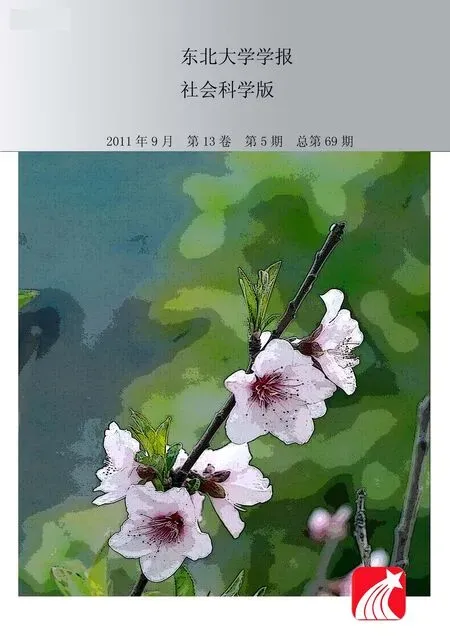一部認真的社會喜劇
----王爾德在《認真的重要》中對傳統的顛覆與重建
曲 彬,尹 丹
(東北大學外國語學院,遼寧沈陽 110819)
生活在英國維多利亞王朝末期的王爾德在他的批評文章和作品中不斷闡述和詮釋著他的藝術主張,并用自己的一生將其充分演繹,成為19世紀末那場唯美主義運動的主將。從他1900年去世到本世紀初這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國內外的學者對王爾德的研究不斷在廣度和深度上得以發展,研究方法不斷豐富。這使得對于王爾德及其推崇的唯美主義的研究更趨于客觀和辯證,減少了對唯美主義的認識偏見,使人們能夠將王爾德和他的唯美主義思想放在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加以研究,體會出王爾德思想的積極意義和價值所在。
王爾德“為藝術而藝術”,藝術高于現實與自然,藝術與道德無關的美學觀點以及他推崇的新享樂主義生活哲學究其本質都是對于現實中虛偽庸俗的社會道德秩序的一種顛覆,是對立于社會主流文化而建立起來的一種話語體系。王爾德在他的《來自深淵》中說過:“我曾經是我這個時代藝術文化的象征”[1]118,“我生來就是一個離經叛道的人,是個標新立異、而非循規蹈矩的人”[1]122。作為唯美主義藝術化的個人,浪蕩子的形象總是以他們的奇裝異服、不凡的談吐和享樂主義的生活態度在王爾德的作品中出場,尤其是在他的最后一部社會喜劇《認真的重要》里,王爾德更是打造了一個純粹浪蕩子的世界。本文將深入探討這部喜劇中王爾德如何在這個浪蕩子的世界里從多方面實現他對虛偽荒謬的傳統道德觀念的顛覆,以及透過劇中浪蕩子角色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情實意來感受作者構建理想道德秩序的渴望,體會這位世紀末的浪蕩子身上可貴的人文主義精神。
一、維多利亞王朝晚期的英國社會和王爾德的浪蕩子世界
《認真的重要》是王爾德最后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社會喜劇。表面上看,這部喜劇沿襲了傳統文學中的婚姻家庭的主題,演出了一場上流社會紳士淑女的愛情鬧劇以達到娛樂觀眾的效果,但這部喜劇真正的價值在于他借助一群浪蕩子形象對上流社會假模假樣的認真和嚴苛不合實際的道德觀、婚姻觀、宗教觀等諸多社會方面的嘲笑和批判。想要深刻地理解漫畫般滑稽表演背后的批判價值和一個純粹浪蕩子世界的顛覆意義,我們須要對維多利亞王朝晚期的英國社會和王爾德傾力構筑的浪蕩子世界首先作以分析。
王爾德進行創作的19世紀八九十年代正處于維多利亞統治的末期,隨著科學技術領域不斷有突破性的進步,英國不僅完成了工業革命,使機器生產取得了絕對優勢的地位,而且整個社會形態也迅速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商業精神隨之確立。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西方文化傳統出現了斷層。隨著尼采發出“上帝已死”的吶喊,基督教信仰在人們的心目中已經動搖,人的獨立自主的自我觀念不復存在,人不再是一個固定的實體,而是被各種外在的力量所異化了。而作為對資產階級經濟迅猛發展的應激反應,上流社會的貴族和精英階層變得更加保守。這時,“資產階級所占據的社會生活實際中的強勢與貴族和精英階層所占據的輿論上的強勢產生了分離,于是就出現了行為上對原有道德體系普遍背離,而輿論中卻對原有道德體系高調堅持的奇怪局面”[2]。顯然,這種高調的堅持既不符合現實,也無法讓人信服,人們的精神世界孤寂空虛,有如一片荒原。
面對著這樣一個嚴苛的社會現實,面對著人類即將失去精神家園的焦慮,作為社會精英藝術家的王爾德更是從自己獨特的角度,感到了這“世紀末的悲哀”。王爾德因為他特殊的身份和經歷,比一般人遭受著更嚴重的身份危機。相對于當時的主流社會來說,王爾德一直處在一種邊緣的社會地位,對于“我是誰”這樣的問題有著更多的困惑。“他一方面扮演著英國上層社會的文化精英,宣揚風靡一時的美學思想,寫出令倫敦上流社會大為贊賞的喜劇,成為當時的權貴們紛紛巴結的明星;但在另一方面,作為一個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的兒子,他身負母親無形中給予他的民族情緒,對愛爾蘭被鄰國統治的屈辱歷史耿耿于懷。加之他在壯年時又陷身于同性戀的地下世界”[3]16-17,所以對于王爾德來說,他一直體會著一個社會邊緣文化體中的個體對自我身份確認的強烈渴望。
在尋找自我、建構自我的過程中,王爾德在19世紀中葉開始的以“為藝術而藝術”為口號的唯美主義運動中找到了與自己的契合點,將藝術作為重塑自我的載體。“……在王爾德心目中,為藝術而藝術的信條還意味著更多的涵義,即對‘自我’的重建,用他的術語說就是人們通過藝術實現自我,強化自己的個性。藝術因而成為誕生主體性的新的現實。”[4]王爾德不僅倡導唯美主義的藝術自律,形式高于一切,藝術超越生活,游離于自然之外,與道德無關,以及推崇抓住每一個瞬間來獲取感官的享受,更為重要的是,他提出“生活模仿藝術”,以自身的實踐將生活藝術化,把唯美主義奉為宗教信仰頂禮膜拜,將唯美主義運動推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樣做是因為“在我們變得高尚起來之前,它必須融合到人的本能之中,克己只不過是人們阻礙自身進步的一種方法。自我犧牲是野蠻民族自殘行為的剩余部分,是對痛苦古老的頂禮膜拜的一部分,這種行為是世界歷史的一個可怕事件”[5]。在王爾德唯美主義的主體建構中有一個代表了唯美主義特征的可以稱為唯美主義藝術化了的人物形象,這就是一個浪蕩子的形象。浪蕩子實踐著唯美主義的各種理想。王爾德本人就是19世紀末最著名的浪蕩子。王爾德總是穿著設計獨特的天鵝絨禮服,手里拿著一朵象征美的向日葵或者百合花,穿梭于倫敦的街頭;同時這位牛津才子的妙語連珠、機智詼諧的悖論更是他用以彰顯個性、炫耀自我的特長。他的新享樂主義生活態度讓我們看到了浪蕩子訴諸感性,以及對瞬間感受強烈體驗的追求。這種對形式、對感官、對變化的體驗的推崇正是唯美主義浪蕩子重塑自我、反抗社會習見的方式。“要有一種新享樂主義來再造生活,使它掙脫不知怎地如今又出現的那種苛刻的、不合時宜的清教主義。”[6]于是我們在王爾德的作品中看到了浪蕩子以玩世不恭對抗盛行于維多利亞社會的假正經,以無所事事嘲笑上中層社會中的唯利是圖,以感官的享樂來諷刺不合時宜的清規戒律。“他們這種反叛的力量之所以強大,正是因為他們自身也處在這種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之中。這其實也就是王爾德自身生活一個寫照。”[7]《認真的重要》這部喜劇呈現給我們的就是這樣一個完全由浪蕩子構成的世界。
二、對婚姻家庭、宗教和教育傳統的顛覆
從《溫德米爾夫人的扇子》中的達林頓勛爵、《一個無足輕重的女人》中的伊靈沃斯勛爵,再到《一個理想的丈夫》中的戈林子爵,王爾德越來越成功地塑造出一個個浪蕩子的形象,他們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機智妙語給予中產階級的庸俗虛偽痛快淋漓的諷刺,與劇中唯利是圖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物質主義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這些浪蕩子就是王爾德用來顛覆傳統道德的有力武器。這里的浪蕩子(Dandy)并不是指花花公子、紈绔子弟,而是指游離于主流社會之外的非常重要的文化先鋒。他們拒斥資產階級的主流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反抗資產階級工具理性和現代性,具有相當的思想修養和藝術追求[3]37。到了第四部喜劇《認真的重要》,王爾德創造了一個純粹浪蕩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所有人物,不分主次,無論男女都過著浪蕩子的生活。劇情圍繞兩對貴族男女的戀愛過程展開,這是一個很老套的主題,有趣的是,兩位貴族小姐格溫多琳和賽茜麗追求的都是一個名叫“哦拿實的”(Ernest)的愛人。“哦拿實的”具有“認真”的意思,對于她們來講,名字比什么都重要,她們追求的就是嫁給一個有這樣動聽名字的人,這就是她們的倫理標準。杰克與愛爾杰龍是劇中的兩位男主人公,杰克是受人尊敬的鄉紳,他杜撰了一個城里的叫“哦拿實的”的弟弟,為的是可以隨時到城里去玩樂,而在城里,他化名“哦拿實的”,常到朋友愛爾杰龍的寓所消磨時光。而這個愛爾杰龍謊稱在鄉下有一個叫“病不理”(Bunbury)的病人,目的是能時常去鄉間游玩,與杰克的謊言有異曲同工之妙。當格溫多琳在愛爾杰龍的府上與杰克相遇,事先并不認識杰克的格溫多琳聽表兄愛爾杰龍說他就是那個叫“哦拿實的”的朋友時,便愛上了他。“我的理想一直就是愛上一個名叫哦拿實的的人。這個名字有某種激勵人充滿信心的東西。一聽愛爾杰龍說他有個名字叫哦拿實的的朋友,我就知道我注定會愛上你的。”[8]366一直暗戀著格溫多琳的杰克擔心她如果知道自己并不叫哦拿實的,會結束和自己的感情,便隱晦地詢問假如自己不叫這個名字,她是否還會一如既往地愛他。格溫多琳堅持表達了自己不可能喜歡是別的名字的人,并說為那些沒有嫁給“哦拿實的”的女人感到遺憾。愛爾杰龍趁杰克不在假扮他虛擬的弟弟哦拿實的來到鄉下結識被杰克監護的女孩賽茜麗時,也發生了和杰克同樣的遭遇。王爾德更是有意地將兩位女主人公對名字的看重用一模一樣的句子表達出來,進一步加強了其中的諷刺效果,暴露出維多利亞人注重外表和形式的虛偽面目。
除了這兩對男女主人公外,劇中還有一個重要人物格溫多琳的母親布雷克耐爾太太。她在兩對戀人的婚姻問題上均設置了障礙。首先,她對杰克的方方面面進行細致的盤問,其取向的庸俗虛榮本質顯而易見。最終她發現杰克沒有一個體面的家庭出身而拒絕同意他們的婚事。她不能讓自己唯一的女兒下嫁到“一個行李寄存處,和一個手提包締結一門婚姻”[8]370。原來杰克從小就被人遺棄在火車站的手提箱里。布雷克耐爾太太告訴杰克除非他能盡快地為自己找個父母,至于通過什么樣的方式,那根本不重要。對于布雷克耐爾太太來說,體面的形式是最關鍵的。在她的侄子愛爾杰龍和賽茜麗的婚姻上,當她得知賽茜麗是擁有13萬英鎊公債的債權人時,立刻改變了立場,同意了她們的婚事。更可笑的是,她還為自己對金錢的追求一本正經地予以辯解。她告訴賽茜麗,“……愛爾杰龍一文不名,只會欠債。但是我不贊成唯利是圖的婚姻。我和布雷克耐爾結婚時,也沒有任何錢財。但是我從來沒有讓這個擋住我的路”[8]409。
通過布雷克耐爾太太的夸張形象,王爾德無情地揭露了維多利亞時代以金錢和出身為標準的婚姻概念;同時,當時的教育和宗教狀況也被王爾德拿到劇中用諷刺的否定性目光加以審視。賽茜麗在她的家庭教師普利茨莫小姐的監護下,只能閱讀那些枯燥的、保守的、缺乏想象力的書籍,這些書籍被認為是最適宜用來教育年輕人的。而如果任由賽茜麗的想象力不加限制地發揮,將是這個社會不可接受的。在維多利亞上層社會的思想意識中,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讓年輕人不要發問,不要對現存的社會體系提出異議。這一點同樣也借助布雷克耐爾太太表達出來。她在盤問杰克的過程中說道:“現代教育的整個理論是極端地不正確的。幸運的是在英國,不管怎么說,教育沒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它真的有了效果,將對上層階級造成嚴重的威脅,而且很可能會導致格羅夫納廣場上的暴力事件。”[8]368看來,英國的教育就是要穩固社會上層的統治,扼殺人們變革的思想和念頭。對社會未來至關重要的教育,正是由于其腐敗的性質令布雷克耐爾太太口中的話既顯得可笑,又是那樣的真實,其諷刺意義不言而喻。
前文提到,在維多利亞王朝晚期的英國,宗教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人們對基督教信仰已經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基督教的沒落和腐敗加之維多利亞上流社會對宗教信念的嚴苛要求必然導致人們對它的褻瀆。這一點在《認真的重要》里面也明顯地體現出來,成為王爾德嘲弄的主要對象之一。兩位男主人公杰克和愛爾杰龍由于都不叫“哦拿實的”而在他們追求愛情的過程中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因為謊言終將敗露,格溫多琳與賽茜麗在杰克鄉下的宅邸相遇,以為愛上了同一個叫“哦拿實的”的人,而杰克與愛爾杰龍此時的不期而遇令他們杜撰假名字的一幕無奈收場。兩個人都想出了同一個荒謬的辦法,就是找牧師為他們重新洗禮而獲得“哦拿實的”這個名字。基督教洗禮本是在孩子身上進行的嚴肅的宗教儀式,卻被兩個浪蕩子變成了隨隨便便的事情。更令人吃驚的是,作為神職人員的牧師對此也樂此不疲。他不僅對教民的布道稀松平常,而且洗禮儀式也可以隨時進行,一切皆可依據上層階級的要求隨心而為。就連這位牧師自己的生活也充滿了對宗教的不敬,他雖然表面上遵循著一個牧師的清規戒律,卻難掩對普利茨莫小姐的愛欲。劇中人物對待宗教極不嚴肅甚至令觀眾恥笑的態度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宗教觀念的虛偽和作態。劇中的浪蕩子們用反諷和夸張的方式把維多利亞人假模假樣的“認真”態度和實質上對宗教的不敬表現得淋漓盡致。
劇中的浪蕩子用隨心所欲的行為和言語無情地撕開了上流社會的虛偽面紗,暴露出諸如布雷克耐爾太太的這些上流人物庸俗和唯利是圖的本質。劇中的幾乎每一處情節、每一段對話都無不滲透著王爾德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婚姻、家庭以及階級矛盾等諸多方面的批判,構成了對維多利亞傳統有力的顛覆。
三、 對建立理想道德秩序的渴望
王爾德稱以藝術來構建生活,希望用藝術的世界構筑起一個新的自我,以反抗工業現代化和商業文明對自我身份的剝奪。他在劇中建立起來的浪蕩子的世界就是這種自我構建的一種實踐。就像王爾德在他的新享樂主義理論中所倡導的那樣,這些浪蕩子不僅用精致的外表找到對自我的感覺,而且用無所事事的生活和對不斷的感官享受的強調確認自己的存在感,來達到顛覆社會習俗和重建自我的目的。這部喜劇看上去確實是摒棄道德判斷而只為享受生活的一群浪蕩子上演的一場鬧劇,愛爾杰龍總是在大嚼黃瓜三明治的場景令每個觀眾和讀者印象深刻,這種強調感官體驗的唯美主義觀點在王爾德的藝術理論中也是被清晰闡明的。可是王爾德可能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在他的這部喜劇里,在他構建一個浪蕩子的世界以顛覆社會傳統的同時,也寄予了對建立理想倫理道德秩序的渴望[9]。
當兩位女主人公在杰克的鄉間宅邸得知她們雙雙受到了欺騙,她們所愛的人并非真的叫“哦拿實的”的時候,她們沒有讓這段感情結束,而都將其理解為出于對方追求自己的真情實意。對于被欺騙的事實,賽茜麗和格溫多琳本想裝出高傲冷漠的態度,卻終于抑制不住內心的強烈感情對她們的愛人訴說埋怨,言語中透出更多的寬容與愛意。
賽茜麗:…… 蒙克里夫先生,請您回答我的問題。為什么你假扮成我監護人的弟弟?
愛爾杰龍:為了我能有機會見到你。
賽茜麗:那看起來確實是個令人滿意的解釋,不是嗎?
……
格溫多琳:…… 沃辛先生,你怎么向我解釋你假裝有個弟弟的事?是為了你能盡可能多地到城里來看我嗎?
杰克:你能懷疑這一點嗎,費爾法克斯小姐?
格溫多琳:…… 他們的解釋看起來很令人滿意,尤其是沃辛先生的。在我看來他說的是真的[8]406。
的確,兩位女主人公在她們的愛情發展遭遇困境時沒有輕易放棄,而是為對方的謊言找到善意的理由。而兩位男主角也最終是為了贏得心中的愛情用“哦拿實的”這個名字來迎合兩位女主人公,甚至在后來想要通過重新受洗的方式來達成擁有一個“哦拿實的”的名字的目的。劇中的諸多細節都讓我們體會到兩對戀人對感情的執著和認真。這不能不說是王爾德在刻意刻畫兩對男女主人公兒戲生活和愛慕虛榮的態度時對他們內心的認真態度的肯定和對愛情倫理理想的渴望。
情節在最后一幕又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杰克的鄉間宅邸,布雷克耐爾太太認出了失蹤多年的仆人普利茨莫,原來她當年將布雷克耐爾妹妹的兒子放在手提包里遺落在火車站的行李寄存處,之后便因為恐懼自己的罪過再也沒有回來。杰克拿出了那個手提包,結果證實他就是布雷克耐爾妹妹的兒子、愛爾杰龍的哥哥,而他們曾是將軍的父親的名字就叫“哦拿實的”,本來徹頭徹尾的謊言現在卻變成了確確實實的現實!王爾德以這樣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尾給予這個喜劇一個圓滿的收場。這里不能不說寄予了王爾德對理想社會的美好愿望。杰克的最后一句“我平生第一次意識到哦拿實的的重要”[8]419在王爾德的筆下完全可以理解為又一個雙關語:擁有“哦拿實的”的名字重要,真正的認真態度更為重要;沒有追求愛情的認真和誠意,恐怕劇中的主人公們也不會有最后的完美結局。
王爾德畢其一生的精力來構筑唯美主義的藝術理想,在他的最后這部喜劇《認真的重要》里成功地塑造了充分體現他的美學思想的浪蕩子世界。不可否認在這個過程中有對感官享樂的過分追求。但畢竟,王爾德根本上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他“是以人文主義者的身份開始他的知識分子生涯的”[10]。他作為藝術家最本質的訴求是尊重人的尊嚴,給予人應有的意志自由,實現人的自我發展以謀求人類更大的幸福。今天,我們也正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商品經濟大發展,而對于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文明體系的建設還尚處探索階段。此時我們更能體會到王爾德對物質財富充斥下人類精神世界的關照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因為這關系著人類是否能找到心靈的歸宿而遠離荒原。
參考文獻:
[1] 奧斯卡·王爾德. 來自深淵[M]∥趙武平. 王爾德全集:第6卷. 常紹民,沈弘,譯. 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 2000.
[2] 吳剛. 王爾德文藝理論研究[M].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9:80.
[3] 李元. 唯美主義的浪蕩子----奧斯卡·王爾德研究[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8.
[4] 周小儀. 奧斯卡·王爾德:十九世紀末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理論[J]. 國外文學, 1994(2):24.
[5] 奧斯卡·王爾德. 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M]∥趙武平. 王爾德全集:第4卷. 楊東霞,楊烈,譯. 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 2000:405-406.
[6] 奧斯卡·王爾德. 道連·葛雷的畫像[M]∥趙武平. 王爾德全集:第1卷. 榮如德,巴金,譯. 北京:中國文學出版社, 2000:84.
[7] 陳莉莎,姚佩芝. 王爾德人文主義思想的顛覆性[J]. 外國文學研究, 2010(1):108.
[8] Wilde O.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M]∥Holland M.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 5th ed.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3.
[9] 劉茂生. 王爾德創作的倫理思想研究[M]. 武漢: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142.
[10] Bashford B. Oscar Wilde: The Critic as Humanist[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