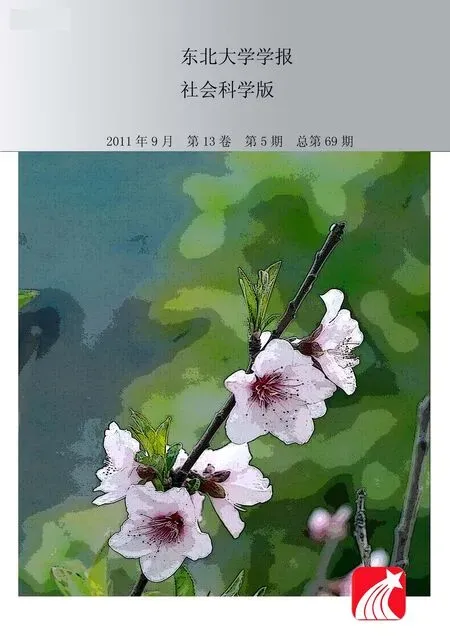物的淪喪與拯救
----鮑爾格曼設備范式與焦點物思想探析
顧世春,文成偉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遼寧大連 116024)
阿爾伯特·鮑爾格曼(Albert Borgmann,1937-)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現象學技術哲學家,是當代技術哲學本質主義的主要代表。他把技術哲學“從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的討論推向一般倫理—政治的分析乃至包括日常實踐的具體建議”[1]。設備范式與焦點物思想是鮑爾格曼技術哲學的內核,是其技術哲學區別于其他技術哲學的重要標志。本文將以物為切入點和視角深入探討鮑爾格曼設備范式與焦點物思想。
一、 物
通常,我們從認識論的角度看,認為物是與人相對的東西,是外在于人的對象,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但是,海德格爾認為用這種對象化的方式看待物,物性就會被遮蔽和遺忘,物就會喪失,因為“物之物性因素既不在于它是被表象的對象,根本上也不能從對象之對象性的角度來加以規定”[2]。要想真正地把握物,必須跳出這種認識論的二元對立,直接進入事物本身,從存在論的層面探討物。海德格爾從存在論考察了物,認為物是一種“容器”,是物所逗留的世界中“天、地、神、人”各要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的聚集和反映。鮑爾格曼繼承了海德格爾關于物的思想,走出認識論的藩籬,從存在論的角度審視物。他指出,物“和它的與境(context),即它的世界,不可分,也和我們與該物及其世界的交往,即參與(engagement),不可分”[3]41。
物會聚了一個有機世界,并喚起人參與其中,人在親身參與的過程中體認這個世界。例如,在前技術時代,火爐是一物,它會聚了全家人的工作和休閑,并作為一個權威的在場,分配不同的任務給家庭成員,父親砍柴,母親生火,孩子添柴。在這些親身參與的活動中,人們體驗到了季節的變化、寒冷的威脅、溫暖的慰藉、木材的煙味和勞動的辛苦;在這些親身參與活動中,人們堅守著自己的職責和進行著技能傳授。這些親身參與和家庭關系的特點是物的世界的初步展現。這些參與行為并不只是簡單的身體活動,人通過身體多方面的感受,獲得了關于世界的豐富經驗。這種身體的感受在技藝中得到了提高和加強。技藝又與各種社會性行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由于每個人的技藝都是有限的,每個人對世界的參與都被限制在一個相對狹小的范圍。在其他的領域里,人通過對從業者的典型行為和習慣的了解來協調自己的行為和習慣。這種了解又通過對其他領域從業者產品的使用而不斷得到強化。“在這些社會活動更廣闊的地平線上我們能夠看到文化和世界的自然尺度是如何展現的。”[3]42存在論意義上的物奠定了鮑爾格曼設備范式與焦點物思想的基礎,成為其批判設備范式、構建焦點實踐的前提和基礎。
二、 設備范式與物的淪喪
隨著從前技術時代向現代技術時代的轉變,生活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現代生活被打上了深刻的技術烙印。根據現代生活與前技術時代的根本不同,鮑爾格曼提出設備范式(device paradigm)概念。設備范式是指現代社會人在追求可用性共同信念的指引下,根據可用性法則,決定自已的行為活動和生活方式。它是現代生活的特征。
在設備范式的作用下,技術成為現代人對待現實典型和統治性的方式,它最為具體和鮮明地體現在設備,如電視機、中央供暖系統、發電廠、汽車等。設備范式威脅和破壞處于生活中心地位的物,把它們分裂為手段和目的,使其喪失深刻性和完整性,淪喪為設備。“鮑爾格曼使用設備范式概念強調物不斷地向設備轉化和隨之而來的生活與社會的技術化。”[4]
在前技術時代,人與之交往的是物,而不是設備。設備包括機械(machinery)和用品(commodity)兩部分。機械是提供可用性,實現設備功能的手段。用品是設備的功能或目的。“一設備的用品就是‘一設備之為何’。”[3]42在前技術時代,在與物的交往即親身參與活動中人體認了物所會聚的全面的生活世界,同時也付出了辛勞等。現時代,在設備范式的作用下人只追求可用性,沉緬于用品的消費中,將原本構成物的世界所必需的其他要素,如參與的辛勞,都視為一種負擔,并利用設備把這些負擔一一克服。具體地說,設備中的機械取代了人對現實的參與,接管了人參與活動中的負擔,而且對人的技能不作要求。例如,在現代供暖技術系統中,人不再需要劈柴、運柴、生火和添柴,不再需要忍受煙味和承擔火災的危險,也不再需要什么技能。與此同時,設備為人提供了即時出現的、到處存在的、安全的和容易獲得的用品。例如,供暖技術系統向人們提供的暖氣就是這樣的用品。設備的機械在取代人對現實的參與和接管人的負擔的時候,也接管了人與世界的關系。機械具有遮蔽和縮減人與世界關系的特性,人與世界的關系因此被隱藏和縮減了。同時,設備的用品是在沒有對任何具體與境的參與的情況下被享受的。由此,設備喪失了物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只為人們提供一種可用性。
三、 焦點實踐與物的拯救
在設備范式的作用下,物不斷被分裂為手段和目的,喪失其深刻性和完整性,蛻變為設備,那么我們應該如何拯救物呢?為了克服設備范式,拯救物,鮑爾格曼通過對現代技術與傳統技術不同特點的分析,倡導圍繞焦點物和實踐進行技術改革。“焦點物和焦點實踐可以允許我們提議甚至立法進行技術改革。”[3]155
鮑爾格曼通過分析“焦點”(focus)的意義和詞源,闡明焦點物(focal things)概念,建立起他的一個重要哲學基礎。拉丁語“焦點”的原意是火爐。它本身就是一物。在前技術時代的屋子里,火爐維持和會聚著房屋和家庭,構成了溫暖、光明和生活的中心。后來,“焦點”一詞被應用于光學和幾何學。光學和幾何學的焦點是指直線或光線在規則或規律的作用下會聚而成的點,或由此發散開來的點。在象征意義上,“焦點”就是會聚其與境中諸多關系的中心。鮑爾格曼就是在“焦點”象征意義的基礎上使用焦點物概念的。焦點物是指具有會聚其所在與境中諸如自然、傳統、文化和歷史等各種要素能力的事物。焦點物“使人的身心共同參與和為我們的生活提供中心。威嚴的在場(commanding presence)、與世界的聯結(continuity with the world)和會聚力(centering power)是焦點物的標志”[5]。
鮑爾格曼的焦點物思想繼承了海德格爾物的思想。在鮑爾格曼那里,“物”成為“焦點物”。之所以如此,“不僅僅在于‘物之為物’,還在于它的‘在場方式’、‘呈現’形式、‘場域’、與‘周遭’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以及那些‘不在場’卻是這個場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要素。它們共同組成了以‘物’為中心的人們生活的有機場域,生活世界由此得以展開,社會由此得以構建,文化由此得以產生”[6]。鮑爾格曼用“焦點”一詞深刻地揭示了海德格爾“物”的要義,用“焦點物”這一概念明確地與“對象”意義上的物作了區分[7]。同時,鮑爾格曼的焦點物思想在兩個方面超越了海德格爾物的思想,從而為在現代技術背景下拯救物創造了可能:一方面,海德格爾似乎認為人需要返回到前技術時代才能與物相遇。絕大多數的現代人從現代技術中享受到舒適和便利,不愿意回到前技術狀態。鮑爾格曼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并看到在現代社會任何這樣前技術時代的物其實就是被它周邊技術環境所凸顯出來的焦點,從而前技術時代的物在現代技術環境下獲得了新的意義,成為焦點物。另一方面,在海德格爾物的“天、地、神、人”四重整體中雖然給人留下了位置,但是我們基本上看不到人的實踐。例如,在海德格爾對酒壺四重整體的描述中,雖然有人,但是我們看不到把持酒壺的手,更看不到酒壺傾倒時的社會背景。鮑爾格曼實現了實踐轉向,他指出焦點物需要一種實踐,只有通過實踐,焦點物才能繁榮。
正是因為鮑爾格曼的焦點物思想在上述兩方面超越了海德格爾,看到前技術時代的物在現代成為被它周圍技術環境所凸顯出來的焦點物,意識到實踐可以使它興盛,所以他倡導圍繞焦點物,構建焦點實踐,拯救物。
焦點實踐(focal practices)就是人們在焦點物的指引下,依照焦點物自身的秩序,維護焦點物深刻性和完整性的實踐活動。焦點實踐不同于設備范式,它認同焦點物,并將其放置在中心地位。焦點實踐守護著焦點物,防止其被技術性地分割成手段和目的。我們進行焦點實踐是要克服設備范式,而不是普遍地反對技術。在焦點實踐中,我們不能拋棄和逃離技術。這是因為一方面,技術能夠制造工具和設備,我們可以運用這些工具和設備與世界進行更有技巧、更親密的聯系。例如,在跑步這一焦點實踐中,運動鞋是一種技術產品,但是作為技術產品的這些輕巧、結實和減震的鞋子不但沒有阻礙我們的焦點實踐,反而使我們跑得更快、更遠、更暢快,使我們更充分地參與世界,使我們與世界進行更富有技巧、更加親密的聯系。另一方面,技術為我們提供了空閑和時間,技術把我們從日常瑣事和耗時的事務中解放出來,使我們有時間進行焦點實踐。在焦點實踐中,我們要對技術采取理智而有選擇的態度。例如,在跑步的焦點實踐中,我們可以穿著輕巧的運動鞋,但是不能用摩托車來實現這樣的運動。在焦點實踐中,我們既要使焦點物在技術環境中繁榮,又要使技術承諾在以焦點物為中心的背景下得以實現。
鮑爾格曼圍繞焦點物和焦點實踐建議在社會經濟領域進行技術改革。他建議將社會經濟部門分為兩個:集中的、自動化的部門和當地的、需要緊張勞動的部門。集中的、自動化的部門包括公共事業、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汽車、電器、工具、原材料和金融等商品生產和服務,以及研究和發展。當地的、需要緊張勞動的部門包括食品、服裝、醫療衛生、教育和音樂、藝術與體育指導等。集中的和自動化的部門是保證和改善現代生活必不可少的技術條件,但是這里的技術應該被看做是生活的背景,而不是生活的準則和中心。當地的和需要緊張勞動的部門是人從事參與性勞動的領域,人在參與中體驗焦點物的深刻性。鮑爾格曼技術改革的實質就是以焦點物和焦點實踐為中心,讓焦點物繁榮起來。
四、 物的繁榮與人的幸福
技術減少了人們的負擔,并使人們富裕。但是,“盡管技術增加了人們的金錢和財富,但人們的幸福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增加,因為保證人們幸福的物質生活水準和財富的數量會水漲船高----汽車剛開始時是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如今在很多國家卻成了人們生活的必需品”[8]。技術帶來的這種富裕是技術范疇的幸福。技術范疇的幸福,即富裕就在于占有和消費最大量的、最精致的和最多樣的用品,它體現了技術所允諾的自由、富有和皇帝般的生活。但是,技術帶來的幸福生活辜負了我們更深切的渴望[9]。以實現物的繁榮為目的的焦點實踐帶來的是另一種幸福。在焦點實踐中,人們會因參與深刻而生動的物的世界而感到幸福。在這個世界中,人全面而深刻地體認世界,事物清晰、穩定地挺立,生活富有節奏和深度,會與優秀的人類同伴相遇,知道自己與這個世界擁有同樣的深度和力量。這種幸福不同于技術范疇的幸福,它所具有的光輝比富裕所擁有的魅力更深刻、更持久。
為了實現個人幸福,構建焦點實踐,鮑爾格曼認為至少應從三個方面進行個人改革:首先,在自己的生活中,為焦點物騰出一個中心位置。例如,為種植花草,在屋前留出一塊空地;為彈奏和欣賞音樂,為鋼琴確定一個寬敞的空間。其次,要簡化和優化焦點物的與境。在技術時代,圍繞和支持焦點物的與境繁雜,不利于焦點實踐的進行,應減少和優化焦點物的與境。再次,應盡可能地拓展參與范圍。在體驗到物的深刻性和自身對物這一中心具有重要作用的喜悅之后,應將參與的范圍積極擴展到更多的生活領域。在參與活動中不應拋棄技術,而應在技術選擇的基礎上,恰當地運用技術,防止外圍的參與阻礙中心的參與。例如,在遠途的郊游中,可以借助汽車、火車等交通工具,以免因長途跋涉帶來的精疲力倦和時間短缺,減少對郊外山水這一中心的參與,削弱對郊外山水這一中心的體驗。
五、 結 語
現代生活與前技術時代根本不同,呈現出新的特征。設備范式深刻揭示了現代生活的特征,反映了在其作用下,物被分裂為手段和目的,喪失其深刻性和完整性,淪喪為設備,從而一方面減少了人對現實的參與,妨礙了人對生活世界的全面體認,導致人和生活日益單向度化;另一方面也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關系。面對這些問題,技術改革勢在必行。以焦點物為中心的焦點實踐為現代技術改革指出了一個可能的路向。焦點實踐既是增加人對現實參與,增強人對生活世界全面體認,促進人全面發展和生活豐富深刻,實現人真正幸福的有效途徑,同時也是堅持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促進社會全面進步的有益之路。設備范式與焦點物思想構成了鮑爾格曼技術哲學的合理內核,推進了技術現象學的經驗轉向,成為經驗的技術現象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參考文獻:
[1] 卡爾·米切姆. 技術哲學概論[M]. 殷登祥,曹南燕,譯. 天津:天津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9:119.
[2] 馬丁·海德格爾. 演講與論文集[M]. 孫周興,譯. 上海:三聯書店, 2005:174.
[3] 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y Inquir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4] Fallman D. A Different Way of Seeing: Albert Borgmann'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J]. AI & Society, 2010(1):57.
[5] Borgmann A. Crossing the Postmodern Divid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19-120.
[6] 翟源靜,劉兵. 從鮑爾格曼的“焦點物”理論看新疆坎兒井角色的轉變[J].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2010,27(6):56.
[7] 邱慧. 焦點物與實踐----鮑爾格曼對海德格爾的繼承與發展[J]. 哲學動態, 2009(4):64.
[8] 舒紅躍. 技術與生活世界[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118.
[9] Strong D, Higgs E. Borgmann'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Higgs E, Light A, Strong D. Technology and the Good Lif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