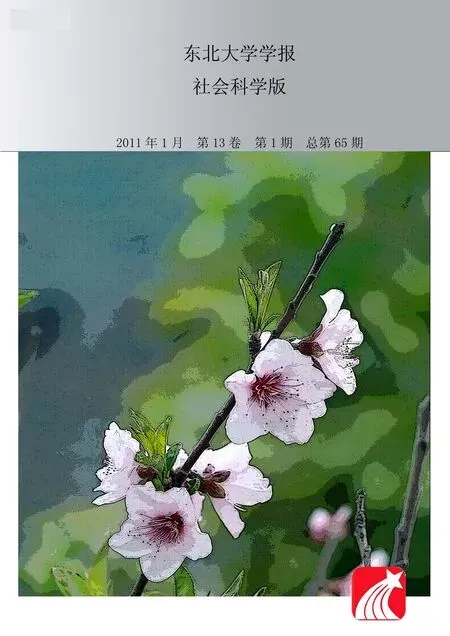論兩種技術哲學融合的可能進路
易顯飛
(長沙理工大學文法學院,湖南長沙 410114)
技術哲學有工程與人文的技術哲學之“二元對立”的區分,這種區分深深地根植于哲學上的基礎主義。基礎主義的哲學傳統以追究哲學牢固的基礎為目的并以精神與物質的二分為其前提預設,然后,在此假設上進行自身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研究。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因襲了這種二元分立的基礎主義傳統,因此,二者相應地凸顯了各自的理論優勢與缺陷。筆者主張,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著手:在研究內容上,加強對技術創新的本體論哲學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采納“經驗轉向”與現象學的視角為主要認識維度;在研究主體方面,注重對技術哲學研究者進行“兩種文化”的教育。以此作為促進兩種技術哲學融合的一種嘗試。
一、 技術哲學中的兩種傳統理論傾向及其缺失
基于技術哲學歷史演變的考察,卡爾·米切姆認為技術哲學有兩個流派:工程的技術哲學和人文的技術哲學。他認為工程的技術哲學始于為技術辯護即分析技術本身的本質,其致力于發現人類事物中到處體現出來的自然,試圖用技術來解釋非人世界和人類世界,并且用技術作為依據和范式來追問和評判其他事物,借以加深或拓展技術意識。反之,人文的技術哲學則力圖追尋技術的意義,即其同藝術、文學、倫理、政治及宗教的關系。具有代表性的是其考察技術如何可能(或者不可能)適應或者應用,并用非技術準則來評價、追問和反思技術[1]。總的說來,第一種傳統比較傾向于為技術辯護,第二種則主要對技術持批判態度。
從本體論意義看,工程的技術哲學凸顯了技術的自主性,將其理解為主體或動因,只關心純粹的技術之“是”和何以為“是”,增強或擴展了技術的意識,甚至將技術高度發揮成一種理性,支配和駕馭現代人的生活,忽略了人、技術與生活世界本真的生態關系。例如,R.舍普認為:“只有在技術的歷史中找到技術的根源和原因,才會更好地理解技術”[2]。卡爾·米切姆認為:“技術哲學是像一對孿生子那樣孕育的,甚至在子宮中就有相當程度的競爭。”[3]而人文的技術哲學把技術理解為對象,它從道德之“善”與藝術之“美”的角度來批判技術,關注人的歷史境遇,強調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解釋學意義上描述技術,而忽略了對技術過程具體的認識。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工程的技術哲學在認識內容上忽略了非技術的要素,只強調技術的主體性。它的研究局限在技術系統里面,而沒有充分關注技術系統之外的政治、經濟、社會和人文等非技術系統。其認識范圍與認識過程較為孤立和片面。而人文的技術哲學在認識內容上強調教育、宗教、社會、哲學等傳統技術系統之外的因素,并運用非技術的知識來批判和反思技術。兩者的認識路線呈現對立與互補的特點:工程的技術哲學是從技術出發向其他領域擴散,是一條從內到外的認識路線;而人文的技術哲學是從外到內的認識路線,它利用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等理論來反思技術本身。總體看來,兩條認識路線都具有自身的優勢與片面性,須要走互相融通之路。
從價值論方面來看,工程的技術哲學展現了技術巨大的功能及技術發明的重要性,并把技術發明活動當成類似于藝術創作的享受性體驗,甚至認為技術能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生態與人文危機等。而人文的技術哲學更加關注技術的后果并對技術的負價值進行反思與批判。它認為技術并不能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所有困境以及人類對這些問題的解決須要借助非技術的力量。總之,工程的技術哲學主要強調技術的正價值,而人文的技術哲學更多地關注技術的負面影響。
綜上所述,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在其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的理論基礎上體現出了各自的特點與不足。二者各自偏執,工程的技術哲學傳統走向技術自我;人文的技術哲學則走向非技術。如何使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走向融合,以促進技術哲學持續、合理地發展呢?本文擬從以下三方面來探討這一問題。
二、 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從研究內容上促進兩種技術哲學融合
從研究內容來看,工程主義的技術哲學與人文主義的技術哲學之所以對立,在于兩者的研究對象都走了“偏鋒”。前者只是以技術發明為主要研究對象,較少考察技術所處的整個社會大環境;后者從社會維度審視技術,較多地蘊涵技術悲觀主義情結,對技術實踐的內在反而缺乏體悟。由于技術創新從其一般理解的意義上講是始于技術構思終于技術的商業化運用全過程,這樣,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可以把工程主義與人文主義技術哲學的關注重心包容在內,從而實現兩者的融合。
技術創新本質是人類社會的實踐活動,是對技術發明的“揚棄”,也是技術的存在方式。發明家的技術成果,只有通過技術創新階段,才能形成技術的最終結果并被應用于消費者。技術創新是技術存在意義的展現,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對技術的領悟。我們正是通過對技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的具體把握,才能領會技術的本質。技術創新過程是一個時空階段,而技術則是無數這樣階段過程的綜合[4]。技術創新是一個展現過程,通過它我們構建了周圍的世界,展現了我們解決人與人、人與自然矛盾的方式。而從哲學的視角對技術創新進行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融合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內容的現實途徑。不少學者都呼吁要加強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陳昌曙從學科建設與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論和現實的社會實踐的需要三個方面論證了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重要性[5]。有學者甚至認為,如果技術哲學定位于馬克思實踐哲學的自然改造論,那么在這樣的定位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就成為了整個技術哲學研究的基礎和核心[6]。
其實,工程技術哲學與人文技術哲學的研究內容都體現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技術創新本身是一個主客融合的過程,在這個技術的展現過程中,技術共同體與其相關的環境因素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技術創新在對技術的揚棄中可以使工程技術哲學的技術理性更加鮮活,并打開與展示“技術黑箱”;另一方面,技術創新實踐是一個開放系統,它的每一階段與環節都負載著價值判斷與價值取向,它本身與社會、文化、政治、習俗等因素緊密融合,而這正是人文技術哲學的落腳點。
技術創新一方面體現了工程技術哲學的技術本體,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人文技術哲學的“非技術”因素,技術創新是工程技術哲學與人文技術哲學內容的二重化。工程的技術哲學在對技術的研究中固然要把技術升華為具有主體性的理性本體,但是不能脫離技術的存在場所——技術創新。而人文的技術哲學在反思技術時要深入理解技術的內在意義。技術創新這個“二重化”的身份在展現技術的過程中把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融合起來。馬克思指出:“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7]馬克思強調實踐對于思維的根本意義,兩者分離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問題,而技術創新實踐正“重合”了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實踐內容,因此,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內容分歧須要通過技術創新這座橋梁來融會貫通。
三、 “經驗轉向”與現象學:從方法上促進兩種技術哲學融合
從研究方法來看,工程主義技術哲學只強調技術理性,從技術這個基礎出發向其他領域擴散,是一條從內到外的研究路線;而人文主義技術哲學運用人文、社會以及哲學思想等知識來批判和反思技術,是一條從外到內的研究路線。兩種技術哲學的研究方法各有所長,但各自也存在缺失。筆者主張,借鑒“經驗研究”與現象學的研究方法可以從方法上促進兩種技術哲學融合。
所謂“經驗研究”,是指一條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相對立,但又不全采納工程的技術哲學理論的技術探究之路。其實,早在1995年,美國技術哲學家皮特就曾關注“技術哲學研究中的經驗轉向”問題,他認為技術哲學家們由研究抽象的形而上的技術對人類的影響轉向研究形而下的技術是如何從物質和觀念上來影響人們的生活的[8]19-21。
我國的陳凡教授也認為,技術哲學家要反思技術,就必須去打開這個黑匣子,使他們的分析基于對工程實踐的內在洞察和從經驗上對技術的充分描述。技術哲學研究中的這種經驗轉向,一方面表明工程技術哲學研究范式中將技術看成是抽象的,并忽視技術本身的缺陷,因而逐漸受到技術哲學家的普遍關注。另一方面,主張“經驗轉向”的技術哲學家們強調,人文的技術哲學也應該更多地關注于應用工程科學和研究技術的經驗科學,而應較少地關注與現實聯系不充分的、抽象的神話和臆想,人文的技術哲學應基于現代技術豐富性和復雜性的經驗式的充分描述之上來反思技術,要打開技術“黑箱”[9]。現代技術的形成是一個歷史過程,并且是高度復雜化的和差異化的現象。要認識到現代技術的這個特點,只有通過從整體水平上的分析轉換到局部層面上的分析才可能,技術的豐富性只有通過對現代技術進行放大鏡式的觀察才能顯現出來[8]28。從人文技術哲學來看,它越來越注重對技術系統的內部結構和運行過程方面進行規范性、描述性和批判性的研究,不是把技術當做一個單一的整體來進行分析,而是開始關注技術的設計、生產、改造、創新等微觀機制,從而能在此基礎上探討各種類型技術系統的人文社會意義。
工程主義技術哲學是從技術理解人和技術,而人文主義技術哲學是從人來理解技術,思想路線的互逆性導致兩者的對立,筆者嘗試從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按照“朝向事物本身”的價值要領,找到一個能夠克服兩者對立的新維度,重新理解技術。現象學的方法主要源自胡塞爾的“第一哲學”。自20世紀初胡塞爾創立現象學以來,現象學為當代歐陸哲學提供了一個較嚴格的方法論工具。該方法主要的特點在于對“理性”這一概念重新加以審視和解讀,認為傳統的理性概念實質上是一種對理性本身的誤讀與背離,其結果造成科學的危機。相應地,將現象學方法用于技術哲學研究,應當首先是一種態度或“范式”的轉變,“整個現象學的態度和屬于這一態度的懸置本質上注定了首先要達到一種個人的完全轉變,從一開始就可以與一種信仰的改變相比”[10]。海德格爾開創了運用現象學進行技術哲學研究的先河。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不僅是手段,其本質是一種展現方式,居于“座架”之中,座架意味著對那種擺置的聚集,這種擺置擺置著人[11]。“座架”支配著一切,人的本質被它要求著、挑戰著。海德格爾賦予了技術各種意向,而不是單純的工具和行為。后繼者伊德沿著梅洛-龐蒂對知覺分析的路徑,認為不存在純粹的技術本身,技術是一種關系性存在,技術的基礎和核心就在于技術與人和世界的相關性,他的技術哲學是一種“人—技術”關系的現象學。
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從本體論意義上通過胡塞爾對理性的重新定義、海德格爾獨特的“詩”與“思”而達到一個自在自為的世界,一個“在”的世界,而不是進入一個“是”的世界。只有在這個本真的存在世界里,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才能融合起來回歸到真理與精神的家園,人類才能真正“詩意的棲居”。運用現象學方法就不能離開意向性,而技術本身就具有意向性,這也是技術與現象學可以交融的因素之一。而從伊德的觀點看,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可以從技術與其相關因素的關系來融通,以這個關系理論為基礎來建構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融會貫通的平臺。陳凡教授也認為,現象學追問技術的本質,使技術既向自身敞開,同時也向人與社會敞開,這是對工程主義和人文主義技術哲學分裂困境的一種解決[12]。當然,兩者之間如何采用現象學范式進行具體融合,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有必要指出的是,“經驗轉向”與現象學不是割裂的兩種方法,恰恰相反,兩者是交互耦合的。技術哲學研究中的“經驗轉向”要求現象學的技術哲學應注重對具體技術的規范性和描述性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各技術系統的人文社會意義;反過來,“朝向事物本身”的現象學對技術的研究由抽象的形而上學層面轉向描述層面,為技術哲學研究的“經驗轉向”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四、 “兩種文化”的教育:從研究主體上促進兩種技術哲學融合
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C.P.斯諾指出:科技與人文正被割裂為兩種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識分子正在分化為兩個言語不通、社會關懷和價值判斷迥異的群體,這必然會妨礙社會進步和發展。當前,兩種文化的分裂非但沒有緩解,反有愈演愈烈之勢。科學文化以物為尺度,推崇工具理性,追求真;而人文文化以人為中心,推崇價值理性,追求善。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其區別主要表現在文化客體的不同。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對立,就是“兩種文化”對立在技術哲學研究領域的具體體現。技術哲學不管是走向“兩種文化”的哪一極都會有理論方面的缺失。而代表這兩極的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研究主體可以通過“兩種文化”的教育來促進其融合。
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分野因襲了“兩種文化”的分野。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從自身的文化基礎出發走向各自的道路。工程的技術哲學以技術為研究核心,強調技術的工具理性,最終走向以物為中心的科學技術的本體。其傳統高揚技術的理性,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物質財富,并革命性地改善了人們在衣食住行、醫療保健等方面的狀況,然而技術的日臻完善會導致一個問題:過去人們主要意識到他們不能做的東西以及自身的局限,在定下方案后,需要很多精力去解決這個方案中的技術問題。現在已經掌握了實現任何具體思想的技術手段的一般方法,人們似乎喪失了提出任何目標的能力。正如奧特加所指出的,技術專家正體現了工程主義技術哲學的人文的缺失。他們深陷于技術的泥潭而失去了人類社會理想與信念的指向。另一方面,人文的技術哲學則強調“非物”的思想意識及生態環境等因素,并運用它來反思與批判技術。人類面臨的價值迷失等也與技術的發展脫離不了干系,人文的技術哲學正是建立在這種人類社會面臨的現實基礎之上對技術進行的反思。“(人文的)技術哲學家必須開始就他們的技術的哲學分析與工程師對話,而為了這一點他們必須學會工程師的語言。”[13]技術之思也應具有規范性,杜爾賓說過,技術哲學要說明的是一個好的技術社會該是像什么樣子[14]。
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分立還涉及到兩類研究主體的“知識完備性(intellectual integrity)問題”。皮特認為,人文的技術哲學家對技術一味地批判,而不是通過開發各種手段,以使我們所擁有的技術知識和對技術的理解與我們對世界是如何彼此聯系在一起的看法結合起來。他認為這樣對技術哲學的發展是非常危險的[15]。他主張技術哲學工作者“必須以哲學家而不是意識形態學家的身份把注意力集中于事物是如何聯系在一起的”[15],以正視目前出現的“知識完備性問題”,努力做到技術哲學團體與其他研究團體的交流和討論上的融合。
有學者認為,之所以會有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區分,就在于兩類研究主體存在明顯的區分[16],工程的技術哲學的反思主體多是技術專家或工程師,如提出“工廠主哲學”的化學工程師安德魯·尤爾、德國技術發明家恩斯特·卡普、俄國工程師恩格邁爾、德國化學工程師埃伯哈德·席梅爾和X射線治療技術的發明者德索爾等等;人文的技術哲學的反思主體多是人文學者,尤以哲學家為多,如芒福德、奧特加、海德格爾和埃呂爾等[17]。要使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的研究主體不至于成為“單面人”,“兩種文化”的教育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要大力推進對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研究主體“兩種文化”融合的教育。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研究主體在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上的合二為一是實現兩種技術哲學融合的保證。從技術哲學對技術實踐的指導作用來看,要實現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的“二位一體”技術實踐的價值目標,關鍵還是取決于人,即工程的技術哲學與人文的技術哲學研究主體本身應該同時兼具“兩種文化”。要做到這一點,還是要從教育入手,使我們的教育真正轉向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加強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的結合,實行“文理兼容”的教育[18]。缺乏(自然)科學技術的教育僅僅是培養信仰而沒有充分的知識支撐,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僅僅是傳授知識而沒有理想信念的指引,因此,二者取長補短才是工程技術哲學與人文技術哲學的融合之道。
參考文獻:
[1] Mitcham C. 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62-63.
[2] 舍普 R. 技術帝國[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3-4.
[3] 卡爾·米切姆. 技術哲學概論[M]. 殷登祥,曹南燕,譯.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9:10.
[4] 易顯飛,張揚. 技術哲學應首先關注技術創新的哲學問題[J]. 長沙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21(1):18-20.
[5] 夏保華,陳昌曙. 簡論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J]. 自然辯證法研究, 2001,17(8):18-19.
[6] 夏保華. 技術創新哲學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4:37.
[7] 馬克思.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M]∥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5.
[8] Achterhuis H.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 Bloom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9] 盛國榮. 西方技術哲學研究中的路徑及其演變[J]. 自然辯證法通訊, 2008,30(5):38-43.
[10] Husserl E.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137.
[11] 海德格爾. 技術的追問[M]∥海德格爾選集. 孫周興,譯. 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1996:924-954.
[12] 陳凡,傅暢梅. 現象學技術哲學:從本體走向經驗[J]. 哲學研究, 2008(11):102-108.
[13] Kroes P.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M]. Amsterdam: Elsevier, 2000:8.
[14] Durbin P T. SPT at the End of a Quarter Century: What Have We Accomplished Techno[J]. Techne, 2000,23(2):35.
[15] Pitt J C. O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Past and Future[J]. Techne, Society for Philosophy & Technology, 1995,1:1-2.
[16] 劉大椿. 關于技術哲學的兩個傳統[J]. 教學與研究, 2007(1):33-37.
[17] 張同樂,邵艷梅. 關于兩種技術哲學的困境之思[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25(1):13-16.
[18] 楊懷中. 科技文化與社會現代化研究[M]. 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 200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