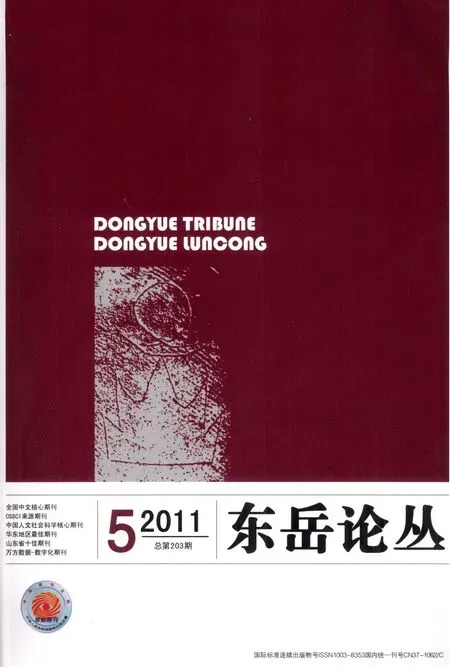楊絳研究述略
于慈江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楊絳研究述略
于慈江
(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875)
有關楊絳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評價,已有幾篇述評概括得較為全面細致,到目前為止的楊絳研究,概其大要,以美國學者耿德華為代表的海外漢學對于現代喜劇作家楊絳的“發現”功不可沒,他的研究對中國內地學界全面認知作家楊絳的創作,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楊絳創作的重心在其中晚年;在對楊絳其人其作的一片贊譽聲中,一些置疑性文字自有其提示和點醒的價值。
楊絳;楊絳研究
截至目前,對有關楊絳及其作品的研究和評價的文獻追蹤允稱賅備,計有兩篇綜述——陳宇的《近十年楊絳研究綜述》①和路筠的《近十年 (1997~2006)楊絳散文研究綜述》②,兩篇述評——劉心力的《楊絳研究述評》③和范宇娟的《回黃轉綠十年間——楊絳新時期研究述評》④。鑒于這幾篇楊絳研究的綜述或述評概括得已比較全面和細致,為避免平鋪直敘、面面俱到,本“述略”將側重于拾遺補缺、撮其大要。
一、作為“現代作家”的楊絳
對現代文學部分的楊絳的關注(如其早期的戲劇創作等)主要始于三個方面:一是“孤島”或淪陷區文學的日益受重視;二是近年來海外漢學研究的直接和間接推動;三是“錢鍾書熱”的余熱或“愛錢及楊”效應。
這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所謂“夏門⑤四大弟子”之一、美國康奈爾大學東亞中心主任耿德華(Edward Gunn)所從事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史”研究。作為這方面的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他于 1980年出版的英文專著《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 (1937~1945)》(Unwelcome Muse)⑥體現了上述三個方面或傾向的聚合:這部書本身來自于海外漢學界,研究的是過去少人問津的中國的八年淪陷區文學,又明顯受到過其師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Modern Chinese Fiction)⑦一書的影響——無可否認,該書對楊絳的“發現”,至少是夏志清對錢鍾書的“發現”的直接或間接的啟發和提示的結果。耿德華在該書第 5章《反浪漫主義》中,為楊絳專辟了一節,且置于專論錢鍾書的一節之前⑧。在這一章的《英國現代文學和中國反浪漫主義概念》一節里,耿德華這樣評說道:“張愛玲的散文和小說,楊絳的戲劇,錢鍾書的散文和小說,(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為排斥浪漫主義作家的裝腔作勢和價值觀念做出了貢獻。”⑨耿德華的這本書不僅擴大了作為現代戲劇家的楊絳在海外漢學界的影響,還幫助推動了中國內地的現代漢語文學界對中年以譯作馳名、晚年以散文著稱的楊絳的全面認知——其促進作用不容忽視。在中國外文出版社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華裔美國學者李歐梵曾這樣提到:“關于抗戰時期的文學,在美國幾乎沒有人知道。……我們以前從未聽說 (過)楊絳,看了這本書 (慈江按:《被冷落的繆斯》)才知道。楊絳在上海寫了許多喜劇,有些喜劇寫得非常成功。”⑩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對楊絳賴以成名的喜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做了頗為細致精到的剖析之外,耿德華還用不小的篇幅,重點討論了楊絳自己后來都似乎不愿再提起的悲劇《風絮》?。當然,他之所以只是約略地提及了一下另外一部喜劇《游戲人間》?,主要是因為,這部戲“似乎沒有發表過,今天顯然也無法找到了”?。
尚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夏志清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因“發現”了張愛玲、錢鍾書和沈從文等作家,進而幫助改變了后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格局外,有關中國內地的現代文學研究界受海外 (包括臺港)漢學研究一定程度的影響和推動,還可以從如下兩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來略見一斑。
其一是,據黃裳在其文章《卞之琳的事》?中所披露的卞之琳寫于 1981年 12月 11日的一封信,卞之琳20世紀 80年代曾應邀赴荷蘭參加某荷蘭人的文學博士學位授予典禮。該博士論文的討論對象正是卞之琳其人其詩:
我最近去荷蘭住了十天(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十二月二日),是應邀去參加萊頓 (Leyden)大學授予一位荷蘭學者(Lloyd Haft)博士學位的隆重典禮。這位博士用英文 (他出生美國)寫了一本相當厚的專著(現印了一些試行本,修訂后將正式出版),題目是我。
卞之琳這段文字除了可用來一窺海外漢學對現代漢語文學的研究動向外,還至少可以作為研究作家心理的一個文本——卞之琳在這段文字中,直到最后一個字才如封似避、猶抱琵琶地把關鍵字“我”作為包袱給抖摟出來,極其耐人尋味,不僅僅是“謙抑”一詞可以了得。
其二是,在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辦的《中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 1期里,有一篇題為《楊絳先生與劉梅竹的通信兩封》的文字,系法國學者劉梅竹 2004年 12月及 2005年 6月通過信件往還采訪楊絳先生的內容摘錄。這些訪談透露了一些極有價值的信息:如楊絳自承,“我不是教徒,(但)也不是無神論者,我信奉上帝”;如楊絳反復強調,她自己古文功底不高 (慈江按:與錢鍾書恰成鮮明對照)——“都是自習,所以功底不深。很差,很差”;如楊絳明確說明,她自己作于 20世紀 40年代的喜劇《游戲人間》的底本是自毀自棄,不是丟失;如楊絳反復強調,研究者使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楊絳文集》第三次印刷本十分必要 (“最好買第三次印刷,因有修改”),等等。然而,筆者之所以在此提到這篇通信訪談文章,除了是為了例行公事地綜述文獻之外,也是想強調一下訪談者劉梅竹的海外學者身份。雖然訪談者為了凸顯楊絳對答的文獻和史料價值,有意略去了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訪談目的,但從這篇采訪錄的字里行間,特別是楊絳的回復里仍可以看出,法國學者劉梅竹訪談楊絳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寫關于楊絳其人其作的博士學位論文——詳見后文。而這一事例至少證明了作家楊絳當前或至今仍為海外漢學所熱衷的現狀,一如上舉卞之琳研究的情形。
總之,耿德華的楊絳研究無疑起到了填補空白——包括研究資料的搜求——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引領研究方向的作用。譬如,在該書中譯本第 272頁當中的三個腳注里,耿德華引用了 20世紀 40年代的兩位戲評家——孟度?和麥耶(董樂山)(1924~1999)?——發表在《雜志》月刊上的楊絳戲評。這些資料直到20世紀 90年代開始,才陸續被中國內地的學者所引用:1991年出版的《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集》一書編入了孟度的《關于楊絳的話》;1995年的《人在邊緣——楊絳創作論》?一文引證了麥耶的《游戲人間——人生的小諷刺》——其實,也就是耿德華所引證過的《七夕談劇》一文的其中一節?;到了 1997年,陳學勇還在質問,當今的楊絳研究者們為什么會忽略 20世紀 40年代的劇評家麥耶??——不僅如此,他還特意提到了《雜志》月刊上麥耶的另一篇楊絳評論文章《〈弄真成假〉與喜劇的前途》,并聲稱,類似的文章他至少看到過不下四五篇;2005年的一篇《楊絳研究述評》?雖然同時提及、引證了孟度和麥耶發表在《雜志》月刊上的兩篇文章,但卻在行文的時候,把孟度誤寫為楊度;在注釋的時候,把麥耶的《十月影劇綜評》誤寫為《十月影劇總評》。
就針對楊絳創作于 20世紀 40年代的戲劇所展開的研究而言,下面幾篇文獻值得注意:柯靈的《上海淪陷期間戲劇文學管窺》(《上海師范學院學報》,1982年第 2期)、莊浩然的《論楊絳喜劇的外來影響和民族風格》[《福建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 1期 ]、張靜河的《并峙于黑暗王國中的喜劇雙峰——論抗戰時期李健吾、楊絳的喜劇創作》[《戲劇》,1988年秋季號 (總第 49期)]、黃萬華的《楊絳喜劇:學者的“粗俗”創作》(《新文學研究》,1994年第 3期)、萬蓮子的《亂世情懷的文化發現——論張愛玲與楊絳在淪陷區上海的創作》(《云夢學刊》,1996年第 3期)、胡德才的《“替沉悶的人生透一口氣”——論楊絳和她的喜劇創作》(《湖北三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 4期)、張健的《論楊絳的喜劇——兼談中國現代幽默喜劇的世態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 3期)、黃樹紅和翟大炳的《楊絳世態人情喜劇與意義的重新發現——談〈稱心如意〉〈弄真成假〉的文學史價值》(《廣東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第 1期)、馬俊山的《重返市民社會建設市民戲劇——論 40年代的話劇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3年第 2期)、敖慧仙的《談楊絳的喜劇〈稱心如意〉的高潮設計》(《戲劇文學》,2006年第 12期),以及楊揚的《楊絳喜劇藝術論》[(安徽大學 2004年碩士論文)(導師:王文彬、王宗法、張器友、王達敏)]。莊浩然和張靜河兩人的論文還被收入了田蕙蘭等選編的《錢鍾書楊絳研究資料集》?。
二、作為“當代作家”的楊絳
目前,從維普、萬方和知網上可以搜索到的跟楊絳相關的研究和評說文字計約五百余篇,來源包括各類報刊和期刊等。刨除因各種原因所導致的一稿多投?及一些詞條性、說明性、介紹性和報道性的過于簡略的文字,共得文章不到四百五十篇。而在這其中,真正學術性的論文所占的比例尚不及三分之二。這些文章的論題涉及楊絳將近八十年創作生涯里的各種體裁嘗試,把楊絳當作所謂“當代作家”來研究的占了較大的比重。這倒也符合楊絳的寫作重心是放在了自己的中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的基本情況。
這些評論文字的基調絕大部分都是捧場、首肯和欣賞。這使得少數提出問題的置疑性文字變得比較耐人尋味和引人注目。以楊絳迄今為止發表的唯一一部不算很長的長篇小說《洗澡》?為例,孟飛的《從〈洗澡〉說開去——略論建國后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一文便明確地表示了不以為然:“楊絳先生以漫畫式手法勾勒的 1950年代思想改造運動,讓很多讀者以為那不過是一場鬧劇,幾乎塵封了真實的歷史。然而千百年以來卻并無人真能夠遮蔽歷史的真相,不管是權力話語還是文人之筆,不管是戈培爾還是楊絳。”——始終自覺地與政治保持適度距離的作家楊絳竟然被和納粹文人戈培爾相提并論,不可謂不觸目驚心!
還有施蟄存 1989年 10月 7日寫的《讀楊絳〈洗澡〉》(《施蟄存說楊絳小說〈洗澡〉》)?,雖然將《洗澡》稱為“半部《紅樓夢》加半部《儒林外史》”,雖然將楊絳稱為當下不可多得的“語文高手”,但除了指出《洗澡》存在一些細節上可以商榷的問題(如指出,過去上海的教會大學其實沒有外文系,“胃癌”一詞 1952年尚不存在等)外,主要是認為其第三部過于匆忙——“寫得太簡了”,令前兩部的鋪墊沒了著落。對此,彥強的《不因同根而護短》?也有同感:“我以為最后一部寫‘運動中’,好像有點草草收來,不太過癮。”當然,這篇文章同時又這樣補充道:“把這想法商之于一個年輕人,她卻不以為然。她覺得最后確已達到全書的高潮,各個人物的性格在運動中都得到了合乎邏輯的發展和表現;她說她第一次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接受改造的如實描寫。回過頭來想我們兩類讀者的這一歧異,不出在作品本身,作品確已如實地寫了當時的人物情事,沒有添油加醋,沒有把后來才可能有的提前貼到改造者們或被改造者的人物身上。而我在讀這一部分內容的時候,實際所想的早已超出書上的描寫,而是這些書中人物在爾后近四十年中所會有和必有的表現了。”
然而,與如上兩篇文章的看法不盡相同的是,周文萍在其《學者機智女性心情——談〈洗澡〉對情節高潮的淡化》?一文中,通過對小說《洗澡》當中的兩個主要情節——許 (彥成)姚 (宓)戀情和知識分子的“洗澡”——的細讀和分析,表達了對情節高潮的這一典型楊絳式的“虛寫淡化”處理的理解態度:“這樣層層鋪墊卻又暗轉筆鋒的情節安排,使全書呈現出溫柔恬淡的風格。至于作者楊絳此中的匠心,研究者理解為出于對作品人物的愛護,因而繞過了人們心靈沖突最激烈的時刻。”?
此外,還值得提請注意的,是張立新的《流落民間的“貴族”——論楊絳新時期創作的民間立場》?和王燕的《論楊絳的自由寫作立場》?兩篇文章。此二文提供了解析楊絳的一個有價值的角度:所謂民間或自由寫作立場,就是在野,就是以良知為準繩的獨立判斷,就是“慈航普渡”和人文關懷,就是廣義的公共知識分子的重要本色。其實,也就是適度的距離或疏離感的一種堅守,就是與民一體的姿態,就是邊緣立場,就是旁觀視角。
至于與楊絳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目前能夠查找到的計有 38篇——包括一篇來自中國臺灣(東吳大學)的碩士論文(葉含氤,2006)和一篇來自法國漢學界[巴黎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研究所 (Inalco)]的博士論文(劉梅竹,2005)。其中,博士論文一篇 (法文),碩士論文 37篇 (其中,直接相關的有 28篇,間接相關的有九篇)。
這些學位論文分別針對楊絳寫作的題材(對女性、對知識分子的寫作或書寫)、體裁 (戲劇或喜劇、散文、小說《洗澡》)、敘事風格(包括總體風格、藝術風格)和寫作姿態 (包括人生姿態)等展開自己的研究和論證。楊絳雖然是一名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但以女性或女權主義敘事視角予以剖析的只有兩篇(韓雪,2006;吳嘉慧,2007)。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筆者所感受到的楊絳寫作的中性立場。或換言之,女性作家楊絳作為敘事主體,在其創作中對傳統的男性視角并不敏感,或并無任何不適之感。整體而言,這些論者對楊絳的作品所反映出來的詩性 (余艷,2006)、智(知)性 (楊靖,2003;宋成艷,2009)、邊緣性 (李彤,2004)和隱身性 (化) (徐靜嫻,2008;宋成艷,2009)傾向,表現了相當程度的關注。納入他們視野的,還有楊絳的作品的喜劇 (幽默)精神(張韡,2006;余萌,2008)、人文精神 (尹瑩,2008)和美學精神 (張希敏,2008)。此外,有的論者還特意探討了楊絳寫作過程中的選擇與得失 (夏一雪,2007)、矛盾與統一 (周虹,2008)。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研究顯得比較突出:有楊絳與錢鍾書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書寫的比較(郭崚,2007),有袁昌英、楊絳的喜劇作品的比較(李克燕,2004),也有丁西林、王文顯和楊絳的幽默喜劇的比較(徐念一,2007)。
三、綜合性的楊絳研究
其實,上述學位論文還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征,那就是整體觀和綜合視角。光是以“楊絳創作論”作為標題或副標題的就有三篇(李曉麗,1999;王燕,2005;徐靜嫻,2008),其他的還有“楊絳簡論”(夏一雪,2007)、“楊絳文學創作研究”(葉含氤,2006)、“論楊絳的文學精神世界”(郭耀庭,1994),以及“淺論楊絳作品”(余艷,2006)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臺灣東吳大學葉含氤的《楊絳文學創作研究》。該碩士論文雖然尚存在文化和哲思層面的深度抽象和提煉的很大空間,但就對作家楊絳的文學道路的描摹和梳理而言,卻是截至目前最為細致周詳的一篇。
該論文以楊絳的文學創作為題,共分九章,凡 202頁。全文依照文類呈現楊絳的創作歷程,并探討其文學風格的延續與轉變。該論文認為,楊絳的作品有兩個顯著的特色,即喜劇性筆法與客觀再現真實。認為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楊絳逐漸找到了“喜劇夸張”與“客觀紀實”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因而實現了其創作生涯的一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楊絳對“家”的描寫的重點呈現,該論文作者得出結論:“《我們仨》是楊絳積蓄了 70年來對于生命的感悟以及創作的力道而釀造的作品,可說是其文學成就的高峰。”?
當然,這里也不能不提及截至目前論及作家楊絳的唯一一篇博士論文——劉梅竹的《楊絳筆下的知識分子人物》?。從該論文的題目、正文、文獻與附錄 (長達 90頁)以及前面提及的《楊絳先生與劉梅竹的通信兩封》一文的相關內容來看,這篇長達 405頁(正文 315頁)的法文博士論文顯然下了很大的功夫 (不僅僅止于數年間一再地對楊絳進行專門的書面和電話采訪),考察的是楊絳對知識分子的關注與刻畫——這無疑是討論楊絳其人其作無法避開的一個重要視角或主題。這篇博士論文內容雖然彌足豐富,但行文命意仍嫌粗糙——特別是細節方面,仍有待細細磋磨:如把董衡巽這個名字里的“巽”(xun)字誤譯為“撰”(zhuan)字 (參見該法文論文第 5頁注釋 1),把童(Tong)慶炳這個名字誤寫為董 (Dong)慶炳 (參見該法文論文第 360頁),把楊絳先生電話里所說的英文 the muse(繆斯;詩才,靈感)誤聽、誤記錄成 the news(新聞)并莫名地把后者理解為“小說”(參見該法文論文第 391頁)?。
學位論文之外,綜合的楊絳研究的比重也并不輕。例如,林筱芳的《人在邊緣— —楊絳創作論》?和胡河清 (1960~1994)的《楊絳論》?雖均發表于十五六年前,卻都很值得一讀。前者命意精準,感受細膩獨到,選擇的切入角度比較恰切:“邊緣”——無論是由錢鍾書發軔、楊絳承傳的所謂“人生邊上”?的那一個“邊緣”,還是楊絳的寫作姿態的真實寫照的這一個“邊緣”。后者則在楊絳生平和作品的互相印證當中,以頗為老練精到的筆觸,詮釋作家楊絳的格調。譬如,該文對錢、楊夫婦如下的比喻相當精妙,真正搔到了癢處,讓人由不得擊節稱道:“錢鍾書、楊絳伉儷,可說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雙名劍。錢鍾書如英氣流動之雄劍,常常出匣自鳴,語驚天下;楊絳則如青光含藏之雌劍,大智若愚,不顯鋒刃。”然而,胡河清這篇文章的引人注目之處還在于,它與余杰的《知、行、游的智性顯示——重讀楊絳》?一文,據說有著某種不同尋常的瓜葛或稱“勾連”?。
在此文當中,號稱歷來“口無遮攔”的余杰對楊絳式的“隱身”或“避來避去”(胡河清語)頗不以為然:“在 20世紀的中國,……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對社會責任的逃避將使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更為多災多難。即使是最純粹的個人主義者,他也應當在完成救出自己后再實施對他人的拯救。在一個危難的世紀里,操作純粹的知識可以是少數知識分子的選擇,卻不能成為知識分子群體逃避義務的借口。僅有‘知’而不‘行’是遠遠不夠的。”?余杰所論自有其道理,但未免有站著說話不腰痛的求全責備之嫌:在特定的政治氣候和社會歷史情境之下,挺身而出的鋒芒畢露和大義凜然自是令人激賞,但不動聲色的“隱身衣”式堅忍也絕對值得肯定——正如楊絳在其《喜劇二種·后記》中曾經強調過的那樣:“這兩個喜劇里的幾聲笑,也算表示我們在漫漫長夜的黑暗里始終沒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里始終保持著樂觀的精神。”更何況,余杰此文“對楊絳寫作姿態的復雜性缺乏足夠的體認。從《干校六記》,到《將飲茶》,再到《洗澡》,楊絳始終如一地據守知識分子本位的寫作立場,尤其是其中‘我們’與‘他們’意識的尖銳對立,更深刻地凸現了文革與前文革時代知識分子的艱難文化處境與精神鋒芒”?。當然,與本話題不無相關的是,余杰這些頗為激進的言論被指以錢鍾書所論的“反仿”的方式,嚴重地襲用了上舉胡河清一文的相關內容?。
[注釋 ]
①《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 6期。
②《柳州師專學報》,2007年第 4期。
③《遼寧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 4期。
④《學術論叢》,1999年第 2期。
⑤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榮譽教授夏志清 (Chih-tsing Hsia或 C.T.Hsia)門下。
⑥該書英文全名為 UnwelcomeM use:ChineseL 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1937-1945,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其中文譯本由新星出版社于 2006年出版,譯者是北京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張泉。
⑦此書英文版初版于 1961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1971年二版;1999年的第三版改由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繁體字譯本有劉紹銘等翻譯的中國香港版(2008年中文大學出版社版)和中國臺灣版(1979年友聯版)——該譯本的簡體中文版目前有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5年版。
⑧詳見該書中譯本第 265~277頁。除錢、楊夫婦外,該章另外討論的兩位作家是吳興華和張愛玲。
⑨引自耿德華:《被冷落的繆斯》中譯本,第 228頁。
⑩摘自李歐梵:《美國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載于《編譯參考》,1980年第 8期。
?楊絳后來只把《稱心如意》《弄真成假》合在一起稱《喜劇兩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收入《楊絳作品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楊絳散文戲劇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和《楊絳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的也是這兩種。
?此劇不僅劇本的下落成迷——未發表,不知所蹤,所記憶的演出時間似乎也存在出入。一般人多認為是 1944年上演。如有人說:“楊絳的第三出戲劇《游戲人間》于 1944年夏季由苦干劇團上演,導演是姚克。”(耿德華:《被冷落的繆斯》中譯本,第272頁)又有人說:“不僅有此一劇,而且確也搬上舞臺,時間大概是1944年8月間,由姚克導演,若(慈江按:系‘苦’字筆訛)干劇團公演于滬上。”(引自陳學勇:《楊絳的第三部喜劇與麥耶的評論》,《博覽群書》,1997年第 7期)然而,楊絳自己則說:“(1945年)4月 1日回上海。《游戲人間》上演,姚克導演,‘苦干劇團’演出。”證諸麥耶的《七夕談劇·〈游戲人間——人生的小諷刺〉》[《雜志》,(1944年 9月)第 13卷第 6期 ],應是楊絳先生自己記憶有誤。
?引自耿德華:《被冷落的繆斯》中譯本,第 272頁。另據《楊絳先生與劉梅竹的通信兩封》(《中國文學研究》,2006年第 1期)記載,楊絳自己表示:“此劇是名導演姚克導演,但劇本無足取。所以我自己毀了,不要了,沒有了。”
?參見黃裳:《珠還記幸》(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 289頁。
?孟度:《關于楊絳的話》,載于《雜志》,(1945年 5月)第 15卷第 2期。
?麥耶:《十月影劇綜評》,載于《雜志》,(1943年 11月)第 12卷第 2期;《七夕談劇》,載于《雜志》,(1944年 9月)第 13卷第 6期。另據陳學勇查考,麥耶即后來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的知名人物董樂山 (詳見陳學勇:《楊絳的第三部喜劇與麥耶的評論》,《博覽群書》,1997年第 7期)。
?作者林筱芳,載于《文學評論》,1995第 5期。
?載于《雜志》月刊(1944年 9月),第 13卷第 6期。
?陳學勇:《楊絳的第三部喜劇與麥耶的評論》,《博覽群書》,1997年第 7期。
?作者劉心力,載于《遼寧師專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 4期。
?由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1990年 1版 (674頁),1997年 2版 (736頁)。
?這種現象其實挺嚴重,有的一稿多至 4~5投:如舒展的《古驛道上悟道者——讀楊絳新作 <我們仨 >》一文,便分別載于《檢察日報》(2003年 7月 25日)、《社會科學報》(2003年 8月 14日)、《民主與科學》(2003年第 4期)和《科技文萃》(2003年第 11期);再如,杜勝韓的《楊絳小說中的賢妻良母形象》分別載于《南京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0年第 4期)、《湛江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 4期)和《中華女子學院山東分院學報》(2001第 2期)。究其實,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大概既來自于作者方面,也來自于報刊雜志方面。
?根據楊絳自己的記載,1991年“11月 1日,動筆寫《軟紅塵里》”;1992年“3月 28日,大徹大悟,毀去《軟紅塵里》稿 20章”(摘自《楊絳生平與創作大事記》,載于《楊絳文集》第 8卷第 398頁)。這說明楊絳在《洗澡》之后,很快又開始動手寫自己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并用五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其中的 20章——純就章節而言,相當于《洗澡》的一半[《洗澡》共三部 42章(12章 +18章 +12章)外加一個“尾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楊絳將已具相當規模的一部長篇放棄?是題材過于敏感,不好把握?是作者自己預估藝術上無法超越《洗澡》?是錢鍾書投了反對或否定票——眾所周知,楊的文字最后都要經過錢的把關(但問題在于,并沒有成稿呀)?這無疑又是一個與錢鍾書在《圍城》之后放棄《百合心》寫作相類似的謎,期待索解。此外,此小說的存在其實早露端倪:在花城出版社 1992年版、三聯書店 1994年版的《雜憶與雜寫》的第二部分“散文”(雜寫)里,有一篇文字顯得比較別致或突兀——這就是最后一篇《軟紅塵里·楔子》。而上引楊絳有關長篇小說《軟紅塵里》寫作的記載可以起到釋疑的作用——這篇看似沒頭沒尾的文字其實自有來歷,是一部待寫的、最終又夭折了的長篇小說的引子。
?《孟飛文集》,載于“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2/69424.html。
?參見《名作欣賞》,2004年第 6期;陳子善、徐如麒主編:《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載于《讀書》,1989年第 11期。
?載于《名作欣賞》,1996年第 1期。
?陳宇:《近十年楊絳研究綜述》,《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 6期。
?載于《當代作家評論》,2007年第 6期。
?載于《常熟理工學院學報》,2007年第 11期。
?引自該論文《中文摘要》。參見:http://etd.library.scu.edu. tw/ETD-db/ETD- search-c/view_etd?URN=etd-0727106-223217。
?以法文寫作的該論文完成于 2005年。論文的中文題目為筆者根據劉梅竹(Meizhu Liu)自己提供的法文、英文題目——《La Figure de l’intellectuel chez Yang Jiang》(The Intellectual in theW ork of Yang Jiang)——綜合譯出。該論文的指導教授系法國巴黎國立東方語言與文明研究所 (另譯:國立東方語言與文化學院)(Inalco)的伊莎貝爾·拉比 (Isabelle Rabut)。可參見英文雜志:China Perspectives(《神州展望》),第 65期 (2006年 5~6月號),http://chinaperspectives.revues.org/document636.html。
?據 2002年 7月 18日劉梅竹與楊絳的電話訪談記錄稿 (該法文論文第 383頁~第 396頁),楊絳曾說:“錢鍾書總說 the news(筆者注:小說。此處,楊先生用的是英語)喜歡年輕人,不喜歡老人。但是我不服,我總想試,哪怕只試一次,就寫一個故事。”(Qian Zhongshu disait toujours que le news(roman)[pronouncèen anglais]prèfèrait les jeunes et non les vieux...)
?載于《文學評論》,1995年第 5期。
?載于《當代作家評論》,1993年第 2期;收入《靈地的緬想》,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
?據《錢鍾書集》,錢鍾書不僅有文《寫在人生邊上》,還有《人生邊上的邊上》;而楊絳則有《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一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載于《當代文壇》,1995年第 5期。
? ? ?詳見李江峰:《余杰的疏誤》,《書屋》,2000年第 9期。
?引自余杰:《知、行、游的智性顯示——重讀楊絳》,《當代文壇》,1995年第 5期。
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3-8353(2011)05-0118-06
于慈江,男,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
[責任編輯:曹振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