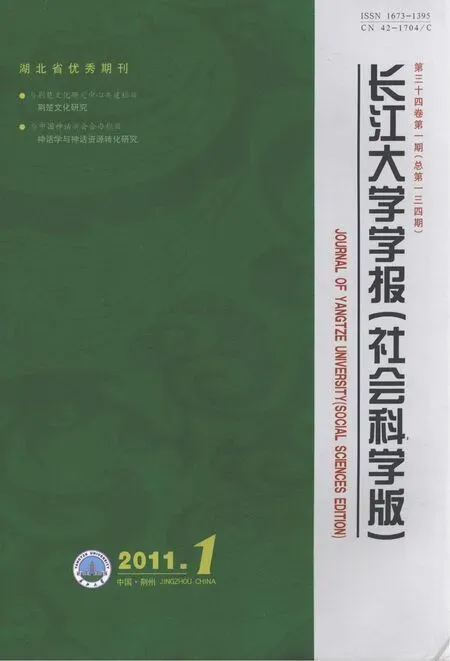從《受活》看新時期作家對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
耿菊萍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從《受活》看新時期作家對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
耿菊萍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閻連科在《受活》中對人民群眾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正是通過狂歡化的抒寫、“革命+戀愛”模式的置換和顛覆、宏觀與微觀的二元對立凸顯出來。《受活》對于探討新時期作家對人民群眾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具有重要意義。
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特征;建構方式
新時期作家對人民群眾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與革命文學時期作家對人民群眾的理解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都表現出對人民群眾盲目和狂熱的想象。筆者試圖從二者的共性入手,以閻連科的小說《受活》為例,重點探討新時期作家對人民群眾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建構的復雜的個性特征和建構方式。
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個性特征
第一,人民具有懷疑精神。這突出表現在以茅枝為代表的受活莊人民的反抗上。曾經參加過革命的茅枝,為了讓受活村與外界進行溝通,想盡一切辦法使受活村入社,可迎接她的卻是“鐵災”、“大劫年”、“黑災”、“紅難”、“黑罪”、“紅罪”等一系列災難。在大饑災時期,豐收了的受活村被外部的圓全人以革命的名義洗劫一空,受活村因此餓死了許多人。茅枝終于醒悟過來:“我不革命了,我茅枝只要還活著,我咋樣讓咱受活入了社,我就死也要讓受活還咋樣退了社。”[1](P171)由此可見,茅枝對革命的話語不再全盤接受,而是具有了懷疑精神。她發現受活莊在入社后經歷的一切苦難,更多的是來自受活莊以外的強權。
第二,人民對革命的理解具有一定的解構色彩。新時期作家對人民群眾的理解,不再單一化、理想化和簡單化,而是更關注人民群眾的個體感受。受活人對革命的理解,不再是革命文學作品中體現的莊嚴和崇高。受活莊的人民本來過著富足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但革命話語的侵入給受活莊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在“大劫年”中,茅枝見到縣長的信后,毫不猶豫地帶領受活人交出糧食以解革命的燃眉之急。外村人在搶糧時說:“在共產黨的天底下,都還是階級兄弟嘛。就把那三五囤的小麥裝上馬車,一粒不留地拉走了。”[1](P159)這實際上是以革命為幌子,對受活人的糧食進行搶奪,是以革命的名義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可見,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是出于某種革命的需要,革命使權力遍布每一個角落,是權力得以實施的保證。作家在這種革命行為中表達了對革命荒誕性的嘲諷,進而對革命的理解有一定的解構色彩。
第三,人民這一整體性范疇中的個體呈現出差異性和多變性特征。這種差異性和多變性集中體現在受活莊人民對是否入社存在著不同的立場,他們同主流意識形態存在著或融合或對立的關系。政黨和階級之所以能引起人民的響應和擁護,除了革命的感召外,還因為其賦予人民具體的利益。因此,人民參與想象共同體的建構是基于其利益的選擇。在受活莊,個人的絕術表演最初只是希望得到個別的物質獎勵,發展到后來希望組成絕術團,共同致富,逐漸由一種無意識的思想演變為集體共識,進而成為大家共同的理想。
第四,作家對人民在現代化進程中逐步被邊緣化的理解。受活人組成絕術團在全國各地進行巡回演出,他們對物質欲望的追逐使他們不顧茅枝的勸說放棄了土地,但是,他們也得不到象征著現代文明高度發達的城市的接納,他們只是為城市徒增娛樂而已。受活人被當作柳縣長籌款的工具而存在。對土地的主動拋棄,在獲得以尊嚴為代價換來的少許物質利益的同時,僅被城市當作一種發展的工具。受活人在少許的物質利益被圓全人全部剝奪后又回到了受活莊。在政治、革命、體制、商品潮等變化無常的重壓之下,人被社會徹底異化了,人變成了“非人”,人性中某些美好的東西也隨之消磨殆盡。圓全人在金錢的驅使下對受活人進行瘋狂的囚禁和掠奪就是最好的證明。小說中,對人們種種怪異而夸張的描寫恰是其病態與扭曲心靈的逼真寫照。
二、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方式
大型非人格化群體不是由個體人格和個人意志所能代表和體現的,而是“想象的共同體”。這個群體不是以個人對個人的關系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而是依賴于某種集體性原則建立起來的。個人及其所屬的傳統村社被融入到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過程被稱為“集中化”,而集中化正是現代性的重要表征。[2](P13)在《受活》中,這種集中化而形成的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狂歡化的抒寫。小說既有“文革”中受批斗、“大劫年”搶糧的狂歡,又有為買列寧遺體籌集資金組建絕術團巡回演出的狂歡,這是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文革”,還是新時期,狂歡化抒寫中的人民都在一系列政治話語的無情規訓下狂歡,民眾變得規范化,權力關系也就創造了一系列非人格化的肉體,這些肉體受制于權力,同時又是權力的工具。兩個時代都具有一定的極端化特征,從極度壓抑走向極度開放,這兩個時代本身所具有的顛覆性、宣泄性符合狂歡化宣泄性、顛覆性、大眾化、離奇怪誕的特征。狂歡化集中體現在絕術團為紀念堂落成慶典的最后一次演出上,場面宏大,幽默戲謔。“剪裁出演那一天,必定是一場少見的完滿圓全的出演哩,必然會讓涌上山脈的千人萬人都驚喜狂歡哩。”[1](P257)這種狂歡化的場景有著極為深刻的寓意,它所反映的社會呈現出殘酷性和荒誕性特征,使讀者在嬉笑之余,產生對社會的深切憂慮和對價值的再度反思,進而得出對人民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想象。
其二,“革命+戀愛”模式的置換和顛覆。左翼作家的“革命+戀愛”模式在文本中被完全顛覆和消解。戰爭年代革命者戀愛的美好在這里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卑劣和痛苦。喜歡茅枝的排長在她發燒時不僅不照顧她,還玷污了她一走了之。新時期,革命不再充滿激進色彩,其內涵被置換為發展經濟,同時,柳縣長和菊梅,石秘書和槐花、縣長夫人等所謂的男女關系,對革命戰爭年代純潔的戀愛是一種徹底的顛覆。作者正是在這種置換和顛覆中完成對人民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建構。
其三,在宏觀與微觀的二元對立中凸顯。非人格化群體不凸顯自我和個性價值。文本選取身體有殘疾的受活人作為建構人民這一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研究視點之一,具有獨到之處。值得注意的是,受活人身體的殘疾、精神本質上的善良和圓全人身體的健全、精神上的殘疾構成了一種宏觀上的二元對立。這種對立在微觀的層面上集中體現為個體人物即茅枝和柳縣長對受活莊話語權利的爭奪上。值得注意的是,閻連科在《受活》中建構的二元對立不僅僅體現在小說中的人物上,還體現在他在文本中所建構的城市——鄉村的二元對立模式上。這是一種宏觀上的二元對立。作者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在小說中真實地表達了與城市相對立且被邊緣化的受活莊在進入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復雜性和曲折性。這種進入現代化的復雜性和曲折性不僅屬于受活莊或某個山區,而是整個中國農村社會的真實寫照。作者給我們呈現這種對立,并非僅停留在共時性層面上,而是將過去、現在、未來三維一體結合起來做歷時性的考察。如果說對城鄉關系在共時的層面上考察是一種空間上的對立,那么對城鄉做三維一體的歷時性的觀照則是一種時間上的對立。
作為政治權利代表,柳縣長的做法是荒誕的,體現了他對于權利、財富的欲望。然而,小說中柳縣長并非是權利至高無上的代表。作者站在清醒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立場上,對人在宏觀、微觀的二元對立中,在城鄉的時間和空間的二元對立中給予審視。作者和敘述者、敘述對象也構成一種文本內外的對立。由此可見,大型非人格化群體的豐富內涵正是在這一系列的二元對立中凸顯出來。
[1]閻連科.受活[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
[2](美)大衛·雷·格里芬.后現代精神[M].王成兵,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責任編輯 葉利榮 E-mail:yelirong@126.com
I206.7
A
1673-1395(2011)01-0034-02
2010 11 -20
耿菊萍(1989—),女,湖北十堰人,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