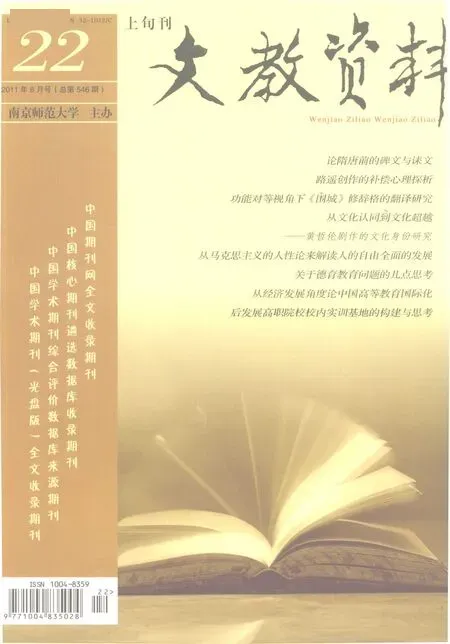19世紀上半葉美國南部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大發展的原因
鄧俊康
(內江師范學院 政法與歷史系,四川 內江 641112)
19世紀上半葉,是美國南部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大發展的半個世紀。其1860年的棉花產量較之于1790年,增長了500多倍[1]4。同時,其使用的奴隸數量增長了4倍,并使奴隸在南方腹地產棉各州達到了最大限度的集中[2]354。南部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為什么得以大發展?
一、市場可行性的具備
美國南部的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是面向市場運作的商品經濟,所以,其發展度如何首先取決于其市場可行性的狀況怎樣。19世紀前半期,工業革命使英國棉紡織工業迅猛發展,同時,工業革命超出英國范圍,擴散到了歐陸一些國家及美國北部,又使得它們的棉紡織工業迅速成長,因而大西洋兩岸的棉紡織業特別是英國棉紡織業對棉花的需求急劇增大,從而對美國南部棉花供給的依賴度也不斷增強。1800—1860年,英國棉紡織業耗用的原棉從5200萬磅上升到10億多磅[3]16。 這促使“英國紡織品制造業者……急切地盡己所能購買美國南方的棉花。在1787年的前軋棉機時代,英國從美國進口的棉花僅2200萬磅”[2]351,1820年便上升到8990萬磅,占英國當年棉花進口總額12052.8萬磅[3]17,16中的74.6%。 到19世紀40年代后期,英國棉紡織業甚至要仰仗美國南部供給其所用棉花的80%以上[4]60。再就美國北部的棉紡織業來說,其對南方的原棉需求1815年為54000包 (每包500磅),1840年為237000包,1860年達到845000包[5]。 這些史實充分說明,在19世紀上半葉,歐美棉紡織業尤其是英國棉紡織業對美國南部的棉花有著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
伴隨著國內外棉紡織業市場對棉花日益遞增的巨大需要,開辦利用奴隸來生產棉花的種植園在經濟上也變得比較合算。如“1859年,棉花種植園奴隸為主人工作的平均年收入是78美元,而吃飯、穿衣、住房的花銷僅僅是32美元。‘每個奴隸的收成值’從1800的15美元增長到1860年的125美元”。[2]355可見,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是相當有利可圖的。
以英國為首的歐美棉紡織業對美國南部棉花有著不斷增長的巨大需求,且使得以奴隸勞作為基礎的棉花種植園相當有利可圖,這就為美國南部掀起該種植園的經營熱潮提供了市場可行性。如此一來,其結果必然是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的大發展。所以,該經濟在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南部大發展的首要原因,便是該地區當時具有大量使用奴隸勞動的棉花種植園的市場可行性。
二、憲法、法律的保駕護航
由于美國自建立聯邦制國家起,便開始走上了法治道路,因而,在美國的任何一種經濟,包括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要想長足地發展,都離不開國家法律的支持。1787年,美國將制訂聯邦憲法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在制憲會議上,南方的代表堅決守護其奴隸制,來自佐治亞州和南卡羅來納州的代表甚至警告道:若視奴隸制為非法,他們兩州則不加入聯邦[6]147,這使北方代表認識到如果不承認奴隸制,就不可能建成聯邦制度[7]47,所以,經過妥協,1788年生效的美國聯邦憲法,“采取了既不冒犯北方,不得罪南方的態度”[8]225,字面上“根本未提及‘奴隸制’一詞”[8]225,事實上卻“拒絕禁止奴隸制”[2]361。 如該憲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凡根據一州之法律應在該州服役或服勞役者,逃亡另一州時,不得因另一州之任何法律或條例,解除其服役或勞役,而應依照有權要求該項服役或勞役之當事一方的要求,把人交出。”[9]60此規定實際上是“認可對逃亡奴隸的抓捕和遣返”[2]231,明確授予了奴隸主追回逃奴的權利;同時也確認了南方奴隸制的合法性。又如,憲法第一條第二款則規定:“眾議院人數及直接稅稅額,應按聯邦所轄各州的人口數目比例分配,此項人口數目的計算法,應在全體自由人民……數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即黑奴——引者注)之五分之三。”[9]51該規定同樣也反映出聯邦憲法對南方奴隸制合法性的認可。正因為此,1853年,富蘭克林·皮爾斯在其就任總統的演說中,更是直截了當地宣稱奴隸制是憲法所承認的,像其他公認的權利一樣是合法的[10]142。
繼聯邦憲法之后,“1793年和1850年,在南方各州的要求下,聯邦政府通過了‘逃奴法’,強制要求拒不服從的北方各州將逃亡的奴隸遣返送回南方奴隸主手中”[11]58。1857年3月6日,“聯邦最高法院……駁回黑人德雷德·斯科特要求自由的申訴”[12]161,并在其裁決書中宣布:“奴隸系其主人的財產,這一財產權在憲法中得到明確的肯定。 ”[9]151對此,“布坎南總統批準斯科特判決作為最終判決”[2]472。這些都從法律上進一步確認了南部奴隸制的合法性。
不僅如此,在南部奴隸制的發展問題上,盡管美國南北兩方存在著不同的訴求,但為了維護國家的團結與統一,南北雙方的政治人物在19世紀上半葉也達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協,并同樣將其妥協的結果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其中,影響最大的便是182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密蘇里妥協案”,它經詹姆斯·門羅總統簽署而成為法律。依據該妥協案,今后在美國新獲土地上有一個新建的自由州加入聯邦,則須有一個新建的蓄奴州加入聯邦;同時,該妥協案規定:“在所有法國割讓給美國的、以路易斯安那命名、位于北緯36°30′以北的領土內……奴隸制和非自愿勞役將被永遠禁止。”[9]110換言之,此緯線以南則是允許發展奴隸制的。對于南部奴隸制而言,“密蘇里妥協案”的一個重要意義,便是其發展的權利也獲得了聯邦國家法律的認可。
從上述史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整個19世紀上半葉,美國南部的奴隸制,不僅受到國家憲法法律的保護,而且享有合法的發展權利。這就為南部地區大量地使用黑奴勞動力來大規模地發展棉花種植園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所以,19世紀上半期美國南部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得以大發展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因為有國家憲法法律的保駕護航。
三、新建蓄奴州的土地的保障
土地是棉花種植園進行生產活動的基礎,加之當時集約化經營的缺乏,這決定了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要想長足發展,還須有相應的土地用作生產平臺。19世紀60年代前,美國的領土擴張使其南部獲得了大面積構筑棉花種植園生產平臺的機遇。本來在1776年《獨立宣言》發布時,美國僅有北美大西洋沿岸90萬平方千米左右的領土。1783年美國與英國訂立的《巴黎和約》,使美國領土面積一下猛增到200多萬平方千米。1803年,美國從法國手里購買了路易斯安那地區,又“使美國的領土規模擴大了一倍以上”[13]119-120。 到19世紀中葉,美國領土已抵達太平洋沿岸,擴大到了約780萬平方千米。快速增大的領土,為南部大量解決棉花種植園生產所需的土地創造了條件。
在新獲的美國領土上增建蓄奴州,是南部為保證奴隸制的棉花種植園能從新領土中有效地取得其需要的土地而采取的主要對策。當美國聯邦憲法最初生效時,南部只有特拉華、馬里蘭、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南卡羅來納、佐治亞6個蓄奴州。隨著美國新領土的不斷增多,南部在新領土上增建的蓄奴州數量也在不斷增多,到1861年,沿西南方向共新建了9個蓄奴州。這樣,至美國內戰(1861—1965年)前夕,南部蓄奴州的總數達到了15個。新建的蓄奴州,為奴隸勞作的棉花種植園提供了空前廣大的土地來源空間。
19世紀上半葉,伴隨著美國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的大發展,“在南部形成了一個寬闊的‘棉花地帶’。它包括了南卡羅來納、佐治亞、亞拉巴馬、密西西比、阿肯色,以及佛羅里達北部、密蘇里東南部、田納西西部、得克薩斯東部和北卡羅來納部分地區”[14]332-333,以及路易斯安納州等地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棉花地帶大都分布在新建的蓄奴州土地上;且該棉花地帶的主要中心又在墨西哥灣平原地區,該地區新建的蓄奴州亞拉巴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三州1859年的棉花產量就占了當年美國棉花產量的68%,即2/3以上[3]31。 這就說明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的大發展,主要是靠新建蓄奴州的土地來獲得的。因此,新建蓄奴州的土地保障作用,自然也是19世紀上半葉美國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大發展的又一重要原因。
總之,19世紀上半葉美國棉花種植園奴隸制經濟的大發展,是當時內外因素作用的結果。
[1]W.E.B.Du Bois.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M].New York:HarcourtBrace,1935.
[2]劉德斌主譯.加里·納什.美國人民(上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3]何順果.美國“棉花王國”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4]H.C.Allen.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A History of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783—1952 [M].London:OdhamsPress,1954.
[5]曹文娟.美國商品奴隸制性質試析[J].世界歷史,1984,(2):43.
[6]Jack Allen and John L.Betts.USA:historywith documents.Vol.1[M].New York:American Book Company,1971.
[7]Peter B.Knupfer.The Union as It Is:Constitutional Unionism and Sectional Compromise,1787—1861 [M].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8]蘇彥新等譯.勞倫斯·M.弗里德曼.美國法律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9]趙一凡,郭國良主譯.J·艾捷爾.美國賴以立國的文本[G].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10]何東輝,李榮耀等譯.大衛·C.惠特尼.美國總統列傳[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11]施軼譯.馬克·列文.美國可以說“不”[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12]謝延光等譯.加爾文·D.林頓.美國兩百年大事記[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13]王琛等譯.孔華潤(沃淪·I.科恩).劍橋美國對外關系史(上冊)[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14]劉緒貽,楊生茂.美國通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