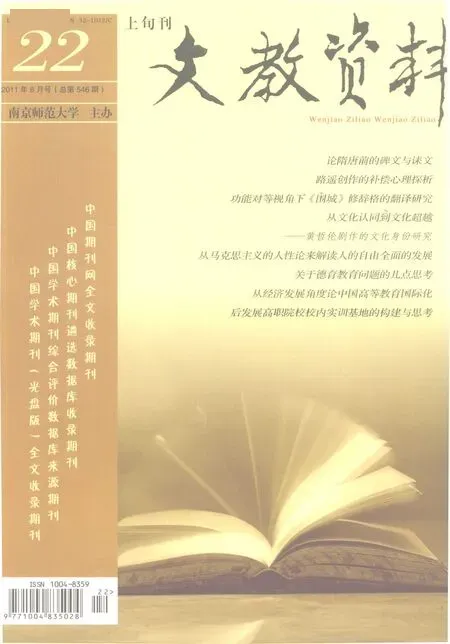論中世紀社會結構變動與近代民主的起興
石莉莉
(徐州師范大學 法政學院,江蘇 徐州 221000)
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在北方日耳曼民族的大規模侵襲下徹底瓦解,歐洲進入了被稱為“黑暗時代”的中世紀。之所以稱之為“黑暗時代”,是因為這一時期的歐洲完全處于神學教會的統治之下,尤其是人們的思想領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壓迫和禁錮。但是在世俗領域,公共權威卻呈現出一個多元的社會權力結構,存在著君主、領主、教會及貧民、市民等多個權力中心。在歐洲封建社會末期,“市民”代表新興資產階級,“諸侯”代表貴族封建割據勢力,而“王權”則代表統一的封建政府。由于利益關系不同,各權力中心不可避免地在中世紀的歐洲大陸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和博弈,嚴重地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但正是這種看似混亂的社會狀態,卻暗暗孕育了西方近現代民主的種胚。
一、王權與教權的博弈
入侵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尚未進入文明社會,沒有文化藝術,甚至沒有文字。在這種狀態下,王國統治者不得不向組織程度更高、管理水平更先進的教會尋求合作,從而實現了日耳曼軍事貴族同天主教會組織一定程度上的結合。一方面,天主教會組織參與國家管理,恢復了西歐社會的秩序。另一方面,教會承認,世俗國王(或皇帝)的政治權力是上帝認可的,例如在11世紀,教會為國王加冕設定了宗教禮儀,由大主教代表教皇替新繼位的國王加冕。但是,王國與教會畢竟不是同一個權力系統,而是兩個分裂的權力實體。公元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發起了一場“教皇體制革命”,宣布國王無權委任主教,主教的任命權在于教皇和教會內部;他還指出,教會有權把一個邪惡的國王驅逐出教會,此時其臣民便再沒有服從他的義務。格氏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鞏固教皇在管治天主教會上的權威,加強教會相對于國家的獨立性和自由度。從那時起,教會權力與世俗權力各自相互分立,二者相互制衡,最終形成了教權和王權的各自對立、制衡的獨特格局。中世紀晚期,隨著教會權力的外部膨脹和內部腐化,16世紀爆發了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改革運動的一個結果就是市民階層和資產階級的崛起,他們為城市和資本的發展開拓空間、掃除障礙。同時一些國家的宗教改革由國王親自主持,實現了王權對教權的強力控制,這一時期是封建制度式微,專制王權興起的時代。
二、貴族與君主的博弈
中世紀領主貴族與君主王權的斗爭進一步引發這一時期社會權力結構變革和西方現代民主興起。這一點在英國早期議會制度的確立過程表現明顯。1199年,英王約翰即位,他就是英國歷史上有名的“失地王”。1204年,因對外政策失當,英格蘭失去了在歐洲大陸諾曼底的大部分領地。“失地王”約翰為奪回失地,組織軍隊與法蘭西開戰,其間大肆征掠貴族和教會財產以籌軍費。1214年,英格蘭再遭敗績,收復失地的希望化為泡影。這時英國大貴族們對“失地王”的不滿終于爆發,發動了叛亂。翌年,反叛貴族進入倫敦,得到中小貴族、教會和市民廣泛響應,王家軍隊失利。1215年6月19日,國王被迫與反叛貴族簽署了《大憲章》。《大憲章》的簽訂為議會產生提供了政策依據和理論支持,即國王權力是有限的,國王必須守法,否則臣民們有權強迫他服從。英國臣民根據大憲章第61條可以用武力迫使國王守法的規定,多次對違法的國王動武,逐步削弱了王權,同時加強了大會議的權力并使之演變為議會。英國早期議會制民主實踐表明,西方代議制民主并不是完全來源于古希臘城邦的直接民主,而是在貴族領主與國王力量博弈中發生的。當然,這一切又少不了其他要素即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配合。
三、市民與貴族的博弈
10—11 世紀,城市在西歐普遍興起。隨著城市的發展,市民階級逐步崛起,市民支持王權反對地方貴族,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平衡,使領主政治向等級君主制政治發展。城市興起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促成了手工業和農業的分離。另一方面也和各級封建領主之間的激烈競爭密切相關。為了增強自身的經濟實力,各封建領主都想方設法吸引外地的手工業藝人和商人到自己的領地上聚居,形成城市。隨著城市的發展、市民數量的增長和財富的增加,也日益增長了反封建的要求和對自由的需要。于是在12、13世紀,市民們紛紛建立各種組織,積極展開了反封建的城市自治運動。當時城市市民主要聯合的對象是王權,因為發展商品經濟需要統一的政治環境、安全的交通、統一的貨幣和市場等,這與加強王權是相一致的;還因為國王頒發的特權證書和自由證書更具有法律的效力。可見,市民階層迎合了國王與領主斗爭的結構性矛盾,在已有的強大權力的空隙中使自己的力量得以持續發展壯大,為今后的最終崛起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四、多元博弈中市民階級的勝出與民主的起興
縱觀整個中世紀,王權和教權是權力結構對抗與變遷的大環境,在這一大環境之下又存在國王、領主和市民之間的三角均衡,由于三股不同的勢力在利益上既有聯系又有對立,因而在斗爭中經常形成兩兩同盟的格局:在鏟除封建割據狀態,促進民族市場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資產階級擁護王權,聯合起來反對貴族;但是等到資產階級力量強大,對王權造成威脅時,國王又與貴族聯合起來,反對資產階級;而當國王力量日益膨脹時,資產階級又與貴族聯合起來限制國王。斗爭的結果呈現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中,王權和市民階層勝出,教權式微,標志性事件當是15世紀的宗教改革,說明了教權在斗爭中的敗落;領主勢力則在王權的統一過程中逐步削弱。第二階段是在前一時段勝出的王權與市民階層的斗爭,最后的結果是市民階層勝出,王權衰落。在經歷了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之后,封建王權政治被逐步摧毀,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得以廣泛建立。在封建社會向王權社會轉換的當口,歐洲社會沒有像中國古代社會那樣,不經過春秋戰國而徑直步入了專制王權社會,這也說明了社會權力結構對民主生發的決定性作用。
五、幾點啟示
中世紀多元力量之間博弈的歷史表明,多個獨立且有抗衡力量勢力的社會,對于民主的發生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構建多元社會結構,為民主發展奠定社會基礎。民主更容易產生于多元競爭的社會權力機構之中,也正如達爾所說:“多元的社會更具有民主的親和力。”[1]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興起與回潮,其實就是民主發展邏輯的外在體現。因此,著力構建獨立、多元、競爭的多元社會結構,積極培育引導市民社會的發展對于民主的實現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2.強化多元社會結構對權力的制約。達爾認為多元社會在民主政治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認為社會對權力的制衡比以權力制約權力的憲法制衡更為重要。他指出,一個由各種獨立的、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社會,可以對權力構成一種“社會的制衡”。如果沒有社會的制衡作用,在政府內部對官員的制約能否有效地防止專制則很值得懷疑;相反,如果充分發揮社會的制衡作用,政府內對官員的制約和政府機關之間的制衡則能夠有效地防止專制[2]。
3.中世紀的遺產。西方現代民主興起于中世紀,歸功于中世紀獨特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模式或許不具有普適性、唯一性,但其中蘊含的邏輯道理是不容忽視的。當今的資本主義民主是經歷了幾百年的制度革新而逐漸成長和發展的,但這一過程還遠沒有達到成熟和完善,發達民主國家關于民主的維持和鞏固,后民主化國家關于民主的生發和培育都是一項艱難而長遠的人類工程,而不管情勢如何迥異多變,成功的要訣皆在于看清情勢背后的關鍵力量,那就是制度之后的社會權力結構。
[1]羅伯特·達爾.多元民主的困境[M].求實出版社,1982.
[2]黃輝.以社會中制約權力——羅伯特達爾的民主新視角.東莞理工學院學報,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