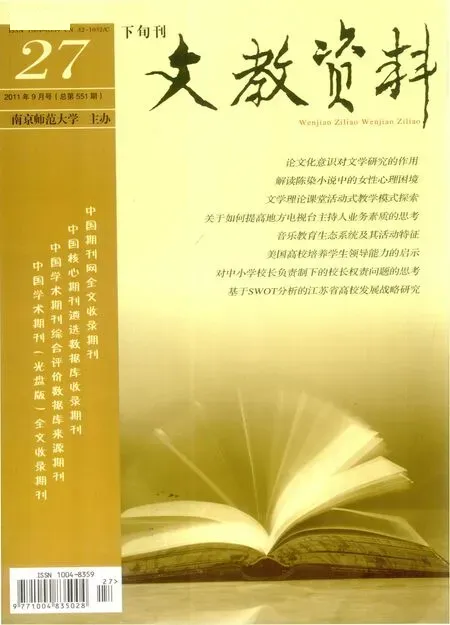論《思家飯店的晚餐》中“思家”的深層含義
堵文暉
(江蘇技術師范學院 外國語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0)
安妮·泰勒是美國當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她的作品主要描寫的是美國家庭生活。家庭是人類社會關注的永恒主題,其內涵非常豐富。泰勒把視線投向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她用簡樸而通俗的語言描述了家庭中各成員間的復雜關系。小說中的家庭遠非寧靜平和,而是內含沖突,局勢緊張,這些沖突和緊張使得家庭成員對家的感情充滿著矛盾。其中最能體現這一主題的當屬泰勒的重要小說《思家飯店的晚餐》。本文將通過細讀法對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進行分析,展現每個人物對“家”的復雜情感及其根本原因,來揭示“思家”的深層含義。
《思家飯店的晚餐》是安妮·泰勒的第九部小說,她曾因此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并獲得了美國普利策文學獎。這部小說講述了塔爾一家的生活。女主人波爾在丈夫貝克·塔爾離家出走后獨自一人照顧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靠在“威斯尼兄弟”店上班的薪水和丈夫每月寄回的錢支撐著整個家庭,直到三個孩子都長大成人,有了各自的家庭和生活。這個故事很簡單,但簡單的故事情節并不意味著這部小說平淡無奇。相反,小說最精彩的就是看似平淡的表面,底下卻波濤洶涌,這也是泰勒最擅長的寫法:通過對生活中的小事描寫,揭示人物復雜的內心情感世界。小說取名為《思家飯店的晚餐》有著深刻的含義。家既是孩子們成長的搖籃,避風的港灣,生活的動力,又是一種束縛,對個人發展的限制,矛盾和緊張關系的來源。因此,小說中塔爾一家對“家”的感情是復雜的,形成的原因也多種多樣,他們對家的思念也與傳統家庭小說中所描寫的有所不同。
一、貝克·塔爾的“思家”——有家不歸
父親貝克是一名推銷員,由于工作的關系他經常在全國各地出差。在與波爾結婚生子的頭幾年,他帶著這個家庭一起奔波于各地。然而,有一天他累了,把家放在巴爾的摩,從此在這個家庭中消失了,直到波爾的葬禮才再次出現。但奇怪的是,在這三十五年中,他每月都寄錢回家,沒有和波爾離婚,也沒有另外成家,而且曾經一個人悄悄地到他們居住的地方看望孩子們。貝克的行為充滿了矛盾,這是他對這個家的感覺造成的。家曾經帶給他溫暖和快樂,在他內心深處還是關心著這個家,思念家里的孩子們,但同時家也束縛了他。為了能升職,貝克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而他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經常要搬家,妻子波爾并不能理解他,正是由于夫妻間缺乏溝通交流,沒能力處理家庭事務,他覺得這個家帶給他更多的是沉重的負擔和壓力。當他覺得難以忍受時便離家出走了。從貝克身上反映出的有家不想歸、不能歸的“思家”不是傳統意義上“游子思鄉”意義上的“思家”,而是情感上受到了壓抑,個人發展受到了家的限制,令其有家而不歸,是個人需求與家庭責任間的矛盾沖突造成了貝克的有家不歸,只能在遠離家庭的地方“思家”。
二、考迪·塔爾的“思家”——逃離家庭
長子考迪的“思家”主要表現在他心靈上對幸福家庭的渴望,這是源于他童年的糟糕經歷。一方面,考迪從小就被認為是一個麻煩制造者,母親波爾經常打罵他。有一次父親教孩子們射箭,次子艾茲拉把箭射偏使母親受了傷,結果母親把責任都推到了考迪身上,因此,考迪認為母親偏愛弟弟。但事實上,母親也很愛他。考迪剛出生不久生了場大病,母親整夜在床邊照顧他,并且想多生幾個孩子作為備用,但由于貝克離家后,獨自撫養三個孩子和照顧家庭的重擔都落到了波爾身上,使她成為了一位脾氣暴躁的母親,在考迪心中“她是一個狂暴,憤怒,有時嚇人的母親”。[3]287考迪不能感受到母親對他的愛,也不能理解對他的責罵并不是因為討厭他,而是害怕“我所愛的人都依靠我一個,想到這點我就害怕!我怕我會做錯事。”[3]63考迪用一生時間想去贏得母親的喜愛,但總是用錯了方法。小時候,演母親少女時學的戲《抵押借款已經過期》;長大后,為母親買下了她租了多年的房子。然而,考迪總是試圖用金錢去買母親的喜愛,而不是通過與母親的交流溝通來表達自己的情感。正如他17歲時為母親買了一張汽車票,其本意是想讓母親去拜訪一下她的老朋友,并不是想讓她在弟弟艾茲拉生日時離開,而母親拒絕他的禮物,也不表示她更喜愛艾茲拉,但正是由于缺乏溝通,彼此都誤會了各自的意圖。另一方面,父親的離開給考迪幼小的心靈帶來了嚴重的創傷。考迪把所有的責任都攬到了自己身上,認為是自己的原因使得父親有家不歸。因此,父親的離家和與母親間的隔閡使考迪擁有了一個不幸福的童年回憶。在長大成年后,考迪成了一位出色的效率專家,擁有了大筆的財富,他買了一個農場,想象著能像其他家庭一樣,全家人住在一起幸福地生活,但最終他還是沒有住在農場。考迪選擇了遠離家庭,離開這個充滿了孤獨寂寞的城市。考迪的“思家”思的是一個溫暖幸福的家庭,是他從未有過的家庭。在現實得不到的情況下,考迪逃離了這個家,在自己的內心深處深深地渴望著,思念著。
三、艾茲拉的“思家”——家庭晚餐
這部小說的名字《思家飯店的晚餐》就來源于次子艾茲拉經營的飯店“思家飯店”。艾茲拉一生都沒有組織自己的家庭,與母親住在一起。從小到大,不完整的家庭,離家的父親,脾氣暴躁的母親,使他和考迪一樣,沒有體會到家庭給他帶來的幸福快樂。然而,艾茲拉與考迪選擇逃離不同的是,他對命運的安排只是被動地接受,從不反抗。艾茲拉把對快樂幸福家庭的向往完全寄托于另一個“家”——他所經營的飯店。艾茲拉在接手飯店后,把飯店的名稱改為了“思家飯店”。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這個飯店上,把飯店改造成家庭式餐廳,用“三個和顏悅色、慈母般的女侍者頂替了三個衣著灰暗的男侍者”。[3]120艾茲拉把飯店改造成家,用心為顧客提供家的感覺以彌補和滿足自己對幸福家庭的渴望。另一方面,艾茲拉的“思家”還體現在他對家庭晚餐的執著。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全家人一起吃一頓“真正的家庭晚餐”——所有的家庭成員聚在一起開開心心地從頭吃到尾。但事與愿違,每次聚會都不歡而散。艾茲拉的“思家”體現在他把自己對家庭的情感轉移到了自己經營的飯店和舉行家庭聚會上,通過移情的方法來實現自己的“思家”之情。
四、珍妮的“思家”——重返家庭
珍妮對家的記憶大都是母親對她的指責辱罵,就連晚上做夢都會夢到“她母親爆發出女巫的尖厲笑聲;當德國納粹蹬蹬上樓時,她把珍妮從隱藏處拖出來;指控珍妮犯下了她連想都不曾想到過的罪孽”,“她養活珍妮就是為了吃掉她。”[3]70珍妮從小到大的愿望就是離開家。上大學后她總是找理由不回去,“家里的氣氛總使她沮喪”。[3]83每次的家庭聚會,珍妮和母親總會為了一些小事吵架,最后不歡而散。然而,在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真正有能力實現自己離家的愿望時,她卻選擇留在了這個城市,并時不時地回家看望母親。在珍妮的內心深處,家永遠是她一生的牽掛。
綜上所述,安妮·泰勒用簡潔而又細膩的語言描述了塔爾一家的喜怒哀樂,對家既愛又恨的復雜情感,對“思家”這一主題進行了深刻的挖掘。無論是貝克的有家不歸,考迪的逃離家庭,艾茲拉的移情于飯店和晚餐,還是珍妮的回歸家庭,都體現了每個人心靈深處對家的思念。
[1]Bail,Paul.Anne Tyler:A Critical Companion.London:Greenwood Press,1998.
[2]Croft,Robert W.Anne Tyler:A Bio-Bibliography.London:Greenwood Press,1995.——An Anne Tyler Companion.London:Greenwood Press,1998.
[3]安妮·泰勒著.周小寧等譯.思家飯店的晚餐[M].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
[4]陳璇.當代西方家庭模式變遷的理論探討:世紀末美國家庭論戰再思考[J].湖北社會科學,2008,(1):7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