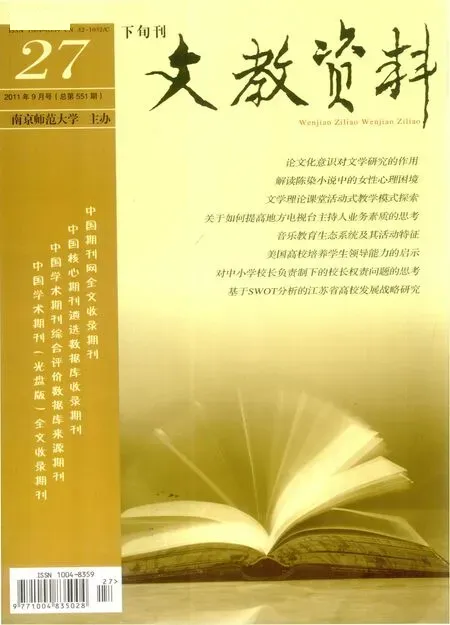解讀陳染小說中的女性心理困境
李秀春
(淄博職業學院 文化傳媒系,山東 淄博 255015)
陳染創造了女性欲望書寫的獨特話語文本,表現女性的感覺、體驗、情緒,通過激進的女性主義態度、強烈的女性意識、暗涌的女性與往來顛覆男權話語。作為一位女性主義作家,陳染曾明確表示:“我的立場,我的出發點,我對男性的看法,肯定都是女性的,這本身就構成了女性主義的東西。”[1]陳染敏銳地意識到,即使在這個強調男女平等的時代里,女性也依然有著獨特的生理體驗與想象力、感受力,于是她站在女人的角度,通過描寫女性的心理困境,開始了對建立在女性特征基礎之上的審美主體意識的強調。那么陳染小說是如何顛覆和拆解男權神話的呢?
一、“戀父”與“審父”情結
“戀父”與“審父”的矛盾糾葛在20世紀90年代的許多女性作家筆下都有鮮明的表現,其中尤以陳染的小說最為突出。在陳染的筆下,父親與成長女性之間既有人倫情感,又含有文化的象征內涵,從而豐富而又意味深長地顯現了成長女性與父親復雜的文化關系。
在陳染反映女性成長的小說中,父親形象在女性成長歲月中往往呈缺席狀態,女性往往對父親充滿了緬懷和想念,并對其進行理想化的想象,一廂情愿地認定倘若父親存在,就一定會改善自己的成長困境,這體現的正是成長女性的一種“戀父情結”。《私人生活》中的倪拗拗不論弒父的愿望多么強烈,卻仍然固執地宣稱:“我就是想擁有一個我愛戀的父親般的男人!”
她們把父親當做認識人生的真諦,沒有了父親形象的引導,她們的生命就會陷入黑暗,人生就不會完美。對此,陳染在與蕭鋼的對話中表示:“我熱愛父親般的擁有足夠的思想和能力‘覆蓋’我的男人,這幾乎是到目前為止我生命中一個最致命的缺殘。我就是想要一個我愛戀的父親!他擁有與我共通的關于人類普遍事物的思考,我只是他主體上的不同性別延伸,在他的性別停止的地方,我繼續思考。”[2]可見,“戀父情結”同樣存在于作者內心,這種存在使陳染在小說中表現父親形象時往往陷入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感境地。
然而,“戀父情結”給女性成長帶來的陰影也促使女性以一種理性反思的姿態審視父親所代表的專制父權。正是“這位‘家父’往往在敘事的開局就不由分說地執掌著塑造主人公人格的權杖,不斷地以‘現實原則’克服主人公身上的‘快樂原則’,在主人公成長所遭遇的第一個空間———家庭里形成欲望與法則的緊張關系”。[3]因此,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對父親的依戀往往伴隨著某種程度的抵制,這種抵制會隨著女性的逐步成熟而愈來愈強烈,并最終形成一種象征性的驅逐與尖銳的批判,“戀父”也隨之演變為“審父”。當然,“審父”并不僅僅意味著對現實生活中的父親的透視與反抗,更多的是對父權意識形態及其運作機制的理性認識和自覺疏離,并在確立性別自我的過程中真正實現女性主體性的回歸。
在男權制社會中,“父親”不僅表現了一個男人在家庭里的血緣地位,而且象征著在社會文化里所擁有的一切特權:強壯威嚴、理性榮耀、家庭中的家長、社會的中堅和對女性的占有。總之,“父親”是男權社會的代理人和執行者,于是“審父”和“戀父”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主題。在父權文化長期壓抑下,女性對父親形象的指認,顯然隱含更深層的含義。強烈的父親情結是陳染女性世界里的一個夢魘。幼年時遭到父親傷害的感情與被年長男性侵犯的場景重合,成為一種心理固置,被小說中的女性在無意中反復重演。“審父往往只是一種形式,真正屬于內容的東西,乃是一種清醒的社會歷史和文化批判”。[4]這種強烈的批判意識,實際上是以一種自我的方式對人性進行審問和超越。
蘇醒的女性主體意識,使她們對“父親”做出了深刻的否定,但在中國文化語境下有一個有趣的悖論就是“越是激烈的反叛者,越是那些將既存秩序深刻內在化的人們”。[5]被內化的性別秩序使她們在以男性權威為參照物而產生的自我缺失感中一面摧毀瓦解著父親形象,一面卻不停地尋找著代償。由此可見,“父親”永遠是陳染小說中女性尋找與確認自我路途上不可逾越的障礙。
陳染小說中對于父親形象所采用的貶抑、缺席及批判的敘事策略,正是從女性文本建構的象征意義上,不僅顛覆了以“菲勒斯”為核心的父權隱喻,而且有效緩解了女性被父權權威壓制的精神焦慮,為凸顯女性的成長經驗,以及尋找女性自我的主體身份,創造了一個女性成長理想化的文本空間。
二、姐妹情誼的書寫
陳染的作品中有大量的關于“累斯嬪”(lesbian,意為“女同性戀”)的寫作,這不僅表達了她對復雜人性的深切關注與同情,更為深層的意義在于:“累斯嬪”不僅是女性可以選擇的性愛方式之一種,而且是對被傳統觀念視為“正常”的強迫的“異性戀”的顛覆和否定,是打破父權文化秩序及其文明規范的有效形式。
陳染作品中的“累斯嬪”的性傾向是受父權傷害或對男性失望后的性心理轉向。她們大多對父權社會中女性受壓抑的生存困境有深刻的認識和體察,因此她們都具有極強的反叛精神與顛覆意識。這些女性在種種創傷的折磨下,在無奈、絕望和痛苦中,開始尋找來自同性的慰藉。“由于心理構造和志趣的不一樣,男女之間真正徹底的溝通,我覺得是世界上一件很難的事,因此有些現代女性(或男性)不得不在同性那里尋找精神與情感的呼應和安慰,這是人類的悲哀,這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尚未發展成熟的標志”。[6]于是她筆下的女性便習慣于把在異性那兒受到傷害的感情投向同性,“我對于男人所產生的病態的恐懼心理一直使我天性中的親密之感傾投于女人”。[7]在《私人生活》中,倪拗拗與禾寡婦這一對“累斯嬪”的性傾向主要是源于男性的傷害及對父權壓抑的反叛。共同仇視男人和與男性對抗的同謀感,使倪拗拗與禾寡婦之間有種天然的親密之感。如果說倪拗拗與禾之間的同性之誼是源于男性在精神和情感上的傷害,那么《空心人誕生》里的紫衣女人與黑衣女人所建立的“累斯嬪”關系,則主要是來自于丈夫在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壓迫與折磨。
女性情誼相對于男性來說也是最易變而不穩固的,它貌似安全可靠,實則不堪一擊。因為居于社會主導地位的男性傳統和文化觀念過于強大、穩固,作為邊緣人群的“累斯嬪”,她們的關系極為脆弱,在其違背傳統道德和世俗觀念的生活中,一旦男性插足其間,其女性情誼即刻崩潰、瓦解。有感于此,在《破開》中,陳染極力倡導姐妹情誼,但“其范圍已遠遠超出了對‘同性戀’通常所作的臨床意義的有限界定了”。[8]它顯然已不僅僅是“累斯嬪”單一的性伴侶內涵,而是女性文化的“烏托邦”。陳染揭開了她“累斯嬪”文學寫作的面紗,露出其創作的真正目的。但是“打破源遠流長”的男性文化,僅有女人的努力是不夠的,“追求真正的性別平等,超性別意識”,如果沒有男性的合作,恐怕也只是女人的一廂情愿。
陳染的創作有助于女性欲望敘事權力的建立,表達了對女性自我魅力的肯定。正如荒林所說:“要強調女性的主體,美化和強化女性欲望經驗成為策略,這能喚醒婦女記憶、尋找女性文化精神。”[9]可以說,陳染的寫作策略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女性寫作的話語自覺,她們希望通過小說的藝術營造強調女性欲望表達,彰顯女性的人性力量。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對人性的挖掘,在終極上就是對人性欲望的一種深度演示;同樣,女性小說對女性欲望的挖掘,在終極上也是對女性人性的一種深度演示。
[1][2]陳染,蕭鋼.另一扇開啟的門.花城,1996,2.
[3]樊國賓.主體的生成:50年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166.
[4]郜元寶.拯救大地.學林出版社,1994:91.
[5]戴錦華.私人生活·跋.陳染文集(第1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405.
[6]陳染.女人沒有岸.陳染文集(第4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1.
[7]陳染.與往事干杯.陳染文集(第1卷).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6.
[8]康正果.女權主義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4.
[9]陳思和,楊揚.90年代批評文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