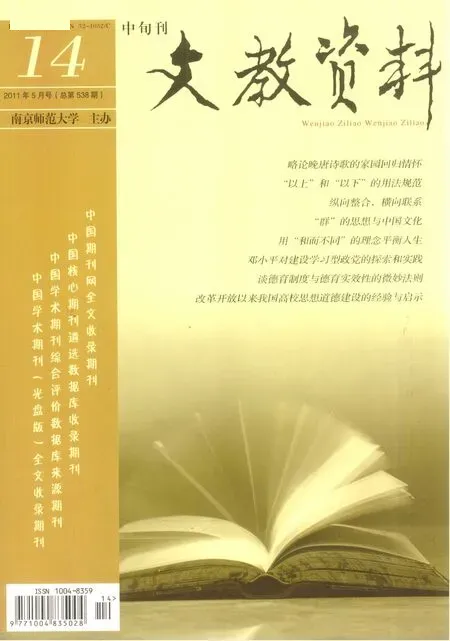老舍女性觀的時代意義
柏 樺
(鹽城高等師范學校,江蘇 鹽城 224000)
老舍的作品,以多彩的筆墨描繪了大量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婦女的抗爭與不幸,對她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關注,并無情地鞭撻和批判了把她們一步步逼上絕境的罪惡社會,抨擊了封建倫理意識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呼喚女性價值的復歸。這眾多的女性形象,不僅豐富了現(xiàn)代文學人物畫廊,而且具有獨特的時代意義。
一
中國的文化并不是在正常的、自發(fā)的進程中與西方文化交融并走向世界的,而是在被動的、屈辱的、被侵害的地位上進入一個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時代,因而世界文化浪潮的沖擊所產生的就不僅是正面的作用力,而且使中國文化在封建底色上又染上了西方“文明”的陰晦色調。因此在“老張”(《老張的哲學》)那里,女子最多不過是“折債的東西”,老張的妻子就是被當作折債品折給老張的,老張可以任意把她打死,李靜、龍鳳同樣都被當作折債的東西折給老張和孫八做妾。代表西洋文明的藍小山、小趙(《離婚》),胖校長的侄子(《月牙兒》),正是畸形文化孕育出的一批西式流氓。他們經過歐風美雨的刺激,剝下了假道學虛偽的外衣,而體現(xiàn)為赤裸裸的獸性人格,對女性以欺騙性的玩弄代替了封建性的占有。“西方文明”包裹下的悲劇更給女性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在此,老舍已觸及到了一個尖銳的命題:婦女與人的關系,也即婦女是否作為人而存在。
正如老舍所感受到的:“男女平等的口號喊了幾十年,可是婦女并沒有得到平等。”[1]當老舍開始創(chuàng)作時,中國文壇上正醞釀著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換;當他的藝術走向成熟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已經成為洶涌的潮流。真正的婦女解放,既取決于社會制度的改革,又取決于婦女自身的覺醒。自然,遠離革命的老舍并無意從這一層面考慮到啟蒙對于革命的直接功利目的,而是從一種人道主義出發(fā),形成一種自覺的文化啟蒙,然而這種自覺的追求恰恰是與“共同事業(yè)”殊途同歸的。
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化人,他們構建現(xiàn)代化人格的的契機和價值尺度最初來自西方文化。老舍在比較中英兩國國民性的小說《二馬》中,就著意刻畫了英國女性的獨立精神。無論是年老的母親溫都太太,還是朝氣蓬勃的女兒;無論是保守膚淺的馬麗,還是向往自由和平、具有現(xiàn)代觀念的凱瑟琳,她們都有著強烈的個體意識,而絕少對男性的依附。以西方女性為參照系,更燭照出中國女性在現(xiàn)代文明中的困境。“五四”以來的新思想固然給女性爭取獨立人格帶來了新的轉機,但幾千年強加在婦女身上的桎梏不可能在一個早晨拆除殆盡。老舍敏銳地感到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二十世紀的新思潮也被篡改了它的原意,在中國女性身上出現(xiàn)了異化。汪太太(《善人》)為顯示自己是個“獨立的女子”,而要人稱她為穆女士;為標榜自己在國外讀過書,連家里的丫頭也取名自由、博愛。這些拋棄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新人物”接受西方文化,只取皮毛,成為膚淺而怪誕的中西混合物。
老舍在深刻的文化反思中體現(xiàn)出復歸傳統(tǒng)美德的意向,對那些未受新思潮影響的下層女性給予了更多的關注,小福子(《駱駝祥子》)便是帶著老舍對傳統(tǒng)美的追求進入老舍的女性世界的。在小福子的身上,閃爍出崇高的人情美和人性美。然而小福子的美德并未得到社會的認可,而是被殘酷地逼進了“白房子”絕望地死去。老舍痛惜于傳統(tǒng)美德被齷齪的都市所吞沒,而把目光轉向了鄉(xiāng)下那些“樸素的鄉(xiāng)民”。這種情感意向使老舍筆下的理想人物幾乎都以娶一個“鄉(xiāng)下女人”為最佳選擇。基于對傳統(tǒng)文化的正面確認,老舍堅信中國現(xiàn)代人格的建設仍要在傳統(tǒng)文化基礎上進行。
二
老舍繼承了“五四”以來我國現(xiàn)代悲劇藝術傳統(tǒng)及新的悲劇觀念,特別是深受魯迅悲劇美學觀的影響,強調人與環(huán)境、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所造成的悲劇。處于社會底層的小人物,他們的生活命運與社會丑惡勢力形成尖銳沖突,但他們對社會的丑惡勢力的反攻是不得力的。他們就像被壓在磐石之下的可憐的小動物,只能微弱地呼吸,悲哀地嘆氣,無聲地流淚。老舍關注的正是這種悲劇,即從這些性格本身所體現(xiàn)出的美的被吞噬被毀滅。雖然這類悲劇缺乏那種“英雄悲劇”的悲壯意識,但卻有著震撼靈魂的效果,同樣能激起人們的沉痛與憤怒,喚起人們的覺醒與抗爭。
老舍小說的價值并不在于他對廣大女性獲得獨立自主的解放道路上進行了指導性的探索,而在于他客觀地揭示了廣大下層女性的真實處境。老舍認為,女性在時代大潮里被推到了以男性為主宰的無遮無擋的光天化日之下,已是不可阻擋,對廣大中下層女性來說,傳統(tǒng)的文化基因還鮮活地流淌在她們的血液中,當新思潮影響她們的時候,她們會感到茫然,感到束手無策,誠惶誠恐乃至誤入歧途,這都是必然的。老舍希望新的觀念能改變女性的命運,但現(xiàn)實是,受新思潮影響的“月牙兒”們比任勞任怨、逆來順受的“韻梅”(《四世同堂》)們的命運更悲慘。月牙兒不愿走母親的老路,想自己養(yǎng)活自己,但“自力更生”的夢在黑暗的現(xiàn)實面前被擊得粉碎;《微神》中的“她”想自由戀愛,但“理想愛情”的夢破滅了。這說明了她們不具備知識女性闖蕩社會的資本,為生計所迫,不得不淪落風塵。從小福子到尤桐芳(《四世同堂》)的不幸遭遇中,我們感到作家對女性無法保存原有的傳統(tǒng)美德的切膚之痛。如果從社會革命的角度去衡量韻梅、小文太太(《四世同堂》),小媳婦(《柳家大院》),她們無疑是缺乏獨立性和自主意識的人物,但老舍更立意于發(fā)掘蘊藏在她們身上的傳統(tǒng)美德,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她們的生活方式,贊賞多于同情。這并不是老舍懷念那個被新思潮撞擊得岌岌可危的舊時代,而正是作家對婦女解放問題思考的獨特之處。老舍對新思潮有著極大的熱情,但又無法回避新思潮影響下處于社會底層女性的生活實況。老舍清醒地告訴人們:在婦女連基本生存權都沒有、處于饑餓狀態(tài)的時候,愛情就只能是買賣,婦女解放就只能是一種空談。
三
老舍在小說中從不表現(xiàn)所謂單純個性解放或自由戀愛題材,他甚至對自由戀愛持嘲諷態(tài)度。在他的筆下,即使那些堅決追求婚姻解放、個性自由的女性,也只不過是仰仗男性錢財而維持自己有限的“自由”。像《四世同堂》里的胖菊子,雖自命新潮,悖于婦道,但當丈夫不能滿足其物質享受時,轉而嫁給藍東陽,不為愛情,而是為物質享受和“處長太太”的頭銜所誘惑。《月牙兒》中的女兒,之所以不愿走母親的路,向往追求更為理想的生活,憑藉的是兩大精神支柱:一是流行于當時的戀愛神圣思想,二是勞工神圣自食其力。這一觀念在“五四”許多作家的筆下都是極力肯定和熱情謳歌的,而老舍卻作了完全不同的處理,他讓作品中的“我”在嘲笑中埋葬了自己個性解放的夢想。
老舍不像魯迅那樣站在理性的高度,探討婦女解放問題,魯迅認為婦女解放首先必須爭得經濟權,同時女性解放建立在社會解放基礎之上,也就是說只有當女性具備了社會角度之后,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男女平等的婚姻關系。老舍雖在其小說中嘲諷了那些不切實際的盲目的自由戀愛,但作為市民意識極為濃厚的作家,他在這方面更多地表現(xiàn)為猶豫和矛盾心態(tài)。因而,老舍的女性觀與其個人的生活經歷和經驗感受亦有關系,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精神的影響。老舍說:“我在精神上物質上都受過他的好處。 ”[2]“五四”運動爆發(fā)時,老舍正熱心辦教育,同時還熱心于基督教的慈善事業(yè),希望能把天國的理想在人間實現(xiàn)。因此,他不僅從傳統(tǒng)文化觀念和倫理意識的角度描寫這些女性,而且從基督教文化精神出發(fā)看待人性和人的精神價值,以悲憫和救贖的情感來表現(xiàn)其筆下的女性。
老舍的女性觀更主要是源于他將“人”放在第一位的人道主義立場。“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最大發(fā)現(xiàn)是“人”的發(fā)現(xiàn),老舍雖未直接參加,但卻受到“五四”運動的巨大沖擊與影響。在《“五四”給了我什么》中,老舍說:“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做禮教的奴隸。”[3]在老舍看來,婚姻自由、婦女解放,首先應該是人的解放,人性意識的復歸,他站在反封建立場上對封建意識下的受害者伸冤訴苦,抨擊封建倫理意識對人性的壓抑和扭曲,并對女性深層心理進行深入挖掘,以期喚醒女性“人性”的復歸,而人性的復歸,人的意識的張揚是實現(xiàn)女性解放的最根本和最實質性的問題。這正是老舍女性觀的“五四”時代精神。
[1]老舍.最值得歌頌的事.老舍生活與創(chuàng)作自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56.
[2]老舍.宗月大師.老舍研究資料(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117.
[3]老舍.“五四”給了我什么.老舍研究資料(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