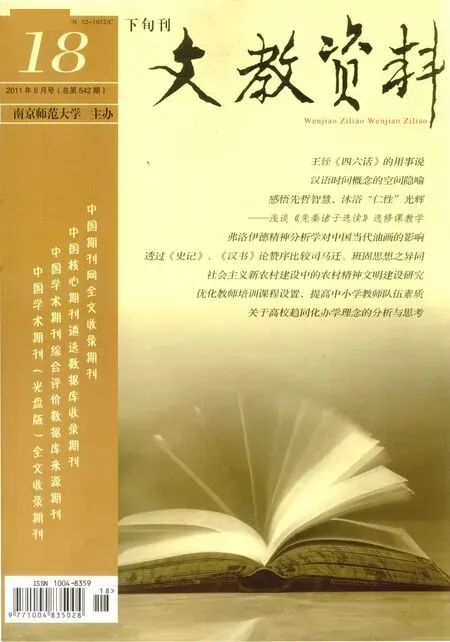論新革命歷史小說創作熱潮的原因
王永劍
(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7)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于市場的刺激、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和商業各方的策劃運作,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再次出現一個創作高潮,特別是隨著同名影視劇的改編、紅火,更加促進了這一題材小說創作的發展,代表性作品有《我是太陽》、《歷史的天空》、《軍歌嘹亮》、《八月桂花遍地開》等,跟“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相比較而言,這一類型的小說同樣站在主流意識形態的立場上對革命歷史進行再書寫,同樣認同革命歷史的必然進程,但是由于時代政治文化語境和作家主體的原因,這一類型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呈現出跟“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不同的風格特征和,被一些研究者稱為 “新革命歷史小說”。[1]新革命歷史小說是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在新時代的因襲與變異的結果,它既有革命歷史小說的某些因子,又有新的時代文化環境下所產生的獨特的審美特質。在世紀之交,新革命歷史小說的創作一度出現熱潮,是在特定歷史語境下主流意識形態、市場經濟、文化心態等一系列復雜因素作用的結果。
一、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倡導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特別是建國以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非常重視文藝創作的政治功能,因而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干預和作家主體主動迎合之下出現了一系列“將剛剛過去的‘革命歷史’經典化,講述革命的起源神話、英雄傳奇和終極承諾,以此維系當代國人的大希望與大恐懼,證明當代現實的合理性,通過全國范圍內的講述與閱讀實踐,建構國人在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體意識”[2]的具有濃烈意識形態味道和文藝為政治服務的革命歷史小說,諸如 《林海雪原》、《創業史》、《紅日》、《紅旗譜》、《紅巖》等一系列所謂“紅色經典”的作品。不論是“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小說創作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學創作,無不散發著濃濃的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味道,文學成了政治的傳聲筒和御用工具。1978年以后國家工作的重點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結束了將文藝作為階級斗爭工具的時期,主流意識形態對文藝的干預也有所松弛,但是這種松弛只是相對的。當文藝創作觸及到主流意識形態所不提倡的領域時便會遭到一系列的干預措施,甚至是以政治手段直接介入方式的進行干預,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尤其是在1989年之后,主流意識形態更加重視文學創作的宣傳性和輿論性,尤其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過程中所涌現的英烈的頌揚和對他們的忘我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的謳歌。
無論是在江澤民時代還是在胡錦濤時代,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都非常重視文藝的政治宣傳功用,“當國家機器正在努力轉換、重建意識形態體系和價值體系的時候,會從國家建立時代的文化資源中積極找尋有用有益的因素”。[4]江澤民在中國文聯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和李長春在中國文聯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5]中明確提出文藝要謳歌英雄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崇高精神,以用來激勵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為此國家采取了一系列的鼓勵和獎勵措施來引導作家的創作。
在作家作品的審定和出版上,作家的創作不得觸及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底線,不得涉及具有政治敏銳性的領域,否則出版發行狀況便會受到影響,“商業化的文學、藝術創作者若想取得商業成功……它不能違反 ‘主旋律’的意識形態前提、預設,否則其創作、發行等環節將面對各種‘不安全因素’和不確定性,影響到其商業性的實現。”[6]不僅如此,國家對宣揚革命精神的作品給予一定的獎勵,例如1990年中央多部門聯合成立了“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領導小組”專門負責審查涉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發行。同時還設立了“五個一工程獎”“國家圖書獎”等多項獎勵措施來獎勵諸如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等 “主旋律”作品的創作,這些獎項本身又是體制評價新聞出版機構的重要依據,因而新聞出版單位極力策劃和改進“主旋律”文學的創作,而革命歷史題材小說作為“主旋律”文學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所當然地成為出版機構策劃的重點。在這些作品出版之后,主流意識形態還動用各方力量對這些作品宣傳報道、組織研討會等,擴大其影響力。在這些政策和獎勵措施的激勵下便出現了一系列獲獎作品,包括《我是太陽》、《走出硝煙的女神》這兩部“新革命歷史小說”。其中《我是太陽》獲得了多項大獎:中宣部第七屆“五個一工程”入選作品獎、第三屆人民文學獎、全國十佳長篇小說獎、屈原文學獎;入選中宣部、文化部、廣電部、新聞出版總署、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建國五十周年五十項獻禮作品;中國作家協會十部獻禮長篇小說嘉獎、武漢市“五個一工程”特別獎、武漢市文藝基金特別獎、首屆湖北文學獎榮譽獎、首屆湖北省少數民族文學獎榮譽獎。《我是太陽》諸多獎項的獲得是主流意識形態對革命歷史才小說創作釋放的一個重大信號,也是對其他作家從事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創作的一個激勵和引導。
二、市場經濟環境的影響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飛速發展的時期,文學的發展受到市場經濟的影響已是不爭的事實。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更喜歡與習慣于視覺刺激,這一時期影視藝術迅速成為人們文化消費的一個重要內容,新革命歷史小說作為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在世紀之交的因襲與整合,無論是作家還是出版商充分利用了影視藝術這一市場消費的潮流。作品能否出版,出版后能否擁有大量的讀者,銷售量問題是作家不得不考慮的,作家的創作能否被影視傳媒集團購買也是作家考慮的因素之一。因為借助于影視藝術才能實現作家利益的最大化,無論是《激情燃燒的歲月》、《歷史的天空》還是《亮劍》,無一不是在影視藝術的帶動之下,發行量劇增,作家名聲大噪。在市場化的今天,只要不違反有關法規的情況,作家也是要實現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軍歌嘹亮》的作者石鐘山說:“以前,作家往往都是埋頭碼字兒,幾乎不關心市場化問題,但是現在文人談錢談市場就庸俗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7]因此從作家主體來看,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暢銷,得到觀眾的認可與支持,實現名利雙收的目的,就不得不考慮到讀者的閱讀需求,不得不取悅于讀者,為此新革命歷史小說家采取了不同于以往革命歷史小說對革命歷史題材的處理方式,而是根據當代人對歷史的理解與臆想來完成革命英雄人物的敘說,消解了以往革命歷史小說中英雄人物身上的神圣光環,于是便有了姜大牙、李云龍等一個個活生生的作為“人”而非“神”的英雄人物。這些都是作家為了實現自身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新革命歷史小有著不同于傳統革命歷史小說審美特質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國的出版事業也被納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成為出版商的重要目標。因此出版商不得不考慮市場需求,不得不考慮一本書能不能得到讀者的認可,能否成為暢銷書。這樣才能實現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了達到這一目標,出版商往往會使用多種手段策劃和包裝圖書。封皮的視覺效應和夸大其詞的點評甚至于書的名字都是出版商進行炒作的一個重要手段,只有這樣才能吸引讀者的眼球,《歷史的天空》在出版的時候曾經經過幾個編審的手,作者徐貴祥根據要求作了相應的變動,書的名字沒有改動曾一度是編輯擔心銷路的重要原因。[8]《我是太陽》版權一方狀告《激情燃燒的歲月》抄襲侵權,在某種程度上與其說是版權的相爭,倒不如說是經濟利益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新革命歷史小說的暢銷帶來的經濟利益不菲,因而出版商熱衷于出版這類作品。
同樣,影視媒體作為一種商業機構,善于發現與捕捉人們的喜好心理,把一些能夠迎合觀眾品味作品搬上熒屏,當然,作為商業媒體,他們考慮的自然是收視率,只有高的收視率才能實現他們利益的最大化,有著國家和政府最強大后盾的中央電視臺節目每年都會根據收視率進行評審改編,更何況作為商人的影視制作商了,“由于電視制作的投入很大,隨著高新技術的不斷被引進,電視的產業化也必然與商業化成為合謀,即使是傳統的國家電視臺、公共電視網也不得不考慮它們的商業回報和觀眾收視率的實際情況”。[9]制作商認識到,在當代懷舊版的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再書寫符合大眾的審美心理,因而他們選擇了這一領域,進行發掘,使得《亮劍》等創下一個個收視紀錄,也帶動了文學作品的再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更多的作家創作新革命歷史小說。
三、大眾文化心理的促使
中國曾經有著漫長的紅色生活,革命歷史擁有固定的神圣不可動搖的地位,革命英雄人物成為激勵幾代人奮不顧身地建設社會主義的榜樣,這些在給人民帶來精神的“圣潔”的同時帶來的還有審美的疲勞。所以當市場經濟降臨的時候,原有的信仰基礎和紅色秩序被商業經濟大潮沖垮,人們掙脫了“紅色束縛”,盡情地沉浸在物質享受里,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盛行。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當物質生活得到滿足之后,人們再度回首,驀然發現精神生活的空虛與生命的困惑。在這個浮躁的時代里人們為了生存下去,逐漸磨掉了性格的棱角,甚至于有些“犬儒主義”,曾經的生活盡管物質貧乏,但是卻很有激情也很快樂,于是人們開始懷念那些革命英雄人物,他們的激情和強旺的生命力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缺乏的,“在這個年代,我日益感到父親身上所擁有的東西,比如非常強烈的責任感、像生命一樣珍貴的榮譽感、堅強的信念,一輩子都不動搖的信仰,等等,對我產生越來越大的吸引力……他們比我們堅硬得多,至今還頑強地堅持著他們的信念,這種精神讓我欽佩,現在這種人已經越來越少了”。[10]因此也可以說對今天人們生活的不滿的一種發泄是新革命歷史小說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經歷了紅色經典的人們對于以往的風格早已產生審美疲勞,再加上人們對主流意識形態強行灌輸的革命歷史觀念的反叛,人們需要的是不同于以往的那種“高大全”式的的英雄人物,而是作為普通凡人的英雄人物,于是便有了新革命歷史小說中不同于傳統革命歷史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形象。
懷舊情緒與好奇心理也是新革命歷史小說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社會急劇變革時期,由于未來的不可預測,人們通常采取的本能的應對方式是‘向后看’,即感嘆現實生活的諸多不如意,暫時不去理會麻煩的未來,把安慰寄托在對已然消逝的黃金歲月的懷想之中”。[11]隨著經濟的深入發展,金錢主義、享樂主義、犬儒主義甚至于腐敗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出現,使得人們懷念紅色時期的生活,紅色時期盡管沒有充裕的物質享受,人的生活卻是那么快樂那么有激情,也因此紅色時期成為了某些人向往的樂園,特別是那些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人們更加懷念那個時期,于是新歷史小說家抓住大眾的這一文化心理進行革命歷史題材小說創作,使大眾重溫當年的激情生活和再度沉浸在美好的回憶當中,因而必然會得到他們的熱烈回應。年老一代對紅色生活時期主要是回憶,而年輕一代主要是對革命歷史好奇。在以往的歷史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中,年輕一代被灌輸的是傳統的革命歷史觀念,隨著社會的發展、思想的解放,人們不再滿足于既有的革命歷史觀,對革命歷史充滿了好奇、猜測和臆想,當一種不同于傳統的革命歷史小說出現的時候正好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和對革命歷史的種種猜測,革命英雄人物形象不再是“神”,而是變成了“人”;革命歷史不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著諸多偶然性、陰謀、錯誤的,這無疑正好滿足了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輕一代的好奇心。有了年老一代懷舊情緒和年輕一代好奇心的驅使,許多作家便選擇了革命歷史題材的在創作,于是便促進了新革命歷史小說的產生與發展。
綜上所述,新革命歷史小說之所以在世紀之交出現一股創作熱潮,主要是因為特殊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國家主流意識形態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勵和引導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創作,在大的環境上給新革命歷史小說的創作提供了諸多便利和實惠;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消費心理特別是影視藝術的介入使得新革命歷史小說迅速傳播,并反過來促進了新革命歷史小說的進一步繁榮;同時大眾的文化心理,特別是人們因對現實不滿而生的懷舊情緒和對歷史的好奇心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新革命歷史小說的發展。
[1]邵明.“新革命歷史小說”的意識形態策略[J].文藝理論與批評,2006,(5).
[2]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2.
[3]劉康.在全球化時代再造紅色經典[J].中國比較文學,2003,(1).
[4]具體內容參見中國文聯網站:http∶//www.cflac.org.cn/.
[5]劉復生.歷史的浮橋——世紀之交“主旋律”小說研究[J].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5:200.
[6]李瑛.兩個出版社同出.軍歌嚓亮.書名相同不算侵權?[J].北京娛樂信報,2003.8.3.
[7]腳印.《歷史的天空》另外的故事[J].出版廣角,2006,(1).
[8]金丹元.關于電視產品的生產與觀眾接受[J].上海大學學報,2005,(5).
[9]鄧一光,韓曉惠.關于長篇小說《我是太陽》的對話[J].當代,1997,(7).
[10]胡鐵強.懷舊情結與紅色經典改編[J].長沙大學學報,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