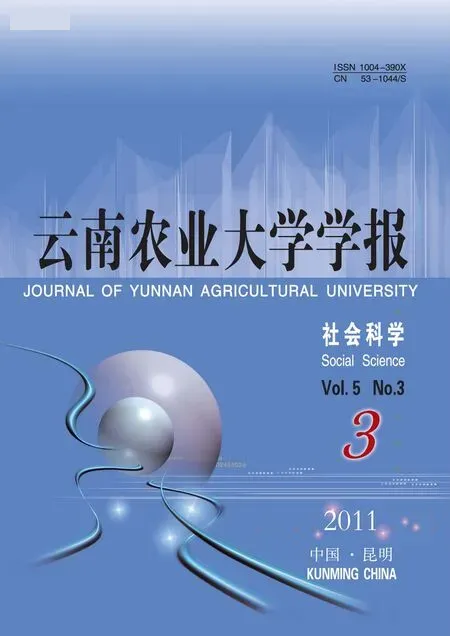《方便心論》的譯入及其影響*
董 華,張曉翔
(1.云南農業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云南 昆明 650201; 2.山東臨沂大學 法學院,山東 臨沂 276005)
《方便心論》是現有資料記載傳入中國的第一部因明著作,是古因明傳入中國的重要標志。這部著作先后有兩個譯本,第一個是由佛陀跋陀羅于公元410年所譯,現已不存;第二個由吉迦夜于公元472年(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 所譯,是流傳于后世的版本。《方便心論》共有四品,在因明的“正”、“似”、“立”、“破”等方面作了系統的闡述,該書的翻譯及傳入我國對《文心雕龍》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方便心論》的主要內容
(一)明造論品
明造論品列舉了八種能通達一切論法之深妙論法,“一曰譬喻,二隨所執,三曰語善,四曰言失,五曰知因,六應時語,七似因非因,八隨語難。”[1]
譬喻是論證道理最不可缺少的形式之一,列為八種論法的第一位,是以實例作譬況來證明論題的方法,分為具足喻和少分喻;本品從內容、性質、次第和種類等四個方面對譬喻予以了解釋。
隨所執是指宗旨、主張、結論等,分為四種情況:“一切同,二一切異,三初同后異,四初異后同。”[1]一切同是立敵共許,雙方共同認可的結論,相當于新因明中的相符極成,這是不被允許的;一切異是雙方完全不同的論點,比較符合因明違他順自的原則;初同后異是指雙方共許前提而結論各異;初異后同是指雙方不認同前提卻能共許結論。隨所執還要依靠四種量(知見):現知、比知、喻知和隨經書;這與后來的現量、比量、譬喻量和圣教量比較相似。
語善是指語句不違于事理,合乎論法形式,因、言、喻都不增不減。
言失正好與語善相反,屬于過失的范疇,分為四種情況:一是“義無異而重分別”,本來意義相同的,而名不同或者名也相同的事物卻加以分別;二是“辭無異而重分別”,三是“但飾文辭無有義趣”,四是“雖有義理而無次第”。
知因是指論證的依據、理由、根據,必須有正確可靠的資料來支撐,主要依靠現見、比知、喻知和隨經書等四種量,現見最為重要,是比知、喻知和隨經書的基礎,就時態的先后關系而言,比知又分為前比、后比和同比三種;知因者能知二因,一生因,二了因。
應時語,又稱隨時而語,強調在語言上要有針對性,根據說話對象的類別和知識層次,而獲得事半功倍的語言效果。
似因非因,即講似因,是指虛妄謬誤的理由,是在論證理由、根據上的過失,是“論法中之大過”。共有八種:“一隨其言橫為生過,二就同異而為生過,三疑似因,四過時語,五曰類同,六曰說同,七名言異,八曰相違”。[1]“隨其言橫為生過”簡稱為“隨言生過”,是論辯的前提中,立敵雙方對于概念未能共許極成,不論是因為概念發生分歧、有意曲解,還是概念在根本上有差別存在,皆屬于此種過失;《遮羅迦本集》和《正理經》都稱此過失為言辭的曲解。“就同異而為生過”簡稱為“同異生過”,也是隨言生過之一,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將兩個不同的概念視為同類,二是有法同異之不當。疑似因是對于事象的真相未能考察清楚,對于道理沒有分析清楚,不能得出必然性的結論,“如有樹杌,似于人故,若夜見之,便作是念,杌耶?人耶?”[1]過時語就是論辯時沒能在適當的時機持有效的理由,而是延后提出,于事無補而導致論辯失敗。類同就是論者用未經證明的前提作理由,把兩對事物作比附。“我與身異,故我是常,如瓶異虛空,故瓶無常,是名類同,”[1]這里論者用了未經證明的“虛空或無身為常”作理由。說同是設想用同一個理由,證明兩個不同的結論,而結論未必正確,“如言虛空是常,無有觸故,意識亦爾”。[1]言異是作為因的概念外延過于寬泛,包括了相反兩種宗的宗法范圍。相違分為兩種,一是因支與喻支相違,稱為“喻相違”,一種是名稱與實質相違,稱為“理相違”。
“隨語難”也稱作“隨言難”,“隨言難者,如言新衣,即便難曰,衣非是時,云何名新?如是等名,隨言難也”。[1]原文中未有詳細的解釋,意謂隨順對方使用的推理形式或義理,采用相同的形式或義理進行質難、反駁。
(二)明負處品
第一品主要論述論者在論辯時對于詞句上的應用,以及應該避免的種種謬誤,第二品則專門論述論者墮負的條件,只是沒有明確詳細論述,概覽原文大體包括以下幾種:
(1)顛倒,論者語言次序顛倒,陳述理由不說產生結果的直接原因,而說其原因的原因,令人不解。(2)立因不正,以似因作為論證的理由。(3)引喻不同,所舉的喻例不能有效地證明宗,甚至是反例而破壞宗義。(4)遲昧,是指使用語言文字要恰如其分,不能遲鈍不明,前言不搭后語。主要包括“應問不問”:在不明了對方話語的時候沒能及時發問;“應答不答”:一是雖然論辯對方作出了解釋,而且聽眾已理解,卻無以應對,二是答非所問,偏離主題;“三說法要,不令他解”:反復多次解釋卻不能使他人有所了解;“自三說法,而不別知”:僅了解自己所學習的知識,而對其他知識茫然無解。(5)不知彼過,即是“彼義短闕而不覺知”,論辯對方有過失而由于自方的原因而沒有察覺。(6)生正義過,“他正義而為生過”,這與前一負處正好相反,前者是對方有過失而沒有察覺,這一負處是對方本無過失而橫加詰難。(7)不悟,“眾人悉解而獨不悟”,或是一般性常識問題,或是對方所立宗義,其他人都理解,而自方卻不能領悟。(8)違錯,“一說同,二義同,三因同,若諸論者,不以此三為問答者,名為違錯。”[1]“說同”是雙方共許同一名稱陳述同一對象,類似于同一律;“義同”是雙方共許用不同的名稱陳述同一對象;“因同”是真正了解對方意趣的原因。(9)不具足,是指在問答中不能同時滿足為避免“違錯”所要求的“三同”,三者缺其一則墮入不具足的負處;如果事先聲明則可免此過失。(10)言輕疾,是指言詞過分輕細,而且速度很快,致使聽者不能領悟。(11)語少、語多、無義語、非時語、義重。“語少”是陳述不完整,或是語句不完整,或是論式不完整;“語多”就是說的太多,可以是陳述理由時沒有重點,過于啰嗦,也可以是所述因、喻過多;“無義語”是指語句內容空泛,沒有實際含義;“非時語”是指不合時宜的話語;“義重”陳述義旨不簡潔、不明確,重復啰嗦。(12)舍本宗,在論辯過程中受到對方責難或者其他原因而放棄原來所立之宗,而換成其他論題。(13)以疑為違,是由“舍本宗”延伸出來的,是把論辯對方對自方的疑惑當成對其論題的否定,混淆了不同的概念和對象。
(三)辯正論品
本品主要是辯正名身范圍及涵義,以作為進行論法有效材料,促使量法正確。通過對“有與無”、“阿羅漢果”、“涅槃”、“神常”等辯題的分析,說明論難常用的方法,以及辯正形態和程序。
(四)相應品
本品是最后一品,是以兩個概念間存在相同,或相異的性質、意義為取舍標準,通過類似類比推理的形式進行辯難。同一概念可能含有多種涵義,而立敵雙方各取有利于自方的論旨為論據,形成同一概念性質之異同。“如斯難者,有二十種:一曰增多,二曰損減,三說同異,四問多答少,五答多問少,六曰因同,七曰果同,八曰遍同,九不遍同,十曰時同,十一不到,十二名到,十三相違,十四不違,十五疑,十六不疑,十七喻破,十八聞同,十九聞異,二十不生。”[1]釋水月將以上二十種立破歸納成八項:[2]
(1)增多類比,包括“一曰增多”,“五答多問少(問少答多)”;
(2)損減類比,包括“二曰損減”,“四問多答少”;
(3)無法質問類比,包括“三說同異”,“十曰時同”;
(4)非理由類比,包括“六曰因同”,“七曰果同”,“十一不到”,“十八聞同”;
(5)同存類比,包括“八曰遍同”,“十三相違”,“二十不生”;
(6)互缺類比,包括“九不遍同”;
(7)疑問類比,包括“十五疑”;
(8)相反類比,包括“十二名到”,“十四不違(不相違)”,“十六不疑”,“十七喻破”,“十九聞異”。
本品主要是論述辯論中的一些過失,其中“五答多問少(問少答多)”、“十三相違”、“十六不疑”和“十七喻破”是屬于立者的過失,其余十六種為質難者的過失。
二、《方便心論》對《文心雕龍》創作的影響
根據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從整體而言,古因明的傳入并沒有給社會政治、生活產生影響,其影響也不過僅僅局限于文化層次,一方面是對文學領域產生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另一方面則主要是對僧人的影響,主要是古因明典籍的研習和注疏增多。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古因明傳入的第一階段并沒有引起僧俗各界的注意,對古因明典籍的研習也不見于記載。這時傳入的古因明對中國文學界具有重要影響,尤其是梁代劉勰的《文心雕龍》,雖然該著是否是受古因明的影響,在學界還存有爭議,但我們認為,劉勰著的《文心雕龍》受到了佛學的影響和啟發,尤其是古因明的著作《方便心論》和訶梨跋摩的《成實論》。
從時間上來看,劉勰的《文心雕龍》成書于齊和帝中興元年(公元501年)前后。在這以前的472年已有三藏吉迦夜與曇曜合譯出的古因明著作《方便心論》;而且還有421年印度僧人曇無懺譯出的《大般涅槃經》,該經已經有了古因明的論證方法;更有甚者,佛陀跋陀羅于410年也譯出過《方便心論》,雖今已不存,但當時是否存世已不可考;鳩摩羅什于姚秦弘始十三年至十四年(公元411~412年)間譯出了《成實論》。這些佛教、因明典籍的漢譯本都早于《文心雕龍》的成書時間,使得劉勰撰寫《文心雕龍》時受其影響和啟發成為可能。
從劉勰個人經歷來看,據《梁書·劉勰傳》記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3]劉勰在定林寺整理佛經十余年,自幼“篤志好學”的劉勰在深研佛理的同時,又飽覽經史百家之書和歷代文學作品,深得文理。其思想受到儒、釋的雙重影響,其創作的文學巨著《文心雕龍》也必將是儒釋思想融合的產物,不僅具有濃厚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而且在構思推理和組織結構等方面也受到佛理中邏輯思辯方式的影響。
從論證方法和行文來看,雖然當時并沒有成熟的五支作法的古因明著作譯出,但《文心雕龍》在整個論證結構形式上卻采用了這一形式。而且《文心雕龍》也有對古因明論辯規則的運用,如“規范本體謂之熔,剪截浮詞謂之裁。……一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詞重句,文之疣贅也。”[4]一篇文章中,一個意思前后重復,是意義上的多余;同一句話說了兩次,是文辭上的多余。因此在選擇的體裁要使內容合于規范,刪去浮詞剩句,使文辭不再拖沓冗長,經過熔意,使全篇的綱領明白曉暢。這些與《方便心論》中所論的“言失、語多、義重”等十分相近。
如果說這些是因為人類思維的相通性而使得二者偶然性地相近,那么在《文心雕龍》行文中出現的佛學和因明術語,則不是偶然的巧合所能解釋的。“然滯有者,全系于形用;貴無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4]是說在當時最突出而又揚名后世的辯論家中,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體的作用;注重“無”的人,又死守著無聲無形的虛無之說。他們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鉆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確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極點,而達到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種有無不分、無思無欲的最高境界。在這里出現了“正理”、“般若”等名詞,前者是因明術語,后者則是佛學術語。劉勰博通經論,他使用“般若”之類的佛學用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正理”卻不是普通的佛學用語,其隸屬于因明術語的范疇,這一術語在《文心雕龍》創作前譯出的《方便心論》(相應品第四)中就已經出現。“若人能以此二十義助發正理,是人則名解真實論;若不如是,不名通達議論之法。”[1]《文心雕龍》中的“正理”與此處的“正理”完全取于同一個涵義,由此也可見,劉勰創作的《文心雕龍》受到了古因明思想的啟發,并吸取了許多古因明中邏輯思維方法。
此外,《文心雕龍》的研究專家王元化,還有周振甫、黃廣華和孫蓉蓉等,因明研究專家沈劍英等,也贊同《文心雕龍》的創作與古因明的傳入有密切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之所以立論綿密,同他運用佛學的因明學是分不開的。”[5]“倘撇開佛家的因明學對劉勰所產生的一定影響,那就很難加以解釋。”[6]而且“《文心雕龍》全書五十篇,由總綱、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和最后一篇《序志》所構成,這種結構形式與古因明五分作法形式極為相似。”[7]
總之,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古因明傳入中土以后,對中華文化產生影響,但是通過支離破碎、零零散散的資料分析,足以看出古因明與其他佛教思想一起對中國文化層次的影響和啟發,《文心雕龍》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不僅表現在嚴密的邏輯分析上,而且還在于整個論證體系的結構形式上。
[參考文獻]
[1]方便心論(卷1)[M]//大正藏(32卷):23,25,26,27,28.
[2]水月.古因明要解[M].北京:中華書局,2006:48.
[3]祖保家.文心雕龍選析[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1.
[4][梁]劉勰.文心雕龍[M].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116.
[5]周振甫.文心雕龍注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6.
[6]王元化.文心雕龍創作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304-305.
[7]孫蓉蓉.《文心雕龍》的產生和形成辨析[J].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2):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