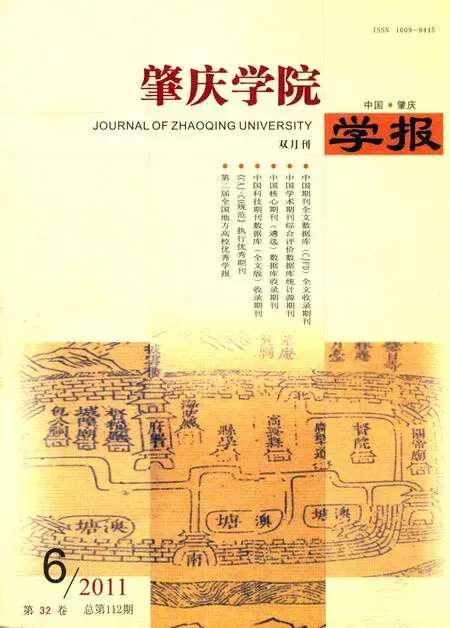論國際法強制執行的必要性
溫樹斌
(肇慶市監察局,廣東 肇慶 526040)
國際法是法律,具有強制性,因而應該被強制執行。反之,如果國際法不能被強制執行,則沒有強制性,因而就不是法律。這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推理。然而,仍有部分學者對此提出疑問。盡管這些疑問未必是國際法學界的主流觀點,但對之進行評析有助于在人們心中樹立起國際法強制執行的理念。
一、強制執行不必要論的主要學說
“否定論”認為國際法是實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否認國際法是法律,自然也不承認國際法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或者國際法中有存在強制執行措施的必要。“弱法論”認為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方法不如國內法那么多,也不那么有效,從而誤導人們否定或懷疑國際法的強制性或者其強制執行的必要性。兩種理論的共同出發點在于國際法中缺少統一的立法機關來制定法律,缺少統一的行政機關來執行法律,缺少具有強制管轄權的司法機關來適用法律,即缺少制裁措施來懲治國際不法行為、確保國際法的遵守。
“法律論者”也有對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提出質疑的。質疑來自于一枚硬幣的兩面:一是沒有強制性或缺少強制執行措施的規則仍然可以是法;二是即便國際法是法,也不必被強制執行。兩者的共同點是:國際法是法,但沒有強制執行的必要性。
(一)強制執行不是國際法的必要條件
為了論證國際法是法,部分歐美國際法學者直接對“強制性是法的標志”或者“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的論點進行攻擊。他們認為,強制性不是法的本質屬性,法不以強制執行為前提。國際法具有自己獨特的實施機制,即使沒有源于主權者的強制執行措施,也仍然是法。例如,德國國際法學者魏智通(W.G.Vitzthum)認為:“規范的強制性并非法的本質特征。同樣,是否成文化或者法典化也不是法的構成要件。換句話說,缺少實施保障的、難以識別的、非成文化的法同樣是法。”“按照制裁觀點看來,缺少制裁保障其強制實施的規則就不算是法。……但是這種惟制裁論不僅對國際法而言過于片面,因為強制性實施只是眾多選擇的一種。即使國際法主要靠人們的自愿遵守來實現,也不能說是國際法就失去了其法律屬性。 ”[1]2,41
美國法學教授費舍爾(Roger Fisher)認為,我們在國內背景下稱之為“法”的東西大多也是不可強制執行的(unenforceable)。例如,當美國國家作為被告卻又不履行對之不利的法院判決時,如何才能對之施加強制?“在國際范圍內不會聽到比國內更多的這樣的論點:由于政府不能被強迫,所以它們是無法無天的。”但國家大多是遵守法律的。“美國國家作為一個實體尊重憲法,部分原因是因為害怕自己不遵守時其國民可能會采取的報復性行動。……而在國際上,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外部力量是其他國家而不是其國民。一個政府決定違反國際法規則時,它必須要考慮其他國家可能作出的反應。”[2]
美國國際法教授達瑪托(Anthony D’Amato)對“強制性是法的標志”的觀點也持不同意見。達瑪托重點反對的是“暴力強制(physical coercion)為法所必需”的論點,而不是反對法的強制性的全部內涵。他認為:“暴力與法律、權力與權利的關系是偶然的而不是必要的,我們可以想象一個沒有暴力卻有法律的社會。在這個田園式的烏托邦里,強制執行沒有必要,因為存在著普遍的自愿遵守。”此時,“激烈的社會不滿(social disapproval)的表達,以及個別情況下的流放(ostracism),可以起到阻止少數人不遵守法律的作用。它們并不總是有效,但它們可以強有力地威懾那些可能考慮去違法的大多數人。”達瑪托的結論是:“武力強制不是法的必要組成部分。然而,我們在承認它是完全不必要時是不情愿的,因為我們看到太多案例:一個國家違反國際法卻因為缺少有效的執行機制而逃脫制裁。”[3]
(二)國際法的實施重在遵守,而不是強制執行
這種觀點的立論基礎是,國際法“得不到實施的問題總是存在;對實施能力的少許提高仍無法實質性改變這一基本事實。因此,我們的注意力應當放在改進國際法律體制的其他方面,以便即使沒有強制執行的改進,也會有遵守狀況的提高”。[4]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首推美國國際法學者亞伯拉姆·查伊斯(Abram Chayes)和安東尼亞·查伊斯(Antonia Handle Chayes)。兩人撰寫的《新主權》一書認為:“設計并將(威懾性的)制裁并入條約的努力大都是浪費時間。”由于制裁成本高昂、缺少合法性,所以,他們針對遵守的“強制執行模式”(enforcement model),提出了“管理模式”(managerial model)作為替代方案。后一方案“主要依賴于合作的、解決問題的、而不是強制性的路徑。 ”[5]
美國環境科學與管理教授奧蘭·楊(Oran R. Young)直截了當地指出:“強制執行在很多情況下無疑是實現遵守的充分條件,但沒有理由將之視為人類行為的多數領域的必要條件。”[6]路易斯·亨金(Louis Henkin)對國際法的強制執行也不太感興趣。他喜歡討論國際法的遵守,而不是強制執行,因為強制執行通常與警察力量和法院相關。“國家制定法律和接受該法律的權威時,表達了它們的自治。它們約束自己去遵守法律:遵守不是自愿的。但盡管不是自愿的,遵守也不是被強迫的。 ”[7]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任總干事約瑟夫·果德(Joseph Gold)基于自己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實現穩定的國際貨幣體制所采取的策略的敏銳觀察,對軟法(soft law)“情有獨鐘”。他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很少使用可適用的救濟程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協商和說服政策在促進調整和義務遵守方面并不比適用救濟程序的可能性小。”在果德看來,“硬法”的制裁程序會產生相反的(counterproductive)效果。[8]
分析表明,上述學者對國際法的實施狀況持樂觀的態度,認為現狀是正常的;但對其改進持悲觀的立場,認為制裁是不必要的。上述學者看重遵守機制的作用,認為該機制的改進有助于改變國際法的實施狀況;貶低制裁機制的作用,認為健全該機制反倒有害于國際法的實施。鑒于此,國際法應當完善促進遵守的法律機制。
二、對強制執行不必要論的反駁
如果說“弱法論”是“法律論”與“否定論”論爭中的第一次退縮,強制執行不必要論即為第二次。“弱法論”是承認國際法具有強制性的,只不過其強制性與國內法不同,相對較弱;“不必要”論從根本上否定了國際法的強制性,從而使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成為多余的。
(一)強制性、強制執行與法
關于國際法強制執行的第一種質疑,其理論根源在于錯誤地割裂了強制性、強制執行與法之間的邏輯關系,否認強制性是法的基本屬性,否認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
中國法理學一般認為,強制性、強制執行與法之間密不可分,這一點幾乎沒有什么爭議。沈宗靈教授指出:“對任何社會的法來說,都不可能指望全體社會成員都會遵守。因此,法必須由國際強制力保證其實施,也即對違法行為實行不同形式的追究以至制裁。”[9]張文顯教授認為:“是否具有國家強制性,是衡量一項規則是否是法的決定性標準。如果一部‘法’雖然是由國家機關制定的,但人們千百次違反它卻不受任何制裁,很難說它是真正意義上的法。”[10]
在國外法理學上,“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的論點一直存在爭論。大多數學者持肯定的態度。例如,意大利著名法哲學家韋基奧(Giorgio Del Vecchio)宣稱:“哪里沒有強制力,哪里就沒有法律。”[11]美國法理學家愛德溫·帕特森(Edwin W.Patterson)認為:“每一種法律在某種意義上都具有一種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每一法律體系和每一項法律規定的必要特征。”[12]美籍奧地利國際法學者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認為:“凡設法以制定這種強制措施(制裁——筆者注)來實現社會所希望有的人的行為,這種社會秩序就被稱為強制秩序(coercive order)。它之所以是這樣一種秩序,就因為它以強制措施來威脅危害社會的行為。”[13]
少數學者對 “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的論點提出了反對意見。主要理由在于:“人們服從法律秩序、履行法律義務,在很多——即使不是大部分——情況下,不是由于恐懼法律秩序所規定的制裁,而是由于其他理由。”“法律是一種安排,……我們可以確立的是,在聯合(association)這一概念的范圍內,法律是一種組織,就是說,一種規則,它分配該聯合的每一成員在共同體中的地位及其義務;……解決爭端所依據的法律規范,供判決之用的規范,只是一類具有有限功能和目的的法律規范。”“在每個法律制度中都有一些具有促進性的(facilitative)規范而不是強制性的規范。”[14]361比如,關于言論自由或選舉權等賦予公民權利的授權性規范,就不是強制性的。
上述關于法的強制性的爭論是可以調和的。當我們說法具有強制性、法需要強制執行、法需要有制裁時,是就整個法律體制、法律秩序而言的。“就整體而言,強制力乃是法律制度的‘一個必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認為所有類別的法律規范都具有強制性、都需要強制執行、都以制裁為保障的觀點是極端化的認識。因為,法律規范可劃分為不同類別,不同類別的法律規范的性質存在差異。英國法學家哈特(Herbert C.A.Hart)將法律分為兩類規則:“第一類規則(rules of primary type)設定義務;第二類規則(rules of secondary type)授予權力、公權力或私權力。”“其他一些法規在這樣一些方面不像命令,即它們不要求人們去做什么,卻可能授權給人們;它們不強加責任,卻提供在法律的強制框架范圍內自由創設法律權力和義務的便利條件。” 按照哈特的理解,由于法的多樣性,并不是所有的法律規范都有強制性,比如授權性規范;但授權性規范也是在法律的強制框架內,所以法在整體上是有強制性的;設定義務的規范不僅有強制性,而且需以制裁為保障。換言之,法的強制性是一個法律體制、法律秩序的基本屬性,與法律規范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必須指出,法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這是從終極意義上講的,即從國家強制力是法的最后一道防線的意義上講的,而非意味著法的每一個實施過程,每一個法律規范的實施都要借助于國家的系統化的暴力。也不是說,國家強制力是保證法實施的惟一力量。”[10]78實際上,反對法的強制執行的學者并不否定法需要制裁,只是部分法律規范不需要而已;若以部分法律規范不需要制裁為理由否定法的強制性,不僅與法的現實不符,而且在邏輯上也有以偏概全之嫌。簡言之,“強制性是法的標志”或“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的爭論不是出于同一視角或位于同一層面上,贊成者是從法的整體來講的;反對者是從法律規范的角度來看的,所以,兩種對立的觀點本質上并無矛盾。
在 “強制性是法的標志”、“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的法理前提下,如果我們認為國際法是法律,就必須要承認國際法具有法的一般屬性,即強制性。強制性作為國際法的內在屬性,必然有其各種外在表現,即強制執行措施。為了證明國際法是法律,去否定法理學上已有的定論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有悖于人們對法的強制性的通常理解以及對法的強制執行的習慣心理。國際法之有別于國內法,不在于其不具有強制性或強制執行措施,而在于它具有與國內法不同的強制性,以及自身獨特的強制執行機制。國際社會的結構特征決定了國際法的強制執行不可能由凌駕于主權國家之上的權威來實施,因此不是自上而下(top-down)的強制,而主要是水平(horizontal)的強制;不是集中的(centralized)強制,而主要是分散(decentralized)的強制。
(二)法的遵守與法的強制執行
關于國際法強制執行的第二種質疑,本質上涉及的是法的遵守和法的強制執行之間的關系。其核心是改善國際法的遵守比實現其強制執行更容易;只要改善國際法的遵守機制,即便是沒有強制執行,國際法的實效也不會更差。
法的遵守的價值得到了普遍認同。無論是在國內法律體系還是國際法律體系中,遵守都是法的實施的最主要的途徑,絕大多數法律主體都能自覺和自愿地遵守法律,而不是故意追求對法律的違反。如果法是經常被違反的、經常需要運用暴力加以維持的,則該法要么是“惡法”,要么無法成為法。因此,與法的遵守相比,法的強制執行處于次要的地位。“一個法律制度之實效的首要保障必須是它能為社會所接受,而強制性的制裁只能作為次要的輔助性的保障。……強制只能用來針對少數不合作的人,因為在任何正常有效的國家中,須用制裁手段加以對待的違法者的人數遠遠少于遵紀守法的公民。 ”[14]364-365
法的遵守與法的強制執行之間的主次關系,在國際法上體現得更為明顯。也就是說,國際法的遵守比國內法的遵守更重要,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比國內法的強制執行更次要,因此導致了國際法的遵守與強制執行的重要性之間更強烈的反差。“在國際領域,正式的強制執行的作用是最小的;對遵守的任何分析必須考慮這一現實。”[16]國際法的遵守更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措施不如國內法那么有效、那么值得依賴。“違反國內法通常會有制裁,并且由國家的公權力來執行;個人無法對抗國家的制裁,但有可能逃避國家的制裁。在國際上有時明知國家違反國際法,卻無法予以有效的制裁,這確是國際法的一大弱點。但是國際法對違法的國家并非沒有制裁的方式,只是與國內法不同,且有時并非有效或且無法執行。”[17]原因之二,在于國際法是國家間協調意志的體現,具有比國內法更穩固的遵守基礎。國家對自己所接受的國際法,有更大的遵守意愿。“自相矛盾的是,不存在一個國際立法機構是大多數國家遵守國際法的一個原因。各國自己立法,與更高的權威強加法律的情況相比,更傾向于遵守法律。”[18]
然而,無論國際法的遵守如何重要,它都不可能取代國際法的強制執行。“至少是象征性(symbolic)的、正式的強制執行的期望依然是任何法律體制的特征。”[19]這不僅是因為,在理論上,否定國際法的強制執行就等于否定了國際法的強制性,從而否定了國際法是法,而且是因為,在實踐中,只要國際社會還有違法行為,只要這些違法行為為國際社會所無法容忍,國際法就需要強制執行。“遵守國際法的意愿依然是緊缺物。”[1]34這意味著,單純依靠遵守去實現國際法的效力是不完全的或者不可能的,或者說,僅靠自愿遵守來維持的國際法是難以存續的。“只要在有組織的社會中和在國際社會中還存在大量的違法者,那么法律就不可能不用強制執行措施作為其運作功效的最后手段。”[14]368
三、強制執行對于國際法不可或缺
(一)理論根據
多年來,關于國際法是不是法、是什么樣的法的爭論,一直以國際法上有沒有強制執行措施、是否有必要存在強制執行措施為焦點。人們已不再糾纏于奧斯丁(John Austin)對法的定義的可適用性問題,而是聚焦于國際法的強制執行。國際法可以被強制執行嗎?如果不能被強制執行,怎么可以稱之為法呢?
關于國際法強制執行的第一種質疑試圖“釜底抽薪”式地解決問題,從法的一般理論上去否定強制性、強制執行與法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系。其邏輯結果必然是將法與道德、宗教等社會行為規范相混同,將國際法歸入國際道德的范疇。
筆者認為,歸根結底,國際法強制執行的法理基礎在于國際法是有強制性的,是有拘束力的[20]。這種拘束力不同于國際道德或國際禮讓,只依靠政治的或道義的力量加以維持。國際法的拘束力是法律上的(legally binding),是以強制執行措施為保障的,這是國際法學界的主流認識。“歸根結底,國際法之別于國際道德,最基本的一點是,國際法是于必要時有外力強制執行的。”[21]“國際法并不是沒有強制力,沒有強制力的法就不能成其為法。”[22]否定國際法強制執行必要性的觀點,必然會在論證國際法是法律的命題時陷入邏輯上的困境,在實踐中也無法令熟悉國內法律生活的人們相信國際法是真的法律(real law)。退一步說,為了論證國際法是法律,去挑戰“強制性是法的標志”或“強制執行是法的必要條件”的命題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這不僅是因為法的強制理念已經深入人心,而且是因為前述魏智通(W.G.Vitzthum)等人的觀點只是以某些類別的法律規范不需要強制執行、或者某些類別的強制執行措施不是絕對必要的為立論基礎,邏輯上存在明顯的“一葉障目、不見森林”的錯誤。
(二)實踐基礎
與國內社會成員數量眾多的情況不同,僅有200個左右的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更需要相互依賴而不是“以鄰為壑”,更容易實現合作而不必“反目成仇”。與強制執行相比,主權國家更希望彼此間都能遵守共同制定或接受的國際法。“在傳統國際法上,條約和習慣法被認為國際法的正式淵源,準確地說,是因為,除了執行的有效性問題外,它們還有很好的機會引發對其他國家遵守的共同信心和有效期望。”[23]即便是發生違反國際法的情形,國家也更愿意選擇強制執行以外的方法解決相互間的爭端。所以,國際社會更熱衷于國際法的遵守機制,著力于發展促進國際法的遵守、預防國際法的違反以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措施。
但是,國際社會的現實需要決定了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是不可或缺的。我們不能忽視這樣的現實:國際法的遵守狀況時常難如人意,違法乃至犯罪行為時常無法避免,要求違法者自愿承擔國際責任時常困難重重。國家對個體利益的追求使國家敢于冒違法之風險、敢于實施違法之行為、敢于逃避法律之制裁。“最終,不顧法律的國家會斷定風險和潛在的制裁不比可能獲得的利益更重要,選擇了違反法律。這就像個人選擇違反國內法一樣。 ”[24]
另一方面,國際法律制度的現實狀況證明了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是客觀存在的。實踐表明,國際法中自始即存在著強制執行機制。傳統國際法依賴于反報、報復、自衛或者戰爭等自助(selfhelp)措施來強制執行。現代國際法揚棄了傳統國際法的強制執行措施,廢止了以武力相威脅或使用武力的措施,創立了國際組織集中化的制裁機制,發展了國際司法機關的強制性爭端解決機制和刑事制裁機制。因此,國際法強制執行在理論上是必要的,在實踐上是有相關法律制度加以證實的。
[1] 格拉夫·魏智通.國際法[M].吳越,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ROGER F.Bring Law to Bear on Governments[J].Harvard Law Review,1961(74):1 134-1 135.
[3] Anthony D’Amato.International Law:Process and Prospect[M].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95:6-10.
[4] DAMROSCH L F.Enforcing International Law Through Non-forcible Measures[J].Recueil Des Cours,1997(269):22.
[5]CHAYES A,CHAYES A H.The New Sovereignty: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Agreements[M].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2-3.
[6] YOUNG O R.Compliance and Public Authority:A Theory with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s[M].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9:25.
[7] HENKIN L.International Law:Politics,Values and Function[J].Recueil des Cours,1989-IV(216):67.
[8] GOLD J.“Pressures”and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J].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1974(7):427.
[9] 沈宗靈.法理學[M].3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7.
[10] 張文顯.法理學[M].3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8.
[11] VECCHIO G D.Philosophy of Law[M].translated by T. O.Martin.Washington,1953:305.
[12] EDWIN W.Patterson.Jurisprudence:Men and Ideas of Law[M].Brooklyn:Foundation Press,1953:169.
[13] 漢斯·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沈宗靈,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19.
[14] 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修訂版.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
[15] 哈特.法律的概念[M].張文顯,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83,50.
[16] MICKELSON K.Carrots,Sticks,or Stepping-stones:Differing Perspectives on Compli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aw[C]//THOMAS J.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98:36.
[17]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M].臺北:三民書局,1998:38.
[18] AKEHURST M.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M].Boston:Allen&Unwin,1987:32.
[19] HANDL G.The Rocky Road From Rio: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J].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1994(5):330.
[20] 溫樹斌.國際法強制執行的法理基礎[J].法律科學,2010(3):80-86.
[21] 王鐵崖.國際法引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
[22] 趙理海.國際法基本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6.
[23]OKUWAKI N.The Changing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Can Voluntary Compliance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esent Nation-state System[C]//THOMAS J.Trilater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Legal Issues:From Theory into Practice.New York:Transnational Publishers,1998:73.
[24] Vaughan Lowe.International Law[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33.
- 肇慶學院學報的其它文章
- 高校校園文化的意識形態解讀
- 中小學美術教育的價值取向及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