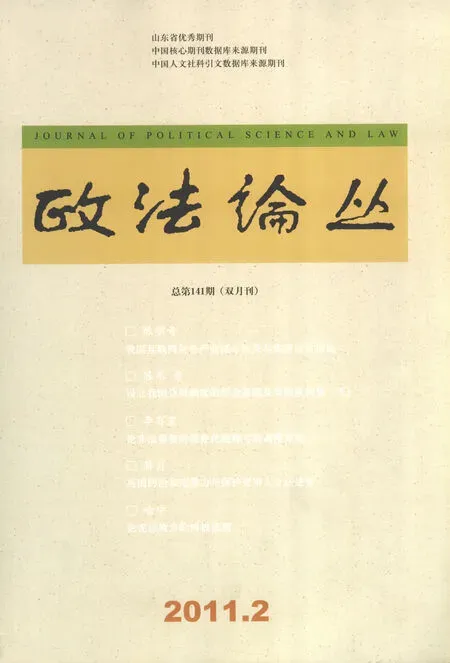流氓罪廢止后原司法裁決效力的憲法解讀
王世濤 湯喆峰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流氓罪廢止后原司法裁決效力的憲法解讀
王世濤 湯喆峰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6)
中國刑法于1997年已經廢除了流氓罪,但公民牛玉強卻將因流氓罪服刑至2020年。從憲法學意義上對本案進行解讀似乎更具說服力,即生效判決既判力的相對性,法的安定性和實質正義之間的相互平衡對我國刑法溯及力的影響,公民平等權的特殊面向,形式法治意義下罪刑法定原則的局限性,以及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憲法涵攝。
流氓罪 司法既判力 形式法治 法的安定性 憲法解讀
據《法制晚報》2010年12月1日報道,27年前,北京青年牛玉強因為和朋友搶了一頂帽子并打了一架,被法院以流氓罪判處了死緩。20年前,牛玉強因身患重病被保外就醫,在北京治療期間娶妻生子。2004年,由于超時未歸,牛玉強的刑期被順延,這樣牛玉強因流氓罪將在監獄里服刑至2020年。而流氓罪在13年前已經從刑法條文中刪除。針對該案,刑法界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依據刑法中的“罪刑初定原則”,除非有證據證明當初的案件有錯誤,才可以撤銷原判決。否則,應繼續執行原判決。①另一種觀點認為,雖然目前在法律上依據不足,但是本案應當撤銷重審,否則不符合法律精神。[1]筆者認為,以上兩種解釋都不能令人信服或者都沒能消除人們對于該案的疑惑,這體現了以部門法理論解釋自身問題所暴露出來的法學理論的窮困。如何對上述案例給予有力的論證,本文從憲法學的角度進行嘗試,試圖給予更有說明力的解釋。②
一、司法既判力的絕對化?
司法機關的生效判決產生既判力,但既判力是否具有絕對意義呢?既判力作為訴訟法學的基本范疇是指確定的終局判決所具有的拘束力。[2]既判力是法院判決所生之法律效力,該法律效力既拘束爭議之當事人使其不得再就判決內容再做爭訴,又指向做出判決之法院使其不得任意變更判決。既判力原則最早可以追溯到羅馬法時期的訴權消耗理論。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以不同方式從羅馬法中繼受了既判力原則。有學者將既判力原則的理論基礎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國家至上主義、‘休訟’主義、訴訟經濟主義、人權主義”。[3]可以說,司法既判力集中反映了國家的法秩序與公民的權利保障之間的緊張關系。當然,司法既判力也蘊含著“訴訟經濟主義”的考量,所謂“訴訟經濟主義”是指運用成本與收益分析的經濟學工具,將司法活動進行一定程度的量化權衡。其目的是節約司法成本提高審判效率,防止當事人就同一糾紛反復爭訟,從而使有限的司法資源的效益實現最大化。司法救濟是一種稀缺的公共資源,當事人無休止的纏訴必然使得司法系統難以高效有序運轉,而使其他需要司法救濟者的權利失去了機會。
依據傳統國家主權理論,國家對內具有至上的權威。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之所以具有法律上的權威與效力,正是因為司法機關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因此,為了維護司法機關的權威,必須由國家宣稱和確認司法審判的效力。這種效力不僅體現為對當事人的拘束力,而且體現為法院自身對其所做出判決的羈束,不得任意變更,即“這種確定判決所表示的判斷不論對當事人還是對法院都有強制性適用力,不得進行違反它的主張或判斷的效果”[4]P156然而,隨著近代以來人權意識的覺醒,傳統國家主權理論的式微,人們開始重新解釋既判力原則。人們意識到既判力原則可以防止國家因同一事由反復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從而有效保障當事人的人權。無論英美法系中的“禁止雙重危險”原則,還是大陸法系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則,都是從保障人權的角度在刑事訴訟領域內重構既判力原則。因此,許多國家將“一事不再理”原則從刑事訴訟法原則上升為一項保障人權的憲法性原則加以確認。
盡管如此,既判力原則有可能與人權保障相背離。這是因為,既判力原則在禁止國家以反復追訴之形式侵害當事人權利的同時,也阻礙了當事人對損害自己權益的終局裁決的救濟申請。③質言之,如果當事人無法通過再審等其他法律制度獲得相應法律救濟,此時既判力原則雖維護了司法權威和降低了司法成本,但卻阻卻了當事人權利救濟的實現。
如果既判力原則的人權保障功能無法實現,那么既判力原則的“訴訟經濟主義”與“國家至上主義”的價值是否具有正當性呢?其實總結各國的司法實踐,絕大多數終局判決的當事人是通過再審等法律程序進行救濟。只有在當事人的人權受到了較為嚴重的侵害,以至于維持原判將嚴重背離憲政要求時,才可能通過人權保障原則否定既判力進行救濟。④雖然對這些案件進行審理必然會增加一定的司法成本,但是由于其總量極少,故并不會造成過重的司法負擔,也不會影響司法系統正常運轉。根據比例原則,保障公民人權免受嚴重侵害優于總量上較為輕微的司法負擔。⑤也就是說,總體上輕微的司法負擔不得成為犧牲個案中重要人權的理由。另一方面,法律的權威除了其安定性、可預測性外,根本在于其正義性。具備正義性的司法判決應當與現行普適價值相一致,否則司法判決就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當然,在二者之間的沖突尚不明顯時,為了保證法的安定性,輕微的正義性瑕疵應當容忍。但牛玉強案中,原判決已經嚴重違背了現行普遍認同的法律價值。亦即出現了拉德布魯赫所稱的“制定法上之不法”,因此,法的安定性必須向人權保障原則讓步,因為“實證法與正義之間的矛盾達到了一個如此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作為‘不正當法’的法律則必須向正義讓步”。[5]P232此時恪守既判力原則并不能維護國家與法的權威。相反,由于缺乏基本的正義性,國家與法淪為純粹而嚴酷的暴力工具。
在牛玉強案中,一方面既判力的適用失去其人權保障的價值,另一方面又無法有效地實現節約司法成本與維護法律秩序的功能。因此,應當基于人權保障原則及比例原則否定已經喪失合理性的司法判決的既判力,這樣不僅有助于保障當事人的權利,而且也無損于法律的權威性和司法的效益性。在本案中,根據我國現行法律規定,牛玉強已無法通過再審程序尋求權利救濟,因此為保障牛玉強免受不義之法的制裁,只能否定已經產生的司法既判力的適用性。對于此種情形是否構成對既判力原則的突破,則需要從憲政層次進行價值上的衡量與取舍,也需要對既判力原則做更深層的考查。
二、“從舊”還是“從輕”?
1997年我國《刑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了“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即原則上新法不得溯及既往,但是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新法比舊法罪輕的則具有溯及力。事實上,“從舊兼從輕”溯及力原則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情況進行處理。這兩種情況又分別建立在不同的理論基礎之上。
其一,以法的安定性為基礎的“從舊”原則。法的安定性并不限于部門法的范疇,而是法治的基本屬性。法的安定性通過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規范形成穩定的法律秩序,并依據這種穩定的秩序形成對自身行為結果以及他人行為方式的合理預期。另一方面,維護法的安定性避免了以未來的法律來約束現在的行為的不合理性。法律規范對人們的行為具有指引性作用,只有在人們明確知曉法律并具有遵守可能性的前提下,才產生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溯及既往的法律因違背法治原則而為各國立法所禁止。可見,“從舊”的溯及力原則是從法的安定性從發,既保證人們免受過于頻繁的法律變化帶來的不穩定預期的損失,又使權利不受未來法律的侵害。
其二,以人權保障為基礎的“從輕”原則。在新法的溯及力上,“從輕”原則應視為“從舊”原則的例外性規定,體現了人權保障原則的價值優位性。原因在于,第一,人權保障是憲政價值的核心,幾乎所有法律原則的正當性都要立足于人權保障基礎之上。法的安定性原則歸根到底也是為了保障人身、自由、財產等基本人權不受侵害,而這些權利正是人權這一抽象概念的具體法律形式。當法的安定性嚴重危害人權保障時,當事人可以直接依據憲法人權保障原則主張權利。第二,法的安定性避免了法律變動給人們帶來的不利影響,但這種權利保護主要方式是維持法律狀態的靜止性,因此只能消極地防止侵害的發生。對于已經受損之正當權利,則不能積極地主張救濟。人權保障原則則不同。人權是一種綜合性和本源性的應然權利,對實在法具有批判功能,[6]可以作為權利主張的正當性依據。當受到侵害時,當事人可以依據人權保障原則行使救濟的請求權。因此,人權保障原則既可以積極地主張權利,又可以消極地防御侵害。第三,由于法的安定性主要是防御性的,所以其意義主要體現在宏觀層次上。在多樣性的個案中,法的安定性反而有可能造成實質非正義的結果。人權保障原則既蘊含于整個法律體系的理論基礎之中,又可以適用于特定個案。第四,法律的滯后性導致法律適用時已經喪失了法律規范的現實基礎,加之立法本身不可能無瑕疵,因此,固守法的安定性并不利于法治的進步和實質正義的實現。因此,形式的法的安定性需要實質的人權保障原則進行補充和調節。
綜上,“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宏觀上注重維護法的安定性,微觀上注重個案中個人權利的保護。依據法律的目的性解釋,“從舊兼從輕”原則的確立,以人權保障的憲政價值理念為基礎。因此,在牛玉強案中,對其應當 “從舊”維護原判還是“從輕”改判其無罪,應依照該原則的立法目的出發。只有依據“從輕”原則改判牛玉強無罪才能真實體現該原則的憲政價值,若依據“從舊”原則堅持原判則是對“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以及法的安定性的片面誤讀。
三、已決犯與未決犯的“分離”抑或“折衷”?
阻礙牛玉強案重新審理的主要障礙在于新刑法所謂“罪刑初定”的規定。我國《刑法》第12條第1款規定了“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第2款規定了“罪刑初定”:新刑法對其施行前已做出生效判決的行為無溯及力,而不適用第1款“從舊兼從輕”之規定。也就是說,“罪刑初定”是一種對已決犯和未決犯區別對待的分離主義。按照這一規定,新刑法雖然已經刪除了流氓罪的有關規定,但對牛玉強卻無溯及力。
事實上,“罪刑初定”是與既判力原則和溯及力原則相關聯的。前者維持依據舊法所做出的判決,后者在審判中適用舊法。從結果上而言,二者都是對舊法的適用,但既判力原則對新法較輕時的例外情況并不予以考慮。因此“罪刑初定”對已生效判決只產生適用既判力原則時的效果,而根本不考慮是否適用“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之問題。但“罪刑初定”又不等同于既判力原則,因為既判力原則是針對所有終局判決的原則,而“罪刑初定”只適用于新舊刑法銜接的情形。這意味著“罪刑初定”完全是從形式法治的角度出發而得出的結論。為了保證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同時實現,需要對其進行憲法審查。可以說,我國《刑法》第12條第2款的合憲性瑕疵是不難發現的。顯然,新刑法對于同一行為以是否做出已生效判決為標準分別采取不同的處理方式,這違反了憲法的平等原則。平等原則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權利,不受任何差別對待,要求國家給予同等保護的原則”,[7]P223-224平等又可以分為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形式平等是指“對所有的人不分其身份或地位適用法律”,實質平等是指“立法者要根據平等原則制定法律,立法過程受平等原則的約束”。[7]P223雖然平等原則承認合理差別的存在,但是任何法律上的差別對待都需要有正當理由。判斷差別正當性的基本原則一般包括:“是否符合作為憲法核心價值的人的尊嚴原則;確定差別措施的目的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采取的手段與目的之間是否有合理的聯系等”。[7]P227“罪刑初定”的刑事立法可能損害部分當事人的人權,同時并不具備差別對待的正當理由,因此違反了實質的平等原則。進一步而言,刑罰屬于對公民財產、自由和生命等基本權利的限制甚至剝奪,必須有合法依據方能做出。當作為刑罰依據的罪名被廢止后,對當事人的刑罰從法律上講已經缺乏依據。因此,從人權保障的角度而言,對當事人的刑罰應當做出相應變更,否則判決將失去實質上的正當性,因為違背了憲法的公民權利平等保護的原則。
當然,形式法治并不必然損害實質正義之實現,關鍵在于對二者區分不同條件進行調和與取舍,力求最大限度地實現二者的統合。具體到“罪刑初定”的規定中,就是要將其區別對待之理由置于實質平等原則之下進行考查。由于對公民權利進行平等保護是一項憲法原則,在價值上具有優先性,因此應當重新確定是否適用“罪刑初定”的標準,以期最大限度地平等保障公民權利。
實踐中,對已決犯和未決犯采取不同處理方式的“分離主義”已經受到挑戰。例如法國采取了更為合理的“折衷主義”原則,即對已決犯而言,新法減輕處罰的罪名無溯及力,但新法廢止的罪名對其有溯及力,應當將有罪判決變更為無罪判決。[8]折衷主義區分了有罪變更為無罪和重罪變更為輕罪兩種情形。前者涉及定罪問題,關系到當事人的重要人權,同時又便于認定,不易產生爭議,故訴訟成本較低。后者涉及量刑問題,關系當事人的人權則較為輕微,重新審理又易于產生爭議,訴訟成本較高。為避免現實性的困難,對于部分當事人所受之輕微損害,折衷主義選擇了容忍。這種區分標準兼顧了形式法治與實質正義,因此從憲法平等原則來看,這種區別對待是具備合理性的。因此,法國的折衷主義值得借鑒。
由于牛玉強案實際上涉及流氓罪被廢止后,牛玉強本人罪與非罪的問題,因此,按照折衷主義原則,牛玉強案不應適用我國《刑法》第12條第2款之規定,而應適用第1款“從舊兼從輕”溯及力原則的規定改判無罪。只有如此,才體現了對其權利的平等保障,實現了實質的平等。
四、罪刑法定意味著“有罪必罰”?
現代刑法的憲政理念即是注重保護犯罪嫌疑人的正當權利。由于刑事判決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有著重要影響,因此法律對刑事審判的控制十分嚴格。為了防止法官的恣意與司法權力的專橫,在刑事判決中,法官必須恪守罪刑法定原則,客觀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社會危害性,同時最大限度地排除個人喜好、社會輿論壓力等因素干擾,從而達到既有效懲治犯罪,又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權的目的。罪刑法定強調定罪量刑必須有法律依據,禁止隨意性的擴張解釋和類推定罪,易言之,“法無明文不為罪,法無明文不為罰”。因此,西方傳統罪刑法定原則的邏輯是“無法,無罪,則無刑”。 然而我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進行了擴展。我國《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也即我國刑法不僅肯定了傳統罪刑法定的理念,同時逆推得出了“有法,有罪,則有刑”的結論。對于我國刑法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創新,有必要予以審視。
“罪刑法定原則作為起源于啟蒙時代自由、民主、人權精神的法治原則,其根本作用在于防止國家刑罰權的濫用,以保護弱小的個人,其根本機能是保障人權”[9]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基于人權保障的價值理念,但我國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有法,有罪,有刑”的法律邏輯卻與上述理念有所背離,實際上是“強調有罪必罰和出罪從嚴,以確保公民的違法行為必然受到法律追究,其根本目的在于確保國家刑罰權的有效行使而不致落空,體現的是懲罰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保護機能”。[9]從刑法本身的特質來看,“懲罰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保護機能”是作為整體的刑法的固有功能,但罪刑法定原則的目的并不在于強化國家刑罰權而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之人權。對權利的保障總是通過對權力的限制來實現的。罪刑法定原則一方面依照法的安定性的要求,強調法律的明確性與穩定性,規定任何罪名都必須由法律明確規定,從立法的層次進行規制;另一方面要求刑事審判必須“以法律為準繩”,避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受到法官和司法權的恣意侵害。“有罪必罰”背離了人權保障原則的初衷,試圖以人權保障之手段,實現“懲罰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秩序”之目的,這實質上是出現了價值偏差與功能錯位。從理論上看,我國罪刑法定原則似乎是克服了西方刑法的片面性,既注重保護社會,打擊犯罪,又注意保障人權,限制司法權。[9]但實際上,“犯罪嫌疑人”不受非法之治及惡法之治,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蘊涵。甚至允許犯罪嫌疑人逃避不正當的立法所確立的刑事責任,是法治國家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有罪必罰”并非是對傳統罪刑法定原則的補充而是疏離。在實踐中,由于權力本身所具有的擴張性,過于強調“有罪必罰”必將對權力的擴張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則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威脅。
質言之,“有罪必罰”突顯的是刑法的懲罰功能,而不是權利保障功能。實際上,并不是所有以法律為依據的處罰都具有合理性和正當性。“形式上的法律依據是否具備內在的處罰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處罰了實質上不該處罰的行為,是檢驗其實質上是否合法的關鍵”。[9]依照刑法理論,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應當基于犯罪嫌疑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在現實生活中許多具有犯罪行為的外觀但實際上則不具備社會危害性,或者社會危害性很小。對于這些行為,如果按照“有罪必罰”的原則就不可避免地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權,最終也背離了刑法罪刑法定的的立法目的。在牛玉強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為屬于輕微違法行為,此時依照“有罪必罰”的原則對其處以刑罰實質上即不符合實質合法性原則的要求。“有罪必罰”從形式法治出發,進一步強化了國家的刑事處罰權,弱化了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這恰恰是以罪刑法定的名義走向了罪刑法定原則的反面。
五、輕罪重罰的該當性?
在憲政國家中,法律體系實質上就是實現憲政價值的體系。因此法律體系的建構應當滿足憲政價值要求。在諸多部門法中,刑法“最敏銳地體現著國家與公民的關系,以及社會的現實價值觀念和社會對于源于本身的弊病的責任感和態度。因此,比之于其他各部門法,刑法更應踏實地反映憲法的要求。”[10]P7所以說,“憲政架構下的刑事法應承載憲政所要求的價值理念”,[11]P6也就意味著從憲法學的角度而言,刑法的最終目的在于人權保障。這里的人權保障對象既包括守法公民,又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即所謂刑法既是良民的大憲章,也是罪犯的人權書。
刑法學界對刑法目的的研究似乎限于學科界限而忽視了刑法的憲政意義。傳統古典報應刑論認為刑罰與刑法的目的是統一的,即“刑法所以對犯罪人科以刑罰者,乃系報復作用”。[12]刑法學界已經認識到報應刑論的不足轉而提出相對報應刑論。相對報應刑論區分了刑罰與刑法的目的,認為“刑罰的目的只在于報應和個別預防”,而刑法的目的則不同,它“包括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社會基本秩序,直接目的則包括保護法益、預防犯罪、確認刑罰權和限制刑罰權”。[12]但如果以憲法學理論考查,“維護社會基本秩序”顯然不具備真正的最終目的性,而是更多體現了一種功能性——它是刑法實現憲法人權保障這一最終目的的手段。因此是否有助于保障公民的正當權利決定了對犯罪嫌疑人的刑罰是否“適當”。刑法中刑罰相適應原則以一般法治的比例原則為標準,包括適應性、必要性與均衡性三方面內容。[13]P55在刑法中,比例原則的適應性表現為對罪犯所處之刑罰能實現刑罰報復和個別預防的目的;必要性表現為對罪犯所處之刑罰在實現其目的的同時對罪犯正當權利損害最小;均衡性表現為刑罰產生之效益大于其不利益,即刑罰所保護的法益應大于受損之權利。按照罪刑相適應原則,對于一定的罪過,如果所處刑罰過輕,則不能滿足適應性之要求,即無法實現刑罰本身之目的,造成犯罪成本低于收益,難以遏止犯罪行為的發生,無法有效保障守法公民的權利免遭犯罪行為侵害,即不利于實現刑法之最終目的。如果所處刑罰過重,則違反必要性與均衡性之要求,雖然刑罰本身之目的的確可以實現,同時也能較為有效地震懾犯罪,似乎有利于實現刑法的最終目的。但事實上,在經過層層邏輯推演得出嚴刑峻罰能夠較好地保障守法公民的權利之前,罪犯的正當權利實際上已經被直接侵犯了。
牛玉強案的判決屬于后一種情況,對罪犯所處之刑罰與其罪過嚴重不相稱,故自始不能滿足比例原則的必要性與均衡性要求。即對牛玉強所處之刑罰所侵害的人權大于所保障之法益。在“嚴打”的特定時期,基于刑事政策的考慮,對特定犯罪進行的過于嚴厲的判決(在上世紀80年代的“嚴打”期間,在全國范圍內,“流氓”罪犯幾乎都被判處死刑,甚至搶一頂軍帽,曾被判死刑),由于有違憲政法治原則及比例原則,所以該司法判決不具有實質的合法性。因此,基于憲法原則,可以否定該判決的效力。更進一步,由于新刑法已經廢止流氓罪的規定,即意味對該行為重新做出法律評價。對不具備相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處以刑罰并不能實現刑罰報復和個別預防的目的。因此,對牛玉強所處之刑罰已經喪失了適當性,同時,由于完全背離了刑法的最終目的而不具有正當性。在新刑法的背景下,對牛玉強順延刑期已經完全背離了罪刑相適應原則,事實上是國家刑罰權對公民人權的侵害。可以說,無流氓罪的國家關押著流氓犯意味著與刑法目的價值的背離。
結語
以罪刑初定為理由主張順延刑期違背了憲法原則。當然,不能認為該罪犯因為流氓罪名被廢止而不應當承擔法律責任。罪犯應當通過改判,否定流氓罪的生效判斷及刑事責任。按照現行法律,對該流氓罪犯牛玉強可以適用刑法中較輕罪刑甚至可以給予行政治安管理處罰。由于該罪犯牛玉強已經在監獄服刑數年,體現了“罪刑相當”的原則。如果刑期折抵,牛玉強應當被釋放。否則,就會出現在一個廢除“流氓罪”的國家,過了幾十年,還有人因背負“流氓”罪名并承受不該當的法律責任的荒誕現象。更荒誕的是,如果按照這一邏輯,可能會出現這樣的一種推論:雖然“投機倒把”罪已經在1997年新刑法中被廢除,但按照舊刑法的規定,當下中國人幾乎無一不是“投機倒把”的罪犯,如果能夠查實在既往已經立案的嚴重“投機倒把”案件,而至今又沒有超過追訴期限,或者立案后逃避偵察不受追訴時效限制的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還要承受“投機倒把”的罪名并入監服刑呢?
“罪刑初定”恪守的形式法治,可能會導致這樣一種困窘:明知道自己是錯誤的,但只能將錯就錯。即使知道司法判決背離憲政價值和正義理念,但卻只能以法治的名義走向法治的反面。
注釋:
① 該觀點認為,所謂“罪刑初定”,即指我國《刑法》第12條第2款“本法施行以前,依照當時的法律已經做出的生效判決,繼續有效”之規定。
② 部門法學與憲法學研究具有互補性,正如憲法學研究不能局限于憲法本身,部門法學研究也不應僅僅在學科內循環論證。所以,一些刑法問題的根本或者完全解決不得不從刑法學理論外尋求證成。
③ 當然,如果當事人的權利受到終局判決的侵害,當事人可以通過再審、申訴等法律途徑尋求救濟,構成終審判決的補充與既判力原則之例外,但這仍然是以承認和尊重生效判決的既判力為前提的。
④ 牛玉強案之所以能夠引起極大的輿論關注,恰恰說明了這類案件的稀奇與極端。
⑤ 其實,繼續監禁牛玉強顯然比立即釋放牛玉強會更浪費司法資源。
[1] 辰光.牛玉強——最后一個流氓[N].法制晚報,2010-12-01.
[2] 葉自強.論既判力的本質[J].法學研究,1995,5.
[3] 葉自強.論判決的既判力[J].法學研究,1996,2.
[4] [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訴訟法[M].白綠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5] [德]G·拉德布魯赫.法律的不公正和超越法律的公正[A].G·拉德布魯赫.法哲學[C].王樸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6] 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7] 胡錦光,韓大元.中國憲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8] 李小銀.我國刑法溯及力原則的辯護與完善[D].2006年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9] 劉艷紅.刑法的目的與犯罪論的實質化——“中國特色”罪刑法定原則的出罪機制[J].環球法律評論,2008,1.
[10] 許道敏.民權刑法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
[11] 劉樹德.憲政維度的刑法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2] 周少華.刑法的目的及其觀念分析[J].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08,2.
[13] 周佑勇.行政法基本原則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ontheValidityofJudicialDecisionsafterAbolitionofHooliganism
WangShi-taoTangZhe-feng
(Law School of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116026)
Due to the crime of hooliganism, which had been abolished by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97, a Chinese citizen called Niu Yuqiang will be jailed until 2020.To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the case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sense seems more persuasive ,namely, the relativity of adjudged force principle; what's the impacts on the retroactivity of China's criminal law coming from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stability of law and substantive justice; civic equality; limit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under formal law; co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of principle of suiting punishment to crime.
crime of hooliganism; adjudged force principle; formal law; stability of law; constitutional explanation.
DF2
A
(責任編輯:張保芬)
1002—6274(2011)02—059—06
王世濤(1966-),男,遼寧撫順人,法學博士,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憲法學、行政法學;湯喆峰(1986-),男,江西九江人,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憲法學、行政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