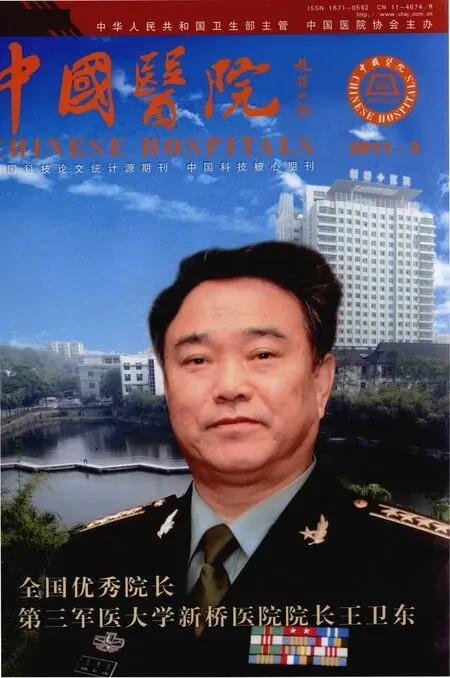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立法必要性與可行性分析
■ 黃宇鋒 楊 帥 田 侃 楊學偉
1979年4月,我國政府積極響應并參與WHO基本藥物行動計劃,成立了“國家基本藥物遴選小組”,開始著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制定工作。回顧30多年的實踐經驗和實施障礙,筆者認為,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立法時機與立法條件已經較為成熟,政府應加強對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的立法工作,并制定具體的配套措施,從根本上提高基本藥物制度的強制力和可操作性。
1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
基本藥物制度是全球化的概念,目前尚未有較明確的定義。孟銳教授[1]認為,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是指國家通過對基本藥物的研制、生產、流通、使用等環節制訂行為準則和推行措施并實施宏觀指導和監督管理,旨在保證社會公眾基本藥物需求,提高藥品的可獲得性和可支付性,合理配置醫藥資源,有效協調醫療、醫藥、基本衛生保障體系之間關系的一項可持續性發展的方針制度。
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具有如下主要功能:一是保證基本藥物的生產與供應,確保社會公眾能夠方便、及時地通過各種渠道獲得應有的治療藥物,從而提高藥品的可及性。二是確保基本藥物價格的合理性、報銷體系的完備性,從而提高藥品的可負擔性。三是確保研制、生產與供應的基本藥物能針對所有常見疾病,實現安全、有效的治療,從而提高藥品使用的合理性[2]。
2 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立法的必要性
2.1 現有的執行依據以政策文件為主,強制力不足
制定政策往往是國家意志得到體現和有效執行的先決條件,但政策的能動作用有限,法律才是最具外在強制性的社會規范,它通過設定權利義務、責任制裁來調整社會關系。社會公眾的法益只有獲得法律體系的支持才能得到根本保障。而且,法律以自由為最高的價值目標,體現了人性最深刻的需要。
1997年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規定“國家建立并完善基本藥物制度”。2006年1月l1日,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整頓藥品生產和流通秩序,保證群眾基本用藥。” 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重點強調“建設覆蓋城鄉居民的藥品供應保障體系,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保證群眾基本用藥”。200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醫改意見》)再次提出:“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 2009年8月18日,衛生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聯合發布了《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并配套下發了《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管理辦法(暫行)》和《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配備使用部分)》。由此,其中涉及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以規范性文件為主,缺乏強制性的推行辦法,也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雖然《實施意見》帶有規章性質,但實質屬于政策性文件,效力層次較低,而且《實施意見》中提出的思路和措施過于籠統,可操作性不強,缺乏違法行為的定性與處罰規定,各地制定的暫行或試行辦法也以指導性為主,亟待通過強化基本藥物制度的法律地位來提高其強制力,以保證社會公眾對基本藥物的自由需要。
2.2 基本藥物制度的認知水平較低
由于基本藥物制度的立法缺失,相關執行部門對其重視程度不夠,對該項政策缺乏有力的普及性宣傳,許多醫藥工作者甚至政策制定者都不甚了解基本藥物。一項關于對基本藥物認知及臨床應用情況的調研顯示,接受問卷調查的醫務人員中,熟悉基本藥物的僅占41.37%。相較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概念,國家基本藥物概念的知曉率最低,醫務人員對于基本藥物了解得并不全面,有72.11 %的醫務人員未參加基本藥物知識的培訓或學習[3]。因此,需要通過立法引起全社會對基本藥物制度的重視程度,提高醫務人員對基本藥物的含義、種類、使用、報銷以及實施基本藥物制度的目的和意義的認知水平,使其在臨床治療中自覺使用并向患者推薦基本藥物。
2.3 基本藥物目錄的地位不明確
現行基本藥物目錄包括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國家基本醫療保險藥品目錄、社區衛生藥品目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藥品目錄、鄉村醫生用藥目錄、醫院處方集、零差率銷售的藥品目錄等,分別由不同的行政部門頒布和管理。眾多層次的基本藥物目錄在不同層面發揮著作用,但缺乏統一協調性,使得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作用無法充分顯現[4]。因此,為保證基本藥物制度的執行一致性和徹底性,需要通過立法還原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的法律和主導地位。明確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藥品目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報銷藥物目錄應逐步與國家基本藥物目錄相統一。
2.4 低價及治療罕見疾病的基本藥物供應不足
由于目前我國對基本藥物的供應采用集中招標、統一配送的模式,在藥品市場營銷中利潤導向又尤為突出,導致一些利潤微薄或治療罕見疾病的基本藥物逐漸失去了生存空間,供應十分困難。如用于骨髓移植手術過程中抗排斥反應的免疫抑制劑“環磷酰胺”,因價格便宜,大部分生產企業都不愿意生產,導致對白血病患者來說的“救命藥”在市場上已很難找到[5]。因此,有必要立法對基本藥物的生產方式進行二元化劃分,即對于市場供應充分的基本藥物應采用非定點生產方式,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對于治療罕見疾病、市場供應短缺的基本藥物應采用定點生產方式,由政府出資給予生產企業相應的補貼。
2.5 醫療機構不合理用藥現象嚴重
由于缺乏基本藥物使用干預機制,臨床工作中開大處方、不合理處方現象較為嚴重。在藥品不合理使用帶來藥品費用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藥源性疾病上升,抗生素、激素等的濫用尤其嚴重,大城市兒童竟有半數以上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6]。《國家基本藥物目錄》和《中國國家處方集》僅具有指導性,不能有效保證基本藥物制度的合理用藥原則在醫療機構中得到貫徹落實。因此,需要成立基本藥物工作小組,制定評估指標體系,考查醫療機構基本藥物的處方使用情況,考核結果作為醫療機構評級標準之一,并以立法的形式予以體現。
2.6 基本藥物的臨床使用率較低
《醫改意見》中提出“通過實行藥品購銷差別加價、設立藥事服務費等多種方式逐步改革或取消藥品加成政策。”但由于部分地區政府財政補貼投入不足,藥品費用在醫療機構的總收入中占有較大的比例,取消藥品加成政策無疑會影響當地醫療機構的發展,導致基本藥物的臨床可及性偏低。盡管通過設立藥事服務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醫療機構的經營困境,但其效果與藥品加成銷售無本質差別,“看病貴”問題難以得到根本解決。立法設立藥品銷售差率上限不僅能夠減輕政府部門的財政壓力,而且能夠降低基本藥物制度在醫療機構中的推行阻力,減輕患者的看病負擔。
3 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立法的可行性
3.1 現有政策法規為基本藥物制度立法奠定了基礎
《憲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國家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現代醫藥和我國傳統醫藥。”基本藥物制度作為醫療衛生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其進行立法推行符合憲法的精神。《藥品管理法》、《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等涉及藥品管理的法律、法規、規章對藥品的研發、生產、經營、使用、說明書和包裝、價格、廣告管理等進行了規定。基本藥物作為藥品的一種內在形式,對其管理同樣適用上述規定。此外,《執業醫師法》、《處方管理辦法》、《招標投標法》、《政府采購法》主要涉及基本藥物的使用和供應管理,理應作為制定基本藥物制度推行辦法的依據。《實施意見》和其他規章性質文件如《河南省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實施辦法(暫行)》也為基本藥物制度立法奠定了基礎。
3.2 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為基本藥物制度立法提供參考
澳大利亞在2000年正式制定并全面實施了國家藥物制度。在藥品的價格管理方面,政府對一些臨床必需的藥品實施價格補貼,從而保證市場供應。在藥品使用方面,制定促進安全和合理的用藥戰略,設立國家處方處,規范醫生的處方行為[7]。印度德里州政府在推行基本藥物制度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實施“兩個信封招標”模式,采購優質、供應有保障的藥物;通過藥物存儲目錄查看各醫院信息,糾正用藥不平衡,保證用藥在醫院不過期及24小時內緊缺藥物送到醫院;藥品按質論價,對國際品牌公司或印度本土公司生產的藥品一視同仁[8]。肯尼亞于20世紀80 年代開始制定基本藥物政策,并一直是該領域的先行者。政府定期公布藥品已確定的批發價,并建立與其他國家交流價格信息機制;定期向醫院、農村衛生所推廣更新的診療標準指南,統一授權處方的水平,將基本藥物概念滲透到所有與醫療有關的培訓中;擴大國家醫療保險基金和其他保險覆蓋面,使保險包括盡可能多的藥品,從而減輕個人負擔[9]。澳大利亞、印度、肯尼亞國家的成功經驗為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立法提供了參考。我國在制定基本藥物制度法規時,可以借鑒上述措施并納入相應的章節。
4 基本藥物制度立法模式及框架
關于我國基本藥物制度的立法模式,目前存在兩種觀點:一是由衛生部聯合財政部、社會保障等其它相關部門制訂出在藥品的研究、生產、流通、使用各個環節推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系統的規定、辦法,提交國務院審議通過,由國務院發布,確立其法律地位[10]。二是國家應盡快修訂現行《藥品管理法》,將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寫入《藥品管理法》,同時制定出相應的、配套的法律法規,從法律層面上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為國家藥物政策的核心地位,并強制推行[11]。筆者認為,第二種觀點提出的“兩步走”模式更為合理、可行。《藥品管理法》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把建立基本藥物制度的規定納入《藥品管理法》中能夠從形式上提高基本藥物制度的效力層次,有利于保證基本藥物制度的推行。基本藥物制度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不僅包括基本藥物目錄遴選,還包括基本藥物的生產、采購、流通、定價、籌資、支付、使用、質量監管、績效考核等各環節,有必要形成獨立的法律體系,即由國務院制定實施關于基本藥物制度的行政法規。具體:《藥品管理法》“第五章 藥品管理”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三條分別對中藥品種保護制度、藥品處方藥與非處方藥分類管理制度、藥品儲備制度進行了規定。實施基本藥物制度作為管理藥品的一種方式,可照此納入該章節即在“第五章”中增加一條“國家建立和實施基本藥物制度。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基本藥物制度包含基本藥物的遴選、生產、供應、使用、籌資機制、監管等各個環節,其中基本藥物的使用是關鍵性環節。在制定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推行的具體辦法時,應涵蓋基本藥物制度的全部內容并重點強調基本藥物的使用。基本藥物制度的立法框架可作如下考慮:(1)第一章:總則。包括立法依據、立法目的、法的效力、職能分工等。(2)第二章:基本藥物目錄的制定與修訂。包括基本藥物目錄的分類、法律地位、修訂期限、基本藥物的遴選程序等。(3)第三章:基本藥物的生產與供應。包括基本藥物的生產方式、供應體系、定價方式等。(4)第四章:基本藥物的使用。包括基本藥物的配備、使用考核、費用報銷、銷售差率上限的設置等。(5)第五章:基本藥物的監督。包括藥品監督管理、衛生行政、社會保障等部門的職責分工,聯席會議制度等。(6)第六章:法律責任。包括行政責任、民事責任、刑事責任,基本藥物不良反應救濟途徑等。(7)第七章:附則。包括用語含義,委托事項等。
5 結語
盡管作為我國醫療衛生保障重要體系的基本藥物制度已推行30多年,但由于缺乏法律體系的支撐,沒有起到優先指導基本藥物生產、供應、使用、報銷、監管的作用。基本藥物制度的推行進程比較緩慢,實然與應然目標之間還有一定的差距,患者的看病負擔依舊較重。因此,政府相關部門應盡快制定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從根本上提高基本藥物制度的強制力。
[1] 孟銳,馬昕,逢士萍.國家基本藥物制度在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中的地位[J].中國藥事,2008,22(12):1060-1064.
[2] 楊佳佳.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概覽及思考[J].中國價格監督檢查,2008(12):47-49.
[3] 曾雁冰,楊世民.對基本藥物認知及臨床應用情況的調查研究[J].中國藥事,2008,22(9):756-762.
[4] 湯涵,楊悅.完善我國基本藥物制度若干政策建議[J].中國藥房,2009,20(5):321-323.
[5] 彭詩榮,楊悅.我國基本藥物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完善建議[J].中國藥事,2009,23(11):1083-1085.
[6] 覃正碧,汪志宏,程剛,等.關于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的思考[J].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8(6):389-392.
[7] 沈璐.澳大利亞的國家藥物政策簡介[J].上海醫藥,2003,24(6):281-282.
[6] 《醫藥世界》資料室.印度 被WHO推廣的“德里模式”[J].醫藥世界,2007(5):36-37.
[9] 《醫藥世界》資料室.肯尼亞基本藥物制度先行者[J].醫藥世界,2007(5):42-43.
[10] 曾雁冰,楊世民.對基本藥物認知及臨床應用情況的調查研究[J].中國藥事,2008,22(9):756-762.
[11] 常濱毓.建立基本藥物制度需要法律政策措施跟進[J].醫院領導決策參考,2008(18):1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