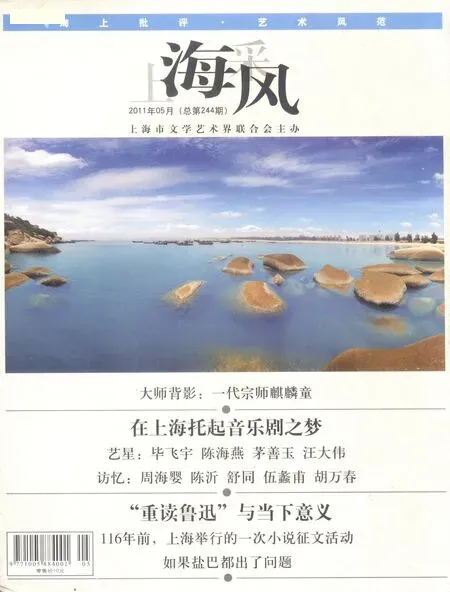116年前,上海舉行的一次小說征文活動
——美國發現清末“時新小說”
文/馬 婕
116年前,上海舉行的一次小說征文活動
——美國發現清末“時新小說”
文/馬 婕

《清末時新小說集》出版
一批被歲月湮沒百年之久的清末“時新小說”手稿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被發現,去年上海世博會期間終于回歸中國。記者日前獲悉,取名為《清末時新小說集》(全14冊)的這批“時新小說”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學界一般認為,中國近現代小說起源的“新小說”肇始于梁啟超1902年在橫濱創辦的《新小說》雜志,梁氏在此雜志上連載發表的《新中國未來記》被公認為導發中國小說從古體邁向現代的首部作品。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趙昌平先生近日接受記者采訪時介紹說,這批在美國發現——卻在1895年誕生于上海,計150篇(原162篇)的清末“時新小說”比梁啟超的“新小說”早了7年。所以,他認為,這批“時新小說”的發現,中國近現代“新小說”起源的歷史可能要被改寫。
那么,這批清末“時新小說”在上海是如何誕生的,怎么流落海外,一百多年后又怎樣回歸上海?趙昌平總編輯向我們細細道來。
2006年11月22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新館落成。當日,中文部館員欣喜地進行搬遷。這時,有人在一間堆滿書刊雜物的儲藏室里發現了兩個塵封已久的紙箱,打開一看,是一疊疊中文文稿,再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批中國清末的“時新小說”的原始手稿。館方查驗后極為重視,而后即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系。
趙昌平告訴說,誰也沒想到,原來這正是一百多年前,曾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小說征文的來稿。因為這些文稿不少學者認為已經失散,而此刻赫然出現,把我們震動了,這不啻是學術界的一件大事。經過查證和研究,116年前,曾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小說征文活動漸漸浮出了水面。
這是1895年5月,一位名叫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的英國人,為針砭當時社會時弊,曾舉辦了一次“時新小說”的征文,其最后征集到共162篇稿件。有學者認為,這批“新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針砭時弊、改良社會的特點,真正揭開了清末“新小說”的革命。也有人認為,很有可能是這批“新小說”直接影響了梁氏。傅蘭雅的“新小說”與梁啟超的“新小說”最大的不同在于其稿件來源多取之于普通百姓。
傅蘭雅是誰?打開傅蘭雅的檔案(《傅蘭雅檔案》三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原來他是當時英國圣公會派至中國的傳教士,他還是當時著名的翻譯家和學者。1865年他擔任上海英華書院校長并主編字林洋行的中文報紙《上海新報》;1867年至1896年,應聘擔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首席翻譯,翻譯了逾百種西方著作,這批介紹西方先進科學和思想的書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很大的作用;1873年至1896年,在上海還參與創辦了一所以介紹西方近代科學新知、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為主的格致書院,并出版了第一份中文科學普及期刊《格致匯編》;1885年至1911年,同時創辦了當時唯一的科技書店——格致書室;他本人還致力于慈善事業,于1911年捐資在上海籌建了中國第一所盲人學校——上海盲童學堂。
傅蘭雅不僅是中國近代將西方科技知識和書籍翻譯成中文最多的一個外國人,且翻譯水準超過了晚清數十年間其他同類翻譯。清廷為表彰傅蘭雅,于1872年賜其三品文官的頭銜,1898年又頒三級一等雙龍勛章。
隨著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清政府的慘敗,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處于動蕩與變革之中的中國,民眾要求一系列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雖為洋人的傅蘭雅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他首先看到危害中國社會、妨礙進步的“三弊”——鴉片、時文和纏足,決定以此作為抨擊對象。他認為,小說可感人心,可表人情。于是出資公開舉辦有獎征文,并在1895年5月25日的《申報》和6月份的《萬國公報》第七十七卷上及《教務雜志》上刊登了以下“求著時新小說啟”的廣告:
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息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茲欲請中華人士愿本國典盛者,撰著新趣小說,合顯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說,結構成篇,貫傳為部。使人閱之,心為感動,力為割除。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雖婦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物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駭目驚心。限七月底滿期收齊,細心評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佳作,足勸人心,亦當印行問世。并擬請其常撰同類之書,以為恒業。凡撰成者,包好彌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馬路格致書室收入,發給收條。出案發洋,亦在斯處。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
刊登在1 8 9 5年5月2 5日英文《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上的“有獎中文小說(Chinese Prize Stories)”廣告,針對不同的讀者群,內容稍許有不同:
總金額150元,分為七等獎,由鄙人提供給創作最好的道德小說的中國人。小說必須對鴉片、時文和纏足的弊端有生動地描繪,并提出革除這些弊病的切是可行的辦法。希望學生、教師和在華各種傳教士機構的牧師多能看到附帶的廣告,踴躍參加這次比賽﹔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價值的、文理通順易懂的、用基督教語氣而不是單單用倫理語氣寫作的小說將會產生,它們將會滿足長期的需求,成為風行帝國受歡迎的讀物。
收據會寄給所有在農歷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漢口路407號格致書室傅蘭雅密封好的手稿。
約翰·傅蘭雅

傅蘭雅起草的征稿啟事
從傅蘭雅的生平來看,他并不是一個文學批評家或小說家。那他為什么會對倡導時新小說感興趣呢?傅蘭雅深信,一部好小說可以脾益世道、感化人心,有移風易俗、啟發民智、改良社會、振興國力的功效。小說也可以承擔喚起民眾,協助社會現代化的角色。1895年7月,在“求著時新小說啟”發表后一個月,傅蘭雅在《教務雜志》(Chinese Recorder)上摘錄了艾德博士(Dr. Eitel)對有獎小說征文的一段評論,充分說明了傅蘭雅舉辦這次征文競賽的目的﹕
一篇寫得好的小說會在大眾頭腦中產生永久性的巨大影響,《黑奴吁天錄》在喚醒民眾反對奴隸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國現在罪惡猖獗,鴉片、纏足和時文,任何一種都夠寫一部感人至深的長篇小說。為了讓這些悲慘遭遇引起各階層人士的注意,就應該通過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從而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無疑義,中國人有這方面的能力。
(《教務雜志》)
傅蘭雅舉辦的這次時新小說有獎征文比賽成功地促成了一批“新小說”的問世。它們擺脫了舊小說的模式,從而引導了晚清時期新小說創作取向。由于選取了新的社會題材,不少作品除了對當時的社會弊害進行揭露和譴責外,還積極地設想改革方法,以促進國家的興盛富強,達到具體教化社會的目標。在這一點上,它們實際上是主張改良社會風氣的社會小說。由于它們激發了晚清小說變革的端緒,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譴責小說發展的先聲。這批“新小說”最具有意義之處就在于它們產生的時間比梁啟超1902年發起的“新小說運動”早了7年,比晚清的“四大譴責小說”又早了8年。我們通過《清末時新小說集》能清楚地看到當時普通百姓對于時弊之認識,對于改革之呼喚。其中《五更鐘》《澹軒閑話》等小說都極具當時之特色,《驅魔傳》等小說也頗顯時人中西合璧之思維邏輯。
1895年9月18日,傅蘭雅的時新小說有獎征文結束。傅蘭雅仔細閱讀了所有的稿件,并邀請了沈毓桂、王韜、蔡爾康等知名人士參與評選作品。1896年3月18日,他在《萬國公報》第86期和《申報》上,刊登了“時新小說出案”和獲獎人名單,不僅嘉獎了諸多獲獎者,并允諾將集結出版。



稿件封面、插圖及來稿信札


小說《驅魔傳》及《纏足明鑒》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小陽春中旬格致匯編館英國儒士傅蘭雅謹啟
本館前出告白,求著時新小說,以鴉片、時文、纏足三弊為主,立案演說,穿插成編。仿諸章回小說,前后貫連,意在刊行問世,勸化人心,知所改革,雖婦人孺子亦可觀感而化。故用意務求趣雅,出語亦期顯明﹔述事須近情理,描摹要臻懇至。當蒙遠近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館窮百日之力,逐卷批閱,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述煙弊太重,說文弊則輕﹔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虛幻,情景每取夢寐﹔或出語淺俗,言多土白﹔甚至詞意淫污,事涉狎穢,動曰妓寮,動曰婢妾,仍不失淫詞小說之故套,殊違勸人為善之體例,何可以經婦儒之耳目哉?更有歌詞滿篇,俚句道情者,雖足以感人,然非小說體格,故以違式論。又有通篇長論,調譜文藝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館所求,仍以違式論。然既蒙諸君俯允所請,惠我佳章,足見盛情有輔勸善之至意,若過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選體格頗精者七卷,仍照前議,酬以潤資。余卷可取尚多,若盡棄置,有辜諸君心血,余心亦覺難安。故于定格外,復添取十名有三,共加贈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諒我焉。姓氏潤資列后:
茶陽居士酬洋五十元,詹萬云三十元,李鐘生二十元,清蓮后人十六元,鳴皋氏十四元,望國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晉修七元,劉忠毅、楊味西各六元,張潤源、枚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儻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羅懋興各二元,瘦梅詞人、陳義珍各一元半。
按,其余姓氏,并無潤筆,公報限于篇幅,不克備登。
(1896年3月18日《萬國公報》第86期)
傅蘭雅在1896年3月在第26期《教務雜志》也談到了這批中文有獎小說文:
中文有獎小說結束了。有不少于162位作者參加了競賽,其中155人討論了鴉片、纏足和八股文這三種弊病,有的寫了4-6卷。我對諸多參賽者所費的時間、心力與金錢毫無回報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13名獲獎者,他們分享另加的50元獎金。這樣,獎金共達200元。優等獎名單在《申報》上公布,162個人名及解說也已經發布,并在《萬國公報》和《傳教士評論》上公布。另外還會轉寄到教會所在地。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會學校或大學有關。總體來說,這些小說達到了所期望的水平……這次征文大賽中也有人寫出了確實值得出版的小說,希望今年年底能夠出版其中一些,以便為讀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義的消遣讀物。
(1896年3月《教務雜志》第26期)
這里,傅蘭雅在原來設定的7名獲獎作品外,又增加了13個名額,一共確定了20名獲獎人和新小說作品。作品中包括了由學生們寫的短短幾頁的文章到由鄉村塾師寫的長達數卷的感人故事,其中不乏頗具水準的小說和詩文作品,有些字體精美,還附有插圖。所征稿件主要來自福建、廣東、江蘇、浙江、山東、河北、陜西、湖北、安徽、江西和上海等地。有相當一部分稿件的作者是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教會學校和教會大學的學生和老師。作品中也不乏空洞和濫竽充數的文章,甚至還有少量淫穢之作,有兩篇作品還被傅蘭雅退還給原作者。應征的作品也不都是小說,還有少量戲曲、彈詞、道情、歌詞等,也有不少是議論文和書信。作品中出現參差不齊的現象也應是意料之中的事。總體來說,這次時新小說征文活動是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新小說大賽,實為開啟時風之舉。
但令人頗為遺憾的是傅氏所征得的這162篇稿件,不知何種原因,居然也隨著他的離華而湮沒在歷史中,在隨后的百年間竟無一得以發表,以至于大多學者都認為這些作品已經佚散失傳。
從《傅蘭雅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1896年傅蘭雅辭職離華,受聘出任美國柏克萊(Berkeley)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首任東方語文講座教授,并于1902年起擔任該校東方語文系主任。他憑借在華35年的學識和經驗,大力開設中文課程,教授弘揚中國文化,鼓勵并協助中國學生赴美深造,直至1913年退休。傅蘭雅于1928年逝世,在去世之前,他將在中國數十年的藏書及文件數據悉數捐贈給了加州大學,創立了該校東亞圖書館。
幸運的是,就是在這東亞圖書館里,這批原始手稿失而復得。2010年恰逢上海世博會圓滿舉辦,這批小說手稿也乘著東風,從上海留美而又回歸上海出版,可謂是一件喜事。
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分重視這一驚人的發現,為力求忠實反映作品的原貌,對全文不做任何刪節影印出版。繁體字豎排,忠實于原貌,讀者還能看到很多有特色的當時信箋,花格和花紋錯落別致。略為遺憾的是,當年時新小說有獎征文共收到162篇稿件,但這次經過整理發表的計150篇,缺了12篇。在傅蘭雅選定的20篇獲獎作品中現僅存15篇,有5篇已佚失,其中包括第一名、第五名、并列第十名的兩件作品和第十一名中的一件作品。
趙昌平總編表示,事過境遷,一百多年之后,我們有幸將這批尚未被世人見過的中國文學史上一次重要的小說征文作品公諸于世,整理出版,以此為百年前的這次時新小說有獎征文活動畫下一個圓滿的句點。在過去的那些歲月里,曾經有許多學者都在尋找這批小說的下落,但都無獲而終。今天,這批小說的出版問世不僅僅給我們展示了中國現代小說的萌芽,而且還把我們帶回到那個久遠的年代。它們反映了中國社會從腐朽的封建時代向科學民主時代的轉變。我們從這些小說中可以看出這個轉變是艱難的,甚至是幼稚的并充滿了舊時代的痕跡,但它們是我們可以見到的、最早向封建社會發起如此鮮明批判的社會小說,是中國現代小說史上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開創之作,與后來以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為代表的20世紀中國社會寫實小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這些作品代表了清末新小說時代的開始,它們的出現可以被看成是以小說為武器向封建勢力發起的一聲號角,而隨后而來的是改變了中國的波瀾壯闊的新文學、新文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