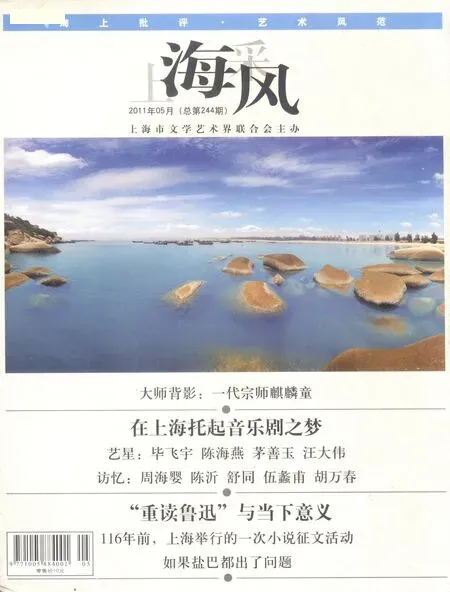“重讀魯迅”與當下意義
采編/海 風
“重讀魯迅”與當下意義
采編/海 風
誠如學者所言:“魯迅的意義在今天來說,非同小可,魯迅既不屬于官方,也不屬于魯家,也不屬于民間,也不屬于一部分知識分子,魯迅是我們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遺產。”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有必要“重讀魯迅”。不但重讀“文本魯迅”,還要重讀“人本魯迅”。
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以往紀念魯迅是國家的行為,這十年來魯迅逐步回到了民間,學術界也開始回到魯迅的原點,講述、研究一個真實的魯迅。無論時代如何變化,魯迅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話題。今天回到魯迅自身的層面上認識魯迅,會發現許多被遮蔽的意義和價值,并啟發對現代文化發展的更多認識與深思。
近日,魯迅的長孫周令飛與同濟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的多位教授舉行了關于“魯迅與現代中國文化”的座談會,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設中魯迅研究的意義,魯迅思想研究的范圍、方式,魯迅批判精神的內涵、價值等諸多問題。

周令飛

張 閎

王鴻生

湯惟杰

董 平

黃 健

徐 亮

高力克

金健人

江弱水

項義華
還原魯迅、重識魯迅
“當今的魯迅是被過度意識形態化的魯迅,一個不太讓人認識的魯迅。”
“現在重新認識魯迅很有必要。我們要把一個真實的魯迅和被意識形態利用的魯迅分開。”
周令飛(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主任、同濟大學魯迅研究中心主任):我是魯迅的第三代。我1969年參加工作,后來當兵去了,一直是從事傳播行業。事實上,以前我跟魯迅的研究是沒有關系的,我們家屬認為在旁邊看就好了。但是,隨著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市場經濟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魯迅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簡單了。1999年我從海外回到了中國,看到了魯迅的情況。1999年開始,我走遍中國各個省市中跟魯迅相關的地方和很多學校。在走遍了這些地方、學校,看到了現狀之后,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我心目當中的魯迅和父親告訴我的魯迅有很大的距離。我認為當今的魯迅是被過度意識形態化的魯迅,一個不太讓人認識的魯迅。
因此,這10年通過對魯迅的調查和研究,我們做了一些事情。2002年在上海由魯迅家屬成立了魯迅文化發展中心這樣一個單位,沒有任何官方色彩。我們也是自己籌辦經費來開辦民間的文化機構,在當今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下來是很不容易的。我們堅持做了很多的事情,2006年寫了一篇文章叫《魯迅是誰》,在當時的魯迅研究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討論。我們舉辦了名為《魯迅是誰》的圖片普及展,在香港、澳門、廣州、深圳舉行展覽。我們還舉辦了全國性的魯迅論壇,現在已經舉辦了五屆。每一屆論壇的出席者都在300人以上,不僅僅限于魯研界的人,范圍、話題都比較寬。我們還辦了魯迅青少年文化獎。因此,我們魯迅文化發展中心做的事情絕大多數是和一般的老百姓、學生們,和大眾比較緊密的。我們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同樣也在考慮另外一個問題:魯迅逝世了70多年,作為被毛主席認為是思想家、革命家的這樣一個魯迅,他的思想體系是什么?思想核心是什么?沒有經過很好的梳理和總結。我的父親周海嬰希望把這件事情推動起來。2009年12月,我們在同濟大學成立了“魯迅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接受了國家的社科課題,對魯迅思想進行梳理和研究。此外,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我們今年將在紹興召開第六屆魯迅論壇國際會議,就在魯迅誕辰的9月25日前后。這個大會的主題是“魯迅與現代中國文化”。
董平(浙江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現在在我們一般的觀念當中,有兩個魯迅:一個是被觀念化的、抽象的魯迅,一個是活生生的、生活在歷史當中的魯迅,這兩個有很大的差別。我們現在是把抽象的魯迅拿來評判。我覺得現在重新認識魯迅很有必要。我們要把一個真實的魯迅和被意識形態利用的魯迅分開,要把魯迅還原到20世紀的前半葉去,20世紀后半葉的魯迅是另一個魯迅了。
一個很坦率的問題,我們怎么來看魯迅?我們怎么看待他對傳統的批判,他對傳統的批判意圖在哪里?他對中國現代文化,現在的中國文化的發展、走向,產生了多大的作用?我們后來看到的中國文化的走勢跟魯迅有什么關系?我覺得恐怕還是要將20世紀前期或中期的中國的社會現狀、文化狀況,與整個國際格局當中的狀況結合起來。我比較傾向于一個歷史人物的活動,要放到當時的歷史過程當中進行評價。我們可能做不到完全的還原,但是有沒有這種態度是不同的。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什么?恐怕還應該是真正去發現魯迅生活過程當中的東西。尤其是他對文化的意義方面。比如說,重塑國民性問題是不是可以是當前的話題?中國文化的問題,比如說像魯迅先生揭示的劣根性的東西仍然存在,只不過現代社會以一種別樣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思潮如果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我覺得會很危險,搞得不好會走到很糟糕的一個境界。所以,我們時時刻刻要保持一種冷靜,我們時時刻刻應該懂得自我反思,我們時時刻刻都應該基于自我反思的基礎,明確自己應該到達的點。
湯惟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我們也不必去神化魯迅,他能夠承擔這個角色有各方面的主觀因素在里面。譬如1920年到1930年,特別是當時的北京、廣州、上海是怎么樣的一個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規定了在中國現代文化當中可以出現這樣一個批判的位置?然后有魯迅這樣一個具體的人來承擔這樣的歷史角色,這是非常有意思的。還有,為什么在之后的文化歷史當中,這樣的一個位置消失了?
那時候在上海,哪怕在南京政府最后的治理下,畢竟有一個租界。包括不光是魯迅,為什么當時在上海還存在一個左翼文化?比如說華界和租界有一種權利的縫隙,你華界的警察來抓我,我逃到租界里面去,那最起碼抓起來比較麻煩。在這種客觀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府結構造成了這樣的一種空隙,這也是這種文化存在的可能性。
王鴻生(同濟大學中文系教授):20世紀已經不是一個時間概念,是一個文化概念,因為這個世紀太特殊了。我們有幸經歷了這一個世紀一半的時間,20世紀一方面是層出不窮的各種偉大的解放計劃;另一方面是層出不窮的災難,這些災難是規模性的。像這種非常特殊的經歷,反而會成為我們重新激活魯迅研究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把魯迅放到20世紀的文化政治概念里面去,我想可以讀出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出來,這種閱讀對我個人來說還僅僅是剛剛開始。
周令飛:這幾年來,我心里面有很大的問號。第一個問號,“魯迅是誰”,我認為面目全非。這是我最大的感覺,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問號放在我面前。我是搞傳播的人,對于一些淺顯的東西比較在意,我覺得在一個共和國大廈建構的過程當中有不同工種的人,魯迅到底在這個共和國大廈建構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監工”,監理可以被收買,監工看著不對就記下一筆,這種監工的角色是不是跟魯迅的角色有一點貼近?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問號。第二,最大的問號就是,魯迅逝世的時候,他到底帶著怎樣的一種情緒走的?有的人說他帶著寂寞、孤獨、怨恨而死的,文本上說“一個也不寬恕”,說魯迅當時是非常絕望的、孤僻的離開的。可是我聽我的祖母、我的父親告訴我,當時在上海雖然他也在打筆仗,但是在上海故居里的生活品質絕大多數是很好的,他喜歡看電影,經常去看美國大片,喜歡逛書店,頻繁地逛書店。生活當中,他不缺吃、穿,他有很多的朋友一天到晚到他家里來聊天。昨天晚上打筆仗,今天一同吃飯。還有,他娶了一位年輕的太太,有了我父親這個孩子,每天抱在手上。生活是這樣的快樂,我覺得是很豐富的,他在離去世前11天還參加了青年木刻的展覽,我們看到了他大量的照片。因此,我在心里劃了一個巨大的問號,這樣的一個人是不是像大家描述的那樣,那么絕望的死去?
江弱水(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我覺得魯迅帶著情緒離開人世,他有悲憤,他也有絕對的精神的超脫,他最終把這個世界、歷史把玩于股掌之上,有非常超脫的心理。我當年寫過一篇文章,形容他是早生了70年的“周星弛”。我甚至想過可以把《故事新編》串寫為一部電影。他早期是激烈批判中國社會的人,晚年有一種開放的心態。他說,中國不是“吃人的”問題,是“吃飯的”問題。魯迅晚年不像早期,晚年的深刻是一種超越性的深刻。
湯惟杰:我們給學生編大學語文讀本,我編小說部分,我想魯迅應該有一篇,可是選什么呢?我想來想去還是《故事新編》里面的。非常有意思,《故事新編》里面的每一篇文字之后,魯迅可以用一個不太確切的后現代來講述。他有某一種游戲的態度。他可以把批判的對象和自身批判的立場、態度,以一種非常自如的方式聯系在一起。而不像早期的《吶喊》是一種過于緊張的態度。這個很難。他臨終前我們老說他“一個都不寬恕”,實際上他是用一個什么樣的口氣說的?也許他是橫眉冷對的,也許是非常隨便的態度。這個都很難說的。
董平:我在紹興魯迅紀念館看到他很多的手稿,我就突然涌現一個不一樣的感覺,因為他的字寫得那么好,從來不出格,我當時覺得太有意思了。
周令飛:他很愛干凈,什么事情都親歷親為。我有一個習慣,回到家里如果有一個紅色的包裝繩,我用完之后,會繞起來放在柜子里面,我是跟父親學的,父親是跟魯迅學的。就是把所有的東西都安排好好的,不浪費。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這樣的一種生活品質,怎么可能是大家描述的那個形象?我昨天講“文本魯迅”與“人本魯迅”,是不是我們過去的研究,絕大多數是從魯迅字里行間里摳出來的感覺?
項義華(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員):魯迅解讀有多種多樣,你祖母口中的魯迅是比較真實的魯迅。其實每一層面魯迅基本上都被講到過,許多公開發表的文章,進入公共領域的魯迅,在學校被教科書間隔的魯迅,這是一個怎么樣整合的問題。
周令飛:我與學校接觸得比較多,小學、初中、高中,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怕魯學。問題就是出在這里,我也是從教科書學來的,“一怕文言文,二怕寫作文,三怕周樹人”。
項義華:魯迅是在一個極其扭曲的文化背景下得到傳播的,這里有很多的經歷。魯迅無論有一個什么新的意識形態,大家都加上去。這個方面,甚至把魯迅稱作為中國文化的守夜人。
魯迅研究的當下意義與探討范圍
“魯迅是一面巨大的鏡子,隨著時代的發展會激發出一些新的問題。”
“魯迅研究應該不光局限于魯學家,要面對更廣的領域。”
張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同濟大學魯迅研究中心主任):我認為魯迅思想研究的問題可以從“現代”、“中國”、“文化”這三個側面展開。
一,“現代性”。這方面的問題這些年也討論了很多,尤其是中國20世紀以來一直到現在的中國文化的關系,有很多的說法和爭議。這些問題肯定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我們要在現代的時代下重新理解,我們要為未來的中國文化發展提供一些目標、方向、框架。
二,“中國”。這些年來,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在國際環境中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方面也發生了很大的爭論。這些爭論否定的也有,肯定的也有,這些都很有意義,對未來中國的國家定位都是有作用的,我們要來探討一下:魯迅在整個現代中國的形象的變革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他扮演了什么角色?給我們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或者是作為中國的人的角色當中起了什么作用?
三,“文化”。魯迅作為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的一些方面,這些年來講了很多。文化作為一種整體,那些都是一個側面。我覺得魯迅對中國文化的言論、他一生的經歷,提供了一種知識分子以及文化精神的“范式”、“典范”。很多人認為魯迅所提供的人格形象是負面的,今天它過時了,但也有人認為要堅持這樣的方向。我認為作為今天的研究者,應該有所解釋,有所回應,而不是窩在自己的書齋里面。在今天關于魯迅的回應和解釋應該是很迫切的問題。
所以,希望研討不光是局限于魯學家,希望面對更大的文學的領域,甚至于經濟、社會、歷史、文化這些大的領域,還包括一些海內外的文化學者。不一定是專門來談魯迅,魯迅作為現代知識分子一個典范的形象,他所面臨的問題,他所遇到的精神的困境,在我們今天依然是問題。我們今天談論魯迅也是對自己內心狀態的一種反思和理解。
江弱水:魯迅的確非常豐富,魯迅即便不算是思想家,也是一個深刻的思想者。有人問魯迅需要不需要了?當然需要,前幾天搶鹽的問題,我覺得太悲哀了。魯迅怎么不需要呢?太需要了。魯迅面對的社會現實幾乎沒有變,搶鹽的心態還是一樣的。魯迅存在的意義,其實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解毒丸,你說他沒有建設性,他不是面包,不是讓你吃下去特別有營養,但他能解毒。
魯迅的復雜性和豐富性非常明顯。可以講《吶喊》《彷徨》是一種魯迅,《野草》是另外一種存在主義、結構主義的魯迅。到了《故事新編》是發散性的,基本上屬于后現代的思維。“五四”關于婦女的論述,多大程度上因為魯迅寫了《祥林嫂》?海外的一個漢語學家,他的序就是:中國女性社會就是“祥林嫂”嗎?我覺得魯迅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他平時在鄉間記錄,早年的中國婦女是什么樣的他很清楚。所以,我們很可能這也有魯迅,那也有魯迅,魯迅是非常復雜的多面體,我們過去是意識形態的一個利用。
我覺得魯迅現實意義也很明顯。中國現在所有問題都沒有超出“立人”和“立國”。在魯迅那個時候就已經說到了這兩個話題,這兩者之間的處理魯迅解決得更好。事實上,我們20世紀整個中國發展的某些方面正不幸朝著魯迅所警惕的、反思的錯誤方向走。我們應該有所警惕,防止國家發展成“人傻錢多,肌肉發達”的社會。魯迅是一面巨大的鏡子,隨著時代的發展會激發出一些新的問題。有一些東西是永遠不過時的,像“孔子”、“莎士比亞”、“魯迅”。隨著中國歷史不斷的延續,還會出現各種各樣的魯迅。
項義華:魯迅不光是被歷史意識形態化,魯迅本身有很濃厚的意識形態性。在新文化中,有兩翼,一個是“左”,一個是“右”。“左”,八十年代有所反思,我們現在還在新文化這樣的傳統中。魯迅之所以有很大的影響,我認為跟意識形態闡釋有關系。
魯迅當時在“新文化”批判傳統、批判中國的國民性的氛圍下,他不是一個原創性的思想家。他是一個思想者,是一個文學家中的思想者,不是一個體系性的思想家。他當時是一個年輕人,寫了很多的文章,他也不想拿稿費,他愛好寫文章,包括對物質的批判。這是他早年的一種傾向,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反抗,這個傾向是存在的。但是后來有沒有發展?在對物質批判上并沒有發展,他對商業文明是很隔膜的。他后來主要批判現實,重復文化批判的這樣一條路。他對1927年到1937年那一段中國民國的黃金時期是有很大貢獻的。
魯迅并沒有對商業運作批判,一方面他有一個初步的社會建構;另外方面之前并不是像現在普遍彌漫物質主義,所以魯迅并沒有對此批判。另外,其實他對農民還是比較隔膜的,他早年的生活里沒有農村的生活,他實際上還是有士大夫的生活。他對中國的農村社會沒有一種社會科學式的思想。他的文本里面農民成了國民性批判的標本。當時有這么一種觀念,把中國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到后來共和體系不能建立,歸結為農民問題,歸咎于國民素質。魯迅的局限恰恰也體現到新文化運動的局限上。我認為自強運動,現在仍然未完成。從政治、經濟、文化來說,我們的憲政仍需要走向“共和”。從經濟方面我們仍然未被承認是市場經濟國家,我們的文化沒有被認為有完整的文化。我們也擺脫不了與魯迅的歷史性的糾葛,我們實際上是主觀的搏斗的過程。
在這個里面,我們把魯迅拉到更大的背景上去,會發現跟孔子相比,他有一些方面跟孔子是相同的。孔子就是立人要立于“禮”,因為人類社會的矛盾就是人的欲望跟資源的矛盾,所以包括孔子、荀子、司馬遷都是這樣,為什么搞一個“禮”?就因為資源有限,所以要禮分,要節制,有根據你的智商也好,家族的社會地位也好,要分出來。現在“五四”就是把這個廢了,對等級制度的批判非常尖銳。包括魯迅道德體系里面,有一個“進化論”的倫理觀。他有“初民”、有“維新的無產者”,包括從早期到晚期的,兩個東西都是理論上的建構。他其實對現實生活中的民眾都是缺乏了解的,包括“五四”很多的文化人都是這樣的。他們都是把自己理念中的社會模式強加給社會,我覺得這是我們近代中國發展的最大的問題。
黃健(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自從互聯網出現之后,網絡上對魯迅的討論是非常的激烈。無論是贊美的,還是反對、批評的,各種聲音都有。我說的網絡主要是社會上,不是學校里面的。具體贊成和反對的比例的量沒有做一個統計。一般來說,主流的門戶網站,還是通過一個正面的方式來邀請魯學界的學者來談,專門開魯迅頻道。
民間也有很多關于魯迅的言論,我記得有一篇匿名的關于魯迅的局限性的文章。我個人認為,從民間的高度,這篇文章寫得不錯。雖然,不一定學理性那么強,但是他講到了魯迅的一些問題,至少我們以往不太容易看到。文章寫得還是有他的想法,不是一般的謾罵式的,非理性的,發泄性的。
我覺得這樣從民間的角度來展示魯迅的層面,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我們可以深入認識和探討的空間。我們從小時候起接受的魯迅大都是塑造得不太完整的魯迅,我們以前接受的魯迅是一個只會橫眉冷眼的魯迅。現在我們逐步地認識,我們也發生了很多的改變。
魯迅批判的雙向性
“魯迅的說話方式是內外雙向的表達,在對世界說話的同時也在對自己說。”
“魯迅激烈地批判傳統同時又是一種繼承。”
王鴻生:今天我們再來重新研究魯迅。這個處境和語境都跟以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怎么來認識這個變化?這跟我們確定的主題有很大的關系。
我們過去研究魯迅的時候,至少在我的閱讀范圍里面,沒有聽到誰談到魯迅的話語。這個問題從來沒有出現過,在今天,魯迅話語里面的內涵太值得發掘了。簡單來講,一般的人認為魯迅是戰士,他好像是在抗擊,在打擊。其實魯迅的話語方式有極其深重的自我反省的味道在里面。他這種說話方式,在現代表達中間,確實是內外雙向的表達。這種表達非常的困難,一個人單純的獨白的對自己說話容易,一個人如果說僅僅對世界說什么也是容易的。但是一個人,能夠在對世界說話的同時,這些話也是對自己說,或者對自己說的話,同時也是在對世界說,這里面涉及到說話者的身份,也包括了他和周邊世界的各種關系,這中間可以深入探討的。即便在話語倫理上,魯迅作為現代文化的一個構成,我覺得特別有價值。我重讀魯迅可以發現過去很多不容易想到的問題,這些都是可以展開來談的。
這說明什么?說明魯迅身上的再生產力,無論是從知識生產還是思想生產來說,魯迅是一個原點,一個源頭。我們不斷走近他,不斷返回他。這一點西方文化比我們有一個好的傳統,西方人的反傳統也反得很激烈。但是,他們和自己的傳統,無論是正相關還是負相關,他們的相關性非常強,他們內部的文化的延續性還是保持下來了。
我們在一個橫向的外來文化的沖擊下面,幾乎一度潰不成軍,主體性喪失。我們向西方學習這是很好的,但是出現了另一個問題:海外很多學者過來,我們跟他們交談,我們有的時候對他們國家文化的了解遠遠超過西方學者對中國的了解。我們學了這么多年以后,問題就來了,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好好來處理自己的問題,這個跟我們文化的喪失是有關的。由此并存的現象是什么?我們不斷反自己,不斷反自己反到最后,我們都成了無本之談,游談,尤其在人文里面站不住腳。
這跟我們的“根”有關,現代文化我覺得我們還要有一個新的“根”,這個“根”就在這里。魯迅的意義在今天來說,非同小可,魯迅既不屬于官方,也不屬于魯家,也不屬于民間,也不屬于一部分知識分子,魯迅是我們整個20世紀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遺產。就像現在談20世紀政治文化離不開毛澤東,20世紀的文化政治就離不開魯迅,離開魯迅就沒辦法談。這就是繞不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巨大的框子。魯迅并不是一個現成品,對魯迅好像這個人也下過定論,那個人也下過定論,這些定論都有他的針對性,我們今天對魯迅的認識必須是重新開始的。
高克力(浙江大學人文學部教授):我是搞思想史的,不是文學界的,我就談一下思想界的魯迅。我給他定位為“批判的啟蒙思想家”,魯迅的文化批判既批判傳統又批判現代性,對現代性進行反思,都是非常有價值的。有學者提出,我們對中西文化應該是雙向的批判,以現代性批判傳統,以傳統性批判現代性。這些魯迅都做到了,魯迅的“拿來主義”還是有相當的文化自主性的。
對魯迅來說,他的思想結構是比較復雜的。我發現魯迅在南京念書的時候,最早是學德語的,他跟德國的思想有很大的聯系,反而跟英美界思想關系不是太大。他更深刻的是接觸了德國的“浪漫主義”。魯迅批判物質。所以我認為魯迅思想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就在這里,我們現在的反現代的思想在魯迅那里找到了源頭。這也是魯迅被爭議的一個問題,基本上文化界、文學界對魯迅是肯定的。現代化的語境中,魯迅先是一個思想家,然后翻譯小說,再然后創造小說。他的思想有兩個面向,既是啟蒙思想家又是后啟蒙思想家。不同的學者從他身上可以找到不同的養分。我覺得魯迅既是現代主義者,追求現代文明;又是一個批判者,從開始就是一個批判者,這是魯迅借助于德國思想的優勢。
魯迅的“當代中國”,現在已經是完全的拜金主義、物質主義還有大眾社會的庸俗。從2008年開始,一個非常新的現象是新左派的國家主義派。我們魯研界有一個“摩羅”,他一直是魯迅的崇拜者。但是后來耐不住寂寞,寫一部小說《中國站起來了》。網民對這個書的評價從0分到5分。50%的人認為他是5分,最高分,還有將近50%的網民認為是0分,就這么極端。他從一個魯迅的批判性知識分子,突然轉變成國家主義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很多的學者也嘲笑,你做批判知識分子,你邊緣化了,你可能在北京買不起房子,你這個暢銷書一寫,幾百萬的稿費就來了,眾多的網民的追捧,他的生活就改善了。
張閎:2008年地震之后中國乃至世界形成了極大的振蕩,很多的朋友,包括原來的同道者,今天都完全改變了,整個分化、重組,乾坤大挪移。剛提到這幾年的一個精神文化現象,我覺得在未來的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摩羅”表現得非常明顯,還有很多我們平時的朋友,有一些還是可以談話、可以爭論的,還有一些甚至是沒法坐在一起的,這是非常重要的現象。
董平:最近幾年,從2008年以后,我們現在的中國哲學界有一股很大的潮流,至少是潛流,開始批判“五四”,重點肯定是批判魯迅。為什么?他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斷絕了,歸因到“五四”,而那個時候是魯迅先生最活躍的時候。所以,現在中國的哲學界有那么一點批判,我不是其中之一。其實這和剛才說的“新左派”呼應的,只不過是表現層面不一樣,現代這種潮流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我們現在所丟掉的恰好是魯迅的價值。我們不再關注社會的現實,我們沒有像魯迅先生當年那樣深刻理性地張揚自己的個性。他把中國的文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細膩的分析,整體的批判。這是今天我們最缺乏的。
“摩羅”這個例子很有意思,表明我們現在的知識分子丟掉了什么?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的魯迅精神。我們現代對于“五四”以來的傳統文化的批判整體上有各種各樣的觀點。我覺得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恰好是他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他是通過批判來繼承的。他對故鄉的感情,這里面沒有一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眷念,這也是一種解讀。
張閎:魯迅激烈地批判傳統同時又是一種繼承。這些激烈的反傳統的人,對古典文化是非常迷戀的。對茶壺、瓦當、拓片、古磚啊這些東西,迷戀到一種很誘人的境界。包括北京的一些研究魯迅的學者發現,魯迅收集很多東西,還包括革命的畫冊、日本的畫冊。這很有意思,一方面他對傳統、文化的東西都很迷戀,對傳統、古典文化中有光芒的東西都有迷戀,像收藏癖一樣的東西;另一方面,世界在他面前,無論東西方都已經碎片化了,他努力在搜集和保存這些東西。
王鴻生:他搜集這些東西,他內心有一種高慕的境界。他一直有一個遺憾,南洋的漢畫像他沒有去看。有一些人為什么迷戀南洋的這些東西?因為在漢以前的畫,從美學上來說是很了不起的。
張閎:所以我后來反思我自己。我們是文化拆遷戶,整個文化的家園和精神根基都已經完全喪失了。我不是說我的感覺,從美學上理念上說這些古董是一個價值很高的東西,但是我跟它沒有感情,甚至我不認為這是跟祖先、跟我血統相關的東西,這不是我依戀的東西。我只是說,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我應該去理這些文化,我盡量去迷戀這些文化。魯迅也許會把玩它,但是我會走神,至少我本人是一個精神無家可歸者。這里面是個人的差異?還是代界的差異?還是文化層級的差異?甚至包括魯迅他內心的某一種東西,我們是否能夠呼應?他內心表達的東西,我們是不是可以聽懂,或者是理性地聽懂,我們是不是可以體會到?這個方面我很困惑。
魯迅的文化批判與批判文化
“魯迅是在徹底的批判上起作用。中國現在需要這樣一個人。”
“說魯迅先生的‘文化批判與文化建構’,倒不如說‘文化批判與批判文化’,前者是一種對象化,后者是一種精神。”
高克力:還有一些政治學、社會科學界的學者,他們從民主、憲政這一個角度,發現魯迅一直是批判民主的。現在有兩種爭論,魯研界認為魯迅才是自由主義者,站在自由角度,胡適是比較穩健的,是在體制內推薦憲政的建設,魯迅是體制外的批判的建設。這里有兩種知識分子,一種是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一種是建構性的知識分子。1929年之前胡適也是一個批判性知識分子,國民黨在通緝他。1929年以后,胡適就乖了。現在對胡適的評價是早年80分、中年60分、晚年40分,胡適跟國民黨越來越近。從批判性知識分子和建構性知識分子角度來說,會對魯迅有不同的爭論。批判魯迅的人認為,魯迅光批判,沒有一個建設性的系統的政治模式。這對魯迅是一種苛求,這是魯迅的思想的短板。魯迅自己說一直徘徊在“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或者是無政府主義。魯迅的一個思想短板,就是“無政府主義”。所以我認為魯迅的價值主要還是在文化意義上,他是文化巨人,主要在這里,他在文化上的批判性和建設性都是兼備的。
徐亮(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我贊同魯迅是一個批判性的非建設性的思想家。在今天中國文化建設,或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建設中,正因為有這樣的地位才會有這樣的作用。剛才談到的一些沉重的問題,比如說,魯迅到底有什么建設性的東西可以留下來作為遺產繼承?我要說其實沒有。因為他的批判涉及到一般人很難接受的地步。他發現無數的悖論,這種悖論讓他自己無法適從,處于矛盾的地步。他有很好的同情心,但是是同情民眾還是批判民眾?像祥林嫂,是該同情還是批判?他顯示出一種糾結。然后對于青年,他覺得青年還是很有希望的,人還是有希望的;但是,他發現青年并非給人以希望。為什么?因為當他批判的時候,他把自己放進去了。因此,他作為一個批判者,他懷疑自己,他所有的句式都是自我懷疑的句式。這種批判的方式,其實是非常具有現代性特征的,就是追求真理,不找到最終的真理是不退縮的。因此他的東西對建設沒有任何作用,可是正因為走到了這么深的地方,他可以不斷地被人拿出來解讀。而且他會作為一種文化的資源,在后世不斷產生影響。
他其實進入到一個階段,他所發現的東西是人所不能承受的,因為人是有局限性的存在。
有人批判魯迅缺乏包容,其實他對自己還要刻薄。他的寫作倫理,反過來都是對自己產生作用。這種文化遺產才是他最重要的文化遺產。而且,周先生說他是一個“監工”,可能還有一點不同。監工是知道怎么做,而魯迅就是知道出問題了,但是知道也不提供解決方法。他的任務就是告訴你有問題。魯迅還是在這個徹底的批判上起作用。我們有一個魯迅和胡適,他們是互補的,他們任何一個人都不能兼有對方的東西。魯迅是人不是神。大家要求魯迅既有這個又有那個,這是不可能的,這根本不是對人的要求。歐洲的哈貝馬斯,他建議我們在相對的情況下,要找到這一種理性的規則,這種理性的規則是有利社會建構的。歐洲還需要福柯,福柯只是告訴你世界上有這么多陰謀,每一個人都在實施這種陰謀。我們要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說中國要有一個健康的發展,要讓他以他原有的方式來發揮作用,我們需要一個這樣的人。中國人很難理解,這種人有什么作用。我們老是認為一個思想家還要有建設性的作用。批判從本質上講就是不斷的問:這行嗎?合法性論證,不斷地揭示這個東西,他的任務就完了。沒有任何義務給任何人來提供答案,提供我的方案。這在今天太重要了。這對今天建設中國文化有很大的作用。
2008年中國的知識分子發生了變化。社會也出現了一個“物欲至上”的潮流,這個潮流里,似乎追求真理是一個過時的行為,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像魯迅這樣去追問,人們可能會懷疑他的利益何在,所以魯迅還是在歷史中比較好。
王鴻生:從政治文化角度看,魯迅沒有談政治的事情。從這一點出發,我覺得他不具有建設性,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是不同的。剛才“監工”這個概念,我不太認同。監工是有施工圖的,而魯迅沒有施工圖,而他也不需要這個施工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對知識分子的弱點看得很清楚。你想想,他不是“新黨”,也不像胡適當國師,他也沒有成為一個犬儒,他在那樣的時代,很警惕自己被意識形態化,而我們現在太容易被意識形態化了。魯迅在這個中間陷入悖論以后,他的力量很強大的。魯迅能做到這一點,他了不起就在這里,所以他不可能多面作戰,這個人在20世紀絕無僅有。
徐亮:魯迅有很多常人沒有的批判的細節。他要去審問人心,這個人心怎么樣?這種很細節的運作過程,他運作出來了。因此建構了一種批判性文化。如果要他在政治建設中做什么事情?那我們完全走錯路了。
金健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韓國研究所教授):魯迅的張力我們沒有好好去發掘它,魯迅有兇煞相,但是他有菩薩心。他把批判社會和自我解剖聯系在一起。實際上革命和改良也是有一個度的。我們現在有一個很不好的傾向,現在因為對革命的質疑,對改良的推崇,對當年的批判性的先行者采取另外一個評價。包括馬克思,我們老講現在北歐的資本主義比你社會主義還人性化。但是,如果沒有馬克思的資本論,沒有工人和資本家的斗爭,資本家會跟你平分嗎?我們的利益在很多情況下,不是矛盾的,我們也可以走共贏的路子。這也是經過二次大戰之后人類的一個大的進步,我們還是有共贏的地方,我們可以一起干。在這個方面,我們實際上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
另外一個方面,魯迅代表知識分子里面最先導的、最精華的、最精英的部分,這部分就是對現實進行批判,為什么呢?因為批判的東西總是現實存在的東西,這個批判是真正發生的東西,我對他不滿,這是真正確鑿的。但是理想的東西,最后得到的東西都不是我們想要的東西。說魯迅先生的“文化批判與文化建構”,倒不如說“文化批判與批判文化”。他就是一個“批判文化”,因為文化批判是對文化的不合理進行批判,是一個對象化,而批判文化是我的一個創意,是永遠有這種精神,對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永遠都要保持這種精神,建立一種批判文化。所以,我覺得這個方面是我們最豐富的一個遺產。
湯惟杰:大家都講到了魯迅的特征,他的寫作,他規定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這個位置是一個批判性的立場。我更關注的是,文化批判這樣的一種行動或者是這樣的位置,在中國當下的文化建構中,本身具有什么樣的價值?而不是說魯迅著作里面有文化建構的部分,我們是不是再去找找,或者說他有文化建構的部分,不是這樣的談法。
如果你有一個規劃,你為文化批判設置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他在整個的文化當中起一個什么樣的作用?魯迅是非常徹底的,他把問題推到一個極致,一般人的思路很難跟上他,跟上他覺得太痛苦了。魯迅最后都是問自己的:我批判他我自己何嘗不是這樣的?
如果按照過去的現代文學來說,我們重點來講那么幾位,但是好像足夠能夠給你提供闡釋的作家只有魯迅。其他的作家都不足以提供一個足夠豐厚的文本支撐你對經典性文本的解釋。但你具體選魯迅的文本是有風險的,他的豐厚性是沒有人可以蓋過他的。
周令飛:你們剛才談到批判性知識分子和建構性知識分子這兩種知識分子。我們現在很喜歡建構性知識分子,對批判性知識分子很討厭,因為他的摧毀力很大,破壞力很強。尤其是近幾年,我的很多跟魯迅有關的朋友,說魯研碰到寒冬了,說魯迅熱沒了現在冷了。至于原因,他們歸結于魯迅這個人領導不喜歡。他們現在領悟到的魯迅是高度符號化的,是跟政府、跟領導搗亂的魯迅。他們變得對這個人不知道怎么處理,他們一代一代傳下去,傳到這一代手上的時候怎么辦?我不能表態,我也不能支持前面,也不能否定前面,那我就無語吧。這是一種說法,我在想魯迅真的是一個搗蛋的人嗎?破壞力這么強的人嗎?
張閎:這就關系到如何認識知識分子的作用問題。假如你狹隘地認為:國家養活你們知識分子是讓你們來挑刺的嗎?那就希望你們不要寫這種批判的文章。知識分子不批判,還是知識分子嗎?
徐亮:現在可怕的是知識分子沒有能力從理論上說明,那種狹隘的認識是不對的。
金健人:回到魯迅的精神。任何社會都有不盡人意的地方,批判的知識分子在任何時代都不受某些長官的歡迎。我們要學習魯迅的精神,在怎樣的情況下學?怎么學習?這里面有一個策略的問題。不能要求把所有很尖銳的話全說出來。我們現在說每一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良心,你在你的位置上怎么寫怎么來說?你要有你的聲音,必須要講究策略。
《百家講壇》誰去講過?我提一個建議,魯迅研究機構能不能在這個方面多考慮考慮?怎么樣以《百家講壇》的形式來講魯迅?在一個有限的容忍度之內來宣傳魯迅?現在已經變成斷層了,我們那一代人在毛澤東旗幟的光輝下接受了魯迅。到中學生這一代,中國的語文課里魯迅的文章減少了。因為原來的那種宣傳,使他們產生了逆反心理。魯迅已經被遺忘了。
現在參加這個會,我一下子產生了很多的想法,讓我們的老百姓接受他,先知道魯迅的地位是精英里面的精英。他走在那么前面,要后面很大的一批人追隨是很困難的。只能是,他走在那么前面,后面跟著弟子幾個,再后面十幾個,再后面幾十個,他的思想要不斷地被消化,然后被轉換,一層一層地影響最后的民眾。影響民眾,這是要經過多少人轉化過來的。我以前閱讀的東西很少,有一本書就不錯了。現在的閱讀呢?再好的閱讀物人家也不一定要看,都要看電視劇,看網絡上的傳播,我們要利用這個東西。你說做一個很有影響的《百家講壇》,就是要把魯迅的東西該還原的還原。這種東西是體制之內完全容忍的東西。現階段的批判文化,我們也有,我們現在網絡上有大量的批判文化,有我們許多公共知識分子的發言。問題是,我們怎么來參與其中的建設?我們怎樣以另外一種方式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