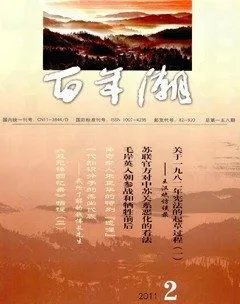協助白求恩鋸臂救彭清云將軍
1931年12月14日,駐扎在江西寧都的國民黨二十六路軍的一部,在董振堂、趙博生和季振同的率領下,1.7萬多人舉起了革命的義旗,宣布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當時只有15歲的我,就是這支起義隊伍中的一員。寧都起義后,組織上看我年齡小,分配我到部隊醫院工作,從此我成了一名“白衣戰士”,長期在我軍衛生戰線工作。
現已進入耄耋之年的我,經常回顧往事。在我作為“白衣戰士”的戰斗生涯中,努力實踐毛主席關于“救死扶傷,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的教導,拯救過非常多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和志愿軍傷病員的生命,留下很多美好回憶。給白求恩大夫當麻醉師,成功搶救彭清云將軍,就是這些難忘回憶中的一個。
1938年10月25日,日本獨立混成第二旅團旅團長常岡寬治到前線督戰,我們三五九旅七一九團在山西省廣靈縣黑市鎮邵家莊打了他們一場伏擊。當時彭清云任七一九團一營教導員,他領導的部隊遭到日軍瘋狂抵抗,日軍三面向一營撲來,并占領了一個有利地形,用一挺重機槍向我軍掃射,給我軍造成極大威脅。團長賀慶積命令彭清云一定要把這挺重機槍搶過來,彭清云就帶著部隊向日軍沖去。在沖到離日軍很近的地方,日軍向彭清云所部猛烈射擊,一槍打穿了彭清云的右臂關節處,血流不止,但他仍堅持帶著部隊沖上去搶到重機槍,并用其向日軍猛烈掃射。把日軍壓下去之后,彭清云帶人沖到常岡寬治的指揮所,看見一個胖軍官正在指揮戰斗,他瞄準后開了一槍。彭清云是神槍手,一槍擊斃了這個胖軍官。事后據情報得知,這個胖軍官就是常岡寬治。在這場殘酷的伏擊戰中,三五九旅雖然犧牲了好幾位連長、指導員和一些戰士,但卻獲得了重大勝利,共消滅日軍500多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
戰斗結束后,彭清云和一批傷員被送到我所在的三五九旅第二休養所。所謂休養所實際上是后方醫院,我那時任所長。我們的休養所設在山西靈丘縣一個深山老林里。這座大山中有一條河,河邊的半山坡上有一所地主家宅院,宅院比較寬大,有正房和東西廂房,我們的休養所就借用這些房子當治療室。那時,我們休養所的條件很差,不僅設備簡陋、醫藥奇缺,而且醫務人員極少,像我這樣在紅軍時期曾在中央軍委衛生部衛校參加過學習、八路軍時期又在延安醫大學習過一年多的專業醫務工作者極少,我這個所長是所里的主要醫生之一。
彭清云被送到我們休養所后,我趕緊為他做檢查。他負傷后在前線只是做了簡單包扎,連藥也沒有敷,前線也只有這個條件。我們休養所的條件雖說比前線好一些,但也只能用鹽水泡的沙布給他清洗傷口,再擦上“二百二”,也就是紅汞,然后用紗布包扎上。至于傷沒傷到骨頭,傷口里的情況怎樣,我們沒有x光機,也沒有其他設備,根本無法檢查。
經過簡單治療后,彭清云的傷口開始愈合,他也以為自己沒事了,還跟我們所里的同志打了幾圈麻將。實際上他的傷口里面已經嚴重潰爛,三天后開始發作,整個右臂腫得發亮,我們開始感到情況不好,加緊治療。又過了兩天,傷口進一步惡化,傷口里殷紅的鮮血直往外涌,我一看知道是大動脈破裂了,急忙用一大塊止血棉壓住傷口,再用止血橡皮筋勒緊,雖然止住了出血,但他整個手臂的血脈不通,皮膚呈現出紫青色。彭清云一陣陣疼痛,一陣陣昏迷。我深知彭清云傷情嚴重,很快會引起并發癥而危及生命。可是根據休養所當時的條件和醫術,根本無法搶救他的生命。
看到這個情況,我非常著急。當時,我們三五九旅的衛生部也設在這個村子里,我就急忙跑到旅衛生部部長兼政委潘世征處報告。潘世征不僅在職務上是我們旅衛生系統“第一把手”,在業務上也是“第一把手”。他看了彭清云的情況后,也感到束手無策,在非常焦急之中,他想到了白求恩,立即向王震旅長報告了情況。王震旅長一聽他的“虎將”生命有危險,非常著急,二話沒說就向正在前線的白求恩大夫求救。
當時白求恩大夫從所在地趕到休養所需要一段時間。為了搶時間,我讓同志們用兩條木棍和麻繩綁成一副擔架,抬著彭清云往白求恩所在的方向趕去。大約走了兩三里路,彭清云又昏迷了,只好把他放在一棵大樹下搶救。正在我非常焦急的時候,聽見“噠噠”的馬蹄聲越來越近,白求恩大夫連翻譯都沒來得及帶,就騎著一匹棕紅色的戰馬,沿著狹長的小路,飛奔過來。穿著八路軍普通灰軍裝的白求恩,翻身下馬后邊聽我匯報情況邊給彭清云查傷。查過傷后,他打著手勢,用夾雜著英語的中文急切地要我們馬上回休養所,就在那里做手術。
我們回到村里,把彭清云安置到土炕上。白求恩連水也沒喝一口就罩上一件白大褂,開始對彭清云的傷口進行檢查。潘世征在白求恩到達時,也來到這里。他會些英語,能用英語跟人作些簡單交談,這樣他就當起了白求恩的臨時翻譯。潘世征邊協助白求恩檢查,邊和他研究方案。白求恩檢查了彭清云的傷勢之后,制定了手術方案,讓潘世征當助手,讓我負責麻醉、止血等工作。
在白求恩的指揮下,搶救彭清云的手術開始了。白求恩一點兒一點兒地剝開彭清云胳膊關節處已腐爛的肌肉,尋找損傷的血管頭。第一次找到后進行縫合,可一縫合血管頭又斷了,說明血管頭已壞死。白求恩又找了三次,進行了三次縫合,可三次血管頭都斷了。四次下來都不行,白求恩抬起了頭,他的臉上呈現出歉疚和難過的神情,無奈地向潘世征和我攤開雙手,緩緩地說了一段話,潘世征翻譯說:“為了挽救彭的生命,只能截肢了。”
隨后,彭清云的截肢手術也做得很艱難,首先就遇到了手術器械問題。當時,別說在我們休養所,就是旅衛生部也沒有一把像樣的手術鋸。情急之中,我想到所里有把從日軍手中繳獲的工兵鋸,讓人馬上找來。白求恩接過工兵鋸端詳了好一陣子,嘆了口氣遞給護士,要他們把鋸的大頭一端去掉,只留下狹長的一端,嚴格消毒之后就用這把鋸做截肢手術。
白求恩原想盡量把截肢的位置截得低一些,先從關節以上稍高位置截起,截開之后發現上面的肌肉組織已嚴重壞死,也就是說切除的部位還得往上移。可是移到什么部位才適當,沒有器材,只能從表面的腐爛情況判斷,就這樣又截了兩次,都發現上面的肌肉腐爛了。第四次截肢定位是齊胳膊切起,也就是從腋窩處截起。我注意到白求恩額頭上已滲出汗水,他知道如果這次再不成功,彭清云的生命就危險了。我們的護理人員給他擦了擦汗,他又開始第四次截肢,這次截肢終于獲得成功!
這個從上午10時開始到下午16時結束的手術,終于挽救了彭清云的生命。從此,彭清云失去了一條胳膊,我軍也多了一名獨臂將軍。
手術結束后,彭清云因為失血過多,臉色十分蒼白,必須及時給他輸血。我們都爭著獻血,白求恩卻用那“英語味”十足的話說: “來不及驗血了,我是O型萬能輸血者,趕緊抽。”我們哪還忍心抽他的血呀,但他堅定地說:“戰士們在戰場上流血犧牲,我獻點血算什么,不要爭了,搶救傷員要緊。”說著,他挽起袖子,同志們望著他那嚴峻的眼神,知道無法改變他的決定,只好把針管插進他的血管,他又把自己的血親自輸進彭清云的身體里。
輸完血后,白求恩又守在彭清云身邊觀察情況。我們怎么勸他,他也堅持不肯休息,他從王震旅長電話里知道彭清云是位擊斃日本將軍的功臣,對彭清云有極大的敬意,說什么也要守在彭清云身邊。彭清云在麻藥失效后,傷口非常疼痛,額頭上流下大顆大顆的汗珠。白求恩讓我們給他打鎮痛劑。那時我們旅衛生部只有8支鎮痛劑,當打到第4支的時候,稍稍清醒了一點的彭清云,搖頭拒絕再用鎮痛劑,他知道這種藥奇缺。
我們陪白求恩大夫在彭清云身邊守了整整一夜,白求恩看到彭清云的傷口沒有異常,臉上露出欣慰的神色。第二天一大早,白求恩的翻譯和前方的同志來接他,因為前方又有一批傷員急需他搶救。一夜沒有合眼的白求恩,拿起聽診器給彭清云做了一次細致的檢查后,站起來高興地說“很好”。他反復叮囑護理人員說,一定要把護理工作做好,這一周是關鍵,七八天后才能脫離危險,說著就往村外走去。我把他送到村口,他騎上那匹棕紅色的馬,跟著翻譯和接他的同志急急向山下奔去。我看著他的背影越來越遠,直到消失在遠方……
彭清云手術后,一連4天處于昏迷半昏迷狀態,第5天才蘇醒過來。當我把白求恩大夫為他截肢并為他獻血的情況告訴他之后,他的熱淚奪眶而出:“是白求恩大夫、潘部長和你挽救了我,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彭清云的傷勢稍好一些后,就上前線了。“半生獨臂,一身許國”,這就是彭清云以后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斗中,在全國解放戰爭的大大小小戰役中最真實的寫照。
1979年4月,在我軍紀念白求恩的一次會議上,我和彭清云將軍重逢,我們又談起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