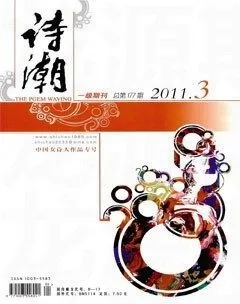對個人“經驗”的回憶
《江心洲》,是路也詩選《一個異鄉人的江南》的第一首,也是她以此冠名的系列組詩的第一首。與系列組詩中后來出現的佳篇比較,盡管此詩不如《鳳凰臺》那樣典雅(“我和你住在一首七律的一聯里/我們有著平仄對仗的關系”),不如《兩只蝴蝶》那樣調皮(“兩只蝴蝶在我們身旁唧唧噥噥/我請求你這個本地人,將它們的語言翻譯成普通話/因為我聽來聽去,似乎只聽懂了那么一句/……‘瞧這個北方女人,多么土氣啊!’”),也不如《憶揚州》那樣機智(“當微醉之后搖晃著走在石板路上/我相信這個夜晚的明月是從杜牧詩中/復制并粘貼到天上去的/哦請告訴我哪是黛玉離家北上的碼頭/我們這樣沿著運河走,在到達賓館之前/會不會遇上南巡并且微服的乾隆”),但它卻具有創世紀般的決定性意義。
江心洲,是長江中的一個小洲,詩人將它比喻成“大江的合頁”,便賦予了該洲以書卷氣。“江水在它的北邊離別又在南端重逢”,不用“東”與“西”而用“北”與“南”,顯然是為了對應北女與南男的遠程之戀,也給“遼闊的感傷”(見《有恒渡口》)創造了條件。此洲雖小,卻植被豐茂(有油菜花、蘆蒿、桑葉、蘆葦塘、水杉樹),荒涼且具野趣(有貓和狗,還有一家報廢的造船廠)……這就為系列組詩提供了一個環境:可以在這里戀愛(“我們初來乍到,手拉著手/繞島一周”),可以在這里安家(“一個像首飾盒那樣小巧精致的家”,極言其小乃強調其珍),可以在這里生育(“像種植一畦豌豆那樣/把兒女養大”,也可以說是種植與生育同時進行,多么美麗的現代版隱居圖!),更可以在這里馳騁想象(“把豪華想法藏在銹跡斑斑的勞作中/每天面對著一條大江居住/光住也能住成李白”);這也為系列組詩尋找到一個載體:既能承載愛情(這是一種火燒火燎的感情,有論者用“天昏地暗的風暴”加以形容),也能承載自然(路也不愧為“來自一個圣人的省份”,她的詩體現了孔子的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既有實錄印痕(路也自白:
“我是打算將我的一生用詩歌記錄下來的”),又有象征意蘊(路也還有一句話:
“所有現實中不能實現的和不能得到的,在詩里都可以實現和得到。”),是感性與知性的結合,形而下與形而上的交融。所以,她在這首詩的結尾,借用了救亡名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改了歌名《我的家在江心洲上》,改了歌詞“這里有我親愛的某某”,就很好地完成了現代對歷史的轉換。
在《江心洲》一詩中,路也對愛情的表現是率真的,也是大膽的,例如第四節:“把床安放在窗前/相愛時可以越過屋外的蘆葦塘和水杉樹/看見長江/遠方來的貨輪用笛聲使我們的身體/擺脫地心引力”,這里涉及到了兩性生活與快感,既美且不落俗,印證了她答《長江周刊》記者問的一段話:“我不喜歡遮遮掩掩,也同樣不喜歡暴露癖,我認為一切都應該服從探索真理和藝術表達的需要。”路也對自然的描寫是親切的,也是細致的,她稱“油菜花為姐姐蘆蒿為妹妹”,“向貓和狗學習自由和單純”,桑葉之于蠶,“那是它的祖國”,想到生育,是“在江南潮潤的天空下”,“像種植一畦豌豆那樣”,這些用詞、造句都相當成功!詩人對筆者說:她這首詩,愛情是背景,自然是演員,讀者一般都把它當愛情詩來讀,而她個人更傾向于把它當成是向大自然致意、探討人類尤其是現代人類與大自然的關系的作品。筆者以為,背景與演員可以互相轉換,作者不必過于執著,見仁見智由讀者去認定,反而涵蓋面更大。
正是因為有了這第一首詩,路也一發而不可收,在2004年6月至12月短短的半年中,她寫了近百首,形成了龐大而豐美的“江心洲”系列組詩。不僅包含了前面提到的幾首佳作,還有把俗世生活寫得十分優雅的《菜地》、大幅度調動地域板塊和奇妙想象的《氣候變化》、可以看齊葉芝的名詩《當你老了》的《還會》等等,一舉震動了詩壇,于2006年全國十大青春女詩人評選中名列第二。
路也回顧“江心洲”系列組詩的創作時,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那組詩并不是在當時當地寫出來的,而是有一個小小的時間差,那組詩的寫作其實帶著對個人‘經驗’回憶的意味,當然寫作者是一直處在那種持續長久的恍惚之中的。”她還告訴筆者,當年她去江心洲只有四次,每次不超過四小時,但卻寫出了那么多激動人心的詩。這種對個人“經驗”的回憶,不是很值得我們研究